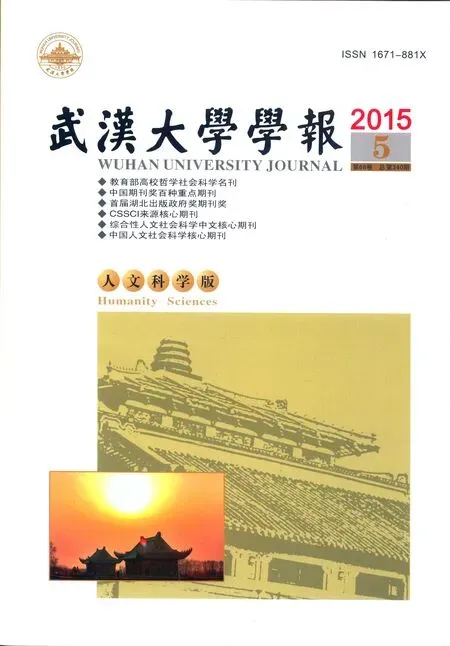一位被忽略的公安派爱国诗人 ——丘坦生平三考
戴红贤
一位被忽略的公安派爱国诗人——丘坦生平三考
戴红贤
摘要:丘坦是一位被忽略的公安派爱国诗人。他的《南游稿》《北游稿》是公安派早期诗歌的代表作,爱情悲剧诗《百六诗》体现了晚明性灵文学尊重普通小人物存在价值的新人文精神,军旅诗集《度辽集》抒发了丘坦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操和淡然名利的闲适情怀。
关键词:丘坦; 公安派; 《南游稿》; 《百六诗》; 《度辽集》
丘坦(1564-?),又名坦之,字长孺,明代湖广麻城人。他是公安派的重要成员,也是晚明时期活跃在辽东边境的一名卓越战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位民族英雄的事迹及文学创作的了解仍十分有限,相关研究基本阙如。丘坦的生平经历至今还尘封在域外汉籍之中。笔者访学韩国期间,有幸获得了记载丘坦英雄事迹甚详的古朝鲜汉籍*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韩国岭南大学图书馆古文献室郭海永先生。本文的韩国文献搜集工作得到了郭先生的大力赞助。。通过对其生平经历及其残存诗歌的综合分析,发现作为公安派爱国诗人,丘坦的诗歌创作至少有三个方面内容值得关注:一是他的早期诗集《南游稿》《北游稿》,二是他的爱情诗《百六诗》,三是他的军旅诗集《度辽集》。本文拟探究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南游稿》《北游稿》与公安派早期诗歌创作
丘坦是晚明公安派的重要成员。万历二十一年初夏,“公安三袁”麻城访学李贽,丘坦与袁氏兄弟订交。万历二十一年冬,丘坦和袁中道结伴从武昌出发,沿长江东游金陵、虎丘、钱塘、嘉兴等吴越胜地,各自创作了不少具有革新意义的诗歌,分别结集为《南游稿》。丘坦还将北游诗歌结集为《北游稿》。万历二十四年冬,袁宗道为《北游稿》作序。同年,袁宏道写给丘坦的信中也谈及《北游稿》*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丘长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钱伯城笺曰:“丘坦本年有《北游稿》,分寄袁氏兄弟。”。宗道《北游稿小序》和宏道《丘长孺》是公安派形成期间有关性灵学说的两篇重要著述。虽然丘坦《南游稿》《北游稿》已亡佚,但袁氏兄弟的相关诗评对于我们认识丘坦诗歌艺术提供了线索。宗道云:“其诗非汉、魏人诗,非六朝人诗,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诗,而丘长孺氏之诗也。非丘长孺之诗,丘长孺也。”*孟祥荣:《袁宗道集笺校》卷十《北游稿小序》,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宏道说:“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决不可观丘郎诗,丘郎亦不须与观之。”*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丘长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宏道还说丘坦诗歌“五言七言信手成,刻雾裁风好肌骨。筇根处处觅糟丘,逸思迸如春草发。”*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五《和丘长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袁氏兄弟欣赏丘坦诗歌不蹈袭古人,不模仿他人,独抒自我性情,赞叹丘坦诗歌具有信手而成,描绘真切,清新自然等艺术特征,而这正是公安派文学创作的核心精神。由此可见,丘坦早期诗集《南游稿》《北游稿》与袁中道《南游稿》《小修诗》等诗歌创作具有共同的艺术趣味。丘坦和袁中道的这些诗歌开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歌创作之先河,为袁宏道性灵说理论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样本*戴红贤:《袁中道早期诗集〈南游稿〉〈小修诗〉考论》,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5期。。
综观“三袁”文集,我们不难发现丘坦与袁氏兄弟的亲密关系,也很容易推导出丘坦其人其诗与公安派同调这一说法。不过,丘坦能迅速与“三袁”声应气求,打成一片,与他的出生及黄安、麻城一带的文化环境当有较大关系。丘坦出生在麻城世家,父亲丘齐云(1541-1589),字汝谦,又名谦之,是嘉靖乙丑进士,出为潮州知府;祖父是万历名臣张居正的知交。丘坦父亲谦之宦情淡薄,曾在潮州署中建立一亭曰“吾兼”,寄兴诗酒,耽情游览,38岁即致仕回麻城*余晋芳:《麻城县志前编》卷九《耆旧·文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谦之工词赋,著《吾兼亭集》《粤中稿》,其诗歌本色通俗,描写日常生活,描绘自然山水。如《咏揭阳景》写道:“登高不尽翠微悬,海色真堪睥睨前。桑浦关门来急峡,蓝田削壁挂飞泉。城中竹树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系船。可是河阳潘令在,于今五岭净风烟。”*陈树芝:《揭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公安派所倡导的诗歌创作艺术倒是与丘坦父谦之诗艺相近。关于丘坦祖父,汪道昆云:“时谦之父自别驾守忠州,上故相书论时政得失。江陵恚甚,立罢之。”*汪道昆:《太函集》卷之五十六《明二千石麻城丘谦之墓志铭》,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7册,齐鲁书社1997年。本段引文未标注者,均同此。丘坦祖父虽是张居正老友,可他信守诤友古道,不计个人得失而敢于直言张氏执政失误。
值得指出的是,万历十三年,李贽由黄安移居麻城,谦之父子开始交往李贽。李贽当年就给丘坦父亲写过信*张建业、张岱:《焚书注》卷一《复丘若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丘坦也可能于此时开始了与李贽的交往。袁中道说:“公遂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十七《李温陵传》,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小和尚怀林说:“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气急,独坐更深,向某辈言曰:‘丘坦之此去不来矣。’言未竟,泪如雨下。”*张建业、张岱:《焚书注》卷四《寒灯小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该文作于万历二十一年,其时李贽与丘坦的忘年交情已相当深厚。丘坦为人率性真诚,不拘礼教,屡被李贽首肯*李贽《寒灯小话》记载:“十五夜,复闻人道有一老先生特地往丘家拜访荆州袁生,且亲下请书以邀之。袁生拜既不答,召又不应;丘生又系一老先生通家子,亦竟不与袁生商之。而人相视,莫不惊骇,以为此皆人世所未有者。”李贽《八物》云:“如丘长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见而遂定终身之交,不待再试也。”(张建业、张岱:《焚书注》卷四《八物》)。
综上可知,丘氏家风和李贽学说奠定了丘坦性灵人学和文学思想基础。万历二十一年,丘坦与“公安三袁”在麻城相见恨晚,志同道合,彼此唱和,互相激发,共同探索“致良知,作新诗”的性灵文学发展道路。
二、 爱情诗《百六诗》与丘坦的侠骨柔情
《百六诗》是公安派难得的爱情诗,与丘坦的爱情悲剧有关*与《百六诗》及丘坦爱情故事相关的晚明诗文主要有四种,即袁宏道《百六诗,为丘大赋》,江盈科《百六诗引》,潘之恒《纪百六诗》,冯梦龙《情史·丘长孺》。。该故事涉及文学史上《金瓶梅》的早期收藏者刘金吾的事迹。现代《金瓶梅》研究论著探究此段故事甚多。不过,时人在解读丘坦和白六爱情故事时还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
首先是“百六诗”题名及其含义的问题。由于“百六”和“白六”音、形皆似,故有学者提出“百六诗”乃“白六诗”之误。其中,丘坦好友潘之恒《纪百六诗》对“百六诗”题名的记叙就存在一些令后人模糊之处,主要有二:(1)“百六诗”为一百零六个字之诗。(2)“百六”或为“白六”。潘之恒说“余诗政得百六字”,意为“百六诗”当为一百零六个字。可是,潘氏所作《纪百六诗》只有96字*潘之恒:《亘史钞·纪百六诗》,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615页。潘之恒诗如下:杀人不持刃,妒者计太深。无端毒人肠,非关陌上金。(一解)一夕即离夕,欢边即憾边。持此博郎怜。(二解)相思不可见,一见欢成变。生前白玉环,是侬情所恋。(三解)奈何许,可怜金阊儿,化作西陵土。(四解)相思结,九死情不移,一寸心常热。(五解)啧啧复尔尔,编膺百六言,萦肠千万缕。(六解),所录丘坦《百六诗》乃三首七言绝句,也只有84字*《亘史钞》保存丘长孺《百六诗》七言绝三首如下:扁舟江上偶来归,八月楼头月正辉。金屋帘中闻绝唱,人间天上会应稀。欢娱何意重成悲,一别今生未可知。涕泪相看留不住,断肠何必听猿时。肠断侯门那得知,去珠宁复有还时。莫言河鼓相思苦,犹有明年七夕时。,皆非106个字。潘文自述《纪百六诗》文章写作旨趣在于保存丘坦和白六的诗文,所谓“余以是知文之不可已也。彼无文者,如聚鹿孳尾等尔,乌知情哉?”故《纪百六诗》所录丘、白诗歌当是尽量存其菁华,汰其繁芜。可见,“百六诗”非一百零六个字之诗。又一误会,“百六”或为“白六”。潘氏《纪百六诗》写“丘长孺怀百六诗云”,“怀百六”很容易让人把“百六”理解为“白六”,当代学者正是将其标点为《怀百六诗》*凌礼潮《冯梦龙〈情史·丘长孺〉考实》,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当然,丘坦以“百六”谐音并暗喻“白六”亦并非不可能。不过,“百六”非“白六”之误,毋庸置疑,因为《纪百六诗》明言:“丘长孺自作诗百六首悼之,中有云:千愁万憾竟成空……”
实际上,所谓“百六”之数,古代多以其与厄运关联。《汉书》云:“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中华书局2000年。汉代《三统历》以4617年为一元,当时人认为,在一元的头106年中,有9个灾年,故称“百六之灾”。“百六”还与寒食日紧密相关。寒食节在夏历冬至后第105日,寒食第二天就是百六日了。如元人赵善庆《庆东原·晚春杂兴》曲云:“百六楚风酸,三月吴姬瘦。”*《薛昂夫赵善庆散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中国的传统,寒食节是纪念无端遭遇厄运的介子推。丘坦把伤悼白六的诗歌称为“百六诗”,旨在痛惜白六无端遭受厄运的不幸人生,而事实上他也写了106首悼诗来怀念白六。
其次是对丘、白悲剧发生的时间、原因等问题的认识还不太清晰。袁宏道《百六诗,为丘大赋》被系年在万历二十五年,这没有问题。不过,丘、白的爱情悲剧当发生在万历二十四年下半年。据《纪百六诗》收录丘长孺“扁舟江上偶来归,八月楼头月正辉”和白六“记得金风八月秋,拜郎灯下阁东头”等诗句,丘、白结琴瑟之好当在万历二十四年八月。然而好景不长,丘、白悲剧很快就发生了。对悲剧发生的原因,潘之恒和冯梦龙的讲述颇有差异。《纪百六诗》写道:
越夕而悔,曰:“适彼何艳,则辞我为鄙我矣。鄙我,我得制其命。”声之母与妹。母,故威福人也;妹,即生之妻,巧于妒。嗾群媵虏以归。
冯梦龙《情史·丘长孺》写道*冯梦龙:《情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居无何,客或言此两人先有私者。刘怒气勃发,疾呼六生来讯。
冯文叙述刘氏抢走白六是受了第三方的蛊惑,潘文则强调了刘氏揣测白六鄙视自己,于是决定严惩白六,争取到母亲和妹妹(即丘长孺之妻)的支持后,抢回了白六。综合考察潘文和冯文,丘、白爱情悲剧故事如下:万历二十四年八月,丘长孺花费巨金从刘氏手中替白六赎身。丘、白二人情投意合。没多久刘氏因各种原因反悔,趁丘长孺不在家时抢走了白六,拷问丘、白私情。白六宁死不服,以死酬答长孺的知遇之情。侠骨柔情的丘长孺再次不惜重金从刘氏那里赎回奄奄一息的白六。丘、白生离死别的场景,冯梦龙的叙述十分动人:“(白六)面如生,惟右手握固。长孺亲擘之乃开。掌中有小犀盒,盒内藏两人生甲及发一缕。盖向与长孺情誓之物也。长孺痛恨,如刳肝肺。乃抱尸卧,凡三宿,始就殓。殓殡俱极厚。事毕,哀思不已。”至于丘、白二人互赠的爱情诗篇,则保留在潘氏《纪百六诗》中*今录其中两首如下。1、白六《临终寄丘郎诗》:女身生命不自由,况复飘零离故丘。一朝失路堕虎口,同舟共济皆仇雠。念我十一十二时,学书学字兼学诗。十三十四善歌舞,名擅教坊天下知。自伤微贱倡家苦,踯躅不如阶下土。忍心讬身事贵人,贵人难事如驯虎。朝来欢笑掌上珍,日未旁午如路人。白衣苍狗日万状,惨毒酷烈何酸辛!自分沉沦无出期,何意得郎顾眄之!譬如解网肉白骨,再见枯树重荣时。人心险恶不可测,未得事君先永别。今生欢聚无复期,留取别时衣泪血。人生有生必有死,彭殇修短空复尔。妾今身得死郎君,万憾千愁不虚矣。佩郎所赠环,生死不相弃。报郎以此诗,知妾死时意。不知遗骨弃何所,一片精魂逐君去。2、丘坦《悼诗》:千愁万憾竟成空,患难生同死不同。留取衣襟双泪血,今生端不再相逢。眼底风波见世情,旧时环玦死生盟。君能不惜千金骨,我却何颜更复生?。丘、白爱情悲剧哀婉动人,长孺所为与刘氏的粗鄙残暴形成鲜明对照,充分展示出丘坦真诚善良的美好性情。
需要大书特书的是,在丘、白的爱情悲剧中,丘长孺的所作所为很好地展示了晚明性灵派诗人的新人文精神。长孺外表英俊,气宇轩昂,多才多艺*袁宏道说他“凤目美髯,魁梧长姣,往时客吴,吴姬呼为‘白描关公’”(《墨畦》),长孺又精通音乐,懂吴语新声,潘之恒说他“能和其声”(《纪百六诗》),冯梦龙说“楚人不操吴音,惟长孺能”(《情史》)。,这些固然能使他赢得白六的芳心,不过,这都还不是让白六以生死报答他的关键。赢得白六生死相许的根本原因在于,丘坦虽为贵游公子,可对像白六这样出生卑微的歌伎,不仅能欣赏白六的才艺,成为白六歌艺的知音,而且尊重白六,平等相待。丘坦这种尊重对方并与其平等相处的人生态度,源自晚明具有启蒙意义的性灵人学思想,即充分肯定那些被单一的仕宦富贵人生价值评判标准淘汰出局的普通小人物(包括妇女)。公安派朋友圈对白六的歌颂与称赞也出自性灵文学精神,即让普通小人物的生命和生活由文学艺术而进入社会历史的视野。潘文和冯文的叙事旨趣正在于传扬白六这样一个卑微弱女子的美好情操。丘长孺对白六平等尊重的态度不禁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宝玉对大观园女孩子的种种多情的言行。曹雪芹的审美情趣当与晚明性灵文学精神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三、 军旅诗《度辽集》与丘坦的文韬武略
丘坦能文善武,是公安派中唯一的武将。军旅诗集《度辽集》抒发了丘坦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操和淡然名利的闲适情怀。万历末期,丘坦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历令人瞩目。其中值得书写的有两点:一是他与朝鲜著名诗人许筠的交往,他俩是将公安派著作传播到朝鲜的关键人物;二是丘坦任镇江游击将军近六年,文韬武略,是辽东边境上一位优秀战将。关于前者,笔者拟另撰专文,在此仅讨论后者。
丘长孺善于骑射*参见袁宏道“七尺身材五尺臂,雕弓往往穿金铁”“射虎韝鹰一健儿”(《和丘长孺》),袁中道“马度秋原百鸟藏”(《送丘长孺南还》),江盈科“尤工骑射”(《百六诗引》)等。。他文试不第,遂改武试,万历三十四年举武乡试第一。万历四十一年八月,长孺赴任镇江游击将军。出发前夕,他在北京辞别诸友,写下组诗《度辽留别京邑诸知己》。见存诗歌如下:
世事何时不可为,盘根错节岂难支。独怜近日边疆事,筑室搏沙无米炊。
与其枯骨裹罗纨,何似沙场绣箭瘢。自得先师等死说,不劳马革与桐棺。
生平知己尽贤豪,推毂勤渠属望劳。此别无成应永别,不能长负九方皋。
清人廖元度选编《楚风补》保存了这些诗歌*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所古典文献室:《楚风补校注》,廖元度选编,湖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钟惺曾说长孺《度辽留别京邑诸知己》有“诸君蘸笔悬相待,不是铙歌即挽诗”等诗句*钟惺:《隐秀轩集》卷第一四《丘长孺将赴辽阳,留诗别友,意欲勿生,壮惋之余,和以送之》(共五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可它们并不在见存诗歌之中,由此看来,长孺这组诗篇当不止《楚风补》中的三首。长孺出任镇江游击将军前期所作诗歌(包括《度辽留别京邑诸知己》)被结集为《度辽集》。《度辽集》由潘之恒主持刊刻,刊印时间当在万历四十三年。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之十二《虞长孺》写道*潘之恒:《鸾啸小品》,崇祯二年刻本。:
盟友丘大,亦字长孺,麻城人,齐云公子,刘司隶婿也,生平好为豪举事,然肮脏不偶,每怀长缨击虏之志,自比博望、定远辈而冀有所树立。囊岁随敕使颁青宫诏,得一寓目朝鲜,而磊落之怀见诸篇咏,其志亦可哀矣。丘大向弟言:“入朝鲜安得不作倭诗,顾安得海外人豪序之”……今杀青将竟,姑以草木乞一言弁首,以发舒壮心。
潘之恒拟请虞长孺为《度辽集》作序,不过,据廖元度丘坦小序“梓其《度辽集》,友人潘景升为之序”云云,或许《度辽集》最终由潘之恒本人作序。万历四十四年二月底之前,袁中道已得到《度辽集》,他说“《度辽集》极有奇趣”*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二十五《答丘长孺》,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长孺笔下辽东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皆迥异于江南,奇特而新颖。
廖氏《楚风补》录存丘长孺诗歌19首,其中《度辽留别京邑诸知己》(三首)《阅武值雪》《八忆诗》(三首)《感怀谢诸知己》《长至夜饮窦靖宇署中赋赠》《咏野烧》《凤凰山闲咏》《山中午日》《闲咏》《无题》(又见《明诗纪事》《湖北诗征传略》)等14首可能出自《度辽集》。另据凌礼潮先生言,麻城《丘氏宗谱》卷二收录了丘坦《度辽集》残存诗词,如《行香子》词七首。此外,袁中道《珂雪斋集》保存了长孺七言歌行一首和《长相思》词一首,它们是万历四十四年正月长孺写给中道的书信所附,不知它们是否收录在《度辽集》中。笔者共搜集到长孺佚诗近40首,《度辽集》诗歌占多数。这里选录三首,以见一斑:
绣旗冲晓雪,羯鼓引鸣笳。卤部兼胡汉,风云护纛牙。箭同飞白羽,枪共舞梨花。望入天山外,茫茫殆一家。(《阅武值雪》)
瓦上阶前一寸霜,晓寒怪地沁衣裳。满墀积雪明庭燎,一派荒鸡出塞墙。昼角声残星月下,竹炉火暖瓮醅香。故人长至天涯酒,只觉今宵夜不长。(《长至夜饮窦靖宇署中赋赠》)
乱山深处且停骖,村酒虽浑亦共酣。日落棠梨花树下,一声布谷似江南。(《无题》)
与《南游稿》《北游稿》《百六诗》相近,《度辽集》诗歌语言通俗本色,自然真切描绘塞外天寒地冻的景色。诗歌表现自我的艺术风格也一如既往。不过,丘长孺在辽东的诗歌创作只是业余雅好,他“驱使兔毫如箭镞”*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六《毕少参舟中见武录,知丘长孺被落,诗以悲之》。,诗人辽东生涯的主要活动还在作为镇江游击将军防守边疆。
丘长孺任游击将军乃受命于危难之际。万历末期,辽东边境危机日趋严重。尤其是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鸭绿江边的镇江边防正处于明朝、朝鲜与后金多边复杂关系的关键之处。那么,长孺在此非常时期赴任非常之地,其文韬武略及其《度辽集》所表达的誓死保卫国家民族的赤胆忠心如何?据韩国古典汉籍记载,长孺在国家危急和民族存亡之际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胆识,其英勇善谋震撼了朝鲜君臣。令人扼腕的是,四百余年来,民族英雄公安派诗人丘长孺的英勇事迹一直尘封在韩国清冷的故纸堆中。据《朝天录》(朝鲜金中清著)《光海君实录》以及《楚风补》等文献,我们了解到丘长孺任镇江游击将军时间为万历四十一年八月至万历四十六年五、六月间。其可书之事主要有如下三点。
其一,六州河大捷。朝鲜金中清《朝天录》抄录本次战捷碑文如下*金中清:《苟全先生文集》及附录《朝天录》,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245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
自嘉靖壬子,虏始跳梁,迄今壬子,俘略民畜,焚我庐舍,殆无虚岁。近虽纳款,阳希赏赍,阴怀窥伺,稍隙即逞。癸丑八月二十九日,虏聚数千,以图大逞,号称万余,翼日迟明,喊噪入境。游击李公涉六州河,左右进战,少遒,广宁左翼营游击高公自东关至,协镇李公自前屯至,镇江游击丘公自中右至,戮力并势,作鱼丽阵突入虏营,往来刺击,折馘二十余颗,贼堕马惊溃泣嗥,伧儜北窜。李公,名继功。协镇李公,名光荣。高公,名铨。丘公,名坦。郡人太原通判吴道隆撰云。
万历四十二年,金中清作为“书状官”随同朝鲜“千秋使正使”许筠出使明朝。七月三日,他们一行经过六州河时,金氏发现六州河城外有“全胜碑”。金氏对碑文真实性有所怀疑,通过询问当地居民,证实碑文所言属实,他说:“疑其过实,讯诸居民,皆言上年之战果快云。”金氏于是将碑文抄录在他所著的《朝天录》中。六州河战役发生在“癸丑八月二十九日”,“癸丑”年即万历四十一年。据廖元度《楚风补》长孺小序云“出镇辽左,领偏师备边,在位九日,即奏六州河之捷”,综合金氏和廖氏所言可知,长孺抵达辽阳在万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六州河捷战表明,赴任镇江游击将军之时,丘长孺不仅早已将个人功名和生死置之度外,正如钟惺“不须更论及封侯”“看君已断身家想”*钟惺:《隐秀轩集》卷第一四《丘长孺将赴辽阳,留诗别友,意欲勿生,壮惋之余,和以送之》(共五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等诗句所言,而且他对辽阳地形、相关军事据点以及敌我双方的对峙多方面情况都非常熟悉,早已充分做好随时投入战争的准备。其《度辽诗》表达的誓死保卫国家民族的赤胆忠心绝非文饰之辞。
其二,与朝鲜作家许筠交往(详情见笔者另篇)。万历四十二年六月,长孺与朝鲜许筠、金中清在镇江会面。他们彼此欣赏,友谊深厚。丘长孺和许筠将公安派著作传播到了朝鲜,共同开启了公安派在朝鲜传播接受的历史。他们的友好往来谱写了一支中、朝文学交流的动人乐曲。
其三,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丘长孺配合抗清主帅汪可受等,三次去函请求朝鲜国王光海君积极备战,做好与明朝共同抗击后金的准备。具体内容如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辑,中华书局1980年。以下引文未特别标注者皆同。:
“为夷情事,奴酋向来与抚顺互市交易,忽于前面四月十日假称入市,遂袭破抚顺。我兵四集,贼即出境。我兵追至境外,遇伏失利。今奉旨议剿,发兵一十四万陆续出关。昨奉抚院明文,与贵国王操练兵马七千以备合剿,宜速启国王,早为预备。奴酋款服一说,未见的报。至于该国邻酋地方,今宜严防。兵马相期听调。”
“查得奴酋自暗袭抚顺之后,将所获财货牛马粮食尽搬回巢,烧屋毁城而去,至今未见动静。奉圣旨调兵十四万、饷银三十万陆续出关。闰四月初三日,总制军门汪已移住山海关矣。剿奴日期,尚俟大军到齐方定出征之期。杨军门讳镐,系原东征者,今起用经略军门。杜总兵讳松,原任辽东总兵。贵国军马,速宜预备,勿致临时迟误。”
“鞑奴西抢犯沙河堡,东抢犯沈阳及青阳堡,皆随入随出,毫无所失。惟是奴酋借入市为由,袭破抚顺,因人之信己而逞其诈,罪大恶极也。清河、叆阳、宽奠、长奠皆近奴酋巢穴,虽风闻奴酋思图再逞,而各城戒严,添兵防戍,一月以来,酋亦不敢蠢动。天朝大兵陆续出关,计秋前必可到齐,但发兵之期,本府难以预料也。贵国军兵只宜预先速练,勿致临时误期为变。杜、刘二位总督尚未见的报,俟再有至以后又票。镇江距抚顺甚远,民间讹传,难可凭信,非据邸报,皆浪传也。贼原未防清河,我兵因贼自抚顺退回,追之失利耳。奴酋计袭抚顺,自前月二十五日回巢未出。其犯沈阳、沙河者皆鞑虏也。随入随出,故无所失。又查杜总兵已见报驻守山海关,亦不度辽。又查刘总兵尚未见报,难以民间讹传,妄相回复。今新总兵乃铁岭李老爷,讳如柏。辽阳副总兵乃贺老爷,讳世贤。本国与贵国,情属一家,事之真的,相应传知。”
遗憾的是,光海君对丘坦联合抗战提议不仅一再拖延、推诿,其君臣甚至还屡屡诬告丘坦,所谓“丘参将于我国事事生梗”“丘坦之欲生衅于我国”“倾陷我国,不遗余力”云云,致使某些明朝官员误以为真,说:“尔国不好的讹言,自镇江流入北京。”对此,丘坦不无感慨道:“羽檄军书尽夜驰,可怜文法密如丝。中才不了趋承事,何用龙韬豹略为。”(《闲咏》)可怜丘坦“不是铙歌即挽诗”报效大明王朝的壮志难酬。防守边疆多年的丘坦不得不抱恨致仕南归。
至于丘坦致仕的具体时间,有《光海君实录》和《明实录》两个版本。前者记录为:“六月,镇江参将丘坦移充汪军门赞画。新参将乔一琦将为上任。”后者记录为:“本年五月,辽东镇江游击丘坦以病乞致仕。”*《明神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上海书店1982年。据《楚风补》丘序“历事六年,凡七疏,始解閫寄归”,或许五月长孺已上疏要求致仕,六月他才正式离开镇江。《明实录》以长孺的上疏日期为准,《光海君实录》以长孺离任镇江游击将军为准,于是出现了上述两种说法。
万历末期,朝鲜政治与明朝一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万历四十六年八月,丘坦好友朝鲜许筠被逮,数日后即被处死。十一月,攻击丘坦的朝鲜尹晖,以辱命卖国之罪论处。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爆发,明朝和朝鲜的联军大败。当然,丘长孺个人不可能力挽明朝大厦将倾之狂澜。值得深思的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涌现出一批像公安派性灵诗人丘长孺这样赤胆忠心、文韬武略的爱国民族英雄*严迪昌:《清诗史》第一编《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上)《遗民诗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文学思想史上对晚明士风及性灵诗人的简单化抨击。
综上所述,丘坦的诗歌创作在公安派中别具一格。《南游稿》《北游稿》是公安派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在公安派文学中具有探索革新的意义。爱情诗《百六诗》所体现的晚明性灵文学尊重普通小人物(包括妇女)存在价值的新人文精神,在四百年来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军旅诗《度辽集》拓展了性灵诗派的创作题材,军旅生活及边塞风景丰富了公安派诗歌内容。侠骨柔情的丘坦正是晚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丰富多样人才之中鲜活的一员。民族英雄、公安派爱国诗人丘坦值得我们永远记住。
●作者地址:戴红贤,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daisy1698@163.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14JYA751002)
●责任编辑:何坤翁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