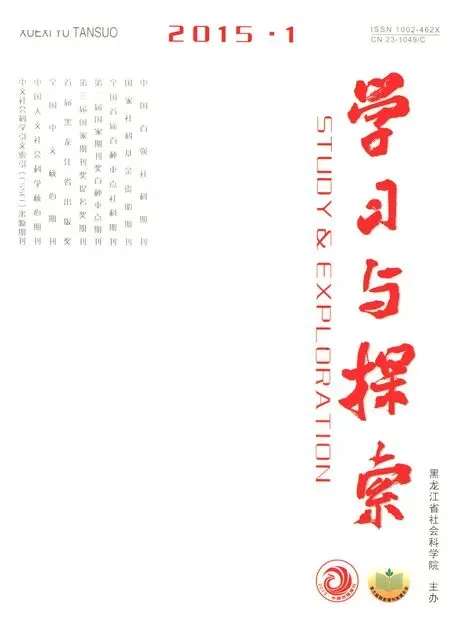《资本论》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
鲁 品 越
(1.上海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2.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重庆 400700)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资本论》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
鲁 品 越1,2
(1.上海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2.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重庆 400700)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创造出的历史,由此形成的物化的社会关系结构既是人与人的关系组成的社会系统,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的生态系统,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作为唯物史观的科学形态的《资本论》既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学说,也是关于这种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生态系统的哲学。《资本论》的生态哲学以劳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为基础,以吮吸生态“自然力”的资本逻辑的正反馈循环圈为中心,以资本逻辑的时空展现对生态逻辑循环圈的撕裂为基本机制,同时也包含如何通过市场建立循环经济的理论,以及对于惠及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萌芽。
唯物史观;《资本论》;生态哲学;马克思
有一种误解,认为《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经济理论,因此它至多只有关于生态问题零星的判断,而不存在生态哲学思想。这是十分错误的观念,它建立在下述理论预设基础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因此“社会哲学”和“生态哲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只有撇开社会关系、专门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才是生态哲学。正是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之下,当今西方一些生态哲学强制性地把生态哲学的主题规定在“人”与“自然”关系之内,对两者谁轻谁重进行价值选择。于是产生了“人类中心论”与“生态圈中心论”“人的权利至上论”与“动物权利至上”等等论争。这些所谓难题实质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伪问题:它把“人类”抽象为一个铁板一块的单纯概念,纯粹理论地讨论“抽象的人”与“自然”两个单纯概念之间的“应然关系”,从而陷入远离实践的抽象概念陷阱之中,陷入在实践中无所适从的盲区。
与上述西方生态哲学完全不同,《资本论》的生态哲学思想融入于对社会关系的现实分析之中。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与其他各种生态哲学的本质差异所在。只有抓住这个主线,我们才能透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透彻分析,发现其中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
一、物化劳动: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的对立统一体
《资本论》之所以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系统放在人类社会关系系统中考察,是因为它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是物质生产劳动,这是人的生命的物化过程。正是这一基本概念,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结成一个整体。
人类历史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所创造的结果,那么它是否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一切历史观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那么,这个决定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环境是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此做出透彻的分析,由此得到了“唯物史观”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2]544。这个“基础”可以概括为“物化劳动”,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已经凝结在产品中从而作为当下劳动的环境与条件的物化了的人的生命(Materialized labor,又称“死劳动”),二是作为劳动过程本身的正在进行物化的人的生命(Materializing labor,又称“活劳动”),这两者都受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因此,虽然人类遵循自己的意志进行的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但是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结果却作为物化了的劳动而形成人类当下实践活动的客观环境,人们只能在这种客观条件制约下进行选择,并且一旦做出选择而采取了某种实践活动方式之后,其实践活动作为活劳动也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因而整个历史便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物化劳动”正是唯物史观中所讲的决定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的“物质”,是唯物史观的最根本的立论根据。
这种创造历史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过程,这个过程及其生成的社会历史环境有两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系统,两者是同一整体的两个方面:
一是,劳动创造了人与自然关系系统,包括生产力系统及其延伸——人类生态系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208这种物质变换过程形成了社会生产力系统。而生产力系统必然通过其产品及其相伴的生成物延伸到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中而生成生态系统: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其生产过程本身、产品与伴生物一道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其产品投入社会后遵循人们的生活需要而进行交换,马克思把这种交换看作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做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做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3]125而交换之后则进入消费的“物质变换”过程。因此交换和消费可以看成是劳动所进行的物质变换的延伸。由此形成了生产—交换—消费的“物质变换链”,它不仅包括产品,同时也产生了排泄物——“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排泄物”[4]115。不仅包括有形的废水、废料等等,也包括无形的影响环境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乃至噪声等等一切污染物。我们把人类劳动和生活的全部物质环境称为生态系统,它是生产力系统向人们全部生活领域的延伸,而其中只有商品进入市场经济领域。
二是,这种物化劳动过程及其对物质生活的延伸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生产过程,由此生成了物化的社会关系。劳动在产生出生产力系统的同时,还生产出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首先,分工性劳动都是为他人服务的劳动,由此形成了人们生命之间最基本联系。而生产资料与各种资源的所有制关系嵌入到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之中,形成人们之间通过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而实现的物质化的社会权力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随着生产过程延伸到生活领域而生成人类生态系统,这种物化的生产关系也投射到生态系统中,形成了人与人的生态社会关系:对生态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物化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态关系反过来作用于人,使人们在它们的支配与制约下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社会性。
于是,物质生产劳动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其自然性产生了生产力系统及其延伸——生态系统,劳动的社会性产生了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延伸——人类生态关系系统,它们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由此产生的物质结果是社会关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统一。因此,物化劳动所生产的物质世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说是生态环境,其被打上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烙印。而人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的社会关系,由此形成“五位一体”。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五位一体”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
因此,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关系的科学分析,同时也就是对这种社会关系下的生态系统的科学分析。这样的论述贯穿在整个《资本论》中,形成了其特有的生态哲学。可以说,一部《资本论》正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魂、而以人与自然的生态物质关系为魄的理论体系。社会关系渗透于人类生态关系中,通过自然定律创造着这种生态关系,并且通过这种物质性的生态关系来表达和实现。
二、《资本论》的生态环境内涵:外环境与内环境
现在通常所说的生态系统,指的往往是社会公共生活空间(如大气、河流、海洋等等)中的环境系统。生态环境的概念其实应当不限于此。广义上说,一切与人类生存有关的自然物质过程,如室内污染和噪音、食物中的有害物质等等都应当包括在内。《资本论》中所研究的正是这样的系统,马克思称之为“生活条件系统”[3]490-491,它比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态系统”更加广泛,我们认为它更符合“人类生态环境系统”的本意。《资本论》描述的“生活条件系统”可分为两类:一是社会生产系统内部生态环境(我们称为“内生态环境”),二是社会生产系统外部生态环境(我们称为“外生态环境”)。
所谓“内生态环境”指的是《资本论》所说的“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3]490-491,其可以进一步再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生产过程(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生态环境,二是生活过程(劳动力的生产过程)的生态环境,这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影响最为直接而巨大的部分,然而也正是现代生态环境概念所忽略的部分。《资本论》花费大量篇幅给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资本所生产的“内生态环境”。在分析剩余价值如何生产的过程中,马克思说,“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难道不对吗?”[3]490-491而这种生产的生态环境还通过产品市场交换系统与消费过程延伸到生活领域,导致人们生活环境的恶化:“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在英国,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都是从十八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这种体现在产品中的生态环境恶化主要由劳动者承担:“由于这种掺假,每天靠两磅面包度日的穷人,现在实际上连1/4的养料都得不到,且不说这种掺假对他们的健康的危害了。”[3]289,291,203这些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与交换系统内部)发生的环境事件。
资本逻辑在直接造成“内生态环境”(发生于室内甚至人的体内)恶化的同时,还由生产性与生活性排泄物及其产生的一系列自然过程,产生“外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在这里讲的“外生态环境”,也即“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之外人们所处的“生活条件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生态环境”。《资本论》说:“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4]115外生态环境的恶化集中表现在产生了穷人拥挤的“住宅监狱”:“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3]762-763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工人居住区环境污染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考察与分析。这里只引出其中一段,就可以看到他对穷人生活的生态环境是何其关注:“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对健康不利,那么,工人区的污浊空气造成的危害又该是多么大啊,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城市人口本来就过于稠密,而穷人还被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2]410
以上内外两种生态环境必须作为统一整体来分析,因为它们在当代具有共同的产生根源——这就是资本逻辑。
三、资本积累与自然资源环境的“贫困积累”
社会关系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对立统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现为“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对立统一,其对立统一运动形成资本逻辑所推动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贫困化”、进而通过“资本—生态”的正反馈循环圈,导致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贫困积累”。
资本积累过程就是资本吮吸“人的自然力”的过程从而造成工人的贫困化和贫困积累。与此同时,资本积累过程也是资本吮吸“自然界的自然力”的过程,从而造成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贫困化”,以及自然环境的“贫困积累”。按照资本逻辑,资本扩张动力一旦得到能够容纳它的市场空间,便会组织起不断扩张的劳动系统,尽一切可能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自然力”来实现其价值增值。这就使自然界的“自然力”被其无限制地消耗而趋于枯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579-580这里的土地泛指各种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成为其榨取与吮吸自然界的“自然力”与“人的自然力”,从而进行资本积累的工具。
而资本之所以能够无限制地榨取自然界的自然力,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这些自然力的榨取“不费资本分文”。首先,资本对产权不明晰的公共资源的利用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马克思指出,“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3]443-444虽然在利用这些自然力时也要支付一定的金钱(价值),但它们只是相关设备所需要耗费的劳动价值,这些自然力本身是不费分文的。马克思说:“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3]444至于这个过程产生的排泄物污染环境更是免费的。因此,这些无代价的免费使用的自然资源,一旦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便会面临着资本不顾一切地疯狂开发与利用,从而导致生态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
其次,对那些具有个人产权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矿藏等等,资本的确要支付一定的租金。西方经济学认为这种租金来自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自然资源的效用价值或者稀缺性价值)。而《资本论》则认为这些自然资源本身只有使用价值而无价值,因为价值的唯一来源是人类的活劳动。作为自然资源的价格的地租来源于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由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而索取和分割出来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也即由超额利润转化而来,而这种超额利润来自于全社会的剩余劳动[4]3。有人说,这种关于地租来源的争论是“形而上学”的争论,因为人们在实践中只能看到生产资料的价格本身,看不到它的来源,因而怎么说都可以。这是十分错误的观念。实际上,对自然资源价格的来源的不同解释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生态结果。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解释,自然资源的价格来源于它的稀缺性,那么价格的高涨必然会因提高了使用门槛而保护这种自然资源免受过度开发利用。然而实际情况常常与此相反,价格高涨并不能起到这种保护作用,反而会促使资源不断被“竭泽而渔”地开采与利用。这种结果很容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解释:因为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乃是瓜分社会剩余价值的工具。某一自然资源的价格越高,能够分割的超额利润就越多,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种社会力量设法通过各种非劳动途径来获取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分割远远超过其劳动价值的社会剩余价值。于是该自然资源不断被疯狂占有,最后面临枯竭和灭绝的命运。以土地为例,由于地价高涨而导致的房价的高涨,驱使越来越多的开发商与投机者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土地与住房的所有权,其目的是不通过劳动来分割全社会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来自最终买家(使用者)用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使他们不得不掏出终生积累的血汗钱来支付这种地价。因此高地价房价不仅不能保护土地资源,反而促进对土地资源的疯狂占有与开发。再比如,长江里的鳗鱼苗价格高涨,其价格大部分来自通过过度捕捞而获得的对该自然资源所有权所能分割的超额利润。正是这种超额利润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狂捕滥捞,最终导致鳗鱼苗面临灭绝。因此,资本在使用产权明晰的自然资源进行生产时所支付的租金只是暂时的垫付。这些租金将会转嫁到最终消费者头上而分割由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因此资本本身对这些“自然力”的使用说到底还是“不费分文”。
因此,由资本扩张力量支配下的社会劳动,的确如马克思所说,不费分文地占有与消耗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资源)。这种“不费分文”(包括由他人支付费用)导致自然资源的使用完全服从资本逻辑的增值需要,由此导致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自然力”日益枯竭而“贫困化”。
而这个贫困化过程,将进一步通过正反馈过程而不断进行“贫困的积累”。在以资本自身积累为唯一目标的资本扩张动力的驱动下,依靠汲取生态系统中自然力母乳而日益强大的生产力,又以更强大的力量汲取生态系统的自然力母乳,由此导致正反馈循环:一方面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贯穿着资本扩张意志的社会生产力系统,其在价值上的表现即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形成了被这个资本积累过程吸收自然力而日益枯竭的生态系统。而资本扩张和积累又必须以这种生态系统的自然力为前提,于是资本扩张将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我们称此为“资本扩张的生态悖论”。一旦生态系统无法支撑与维系这样的生产力系统,便陷入生态危机。如马克思所说:“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580
四、资本逻辑的时空展现对生态逻辑循环圈的撕裂
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生生不已是因为存在着生态循环圈,如碳循环圈、水循环圈等等,从而形成一种动态的生态平衡。然而资本一旦得到能够容纳它扩张的市场空间,便会因不费分文而无节制地吮吸生态系统中的“自然力”,按照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由此形成了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时间周期。资本作为社会关系权力将这种周期性时空布局强加给自然界,撕裂和打断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循环过程,由此产生生态危机。这是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矛盾,是资本逻辑对生态循环圈的撕裂,《资本论》具体地提出了它的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对生态循环圈的撕裂。资本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发生两种分离:一是手工业转变为工业而与农业的分离,二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资本论》指出了这种人类生态史上的巨大变化的意义:“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3]408而这种分离所造成的关键性生态后果,是撕裂了生态系统中物质变换循环圈,导致生态循环的断裂。首先是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导致的生态循环的断裂。随着手工业发展为工业,传统生产力体系发生了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打断了原来农业社会中的生态循环过程,从而使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失去了自我修复的机会。此外资本向农业的渗透,加大了对农村的生态环境的破坏。马克思说:“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两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4]919工业化的农业导致农田无法按照原有的生态循环来恢复其肥力。这种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随着城乡分离而更加突出。
城乡分离对生态循环圈的撕裂。由资本集聚形成的城乡分离,是资本逻辑在经济空间中的表现形式。它在不费分文地吮吸生态系统的自然力的同时,使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链被打断,被消耗的物质无法再回归到自然界。由资本不断集聚而形成的城市,产生了以下的生态后果:“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3]579-580《资本论》第3卷进一步指出了城乡分离所产生的物质变换联系中(即生态关系中)“无法弥补的裂缝”,这是因为大量的“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无法回归到自然的生态循环中,从而造成对城市的污染与农村土地的贫瘠[4]115。
马克思富有预见性地指出,资本积累有城乡关系上表现为城市人口的集聚与膨胀,以及相应的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从而造成生态链的断裂:“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4]918-919
资本运转周期对生态循环周期的撕裂。资本逻辑不但通过资本的空间集聚状态打断生态循环链,而且通过资本运行的时间周期打破生态系统的时间周期,而造成生态循环链的断裂。《资本论》第二卷在分析资本循环周期时说:“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括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漫长的资本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5]这就是说,资本逻辑要求在较短的资本运转周期中通过吮吸森林的自然力来实现增殖,而这个周期必然打断林业的漫长的自然生态周期,于是形成了对森林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资本如果按照森林的自然周期来运行又会面临破产的命运。所以,马克思认为造林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
总结以上所述,我们看到,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在空间分布与时间周期上的展现,指出了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冲突与矛盾。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预言今天发生的一切,但是他的确发现了这种冲突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基本机制。
五、《资本论》中的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观念的萌芽
《资本论》在批判资本逻辑造成的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的同时,还提出了世代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观念的萌芽。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以消耗几十万年积累的自然资源为前提的。他说:“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3]586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他认为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界亿万年进化的结果,没有理由部分人所有,不仅不能被个人私有,而且也不能由某一代人组成的社会集体所有,而只能由世世代代的地球上的人们所共享。他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4]878这就是说,土地占有者不仅具有使用资源的权利,更有保护与恢复资源的义务。这可以看成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的萌芽。而由此导致的危机会导致这种发展方式的结束:“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蜕皮的地步,这种权利(指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的、在经济上和历史上的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4]877-878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世代相续的发展呢?马克思当然希望建立一种对人类生产与生活进行理性安排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市场机制也具有建立人为的生态循环系统的可能性。《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Ⅵ节专门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为了节约与增值,会自动利用生产排泄物进行循环生产:“关于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个大类,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探讨的这一类节约,也是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4]115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促使对排泄物的再利用从而实现循环生产的三个条件:一是“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二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些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三是技术上的进步使这种利用成为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4]94,115
《资本论》中关于在市场内部建立循环经济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资本追求其自身利益,其应对生态危机的基本方式不是消除环境污染本身,而是通过资本的全球化,实行污染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其循环经济活动只能是偶然的、自发的零星行为。只有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力量,才能够在全社会的范围自觉地创造条件,利用市场机制,建立生态逻辑相一致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循环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47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2.
[责任编辑:高云涌]
2014-10-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2AZD066)
鲁品越(1949—),男,教授,特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哲学研究。
B1
A
1002-462X(2015)01-0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