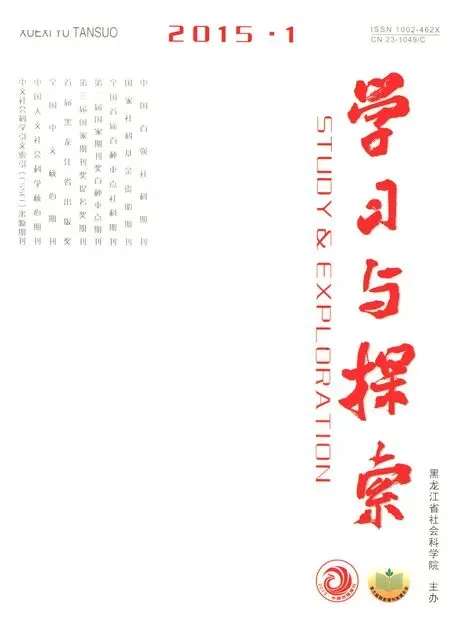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
贾 根 良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
贾 根 良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李斯特经济学总结了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以前西方世界兴衰的经验教训,是经济学中最早系统地揭示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规律的经济学说,对美国和德国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是导致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史上发展道路“大分流”及其截然不同命运的首要根源。“二战”后的冷战环境导致了李斯特经济学的衰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呼唤李斯特经济学的归来。李斯特经济学所开辟的发展道路曾是历史上发达国家崛起的普遍道路,而“中国模式说”却假定了“中国例外论”。为了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开设了“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专题讨论,其目的就在于“为往圣继绝学”,改变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过程中,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
李斯特经济学;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日大分流;中国模式;中国例外论;新李斯特学派
一、李斯特经济学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是反对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创建者,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仅次于马克思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最多的德国人的著作,对19世纪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斯特在美国流亡期间曾成为第一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和该学派保护主义经济理论的整理者,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家迈克尔·赫德森曾把包括李斯特经济学在内的美国学派与李嘉图的自由市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并称作1815年至1914年间发展起来的三种主要的经济学说[1]17-18。李斯特总结了在他之前西方世界兴衰特别是英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批判性地继承了重商主义经济学现实主义的经济学成就,为当时的落后国家追赶发达的英国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民经济学说及其政策建议。
李斯特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之前西方世界兴衰的历史考察,提出了一种与技术革命导致工业革命的老的经济史学、诺思有关西方世界兴起的“新经济史”,以及彭慕兰、王国斌等有关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大分流”(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2]都有重大不同的经济史解释。①民族国家竞争导致了英国选择高质量经济活动作为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原则,以及以这一原则作为一系列国家建设措施的轴心,这是导致英国崛起、工业革命爆发和中西方“大分流”的根本原因,笔者所倡议的“新李斯特学派”将运用演化经济学的现代语言,发展李斯特有关西方世界兴起的经济史理论,这可以被称作是“新李斯特经济史”,笔者在几年前曾把这种经济史研究称作“演化经济史学”。在李斯特看来,西欧各民族国家为争夺霸权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这种激烈的竞争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国富国穷发生机制的探索和发现过程,它最终从实践中发现了“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致富原则,这一原则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诞生和随之而来的殖民主义时代的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的,但悖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却导致了旧殖民主义的瓦解,但在此之前,“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一直都是国家崛起的一种“普遍的真理”,所谓殖民地在经济学上的经典定义就是沦为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
虽然这一原则早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就被意大利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焦万尼·伯特罗和安东尼奥·舍拉明确阐述,并在西欧大陆得到了传播,但只有英国对其理解最到位,并得到了最早的系统性实施。英国以这一原则为指导,在内政外交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国家建设,通过“对外关税保护和对内自由竞争”,不仅在西欧国际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主导产业上依次打败了原先在麻纺织业、丝织业和毛纺织业占据国际领先地位的国家,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3],而且还通过对当时印度次大陆占据世界统治地位和技术领先地位的棉纺织品的禁止性关税保护,在进口替代战略之下,最终催生了震撼世界的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4]。但当英国在大机器工业占据世界垄断地位后,转而诋毁贸易保护,大肆宣扬自由贸易等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李斯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一个人已经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5]307。
李斯特经济学就是建立在上述西方世界兴衰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李斯特指出,“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准则,即一个国家出口的工业品越多,进口的原料越多,消费的热带地区的产品越多,它就越富裕、越强盛”[6]。他所提出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生产力理论、工业化理论和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实际上都是针对“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在国家崛起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典型化事实而提出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李斯特并不热衷于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他最为关心的是在英国的排挤性竞争中,他的国家如何才能不沦落为英国的附庸。因此,笔者在下面将要简单地说明“他的经济学说这种在实际影响上的确凿现象……(它在)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5]1,以及对许多国家经济事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李斯特在年轻时,由于作为德国激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代表人物和创立旨在于德国经济统一的德国工商业联合会而触犯了德国各君主国的利益,被迫不得不于1825年流亡美国。在美国,李斯特接受了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幼稚工业”理论,结识了众多的美国保护主义政治领袖,并参加了美国当时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论战,1827年出版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美国体系),成为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不仅对美国内战前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通过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对美国内战后狂飙突进的工业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斯特在1841年曾预言到:“看上去在我们孙子一辈的时代,(美国)这个国家将上升到世界第一等海军与商业强国的地位。”[5]87如果一代人按照25年计算,两代人也就是大约50年之后的1894年,美国果然崛起为世界第一的工农业强国。这是一个非凡的准确预言!
李斯特在1830年加入美国国籍后,美国总统杰克逊为了答谢李斯特对1828年竞选总统时对他的支持,询问他需要什么样的回报,李斯特回答说他还是心系德国,因此他最终作为美国驻巴登领事的身份重返德国。回到德国后,李斯特全身心地投入了宣传关税保护、创立德国关税同盟和建设铁路的伟大事业,但德国封建反动势力一直都在迫害他,最终迫使他于1846年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那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涯。但在李斯特去世三十年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却成了德国“最受欢迎的一本书”[7],在德国广泛流行并成为“铁血首相”俾斯麦的案头书,对德国在其崛起的关键时期(1879—1914)实施保护主义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对俄国、罗马尼亚、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业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沙俄帝国晚期重臣和政治领袖谢尔盖·维特(1849—1915)是李斯特的忠实信徒,他不仅于1889年在俄国出版了宣传李斯特学说的著作,而且在其任期(1892—1900)内实施了尊奉李斯特精神的“维特体制”,发起了俄国现代化的第二轮“大冲刺”(第一轮是由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发动的)。
二、李斯特经济学与中日大分流
对于19世纪的两个后发工业化国家——美国和德国在1900年成功地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工业化大国来说,李斯特经济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在学术界已经得到较普遍认同的历史事实。但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和事实却是: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1912)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国家精英们集体接受了李斯特经济学,并尊奉为治国的圭臬;而从洋务运动一直到辛亥革命,不仅洋务运动领导集团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严复除外),无一人知晓李斯特经济学,而且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和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还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说,正是这一因素并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近代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出现了“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而中国却沦为了其半殖民地。
我们知道,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主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但我们并不知道的则是:他们是李斯特经济学说的信奉者。大久保利通不仅撰文宣传日本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而且在上呈天皇的备忘录中,大力推荐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但对亚当·斯密则不屑一顾[8]。伊藤博文在1870年曾作为大藏省少辅前往美国考察财政金融制度,由于受到美国高关税保护和国家银行制度的启发,在给政府的意见书中建议对其幼稚工业实施关税保护[9],当伊藤博文回国时,他已经成为以关税保护、国家银行和内部改善为核心的“美国制度”在日本的坚定推行者。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家、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曾担任日本天皇的顾问,当他离任返回美国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达成了普遍共识”[1]157。正是在李斯特经济学的决定性影响下,日本形成了导致其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制:保护民族经济、建立现代财政金融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和统一国内市场。
李斯特经济学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传播和广泛普及也是令人吃惊的。1870年,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大藏省官员若山则一就出版了宣传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保护税说》。1889年,日本出版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日本经济思想史家铃木指出,“在李斯特去世至其思想在日本普及的40余年里,历史学派的理论在德国经历了长足的发展”[10]70。请注意,铃木在这里使用的词汇是大致在甲午战争前“李斯特的思想在日本的普及”,这说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不仅对明治维新领导集团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日本知识界也是占主流的经济学说。铃木还指出,“在国家对倡导和保护工商企业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不如德国历史学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具有吸引力是毫不奇怪的”[10]5,这再次证明了李斯特经济学作为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的官方经济意识形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是,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却无人知晓李斯特(可能严复除外)。虽然李斯特经济学在戊戌变法之后已经被个别中国人所知晓,但只是到了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刘秉麟所撰《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李士特”是当时对“List”(李斯特)较普遍的汉译。和同年春王开化翻译完成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王开化1925年将李斯特的这本著作的书名翻译为《国家经济学》,直到1927年8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李斯特经济学才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因此,我们把1925年作为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性的一年而加以纪念,本组专题严鹏的论文对清末和民国时期李斯特经济学在华传播过程进行了研究。对比一下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当时中日两国被接受的巨大时间差,我们就可看出它对各自不同命运的深远影响:在中日两国迎接西方列强挑战的关键时期,刘秉麟与若山则一介绍李斯特经济学相差了55年;中日两国翻译出版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相差了38年。由于缺乏李斯特深刻的工业化思想和可借鉴的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所提供的话语体系根本就无法分析西方的挑战并提出适应世界大势的战略和政策,这是导致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挑战上出现“大分流”的最重要因素。
李斯特经济学自1925年传入中国,特别是李斯特的著作在1927年出版后,其就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并对当时的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从刘秉麟和李斯特的著作再版情况可以看出:刘秉麟的著作于1931年4月收入《经济丛书社丛书》再版,并以《李士特》为名在1930年和1933年再版两次;李斯特的著作在1929年再版,并在1933年和1935年出版“国难后一版”和“国难后二版”(见本组专题严鹏的论文)。其次,李斯特的经济学对民国时期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之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与现在中国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信奉者不同,即使是当时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民国经济学家们也都赞同李斯特的保护民族工业学说。然而,由于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等因素的严重影响,李斯特经济学并未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作用,其历史教训至今仍需深入探讨。随着1949年的政权更迭,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原有的发展理念已无用武之地。因此,虽然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的争论中所得出的结论被肯定为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在196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重译本主要是作为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参考资料而出版的。然而,由于战后的冷战环境,社会主义中国被迫走上了与资本主义世界“脱钩”的发展道路,高关税保护一直持续到1995年开始为加入WTO大幅度降低关税时为止,例如,1993年中国的加权进口关税率仍高达38.4%。近半个世纪的高关税保护无意中创造了李斯特式追赶型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中国奇迹”的重要成因,而且也为加入WTO之后仍保持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三、李斯特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
正如德国经济学家迪特·森哈斯指出的,李斯特经济学对当代世界来说,“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在19世纪上半叶,正当欧洲大陆面临工业革命后英国所构成的重大挑战时,李斯特就发展政策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欧洲大陆各国如何才能经受住生产力更强、效率更高的英国经济所发起的‘排挤性竞争’,不至于沦为工业革命领先者的边缘性附庸?”[11]李斯特认为,为了抵抗英国的“排挤性竞争”,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战略性新兴工业,美国和德国应该针对英国已领先的这些工业构筑关税壁垒,拒绝其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从而使美国和德国的战略性新兴工业独占国内市场。只有当美国和德国的战略性新兴工业通过国内市场发展壮大后,才能够对外开放其国内市场。实际上,李斯特向美国和德国推荐的这种战略只不过是英国在工业革命前针对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印度次大陆棉纺织手工工业所采取的战略而已,但意外的是英国却因此而爆发了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通过模仿英国的这种战略,领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超过了英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由高筑关税壁垒的国家发动的,这个历史史实无疑值得把自由贸易看作是自由的化身和普遍真理的主流经济学界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思。从这种历史经验和李斯特为之提供的理论来看,李斯特经济学具有如下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李斯特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普世性”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是一种“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经济学的宗旨就在于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建立关税壁垒,使欠发达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隔离开来,阻断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赢者通吃”这种高效率的市场机制毁坏欠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兴工业。国家干预的目的在本质上与纠正市场失灵或者提供短缺的生产要素是不相干的,而是为了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新兴工业成长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从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据此,李斯特通过总结到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有关贸易与发展的三阶段理论:落后国家为了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可以对发达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但当一国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基础之后就必须实行贸易保护;而当该国通过贸易保护开始进入发达阶段之后,才能够再次恢复自由贸易,对国际市场开放。
其次,李斯特经济学提出了一个被当代经济学家赖纳特运用演化经济学深入阐发的国家经济学原理:不同的经济活动创造财富的能力是不同的,只有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才能富国裕民,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被世界经济史反复证明为完全正确的原理。李斯特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所谓财富的生产力也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在他看来,制造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国民财富的基础,为了突出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李斯特使用了“制造力”一词。国外有经济学家指出,“认为制造业‘根本’不同于农业和贸易,并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这一主张之上,李斯特是这样做的首位经济学家”[3]372。历史证明,重农学派强调农业和土地是国民财富的唯一源泉对法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而亚当·斯密虽然突破了重农学派的观点,认识到劳动而非自然是价值和国民财富的源泉,这是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重大贡献,但是,他却认为劳动的质量没有区别,甚至更强调农业在创造财富上的能力,所以,亚当·斯密以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不能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行之有效的战略。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国家是比个人和市场更为基本的力量,它不仅塑造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关系,而且也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石。在李斯特及其继承其传统的经济学来说,对外建立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经济关系,对内建设社会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这是自由市场根本无法承担的两大重担。在李斯特看来,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一国范围以内的贸易自由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自由……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都截然不同,犹如天渊之别。”[12]因此,欠发达国家就不能在世界市场上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因为对不利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国家干预对其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李斯特在国内市场上强调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进而强调市场在国内经济中起决定作用是否正确呢?也不完全正确。李斯特强调国内市场上不受任何阻碍的自由贸易无疑是正确的,但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竞争则大有问题。举例来说,美国“镀金时代”的自由放任政策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从而催生了以政府干预和社会保护运动为特征的“进步时代”[13]。总而言之,“驾驭市场”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相继崛起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成功经验。
那么,如何评价李斯特经济学呢?在笔者看来,李斯特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早系统地揭示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历史规律的经济学说,这就是李斯特经济学的重大意义之所在,也是它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作为三大理论体系之一而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认为“李斯特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一门研究特定国家的国民经济的科学,从而否认了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联系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5]8的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自法国的孟克列钦在1615年出版《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直到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作为关于民族国家经济的科学而得到发展的,只是从亚当·斯密开始,它才变成了关于一般经济规律特别是关于阶级关系的科学,而恰恰就是这种转变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对民族国家经济发展这一重大主题的忽视。我们无法否认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存在着普遍的客观规律,也无法否认这一重大主题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联系的客观规律”的研究,我们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目的之一就是强调这一主题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
李斯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矛盾,两者可以统一起来,这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确实,马克思在1845年的手稿《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李斯特进行了批判,许多学者因此就在有关马克思与李斯特的关系问题上长期停留在马克思的这个早期手稿上。但我们的研究说明,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14],特别是马克思于1867年11月在有关爱尔兰民族发展问题上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15]已充分表明,马克思实际上已放弃对李斯特的异议,完全认同了李斯特关于欠发达国家保护幼稚工业的观点。笔者的研究还说明,幼稚工业保护也是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建设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基本保障[16]。因此,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恩格斯在1859年曾指出,“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17]。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是不准确的,在恩格斯写这段话之前,李斯特无疑已是德国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大师。
四、国际金融危机呼唤李斯特的归来
然而,虽然李斯特经济学在19世纪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等许多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正如赖纳特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环境导致了以李斯特民族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文艺复兴经济学传统的几近绝迹[18]。莱维·福尔(Levi-faur)也写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主要流派——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提供了基本的专业文献。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自由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之间的敌对状态下,经济民族主义变成了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从而在理论和分析上都得到了更细密的研究。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并不是这样,在当时被广泛阅读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经济民族主义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吸引了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的注意力。”[19]由此可见,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李斯特经济学在当时的经济思想界曾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受到战后这种环境的影响,在发展经济学这个专门研究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向发达国家历史性转变的领域中,李斯特经济学在该领域中受到了不应有的严重忽视。例如,由英国经济学家A.P.瑟尔瓦尔初版于1972年并分别在1978年和 1983年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的《增长与发展》的教材中,无论是在回顾“学术界对发展问题的兴趣”时,还是在第三篇讨论“发展的障碍”中,通篇都没有提到过李斯特[20]。又如,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本大部头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中,当介绍“1950年以前的经济发展思想”时,列入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熊彼特的经济发展思想,但却遗漏了李斯特[21]。
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忽视了李斯特经济学对当代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分支学科仍是受“亲”李斯特传统的结构主义经济学所支配的,这被称作经典发展经济学的时期。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卷土重来,这被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称作“新古典反革命”,以至于目前在几乎所有的大学中,除了韩裔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参见张夏准《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政策史》,王晓蓉译,贾根良校,《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5月27日(第21期)。“踢掉梯子”一词就出自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一书,张夏准的这本专著最后在2007年以《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为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样的个别经济学者外,发展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都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支配。随着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和随后的“里根革命”,以及苏联东欧的剧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获得所谓“只有一种经济学”的独家垄断地位,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几乎陷入了绝迹的境地,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被妖魔化,在中国几乎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贬义词。
然而,世事难料。进入新世纪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遭到惨败,开始逐渐地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坚持李斯特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两位经济学家*这两位经济学家是挪威经济学家埃里克·S. 赖纳特和韩裔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他们的主要著作都已经翻译成中文。的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英国著名报刊《金融时报》在2007年专门对其学说展开讨论[22]。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方案的多种选择,李斯特主义的呼声虽然微弱,但也与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和平等主义并列为选择之一[23]101。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了李斯特经济学的回归,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李斯特最新传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具有前瞻眼光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于2013年8月在德国出版后,目前已有英、法、西、日、汉等译本都在翻译中。该书著者温德勒教授对此评论说,“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背景下,李斯特学说突然显得非常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思想感兴趣了”[24]。
五、对“中国模式说”的“中国例外论”的质疑
在中国于1995年为加入WTO开始大幅度降低关税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在90年代初就已出现的“用开放倒逼改革”思维模式的指导下,中国最终形成了目前仍占支配地位的发展模式:通过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和2010年,按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这种模式的各种弊端也日渐得到暴露,自2003年以来,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执政方略,如“建设和谐社会”“自主创新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环境与资源友好型社会”“扩大内需”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际上都是针对这种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而言的。
由于所接受的经济理论不同,人们观察到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方面也就不同,学术界对“中国模式”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评价。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中国崛起”或“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从2004年“北京共识”概念的提出开始,“中国崛起”以及所谓“中国模式”的论说日益风靡全球,“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成为国际社会和中国精英阶层的高度共识,他们坚信,“自贸区”、更大规模地开放国内市场和金融自由化是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
但是,国内外学术界也不乏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质疑之声。事实上,当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崛起之时,它们无不达到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名列世界前列的地位,而如今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乃至第一大经济体的同时,中国的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仍处于第100位之后,不知“中国崛起”是从何谈起的?笔者曾在一系列的论文中指出,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中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25]。美国历史学家弗格森的“中美国”概念分明指的是宿主(新型殖民地)和寄生虫(新型宗主国)的关系,而一些中国人不察,反而对“中美国”的“夫妻”关系津津乐道,这无疑是对“中国崛起说”或“中国正在崛起说”的莫大讽刺。实际上,自由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美元霸权、全球价值链和金融开放是“套在巨龙(中国)头上的五条致命绞索”,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危急时刻: 独立自主还是依附型国家[26]?
伦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博士岳健勇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崛起”和 “中国模式”的神话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狭义指赶超)”的发展模式,它本质上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是一种有别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发展”的新型依附,中国已深陷全球化陷阱难以自拔。正如岳健勇指出的,在世界经济史上,工业化从来都是先于经济自由化,而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即已大规模开放国内市场,难道中国可以成为通过自由主义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工业化的成功例外吗[27]?进一步说,历史上的发达国家在其经济追赶阶段(中国无疑仍处于这个阶段),无一不是通过保护国内市场、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拒绝加入领先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而实现崛起的,难道中国可以违背这一历史规律而实现崛起?“中国模式说”实际上就假定了这样一种“中国例外论”。
“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话语或论说是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之后,才开始迅速大量出现的。但笔者早在2008年就已指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美国经济战略家有意麻痹中国人意识的一种圈套,目的是让我们陶醉在虚假的幻象中,而不是去反思,从而找到一条真正的“强国富民”的经济发展道路。岳健勇也指出,真正令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感到不安的,是中国探寻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自主发展[28]。在笔者看来,这种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发展模式就存在于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跳跃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中,而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包括李斯特)和李斯特经济学则分别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自20世纪初以来,与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时的环境相比,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必须有所创新,才能取得与英国、美国和德国相同的成功,但国家崛起的基本原理仍是具有共同基础的。
结 语
然而,对于中国在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探索一种新模式来说,却存在着巨大的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日益取得主流地位,虽然有个别学者如何新、梅俊杰以及笔者等一些学者仍心仪李斯特经济学外,但本来就被戴上“庸俗经济学”帽子的李斯特经济学一直没有得到正名,到现在就越来越不被人们所了解,更谈不上发展和创新这一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经济学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对外国家干预、对内自由主义”的李斯特经济学不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完全接受了无视欠发达国家利益的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而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也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以至于存在着坠入“新洋务运动”彀中的巨大危险[29],李斯特经济学完全被边缘化了,继承和创新李斯特经济学的美国学派政治经济学更是不为人所知。缺乏经济思想基础几乎使得中国探索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成为不可能。
正是出于对这种不利的思想和学术环境的忧虑,已经按捺多年的我们禁不住要大声疾呼:中国迫切需要李斯特!目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猛醒。首先,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近代史上,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与日本不同的命运,“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上迟缓软弱以及与日本命运截然不同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23]95在笔者看来,近代以来,凡是没有受到过李斯特经济学洗礼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的,难道我们还要重蹈历史覆辙?其次,如果承认“中国模式”存在着某种不可持续性的因素,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了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因为美国及其战后盟国出于地缘战略而成功地得到“受邀发展”外,发展中经济至今仍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先例,而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成功却与李斯特经济学存在着密切联系。①Ian Patrick Austin,Common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and East Asian Modernisation: From Alexander To Junichero Koizumi,Select Books: Singapore,2009,p.11.
中国经济学界有义务为中国社会各界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只有深受李斯特经济学影响的国家实现了经济崛起,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如何绘制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蓝图?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李斯特,重读李斯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基本原因,其目的之一就在于要改变近代以来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为中国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补充新的思想基础。北宋哲学家张载曾提出反映中国知识分子恢宏志向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虽不敢言“为天地立心”和“为万世开太平”,但我们应该并且也能够“为生民立命”和“为往圣继绝学”,我们开办这个“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创立一个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核心的“新李斯特学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1] 赫德森 迈.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4] 帕塔萨拉蒂 普.为什么欧洲富强了而亚洲却没有[M].王中华,译.贾根良,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 李斯特 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6] 阿尔金.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M].晏智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08.
[7] HENDERSON.Friedrich List: Economist and Visionary 1789—1846[M].London: Frank Cass,1983:215.
[8] 格林菲尔德 里.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381.
[9]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34.
[10] 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M].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0.
[11] SENGHAAS D.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M].New Hampshire: Berg Publishers Ltd,1985:151.
[12]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8.
[13] 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2).
[14] 贾根良,陈国涛.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比较与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9).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62-363.
[16] 贾根良.保护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J].当代财经,2010,(12).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5.
[18] 赖纳特,贾根良.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M].贾根良,王中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6-47.
[19] FAUR L.Economic nationalism: from Friedrich List to Robert Reich[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23): 359-370.
[20] 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1] 杨敬年.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55-56.
[22] 贾根良,黄阳华.评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的新争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5).
[23] 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J].学习与探索,2012,(3).
[24] 梅俊杰.李斯特回归[N].社会科学报,2014-07-04.
[25] 贾根良.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致命弊端[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6).
[26] 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J].社会科学战线,2010,(1).
[27] 岳健勇.全球化导致了中国崛起吗?[J].领导者,2014,(8).
[28] 岳健勇.中国为何热衷于自由贸易?[J].南风窗,2010,(25).
[29] 贾根良.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4,(1).
[责任编辑:房宏琳]
2014-11-20;
2015-01-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重大基础理论研究”(14ZDB12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经济思想史”研究(14JGA005)
贾根良(196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从事演化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研究。
F091.342
A
1002-462X(2015)01-00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