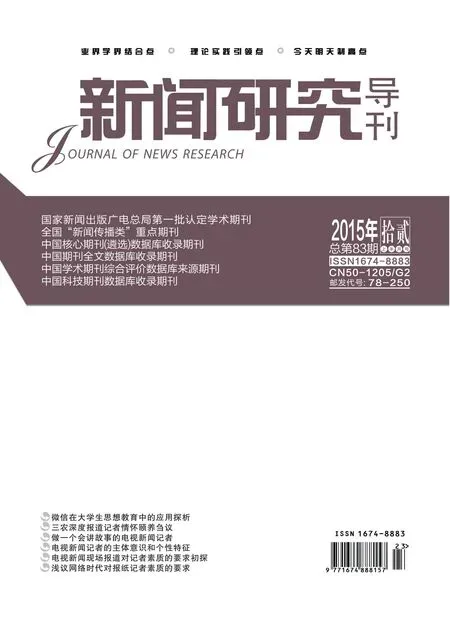生活政治视野下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民主化传播实践探析
陈佑荣
(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0031)
电视娱乐不仅成为当今中国电视媒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构成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在传统政治逐渐有所式微的当下,看似非政治化叙事的电视娱乐实则以生活政治作为重要表现内容,其在展现大众日趋多样的生活价值观念进而满足公众选择诉求的同时,更有力地唤醒了公众的个人主体意识,促成了公众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尤其是以选秀节目为代表的电视娱乐通过自身的传播优势吸引数以万计的公众集体进行一场场参与式民主实践,其对于几千年来都少有公民参与的传统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更对当下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示范性价值。
一、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中的生活政治议题
长期以来,电视娱乐就被传统自由主义传媒研究排斥在民主政治的讨论范围之外,其主要理由是“娱乐节目不是理性交流的一部分,也不属于政治领域”,往往“毒害人民”,尤其滋生人们的政治冷漠,鼓励人们逃避政治和现实生活。[1]用经济学中“葛氏定律”来说,传媒用大众娱乐的“纸币”驱逐了政治的“硬币”。[2]传统媒介研究长期以来将娱乐排除在政治之外,其前提是将“政治”定义得相当狭窄,仅仅局限于政府选举。如果说当时自由主义媒介理论因其诞生于传统政治主导一切的历史性背景,没有办法预知会有生活政治的到来而情有可原的话,那在政治实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如果还是不作变更地照搬理论来关照当下,就实在需要进行自我反省。库兰甚至明确指出,今天还把娱乐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娱乐不仅为公众提供认知现实的图谱进而提供各种具有政治含义的社会理解,还往往与各种社会价值观、身份观的争论紧密相关,甚至已成为某些政治议题的载体。[1]换而言之,电视娱乐不仅触及传统政治的核心议题,还会涉及当下生活政治的丰富议题,而且往往通过生活政治议题来促进传统政治的进一步变革。
对于中国电视娱乐而言,其诞生之初就与政治处于过密的复杂关系之中。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电视娱乐节目长期以来致力于为传统政治权力服务,国家叙事的传统政治议题往往成为重要传播内容,深受集体主义意识浸染的公众往往也是娱乐节目的宣教对象,其自身本应承担的娱乐功能反而遭到严重削弱乃至阉割。不过,随着市场经济和西方思潮的双重驱动,中国民众慢慢从集体无意识的睡梦中苏醒,开始关注个人自我感受、注重自我价值追求乃至选择个性化生活方式。与之相应的是,市场驱动下的电视娱乐也逐步与传统政治有所疏离,转向公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不断涌现的诸多娱乐真人秀,多方位展现多样化生活政治议题,不仅关注消费、环保、生活方式等个体化议题,甚至涉及诸如夫妻关系、社会性别、爱情乃至个人激情等传统上认为不应登上大雅之堂的私密议题。例如,在不同时期引发全国娱乐风潮的《超级女声》和《中国好声音》,不仅让观众领略了投票选举的参与魅力,更让无数公众知道了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超级女声》节目中诸如李宇春、尚雯婕等一个个走着中性路线的选手被公众通过投票推上冠军宝座,极大程度上颠覆了中国传统对于女性审美观念的标准,进而引发了社会对女性美标准的大讨论。社会学者李银河甚至认为,这些选手通过中性化打扮和中性化唱腔赢得最高民意支持,明显表明民众对传统性别审美的标准开始动摇甚至开始反思,这即便“没有构成对男性权威的挑战”,但无疑也是一次“‘跨性别主义’的胜利”。[3]《中国好声音》对于选手“梦想”的不断强调,尤其通过对选手追梦过程的生动呈现进而展示个体价值的多元,最终给普通大众提供了一种表达人生梦想、实现个体价值的通道,也反映出个体“在家国同构的古老中国被渐渐挖掘,从计划经济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慢慢凸显”。[4]
由此可见,深处市场化浪潮中的电视娱乐节目“并不仅仅只是为行业带来了经济利益”,也“制造了新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政治”。[5]中国电视娱乐在逐步走向大众日常生活并为其带来快乐的历程中,并非是对政治的决然抛弃,而是转向社会价值观、身份认同、性别关系等似乎相对私密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只涉及特定个人,而是整个社会都须面对。所以,克罗图和霍伊尼斯富有洞见地指出,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有政治性。虽然大部分人经常认为电视娱乐“仅供娱乐”,但他们还是会直接或间接地赋予角色和故事情节以政治意义,最终从政治的角度来阐释所有的媒介内容。[6]
二、生活政治: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民主化传播实践通路
传统传媒研究对于娱乐内容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忽视乃至误解了娱乐本身的政治意义和民主价值。库兰明确指出,“娱乐应该被看作是媒介促进民主进程的积极部分”,尽管不能用“娱乐内容取代公共信息和政治辩论”。对于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来说,在传统政治权力主导一切的时代,它的确没有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发挥出太多积极作用,与同时期的电视新闻所表现的几乎一样乏善可陈,主要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载体。但随着政治的松绑和市场经济的推动,电视娱乐节目开始娱乐化叙事,其通过采取所谓的“非政治”策略积极开发娱乐内容,这种策略本身则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因为对于有过传统政治长期统摄一切的特殊历史的中国来说,长期受制于传统政治的电视娱乐并没有真正为公众提供名副其实的娱乐内容,而公众也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和发言的权利。正因为这一特殊原因,所以对于今天愈来愈具有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公众来讲,其对电视娱乐的追求和选择本身就极为鲜明地体现了一种个体权利政治,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政治权力无处不在的长期越位的强烈反叛和抵抗,这也是中国特色式的政治性。换句话说,电视娱乐通过为公众提供大量娱乐内容,不仅仅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也是在满足公众大胆追求的一种个人权利。而电视娱乐越“非政治化”,则越体现了公众个人权利的有效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娱乐就在从娱乐功能向娱乐内容积极转化的过程中,恰恰找到了一条积极建构中国民主的可操作性路径。一方面,由于公众长期以来对于娱乐充满强烈需求但却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的多年压抑,电视娱乐的大力开放自然能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尤其是电视娱乐不断由明星模式向平民模式的转向,能够非常有效地抓住日益想要表达自身诉求的公众最敏感的神经,让公众感觉其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这种权利不仅仅在于娱乐需求的满足,更在于为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表演舞台,而这个舞台长期以来一直被传统政治权力所牢牢掌控,普罗大众对之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电视娱乐正是利用公众对于娱乐的需求和对于权利舞台的渴望,并以各种新颖的方式和新颖的内容最大化地吸引公众的积极参与,扩展了生活政治的影响力,促使公众更加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电视娱乐所展示的生活政治议题,无论是一种个性观念还是性别取向,无论是爱情选择还是婚姻问题,其相比于电视新闻涉猎的其他诸如教育、就业、医疗、交通等生活政治议题而言具有极低政治风险性,更不会直接冲击传统政治权力的核心敏感地带,往往不会受到多少政治约束。而这类相对体现多元诉求的政治议题尽管被批评者认为是“公”“私”混淆,但毫无疑问往往打破新闻具有的地缘性缺陷而能获得不同地域、不同阶层观众的共同关注,最终形成全国性争论。而讨论议题的政治低敏感性甚至无敏感性决定了公众即使大规模的参与卷入也不会引起官方的强烈反感,尽管偶尔也会有一些官员批评性的片言只语,但不会像电视新闻那样往往被官方实行“腰斩”,因而可为中国当下民主化实践提供一种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示范策略。
三、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民主化传播实践内容
随着市场的驱动和官方的民生化导向,中国电视娱乐与电视新闻一样聚焦于公众日常生活,并以生活政治为有利的民主化传播实践的重要路径,规模化建构中国参与式民主实践,而这种民主参与的广度性往往比电视新闻的民主化建构实践更具彻底性、持续性和影响力。
(一)从娱乐大众到大众娱乐:唤醒民主参与的主体意识
尽管电视娱乐长期以来都在喊着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口号,但事实上只有在今天人民摇身变为消费者才真正获得了相对娱乐主动权。对于需要自负盈亏的电视娱乐制作者来说,随着市场化力量的驱动,如何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成为其无法回避的一个考量中心,尽管其最终还是想借收视率去向商家置换高额的市场利益。作为电视娱乐的制作者也深刻明白中国电视娱乐内容长久的名不副实已致公众正常的娱乐需求受到过度抑制,更能体察特殊的历史背景已致本来只是作为大众普通正常需求的娱乐偏偏升格为一种其必须要始终坚持奋斗方能争取到的权利。这意味着,如此背景下的电视娱乐当其走向大众的时候,尽管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看来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但公众所获得的远不只是一种纯粹生理需要的感官满足。
纵观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历史,从《正大综艺》《综艺大观》到《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再到后来的《超级女声》《快乐男生》乃至当下持续火爆的《中国好声音》,这一系列节目的起承转合清晰地反映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通过由娱乐大众向大众娱乐转换,进而唤醒公众主体参与意识的清晰路线图。这些深处市场化冲击浪潮下的电视娱乐节目为了吸引公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卷入,不仅脱掉了过去宣传教育的外衣,更是扭转明星娱乐取向而朝大众娱乐方式转向。因为在公众越来越有快乐欲望和制造快乐欲望的今天,电视娱乐制作者明白只是简单请明星来博得观众为之一乐已经不再那么管用。在大众化路线策略的运用下,电视娱乐为了鼓励公众的参与热情,制作者运用了大众文化所特有的开放性、丰富性乃至暧昧性,用极具政治性的权力话语刺激对传统政治既有热情又有警体的公众本身具有的丰富想象力,从而在大众与娱乐的短暂相遇中即刻产生非同凡响的激情火花,迅速唤醒大众沉睡已久的自主意识和参与热情。电视娱乐以如此鲜明的方式为公众赋权从而唤醒公众的自我主体性,这是一直受到众多政治束缚的电视新闻节目所远远不可想象的。例如,《超级女声》不仅宣称“一切权力交给大众”,更是宣扬“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的自由个性——从节目主题歌到选手宣传片甚至再到各路媒体狂轰滥炸式的报道,反复诉说着大众本应具有的主体性权力,更激发了公众对于娱乐之外的权力想象。该节目动辄数十万的参与报名以及随之而来的上亿公众围观,更被研究者誉为“启蒙理性在现代中国最成功的一课”。[7]近年来的《中国好声音》更是处处传递着草根大众的梦想,这种个人化梦想反映出个体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而节目“导师转身”环节的设置更体现了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的公正性,这一公正性环节也有力回应了大众希望在公正规则下实现个人梦想的殷切期待和朴素愿景。
(二)媒介融合下的电视娱乐:多维演绎的民主参与奇观
对于以参与为核心的民主来说,如何保证公众充分而有效的参与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但无论争议性有多大,都会认同一点:如果一个民主制度最终无法让大众参与,民主制度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甚至根本不能以民主来命名。科恩就认为,民主的真正有效首先要有一个广度,即要有足够的参与人数,其次才是参与的深度。而正因为民主对参与性的天然要求,所以哈耶克认为民主其优越性并不在于选出某位统治人员,而在于大部分人都积极参与了形成意见的活动,进而有相当数量的人员可供遴选。[8]而以选秀节目为代表的电视娱乐节目之所以体现了鲜明的民主建构作用,不仅在于其借助大众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开放性和暧昧性,利用诸如“赋权”的策略方式向主体意识处于沉睡状态或压抑状态的公众发起了一次次让电视新闻难以发出的“权力宣言”,从而激发了公众民主参与的强大热情,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娱乐利用当今媒介融合的技术优势、联动其他媒体渠道一起为公众的规模化参与提供实实在在的演练场域和民主参与机会。尤其是选秀节目大都通过电视媒体与其他媒介技术的联动来为公众创造更多参与空间,从而使得公众的参与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相比以往节目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联动最大化地向公众传达相关信息,也使公众可以表达相关意见,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聚合效应,从而让更多无法亲身走进比赛现场的观众的参与诉求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实现,也往往更能体现民主参与的广度。更为重要的是,选秀节目借助短信投票使公众个体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借此从口号宣言真真切切地演变为一种有效行动,甚至演绎为席卷全国的大众民主狂欢。尽管官方一再宣称,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有许多实践形式,并非只有全民选举才是民主,但其“民主不是选举”的宣称无法遮蔽“民主需要选举”这一事实。公众对于西方的选举大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于将之运用到中国的传统政治领域抱有极大期待。所以,电视娱乐对于投票选举的短信活动的开启,对于几乎没有经历过投票选举的中国公众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震撼力。因此,长期处于投票饥渴状态的大众,“一旦有机会享受这样的权利,即便是参与一项娱乐活动,也会表现出异常强烈的欲望,尤其是观众只需要动一下自己的拇指,就能完成这一投票的过程,而且只需要一点点费用就可以形成一次有效的参与……不管是否存在什么黑幕,或者某种不公正,单从过程来看,‘拇指风暴’引领的民主投票,是具有‘民主性’的。”[9]
四、结语
深受市场力量的强劲裹挟,电视娱乐节目已然成为了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电视媒体机构的重型竞争武器。出于市场利益考量的电视娱乐节目,一方面与传统政治议题谨慎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则积极呈现公众日常生活政治议题。更为重要的是,生活政治议题的低敏感性为娱乐节目民主化传播实践提供了有效通路,进而促成极具规模化的参与式民主实践。不可否认,电视娱乐节目的这种民主参与实践存在诸多瑕疵,也不否认其背后存在市场利益的考量,但不能因此而对于民主化实践本身视而不见,更不能苛责它没有一步到位或不够彻底,毕竟民主本身无法一蹴而就。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刻体察电视娱乐民主传播实践对于中国当下社会的重要价值,也才能清晰洞见当下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演绎现状和复杂逻辑。
[1]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M].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34.
[2]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M].王崑,朱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0.
[3]鄢烈山.板起脸来说超女[N].南方周末,2005-8-26.
[4]张梓轩,刘春阳.从《中国好声音》看大众文化中蕴含的启蒙意义[J].新闻春秋,2014(4):37-44.
[5]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83.
[6]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M].邱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95.
[7]肖慧.超级女声的几个关键词[J].天涯,2005(6):27-34.
[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32.
[9]郑欣,等.平民偶像崇拜:电视选秀节目的传播社会学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