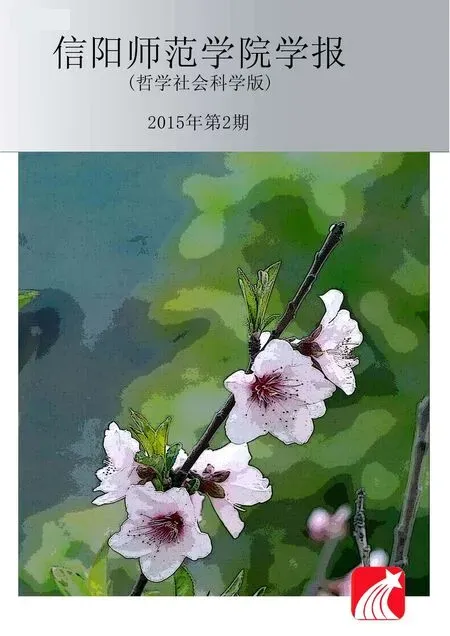论束皙的《诗经》学及其《补亡诗》创作
赵 婧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文学研究·
论束皙的《诗经》学及其《补亡诗》创作
赵 婧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束皙的“兴”理论是魏晋《诗经》学者第一次从诗歌表现方法的角度论述“兴”的含义。所谓“兴”,或为引譬连类,或为由见而感,是取之用以表达特定的含义。其《补亡诗》6首,贯穿了他的政教思想,并将自己“凡诗人之兴,取义繁广,或举譬类,或称所见”的“兴”理论运用到自己的诗歌中,且运用得相当娴熟而巧妙。
束皙;《诗经》学;《补亡诗》;诗言志;诗缘情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魏晋著名经学家。束皙才学广博,据《晋书·束皙传》载:“皙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遇乱亡失。其《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文集数十篇,行于世云。”在经学、文学、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均有造诣。然而,束皙之作大多亡佚,今存《补亡诗》6首与赋、诔、奏、议等文约18篇,收录在萧统《文选》、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学界对于束皙之研究,多集中在其赋作和《补亡诗》上,而对束皙的诗学观点研究极少。目前尚没有专门著述研究其诗学理论对其《补亡诗》创作的影响。
束皙作为一位经学大家,他的经学思想必然会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尤其是《诗经》学思想必定会对拟《诗经》之《补亡诗》产生影响。本文试就束皙经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之关系进行详细论述。
一、束皙之《诗经》学思想
观史书记载,《五经通论》应是束皙专门的经学理论著作,其中包括对《诗经》的研究与论述,可惜亡佚。但是在他《补亡诗》序以及其他几篇文章里,束皙所表达的《诗经》学思想,弥足珍贵。
1.《补亡诗》之“亡诗”实为“亡其辞”
束皙《补亡诗》中所补之“亡诗”,即是《小雅》中“有目无辞”的6篇“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关于《诗经》之“笙诗”究竟是“亡其辞”还是“有声无辞”,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
持“亡其辞”观点的以《毛诗传》为代表。毛传认为《小雅》中的“亡诗”是“有其义而亡其辞”,并解释其本义:“《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1]609又曰:“《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也。”[1]615郑玄《笺》亦以为是本有词句,后来亡佚了。孔颖达《疏》亦持此说,以为:“此三篇,盖武王之时,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遭战国及秦而亡。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1]609
持“有声无辞”观点的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诗集传》卷九《南陔》《华黍》篇所说:“此笙诗也,有声无辞。”[2]127“乡饮酒礼,鼓瑟而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然后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南陔》以下,今无以考其名篇之义,然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经篇题之下必有谱焉,如投壶、鲁鼓、薛鼓之节而亡之耳。”[2]127以为这6篇笙诗,不是“亡其辞”,而是本无其辞,仅是有声之作,即只有乐曲而没有词句。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宋代王质《诗总闻》卷十亦曰:“毛氏不晓笙歌而一概观之。大率歌者,有辞有调者也;笙者,管者,有腔无辞者也。”“有其义者以题推之者也,亡其词者莫知其中谓何也。”至近代,梁启超认为:“笙诗六篇有声无辞,晋束皙谓其亡而补之,妄也。
窃疑歌与笙同时合作相依而节,如今西乐所谓‘伴奏’。例如歌《鱼丽》时即笙《由庚》以为伴,《由庚》但有音符之谱而无辞可歌,其音节则与所歌鱼丽相应也。《南陔》之与《鹿鸣》、《白华》之与《四牡》、《华黍》之与《皇者华》、《崇丘》之与《南有嘉鱼》、《由仪》之与《南山有台》并同。”[3]65亦认为“笙诗”是“有声无辞”之作,且其乐谱已亡佚。
束皙《补亡诗序》曰:“皙与司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4]910从束皙所言“有义无辞”“补著其文,以缀旧制”来看,他是秉承毛传、郑笺“有其义而亡其辞”的“笙诗”观。同时,这也是魏晋时代普遍的“笙诗”观,从上文所引材料看,夏侯湛所做的《周诗》,其补亡辞之性质与束皙相同。
2.重视《诗经》之教化陶冶作用
束皙《读书赋》重点提到了《诗经》的教化、陶冶作用,其曰:
耽道先生,淡泊闲居。藻练精神,呼吸清虚;抗志云表,戢形陋庐。垂帷帐以隐几,被纨素而读书。抑扬嘈囋,或疾或徐。优游蕴藉,亦卷亦舒。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称《硕鼠》则贪民去,唱《白驹》而贤士归。是故重华咏《诗》以终己,仲尼读《易》于身中;原宪潜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倪宽口诵而芸耨,买臣行吟而负薪。贤圣其犹孳孳,况中才与小人。[4]905
在《读书赋》中,束皙对《诗经》的教化、陶冶作用的认识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方面认识到《诗经》的情感教化作用。所谓“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称《硕鼠》则贪民去,唱《白驹》而贤士归”,就是《诗经》的情感教化作用之体现。依据《毛诗序》的解释,《周南·卷耳》为后妃“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之作。束皙依《毛诗序》之解释,认为诵读《卷耳》,可以使人主识才,贤者益进,故而“忠臣喜”。《小雅·蓼莪》诗序曰:“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1]776郑玄笺云:“不得终养者,二亲病亡之时,时在役所,不得见也。”[1]776作为子女,因行役无法终养父母,甚至双亲病亡之时,仍不得见。因此孝子读到《蓼莪》之篇,便悲由心生。《魏风·硕鼠》诗序曰:“《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1]372因此“称《硕鼠》则贪民去”。《小雅·白驹》诗序:“《白驹》,大夫刺宣王也。”[1]673郑玄笺云:“刺其不能留贤也。”[1]673故吟唱《白驹》,呼唤贤士,而贤士即归。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诗经》等经典具有这样的情感教化的力量,因而历代圣贤重视经典,甚至于困厄之境也不忘诵读,寻求精神支柱,终成人伦楷模。如“重华咏《诗》以终己,仲尼读《易》于身中;原宪潜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倪宽口诵而芸耨,买臣行吟而负薪”。因此,“中才与小人”更应该研习诵读。
束皙的这一认识,仍是传统儒家诗教观的体现。但是他发掘了诗歌中所蕴含的情感意义,将诵诗与陶冶情操联系起来,将诵诗与有助于邦国之政联系起来,鼓励社会底层之士学习经典,则有现实意义。
3.关于《诗经》“兴”之论述
束皙针对有人以《诗经》中一些诗篇描写男女婚嫁的季节和时间,认为古代礼制规定婚嫁之礼必须在仲春至季秋这段时间内进行的说法,专门写出《嫁娶时月议》一文,并根据《春秋》从正月至十二月都有王公贵族举行婚礼的记载,指出古时对婚嫁季节、时间的描写,不能作为考证古代礼制的依据,并引用《桃夭》《摽有梅》《匏有苦叶》《草虫》为证,指出:“《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时’,盖谓盛壮之时,而非日月之时。故‘灼灼其华’,喻盛壮,非为嫁娶当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叶溱溱,有蒉其实,之子于归’,此岂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虫喓喓,未秋之时。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时,然讠永各异矣。’”[4]912最后得出结论:“夫冠婚笄嫁,男女之节。冠以二十为限,而无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设,不以日月为断,何独嫁娶当系于时月乎?”[4]912
由从“嫁娶时月”这个问题出发,束皙表达了他对于“兴”之论述:“凡诗人之兴,取义繁广,或举譬类,或称所见,不必皆可以定时候也。”[4]911-912《诗经》中诗歌作者所采用的“起兴”的方法繁复多样,或取物与所兴之物之间的譬喻连类关系,或取眼前所见之景起兴,不必以此来断定所叙之时间。接着指出:“故‘灼灼其华’,喻盛壮,非为嫁娶当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叶溱溱,有蒉其实,之子于归’此岂在仲春之月乎?”[4]912明确地指出了以桃花之“灼灼光彩”喻女子之曼妙年华,并非是写嫁娶必须在桃花盛开之月。并反问,若嫁娶是在桃花盛开的“仲春之月”,那么“其叶溱溱,有蒉其实,之子于归”又怎会是在仲春之月呢?岂不是自相矛盾?又说《摽有梅》第三章郑笺云:“此夏乡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余三耳。”婚嫁之时在夏末;《匏有苦叶》篇语:“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嫁娶之时在隆冬;以及《草虫》“喓喓草虫”言嫁娶之时在晚秋。诸篇所说均不一,故而得出“何独嫁娶当系于时月乎?”的结论,令人信服。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魏晋《诗经》学者第一次从诗歌表现方法的角度论述“兴”的含义。束皙通过研究《诗经》起兴的艺术手法与艺术效果,明确地认识到,所谓“兴”,或为引譬连类,或为由见而感,并且已经不拘泥于现实所描述的时间,而是取之用以表达特定的含义。束皙在强调“诗人之兴”时的另一层意思,乃是强调研读《诗经》应该重在理解诗意,而非拘泥于《诗经》的实用价值;强调以“诗人之情”理解全篇之意,已经蕴含着摆脱经学桎梏而重情感抒发的因素,这是对王肃释“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亦可以看出,束皙、陆机时代“重情理”的学术氛围,因此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便非毫无来由了。
二、论束皙的《补亡诗》
束皙《补亡诗序》曰:“皙与司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4]910束皙的《补亡诗》创作应该是他为官期间为了修复礼度而作。它依照《毛诗序》之义而补填亡诗。《补亡诗》6篇,内容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思亲存孝之作。如笙诗之《南陔》《白华》之篇。《南陔》篇序曰:“孝子相戒以养也。”[1]609《南陔》首章首句以循南陔采兰起兴;次句写到眷恋父母,思归供养父母;第三句言戒自己盘游无度;第四句写具体侍奉父母的方式:要朝夕供养。次章首句以油油绿草起兴,喻自己当以如绿草之油然柔顺侍奉父母,应该朝夕供养。三章举《礼记》河獭之例,暗示自己应该像河獭一样归养其亲;又举林乌反哺之例,暗喻自己应该侍奉双亲;最后提出若养隆敬薄——即用很隆盛、丰富的物质条件去供养双亲,而不注重礼仪之敬的话,就只是与禽兽之供养相似;末句提出侍奉双亲更高的要求“勖增尔虔,以介丕祉”[1]639,即以虔诚敬重之心侍奉双亲,以祈降福祉。沈德潜将此诗分为三章,并曰:“首言养,次言色,末言敬。”[5]153吴淇将此诗分为四章,曰:“此诗四章,首章言养,二章言色,末三章言敬,能色能敬,方才完得养字。”[6]166
这一类诗歌以孝义为先,虽为补缀《诗经》之亡诗,却又融入真情,故写得感情深挚,以情取胜。《南陔》写眷恋父母,“眷恋庭闱,心不遑安”,“眷恋庭闱,心不遑留”[7]639;《白华》写孝子“竭诚尽敬。亹亹忘劬”[7]640。似是宣讲儒家伦理孝义,然并非枯燥的说教,而是蕴含着孝子对父母深切可感的情感。
第二类是赞美民胞物与之作。如《华黍》篇,序曰:“时和岁丰,宜黍稷也。”[7]640此诗从民本出发,歌颂的是风调雨顺时农业繁盛的景象,到诗歌末尾才点出歌颂王道,蕴含着束皙对劳动人民生产劳动的情谊。吴淇评曰:“三章只写得时和岁丰四字。前二章先写时和,次写岁丰。末章先写岁丰,后写时和。”[6]168在“九谷斯丰”“九谷斯茂”“黍发稠华”“禾挺其秀”“芒芒其稼”“玉烛阳明”之词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蕴含在词语之中的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
第三类是体物玄道之作。如《由庚》《崇丘》之篇,《由庚》赞美万物得其道,束皙此诗是写玄理,表达其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这在《诗经》中是没有的。《诗经》中的时节常常是作为诗歌中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的背景或者是带有隐喻、象征意义的自然景物。次章次句举鱼、兽之例,皆言各得其所,得其时宜;三句言四时变化、八风代谢,均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四句言星月变换;五句言五是、六气皆不改其常行;六句赞美我王能继文王之迹。吴淇评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6]166此篇承接《华黍》而来,《华黍》仅歌颂了农业繁荣的景象,还属于具象的描写,《由庚》却将其提升到“道”的境界,赞美自然之道、君王之道。
第四类是赞美君王政教之作。《补亡诗》最后一首《由仪》,首句言君子容仪谨慎,天地万物各得其宜;次句言人君施行仁政,洞察明鉴;三句言鱼儿在清水中嬉戏,群鸟集萃在林中;四句写鱼儿欢游,鸟儿振翅;五句写这是因为君臣各尽其职的缘故;六句写时世既然已经平顺,该思何修何呢;七句写内以文化治世,外以武德远加海外。
从艺术上来看,《补亡诗》6首有着突出的艺术特点。
首先,运用《诗经》重章迭唱的篇章结构方式,并善用叠词。重章迭唱是《诗经》最常用的章法方式,大约三分之二的诗篇都采用了这种篇章结构方法,且大都集中在《国风》与《小雅》中。《白华》一诗,共分三章,每章六句。句式整齐,每章意旨大致相同,只是调换了一些词语。吴淇评曰:“三首词调皆同,只有换字之法。此三百篇反复唱叹之常,其文亦只就题敷衍。但劈首便用渲衬之法,衬出妙意。华之萼曰‘朱’,华之趺曰‘绛’,华之足曰‘玄’, 连用三个火焰字面,衬出洁白,最为好看,门子、士子、处子,人之洁者。”[6]167
束皙善用叠词。在《华黍》一诗中,多用叠词,如“黮黮”“习习”“奕奕”“芒芒”“参参”等等。吴淇评曰:“前‘黮黮’云云,‘奕奕’云云,已含‘宜’字意。此章‘无高’句,正专写‘宜’字。”[6]168在其余几首诗中,束皙也喜用叠词,如《白华》《崇丘》等。
其次,结构精妙,在意义上叠进一层。《南陔》一诗,在结构安排上巧妙变化。在整齐中充满跌宕错落之感,首章为:“循彼南陔,言采其兰。眷恋庭闱,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盘。馨尔夕膳,洁尔晨餐。”[7]639若按照对称的句式,下章则应该为:“循彼南陔,厥草油油。眷恋庭闱,心不遑留。彼居之子,色思其柔。馨尔夕膳,洁尔晨羞。”然而,束皙却将“眷恋庭闱,心不遑留”与“彼居之子,色思其柔”互调,变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恋庭闱,心不遑留。馨尔夕膳,洁尔晨羞。”反而使情韵更为生动。
另外,《南陔》最后一章安排巧妙,使意义叠进一层,“有獭有獭,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鲂捕鲤。嗷嗷林乌,受哺于子。养隆敬薄,惟禽之似。勖增尔虔,以介丕祉”[7]639。吴淇又评第三章:“前二章只用换字之法,此章忽为变调,最有风致、最有蕴藉。‘噬鲂补鲤’,正取《月令》獭祭鱼,有报本之义。而‘凌波赴汨’四字,乃其不遑安不遑留处,绝得相戒之神。”[6]166是赞美束皙在文义转折处的别有用心。这是文义的一大转折,若人之供养双亲仅仅重饮食上的隆重,那么与禽兽反哺父母并无区别,从而使意义转折到该如何侍奉双亲——重礼敬孝,故而既有蕴藉又有风致。
三、束皙经学思想与《补亡诗》创作之关系
1.《补亡诗》实为传统诗教精神的体现
束皙《补亡诗》6首,全部贯穿了他的政教思想。如上文所述,《南陔》《白华》是思亲存孝之作,《华黍》是赞美民胞物与之作,《由仪》是赞美君王政教之作。全都符合《毛诗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10的政治教化要求。《由庚》《崇丘》,虽然是写自然之道的,明显受到当时玄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在赞美万物之道的同时,仍然不忘赞美“愔愔我王,绍文之迹”“周风既洽,王猷允泰”[7]640的君王之德政教化。因此,《补亡诗》6首完全是束皙注重政治教化的《诗经》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2.将“兴”之理论运用到《补亡诗》创作
束皙《补亡诗》6首,已经将自己“凡诗人之兴,取义繁广,或举譬类,或称所见”的“兴”理论运用到自己的诗歌中,并且运用得相当娴熟而巧妙。
《南陔》一诗,吴淇以为首章首句言“采兰”是起兴,而《文选》则认为是赋,所言乃“采兰以养亲”。吴淇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束皙已经明确意识到《诗经》毛诗在首句下标“兴”的文学表现手法,并能够娴熟地运用这种起兴的方式了。
值得注意的是,《白华》一诗,已经不是在不同的章节简单以“白华”的起兴了,而是带有强烈的隐喻意义。不仅将孝子比作白华,而且用白华来象征孝子的精神,象征其精神之高洁。由此可以看出束皙以《白华》不同章节起兴的隐喻意义。
联系束皙的《诗经》学理论来看,《南陔》之篇,运用的便是“或称所见”的方式,“言采其兰”“厥草油油”是束皙想象诗人触目所见,借以起兴,与“采兰”之字面义无关;而《白华》运用的便是“或举譬类”的方式,以白华之“朱萼”“绛趺”“玄足”起兴,则是取其高洁的象征意义,象征孝子的品格如白华般高洁。
束皙在《补亡诗》创作中贯彻了自己的《诗经》学理论。重政治教化的思想是《诗经》学思想的内核,这种思想已经完全贯穿于束皙《补亡诗》6首的创作中。萧统《文选》将其置于诗类之首,即是对其诗中贯彻重政教思想的认可。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首之以补亡诗编集。欲以继三百篇之绪,非苟然而已也。”另外,束皙对“兴”作为一种表现手法的认识,具有文学发展意义,也符合文学的创作规律。他在《补亡诗》中有意识地运用了“兴”的手法,并且达到了相当精妙的艺术境界。萧统《文选》序言编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夏侯湛等人的补亡诗未被选入,束皙《补亡诗》6首却被全部选入,这也与束皙在诗歌中巧妙运用“兴”的手法,使诗歌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是密不可分的。
[1]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宋]朱 熹.诗集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七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5册)[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5] [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 [清]吴 淇.六朝选诗定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9.
[7]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韩大强)
2014-12-26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14BZW043);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规划项目(2015-GH-552)
赵 婧(1983-),女,安徽萧县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207.22
A
1003-0964(2015)02-012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