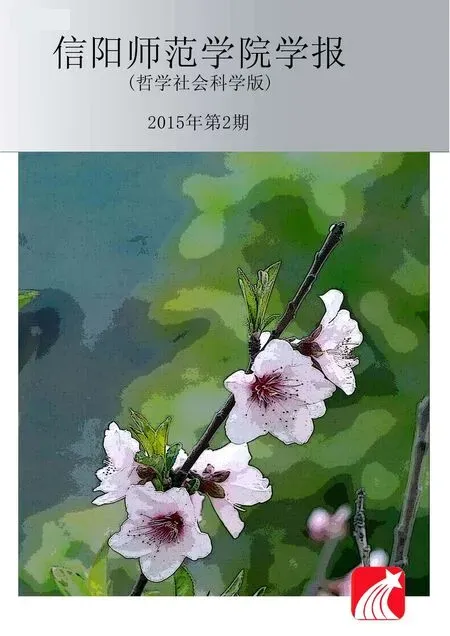论孔子美学思想
王晓明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文学研究·
论孔子美学思想
王晓明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孔子在整合梳理先前文化的基础上,以中和为审美尺度,以仁为审美思想的核心,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学思想。他用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去实践理想中的君子人格,在诗、礼、乐的有机相融中实现他崇真、致善、尚美的价值取向。他的审美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可贵的人生境界。
孔子;诗;礼;乐;中和;仁;人生境界
司马迁曾评价孔子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1947继古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被史家司马迁赞为华夏民族之“至圣”的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他的言行可从哲学、政治、教育等多维度进行解读和阐释,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珍贵财富。如果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2]2350,那么孔子的美学思想可说是结束漫漫长夜之曙光中最瑰丽的部分。
一、孔子美学思想渊源
孔子作为文化圣人,他的意义在于对前于他的文化进行反思、整合、抽绎,为后于他的文化奠定坚固的思想基础,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建立起一个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模式。他的美学思想也是在传承中进行创新。诗、礼、乐在中国上古时代就有着悠久的传统,并且“乐”常指诗、乐、舞融为一体的一种先民的宗教或艺术形式。《吕氏春秋》叙述古代的乐舞:“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3]4周之前巫风盛行,先民常在原始的祭祀活动中通过颇具规模的乐舞来娱神,比如祈雨,请求神灵保佑五谷丰登,远离灾害,这其中即伴有诗歌源头性质的卜辞,比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3]4在诸多巫术祈祷的活动中,诗、乐、舞的文化形式都得到了发展,这其中既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审美意味,同时在人神之间的关系中,也依稀可见礼的等级意味。
随着时代的发展,上古文化出现了从巫术向人文、从以神为主到以德为尊的转型,如《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4]1485—1486;《尚书·蔡仲之命》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5]453在周代,德成为周公制礼作乐的意识形态依据,周代礼乐的主要功能在于协调社会人伦关系。天子、诸侯、大夫、士要践行《周礼》概括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比如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等。周代的乐包括乐、舞、诗三大因素,《周礼·春官·乐师》把舞分为羽舞、皇舞、干舞、人舞等六类,《周礼·春官·磬师》把乐分为王夏、纳夏、章夏、齐夏、械夏等九类,舞、乐根据不同的内容与诗相配。《周颂》即是周具有代表性的乐舞,大概创作于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其功用是为了歌颂王室圣德,昭告神明以福佑周室子民。
由上看来,礼乐传统萌芽于上古时期,由周公进行树立完善并确立为国家制度。中国诗性文化的渊源可溯流到上古时期,在那个还没有文字的时代,先民把对宇宙的感知、对自然的体认、对生活的体验融合进了原始乐舞、巫术之中。他们以原初的,甚至是本能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文明的曙光出现之后,先民的诸多活动渐渐具有了更多的人文色彩。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是一个连续体,文字的出现使得早先口口相授的事件、活动有了又一个重要的记录载体,典籍中保留着大量关于史前文化的记述。古代文化在夏、商、周三代已经表现出很高的发展水平,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代表的礼乐文化是其文明高度的佐证。特别是西周时期,礼仪、乐舞、典章、制度都有了系统化的发展,世俗化倾向加强,开始注重对人自身的关注,其蕴含的思想观念充满了理性之光。孔子曾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6]182他在敬仰、继承周公文风的同时,结合时代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审美文化上为后世奠定了基石,确立了基本原则。
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学内涵
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以周公为偶像,志在维护与传承周代的礼乐文化。在孔子之前,礼和乐被分开论及;孔子则把二者放在一起谈论,把先前较为独立的礼和乐提升为一种礼乐思想,这种思想在后世得到延续并成为儒学审美文化的标志和主要内涵。孔子也把先前融合在广义的乐中的诗独立出来,将诗、礼、乐视为其整体礼乐思想的三个维度,并表述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6]529—530。
诗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文学艺术,可抒情,可言志,兼有感性与理性的特征,富有很强的审美意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心性。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6]1212诗首先通过其“可以兴”的功能来唤起人的情感上的共鸣,“兴”即是起情,以情动人,情则贵在一个真字,这是诗最直接的作用。内在的感化人心是获得人心对某事物认同的基础和最有效的途径。诗作为由语言文字组成的文本,或经口头表达,或经书面记叙,其情感的水流在浸润人心之时,其思想的光辉也会照射人脑,启迪人理性的思维。首先从人的情感入手,以情起兴,在情中渗透理,为后续“立于礼”之纵深人格的树立提供一个饱含真情的支点,使得以理性为主导的礼具有温暖感,所以说“兴于诗”。
礼的核心是等级制度明确严格的宗法制,人伦关系以血缘为重要(不是唯一)准则。孔子主张分别以孝、悌作为纵向、横向伦理关系的维系依据,这是对人的情感本能所进行的理想梳理,其中无不渗透着礼。由“亲亲”到“仁民”,礼的功能也就从人伦扩展到了人际关系。礼本身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可操作性,在制度方面对人的外在行为确立规范。礼既涉及非常具体的在祭祀、政治、人伦等方面如何做,也会以抽象概念的形式来警示人心,其作用的发挥主要以人的理性和意志为基础。孔子曾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6]417,“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68,“非礼勿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6]821。“约”“齐”“勿”即明显带有外在的、强制性的特征。从审美角度来看,礼本身包含的是一种制度美,由于以尚真情的诗为支点,它本身就不那么冰冷与生硬。礼为人提供基本的处事原则,它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放射着理想光辉的行为尺度美,塑造了人纵深维度的人格,成为人的脊骨,所以说“立于礼”。
乐是极其强大的抒情艺术,它所具有的最直接的穿透人心的力量是诗和礼所无法企及的。诗由语言文字构成,它要经过人脑的概念感知后,再转到人心成为情感体验,礼则更是需要人脑来进行理性分辨,对自身施以控制,二者都首先需要人主动的配合。乐作为由乐音构成的纯粹情感符号,完全不需要人首先做什么,人只需被动地接受即可,乐会直接作用于人的听觉,由耳入心,激起人内心的波澜。乐对人心灵的奇异功能最切合人的本性,因为人首先就是感性动物,总会绕着情感徘徊。孔子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乐的这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他慎重地为乐选取的位置是在“立于礼”之后,并且高于礼。于是这时乐所抒发的情就不再具有任意性,而是经由理性过滤并溶解了理性的情。这种形式的乐对人心的感染是延绵深远的,它在礼之后进一步持久地、全面地完成了对已经由诗、礼所建立起来的人格的塑造,所以说“成于乐”。
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学主张中蕴含着诗、礼、乐三者的逻辑关系。具有理性光辉、代表着行为美的礼是诗与乐的最终依据。《论语》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6]157-159对于“礼后乎”,一般认为“后”的意思是基础,即是说天生丽质是动人笑靥的基础,白绢是画的基础,礼是诗的基础。那么以此推之,礼也是乐的基础。在孔子美学思想中的诗与乐,是经由礼的尺度衡量过的。对于诗,他进行删选的结果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6]65;对于乐,他取舍的态度是“恶郑声之乱雅乐也”[6]1225,“乐则《韶》、《舞》。放郑声……郑声淫”[6]1085—1087。诗、乐本身所代表的是一种尚真的情感美,礼所代表的是一种重制度伦理的理性美,诗为礼注入了情,礼为诗提供了规范,经过以真情为基础的礼过滤后的乐,则最终拔高了礼。从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成为情感与理性有机相融的审美思想体系。
三、中和作为美学尺度,仁作为美学核心
取中的思想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如尧曾对舜说道:“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6]1345即是要求舜继位后要以中为尺度,为天下苍生谋福祉。《尚书》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5]79从中可见,“直而温”等人品素质的衡量标准是中,而作为乐师的夔要想通过乐来教化人心,他所选用的也必然是合中的乐。孔子继承了古圣先贤所确立的用中的传统,如子张询问“何为五美”时,孔子答:“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6]1370即为他理想的人格美提供了一个中的范式。他在弟子心中的形象则是“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6]505。同样具有合中的特质。
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审美思想体系确立后,需要进一步明确诗、礼、乐的取舍标准,对此孔子谈到了他所认同的尺度,也就是他对《关雎》的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6]198这实质上是以中和为尺度来衡量诗歌。以中和为标准,孔子理想中的乐是《韶》,因为它“尽美矣,又尽善也”,相比之下,《武》则不及中和,因为它“尽美矣,未尽善也”[6]222。中和的思想在孔子后的儒学中得以传承,《礼记·中庸》解释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1422诗、礼、乐都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喜怒哀乐之情,中和即为情感的抒发提供了一个审美尺度,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6]1152。礼由于具有理性和规范性,本身已作为诗与乐的取舍依据,孔子对待礼乐,不仅主张“节乐”,而且要求“节礼”,为礼也确定了适度原则。如林放问礼之本时,孔子答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6]144-145可见,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审美思想内在地以中和、节制为基本依据。对于“节”,孔子的态度是“乐”,即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主观上愿意去这么做,通过节的途径达到中和的审美效果。孔子把欣赏具有中和之美的乐作为人生之大乐,如他的亲身体验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6]456
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审美思想,其最终依据与核心是仁。他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6]1216“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6]142孔子认为,诗、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诗背后的一种真情表露、礼背后的一种道德自觉,从而达到乐背后的一种情理交融之美。如果礼只限于玉帛,乐只限于钟鼓,那么一切就只能因为流于形式而失去意义,孔子对此有清晰的认识,所以他特别强调以仁作为礼乐的最终依据,作为其诗、礼、乐美学体系的核心。何为仁?《论语》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6]873孔子与其弟子还有一段涉及仁的对话:“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6]1231—1237在这段关于为父母守丧三年之礼的问答中,安与仁建立了联系,孔子认为宰我对此所持的安的心态即是不仁。在孔子看来,仁应是一种不安的状态,这种不安涉及情感的自发、道德的自觉,换言之,仁内在地与情感的真、道德的善相连通,其高层指向必然是兼具脉脉真情与理性光辉的美。
在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审美思想体系中,诗、礼、乐即分别从真、善、美三个维度对其内在核心仁提供了形式与内容表征,做出了各自向度的诠释。诗以情起兴,抒发与引起的都是真情,可贵之处正在一个真字;礼具有较强的外在规范与道德实践性,其实质指向的是一个善字;乐以情真为基础、被善意过滤后自然通往了孔子理想中的美,这种真、善、美的有机统一,也可说是中和美的更高体现。孔子美学思想的内涵融“诗、礼、乐”为一体,崇真、致善、尚美,所有这些都是他所主张的仁之内核的外延与扩展,如果缺失了仁,所剩下的仅仅是失去了灵魂的躯壳而已。
四、孔子美学思想的实质
孔子总是努力用一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去实现他理想中的君子人格。何为君子?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400质可作为上述仁之内核的一种表述,文相对于质而言则可视为一种外在形式美。对于文,孔子在答子路“何谓成人”之问时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6]969在这里文是动词,是作为礼乐对成人之意义的一种表征,以礼乐为工具,以文为途经,文之以礼乐,礼乐是实现成人的一个方面。“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与“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连起来看,可理解为:要成为君子,要兼具质与文即内涵美与形式美相统一的特质;礼乐的功用是使人具备文的质素,塑造形式美,文的实现要通过礼乐的熏陶,礼乐对内涵美也会有培养作用。孔子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追求人格之雅,正如《论语》所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6]475在审美实践上,他自然会倡导雅言、雅行。
孔子对成人、君子人格的简短谈论充满了审美意味,他试图在诗、礼、乐的交融中经历艺术化的人生。孔子美学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是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6]479在这里中国文化传统极其重要的两个概念忧、乐二字同时出现。孔子之忧,是一片兼济天下的深情,他为理想周游列国、发愤忘食,生民之福祉是他真正的忧;孔子之乐,是一种乐天知命的情怀,即使困于陈蔡、遭受重挫如丧家之犬,也不怨天尤人,通达之怀是他真正的乐;孔子之忘忧,是以宽广的心胸去包容俗世的纷扰,不以功名利禄得失为忧。他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6]465有如此的忧乐意识,有深沉、厚重的仁心,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主张与实践,孔子的人生必然是审美化的人生。这在他与弟子的交流中也有很显著的体现。他对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称赞是:“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6]386在别人眼里生活忧苦不堪的颜回,自有其可乐之处,对此孔子是非常理解的。能够与老师在忧乐取向上达到如此一致,众弟子中也只有颜回了,于是“孔颜乐趣、安贫乐道”传为美谈,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养料。另有一次孔子询问弟子们的志向时,曾点答:“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6]806孔子对此最为赞成。与做官、发财、做“小相”和“司仪”等相比,曾点之志最为简单,也最具美感,恰与老师之志暗合。
正是因为以审美的态度去生活,让生命上升到富于审美意味的境界,孔子才能对其人生以“乐”字概之,自得其乐。《关雎》让他体验不淫之乐,《韶》让他体验三月不知肉味之乐,礼让他体验人伦、人际关系之协调文雅之乐。他品诗、弹琴、鼓瑟、学礼,他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6]404,在“知、好、乐”三者中,乐是最高的人生态度和境界。孔子的人生是审美的人生,是艺术的人生,是快乐的人生,达到了乐水亦乐山的境界,于是他可以怡然地践行自己的想法:“……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6]73-76“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6]443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个天下有共主兼有霸主的时代,社会动荡、思想多元,西周社会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走向解体,与此同时华夏民族的文化自觉正在生发、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正在形成,士群体对天人观念、宇宙秩序等展开思考,孔子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代表,他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难能可贵的是,他所追求的人生极具美学意味。孔子的美学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富于美感与乐感的人生境界,为后世留下极其珍贵和美好的精神财富。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4]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程树德.新编诸子集成·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辑:韩大强)
On the Aesthetic Thoughts of Confucius
WANG Xiao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integrating previous culture, Confucius proposes the aesthetic thoughts of beginning from poetry, standing on rite and achieving through art, which regards zhonghe (harmony) as the aesthetic standard and ren (benevolence) as the aesthetic core. Confucius practices his ideal concept of noble person with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and realizes his value of worshiping truth, kindness and beauty. The nature of Confucius' aesthetic thoughts can be conceived as a precious state of life.
Confucius;poem; rite; art; zhonghe; ren; state of life
2014-11-1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32)
王晓明(1984-),女,河北张家口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审美文化。
I207
A
1003-0964(2015)02-01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