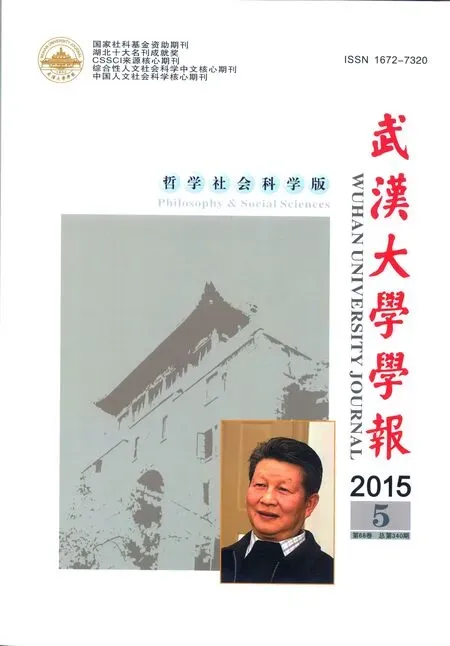战后的战犯审判与普遍管辖权:实践、发展与问题
宋 杰

战后的战犯审判与普遍管辖权:实践、发展与问题
宋杰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胜国在对次要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过程中,部分案例是建立在直接或间接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基础之上的。冷战爆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到了20世纪80年代,部分国家再次基于普遍管辖权而启动了对战争罪犯的追诉,如以色列、澳大利亚、英国等。从这些国家的实践来看,针对战争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既涉及需要相应政治意愿,还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需要精致的程序予以配套支撑。国家针对战争罪犯的普遍管辖实践不仅彰显了国际社会惩治战争罪犯、终结“有罪不罚”的政治意愿和决心,也丰富和发展了普遍管辖权的理论,为普遍管辖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罪; 惩治战争罪犯; 普遍管辖权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对于战争犯罪*本文所使用“战争犯罪”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管辖的战争罪、反人道罪和反和平罪等。的审判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对于主要战犯,是通过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对于非主要战犯,则是由国家通过国家法庭审理进行。而国家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又存在着两类情形:一类是由相关犯罪发生地国的国家法庭进行,如发生在中国的太原审判,由英国主导的在香港的审判等(Suzannah,2013:1-214);一类则是由与犯罪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法庭进行,如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就后一类而言,由于缺乏与犯罪的相关联系,即犯罪并非发生在本国,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受害者也非本国人,国家法庭就需要借助于普遍管辖权来进行审判。而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就与战争有关问题的处理而言,战后存在着两类不同的普遍管辖实践:一类是普遍刑事管辖,即针对战争罪犯的刑事审理实践;一类是针对与战争赔偿问题有关的普遍民事管辖(宋杰,2011:181-195),即一国在本国法律体系内为他国战争受害者提供民事侵权救济。国际法院审理的德国诉意大利(希腊参加)“国家管辖豁免案”即与意大利和希腊的此类实践有关*针对国际法院2012年2月3日的判决(意大利败诉),意大利最高法院很快决定执行该判决,但最高法院的决定随后被宪法法院裁决违宪。关于意大利宪法法院判决,参见网页:http://www.cortecostituzionale.it/documenti/download/doc/recent_judgments/S238_2013_en.pdf,2015年6月5日最后访问。。限于研究主题的原因,本文仅研究前一类实践。
本文主要关注对象即为不同国家基于普遍管辖权而对二战中的战争罪犯进行追诉和审理的相关实践。由于不同国家在此方面的实践差异较大,因此,笔者将首先对之进行一般性描述,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比较典型国家的具体实践。最后进行简要总结。
一、 基于普遍管辖权审判的一般性实践
二战后战胜国对于非主要战争罪犯的审判,适用的主要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所颁发的第10号法令。各国基于此法令所进行的审判,按照大赦国际的统计,总数超过1000起(Amnesty International,2001:26),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基于普遍管辖权进行的。
总体而言,战后国家基于普遍管辖权而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相关实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援引普遍管辖权,一类是间接援引普遍管辖权。而无论是间接援引还是直接援引,纽伦堡军事法庭都予以了含蓄认可。纽伦堡军事法庭在解释盟国作为占领当局,有权以《伦敦协定》为依据来为德国制定相关立法时指出,“(协定)签署国创设了本法庭,为本法庭制定了适用的法律,以及审理所需遵循的规则。而就所制定的这些法律和规则而言,每一个签署国是有权单独制定并适用的。毫无疑问,每个国家都有权创设特别法庭以适用其所制定的相关规则。”*See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Trial of German Major War Criminal,Nuremberg,30 September and 1 October,1946,p.217.这实际上意味着,每个战胜国都有权在本国创设适用于战争罪犯审判的本国法庭,以及法庭应予适用的相关规则。而当有关犯罪并未发生在本国领土内,受害者和犯罪者均不具有本国国籍时,国家所创设的法庭及由此所展开的审判,当然就需要建立在普遍管辖权的基础之上。国家之所以有此权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那些本国国民遭受到直接影响的国家(在审判战争罪犯问题上)享有基本利益,所有文明国家在此事项上却也同时享有非常实在的利益”,因为违背战争法的相关犯罪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而对于此种违背,所有国家均享有普遍性利益,都有权关注”*See Willard Cowels,Universality of Jurisdiction over War Crimes,33 California Law Review,1945,p.177.值得注意的就是,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在其所编纂的《战争罪行审判报告》第15卷中,在谈到不同国家设立法庭以审理战争罪犯的法律依据时,原文引用了Willard Cowels文章中的这句话。Se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5,p.26.。
在国家的实践中,美国对战争罪犯审判的实践极具特色。
一方面,在某些案件中,美国明确地提到了普遍管辖权。例如,在哈达马尔案(Hadamar Trial)中*本案涉及的主要犯罪实施是: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哈达马尔(德国城市)屠杀了约500名俄罗斯和波兰平民。,由于相关犯罪发生在德国,受害者、犯罪嫌疑人均不具有美国国籍,因此,被告质疑美国是否拥有管辖权。美国军事委员会对此质疑予以了驳回。其指出,“最近详细讨论的被称为‘针对战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理论,已获得了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支持。根据此理论,依据国际法,每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有权惩治海盗犯罪,还有权惩治处于其监控下的战争犯罪。而在惩治战争犯罪的时候,相关国家是不需要考虑受害者的国籍,或犯罪行为发生地的。特别是,不需要考虑相应犯罪是基于何原因、在哪里发生的。不受制于这些因素是非常必要的,否则,相应的犯罪就不会受到有效惩治(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1947:52-53 )。”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案”中,针对被告所提出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抗辩,检察官通过援引格老秀斯的相关论述驳斥称,每一国家不仅有权惩治加害于本国及其国民的行为,还有权惩治那些以严重违背国际法的方式来加害于他国及其国民的行为。对于这样的加害于他国及其国民的行为,每一国均有权行使普遍管辖权(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2,1949:61)。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为了论证自身的普遍权的“理论依据”,在缺乏先例可予借鉴的情形下,是通过与海盗相类比的方式来确立对相应罪行的普遍管辖权的。
另一方面,在其他一些个案中,尽管没有直接提及普遍管辖权,却间接地论证了自身所行使的管辖权正是普遍管辖权。如在“李斯特案”(List case)中,尽管相关犯罪的受害者为希腊、南斯拉夫、挪威、阿尔巴尼亚等国人,美国依然对其进行了审理。美国军事法庭指出,“一项国际犯罪是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为犯罪的行为,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基于正当理由,相关犯罪就不应完全排他地由该犯罪行为发生地国管辖。就一项战争罪行而言,此罪行的内在本性就足以让控制该罪犯的战胜国法庭有权审理之(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8,1949:8-9)。”在本案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普遍管辖权,却提到了犯罪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并认为,对于这样的犯罪,每个国家都有权审判。同样,在“上海审判”中*在该案中,几名德国人涉嫌在德国投降之后参与了一次针对剧院的军事行为,从而既违背了有关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盟军规定,也构成了对日本的协助等。关于案情的基本描述,参见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4,pp.8-9.,美国军事委员会驳回了美国无域外管辖权的抗辩。军事委员会指出,“某项战争罪行……并非是违背某一国家法律或刑法的罪行,而是违背国际法的一项罪行。有关战争的规则和惯例是普遍适用的规则和惯例,是不受国家法律和边界的局限的。那种认为只有犯罪地国家才有权管辖的观点是没有依据和不能被接受的(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4,1949:15)。”
美国的实践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在部分案件中,美国将其扩及到了自身参战之前所发生的相关犯罪。例如,在“约瑟夫案”(Josef Remmele case)中,被告被控在美国卷入战争之前(1941年12月11日),涉嫌对几名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俄罗斯人犯有战争罪行。军事法庭在审理中认为,两国之间存在战争状态是“战争罪行”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却并非一国对违背战争法规和惯例罪行进行审理和惩治的必要条件。被告在美国和德国进入战争状态之前犯有这些罪行的事实,不能构成美国审理并惩治之的阻却条件(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5,1949:44)。
英国的实践与美国类似,亦存在着直接和间接援引普遍管辖权的情形。
首先看直接援引的情形。在阿尔米罗案(the Almelo case)中*该案涉及到几名德国被告在战争中涉嫌屠杀一名荷兰平民的战争罪行。,军事法庭在解释自身管辖权时指出,“根据针对战争犯罪的普遍管辖这一普遍性理论,每一国家均拥有对处于其掌控下的海盗犯罪和战争犯罪的国际法上的管辖权,并基于此而惩治之;国家在行使此种管辖权的时候,是不需要考虑受害者的国籍或犯罪行为的发生地的(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1947:42)。”此论点在“齐克隆案”(Zykon B case)(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1947:103)和桑德科案(Sandrock case)*Sandrock,Ludwig Schweinberger,Franz Joseph Hegemann被指控于1945年3月24日杀害了一位叫Bote van der Wal的荷兰平民。英国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14日指控他们违反了战争法和战争惯例。See War Crimes Commission,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p.42.中再次被重申。显然,同美国一样,英国也是通过与海盗罪的类比来论证和确立自身的普遍管辖权的。
而在另外的一些个案中,英国军事法庭则没有直接提及普遍管辖权。例如,在1947年针对两名日本战犯的“眉苗审判”中*该审判在缅甸进行。被指控的两名日本犯罪嫌疑人被控涉嫌针对一些中国人和印度人犯下战争罪行。,军事法庭尽管确立了管辖权,却并没有明确提及普遍管辖(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5,1949:43)。类似实践还存在于在新加坡针对日本战犯TomonoShimio的审判中*本案主要案情涉及到作为被告的TomonoShimio在西贡(今胡志明市)涉嫌杀害美国战犯。被告最后被判处绞刑。相关案情参见:Prrofessor L.C.Green,The Maxim NullumCrimen Sine Lege and the Eichmann Trial,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8,1962,p.463.。
就法国而言,一方面其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案例极少,另一方面,即使行使,也是以间接的方式来行使,在审判实践中不直接提及普遍管辖,如其军事法庭在1947年所审理的“蒙特案”(Monte case)*1940年至1945年期间,一名叫Lendines Monte的西班牙人被拘禁在德国集中营。在此期间,其曾对集中营同监舍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施以虐待,并曾杀害过一位西班牙人。1947年4月25日,法国军事法庭就此对其加以审判。Se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1949,vol.XV,pp.45-46.,以及“瑞思金案”(Albert Raskin case)(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5,1949:46)。
另外一些国家尽管也确立了对战争罪犯的普遍管辖权,并基于此而在实践中启动了对相关战争罪犯的刑事追诉机制,但受限于证据的难以获取,结果最终很少做出定罪量刑的实体判决,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相关实践*关于此点的更多描述,参见John Terry,Taking Filártiga on the Road:Why Court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ccept Jurisdiction Over Actions Involving Torture Committed Abroad,in Craig Scott (ed.),Torture As Tort: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Human Rights Litigation,Hart Publishing,Oxford-Portland Oregon,2001,p.118.。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没有相关实践,却在战后制定的相关法律中保留了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可能性,从而为相关审理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例如,中国于1946年制定了《战争罪犯处理条例》。根据条例第7条的规定,条例同样适用于针对盟国及其盟国国民的相应战争罪行,而没有限定相应罪行是否一定要在中国领土内或中国控制下的领土内发生*值得注意的就是,正是基于此原因,在《战争罪行审判报告》第14卷中,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才从普遍管辖的角度将中国的相关立法予以了特别介绍。See UN War Crimes Commission,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14,pp.156-157.。类似的还有挪威。挪威于1946年12月13日制定了第4号法令,即《外国战争罪犯惩治法》(Punishment of Foreign War Criminals)。根据该法第1条的规定,其不仅适用于侵犯挪威利益的战争犯罪,也适用于侵犯盟国利益等的战争犯罪(Law Reports 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vol.3,1948:83)。
然而,除了少数国家如以色列、前苏联等国家外*前苏联等国的追诉主要是建立在属地管辖权的基础之上,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因此,这里不予介绍。,其他多数国家针对二战中战争罪犯的追诉努力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冷战战幕拉开之后,属于西方阵营的多数国家很快就失去了追诉战争罪犯的政治意愿。不仅如此,部分国家甚至还帮助某些战争罪犯逃避追诉,赋予他们以新的身份,甚至雇佣其从事情报等相关工作*See Christine van den Wyngaert,The Suppression of War Crimes under Additional Protocol Ⅰ,in Delissen,A.$ A.Tanja,eds.,Humanitarian Law of Armed Conflicts:Challenges Ahead-Essays in Honor of Fritz Kalshoven,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1991,p.204.。其中最典型者,当数美国在远东有关日本战争罪犯审理政策的转变,以及此种转变对其他盟国的显著影响。
1947年中期,盟军驻日本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就已督促各盟国不要再进行战争罪行审判(R.John Pritchard,1996:17-18)。英国很快就对“敦促”做出了正面回应。1948年4月12日,英国内阁海外重建委员会决定,自1948年8月31日起,“不再审理新的战争罪犯”。三个月之后,英国又给英联邦各成员国发了一封秘电,建议各该国自8月31日起,“不再审理新的战争罪犯”。加拿大7月22日回电,称自己对此“没有评论意见”(Amnesty International,2001:29-30)。
盟国不仅失去了对日本战争罪犯继续进行审判的政治意愿,对于意大利战争罪犯,同样也缺乏相关意愿。尽管根据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的调查确认,至少有超过1200名意大利战争犯罪嫌疑人涉嫌在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犯下战争罪、反人道罪和反和平罪,最终受到审判的却很少(M.Cherif Bassiouni,1992:228)。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盟国帮助甚至庇护战争罪犯的相关事实被更多披露,民众的反感情绪被激发。在此背景下,出于自身“正面”形象建设的考虑,第二波针对战争罪犯的调查和公诉行动开始出现,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先后出现了针对战争犯罪的新的普遍管辖实践。下文将对此予以介绍。
二、 具体考察:以以色列等四国为例
在针对战争罪犯的普遍管辖方面,以色列、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的相关立法与实践值得关注。就以色列而言,在他国已经失去了追诉战争犯罪的政治意愿后,其不仅通过国内立法直接规定了针对战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还规定了该法的可溯及性,从而不同于前述直接和间接援引普遍管辖权以审判和惩治战争犯罪的国家的相关实践。就澳大利亚、加拿大而言,其在经历了前期追诉(通过军事法庭进行)的不成功后,通过修改法律,又采取了基于一般法律的普通追诉行动,从而凸显了自身惩治战争罪犯的意愿。就英国而言,通过单独制定《战争罪法》,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追诉,从而明显地不同于其早期相关实践。
(一) 以色列的相关立法与实践
以色列于1950年制定了《纳粹和纳粹合作者(惩治)法》(下称法案),规定了针对反人道罪、战争罪和反犹太人罪的普遍管辖权。法案具有溯及力。法案在适用中所涉及的典型案例主要有两个:“艾希曼案”和“德米亚纽克案”。
其一,“艾希曼案”(Eichmann case)*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其被控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和反犹太人民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并定居下来,后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追查到,并于1960年5月11日被绑架并秘密运至以色列接受审判。1961年12月艾希曼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其被处以绞刑。。在本案中,在论证自身管辖权时,以色列法庭指出,法案的制定就是为了在以色列审判纳粹、纳粹协从者和合作者,具有溯及性,能域外适用。就法案的溯及力而言,法庭解释称,法案所规制的犯罪,并非是一种所创造出来的、此前不为人知的新的犯罪;犯罪嫌疑人在犯相关罪行的时候,都知道相关行为构成犯罪,因而不能辩称自己不知道或不能知道自身行为构成犯罪。针对被告律师提出的“法案违背了国际法,相关检诉与国际法相冲突”的观点,法院指出,以色列有权制定这样的法律。由于相应犯罪攻击的是整个人类,属于严重违反国际法,在缺乏一个国际法庭审判的背景下,国际法非但不限制国家行使管辖权,反而需要每个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机关采取行动,展开对相关罪犯的审判。在国际法上,审理这些犯罪的管辖权是普遍性的(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vol.36,1968:20-22)。
其二,“德米亚纽克案”(Demjanjuk case)*有关本案的细节及相关进展的详细描述,参见网页:http://www.nizkor.org/hweb/people/d/demjanjuk-john/israeli-data/demjanjuk-s1-2.html,2015年6月9日最后访问。。被告原是一名乌克兰红军。被德军俘获后,其自愿为德国纳粹服务,在波兰帮德国实施消灭犹太人计划,涉嫌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和反犹太人罪。自1951年起,他就在美国居住。后根据前苏联利用德国档案所披露的资料,其所犯罪行被美国发现。美国据此剥夺了其美国国籍,并将相关信息通报给以色列。以色列在确证了其身份和罪行之后,随即向美国提出了引渡请求。对于该引渡请求,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以色列有权根据国际法对德米亚纽克行使刑事管辖权*18 USC §3181.。以色列在法案中所确立的普遍管辖权获得了美国的承认与配合。
1986年2月26日,该嫌犯被引渡至以色列。1988年4月25日,德米亚纽克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vol.91,1993:25-30)。由于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成功,德米亚纽克被释放并于1993年回到美国。尽管其随后被遣送回德国并受到审判,但至其2012年死亡时为止,其尚未被最终“定罪量刑”*其于1993年回到美国并被恢复美国国籍。但到了2001年,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又发现了其涉嫌犯罪的证据,其国籍再次被剥夺。2009年5月11日,德米亚纽克被遣送回德国接受审判。2011年5月11日,其被判有罪并判处监禁刑5年。但由于其上诉并死于2012年,而此时上诉审未终结,因此,在理论上,其至死都是无罪之人。。尽管如此,以色列依然通过自身实践展示了其惩治二战战犯的政治意愿与决心。
(二) 澳大利亚的相关立法与实践
澳大利亚于1945年10月11日制定了《战争罪法》。根据该法序言和第7节的规定,该法适用于自澳大利亚卷入战争之后,“无论在何地实施的、无论是否在澳大利亚境内实施的、针对英国臣民或任何与女王陛下在任何战争中结盟或联合的国家的公民以及针对任何时候在澳大利亚居住的人实施的战争罪。”1988年,澳大利亚对本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第11节规定,“只有澳大利亚公民或居民才能够根据本法律受到刑事追诉。”至于犯罪时是否是澳大利亚国民或居民,则在所不问。
1945年法案通过之后,澳大利亚尽管也据此启动了对部分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犯罪的追诉程序,行使了普遍管辖权,但正如前文指出的,受限于证据获取的困难,以及系由军事法庭进行,大多“只开花不结果”。此种状况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始“有所改观”。“玻利科维奇案”(Polyukhovich case)即为代表。
被告玻利科维奇涉嫌在1942~1943年中犯有战争罪。二战后,其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1988年,澳大利亚根据修改后的《战争罪法》对其提起公诉。随后,被告以“《战争罪法》第9节涉嫌违宪,因而无效”、“相应行为实施时,澳大利亚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将一个非澳大利亚人在乌克兰所为的相关行为界定为犯罪”为由,提起上诉。1991年8月14日,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就此上诉做出了否定性裁决。裁决指出,1988年法案首要和实质性的规制对象是发生在澳大利亚之外的战争犯罪,尤其是二战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犯罪。根据法案规定,只有某人在遭受到指控时是澳大利亚国民或居民,法案才能适用。显然,根据法案规定,行为人在实施法案所规制的犯罪行为时,相关犯罪与澳大利亚没有相关联系。1988年法案并没有构成对宪法第51(6)和51(14)节有关“外部事项权力”的违背。在行使制定“外部事项”法律的权力时,宪法并不要求澳大利亚在相关主要事项上享有利益,而仅要求事关澳大利亚的利益或关切(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vol.91,1993:7-14)。
(三) 加拿大的相关立法与实践:芬塔案(Finta case)
1987年,加拿大通过了“修改刑法、1976年移民法和国民法”的修正案*See Act to Amend the Criminal Code,the Immigration Act,1976 and the Citizenship Act,S.C.1987,ch.37,Can.Stat.1107.。修改后的法案规定,凡犯有战争罪或反人道罪者,如果在为相应行为时,该行为在加拿大被视为是一种犯罪,那么,该犯罪得视为是在加拿大所为。制定此修正案的目的,即在于呼应民众有关审判纳粹罪犯的呼声,因为加拿大民众不愿加拿大成为纳粹战犯的“庇护国”。芬塔案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
该案的被告芬塔是匈牙利人。1944年,其在匈牙利针对犹太人涉嫌犯有反人道罪和战争罪。1947年,被告曾在匈牙利法院被缺席指控。但受限于法律时效,当时未被判刑。1951年,被告获得加拿大国籍并从1956年开始定居于加拿大。1987年12月1日,加拿大多伦多公诉人根据刑法典第7(3.71)节的规定,对其发起了刑事指控程序。在庭审中,应被告律师要求,审案法官向陪审团出示了被告在匈牙利受审时的相关录音和录像证据。在定罪事项上,审案法官决定将被告是否构成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问题留给陪审团决定。1990年5月22日,陪审团一致裁决,指控不成立,被告无罪释放。公诉人随后上诉但被驳回(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vol.98,1994:520-663)。此案随后被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94年3月24日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尽管驳回了上诉,但还是再次确认了加拿大对被告的管辖权。法院指出,如果一项犯罪行为损及了国际法律秩序,普遍管辖原则是允许一个国家对其管辖的,即使相关犯罪是由他国人实施的,受害者也非本国人。根据《权利和自由宪章》第11(g)节的规定,加拿大有权基于习惯国际法来对战争犯罪进行公诉,而不考虑相应行为发生于何地、何时(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vol.104,1997:287)。
(四) 英国的相关立法与实践:萨沃尼奇案(Sawoniuk case)
英国于1991年制定了《战争犯罪法》。该法第1节规定,如果某人在1939年9月1日到1945年6月5日期间,在德国或德占区涉嫌谋杀,违反了战争规则和惯例,并且,自1990年3月8日始,该人即在英国居住,则不论该人国籍为何,均应适用该法。萨沃尼奇案的审判即是根据本法案进行的。
被告萨沃尼奇在二战期间涉嫌作为纳粹同伙谋杀犹太人。战后,其移居英国并获得英国国籍。其犯罪行为直到1993年才被发现。随后,其被指控违反了《战争犯罪法》。在审判过程中,英国法院认为自身管辖权不存在任何问题。被告被陪审团裁决犯罪成立并判处终身监禁。萨沃尼奇随后以法庭将目击证人证言作为定罪的首要证据、证据不充分为由提起上诉。2000年2月10日,法院驳回了其上诉。2005年,被告死于狱中*有关本案的介绍及判决,参见网页:http://www.internationalcrimesdatabase.org/Case/744/Sawoniuk/,2015年6月19日最后访问。。
(五) 对四国立法与实践的简要小结
通过对上述四国立法和实践的梳理可以看出,针对战争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涉及了复杂的政治与法律问题。从政治要素来看,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是问题的关键。欠缺相应的政治意愿,法律程序的启动无从谈起。从法律角度来看,技术问题的处理是关键。论证自身拥有普遍管辖权仅仅是系列问题的起点。从程序的启动到最终定罪量刑判决的做出,里面涉及了大量复杂而精致的程序问题,如证据的获取问题、法律适用的溯及力问题、一案不二审问题等,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导致此前相关程序的“功亏一篑”。
而从英国的实践来看,在军事法庭短暂存在并审理过一批战争犯罪之后,随着军事法庭审理模式的终结,针对战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也相应地失去了行使的基础与依据。在此背景下,在普通法框架体系内确立针对战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就非常必要,也是继续审理二战期间战争犯罪的唯一可行方法。在审理萨沃尼奇案的过程中,法院也明确地指出过,如果没有制定1991年《战争犯罪法》,英国是无法行使对被告的管辖权的*See Judgment,R.v.Sawoniuk,Court of Appeal (Criminal Division),10 February 2000,参见网页http://www.internationalcrimesdatabase.org/Case/744/Sawoniuk/ ,2015年6月20日最后访问。。
三、 总结性评论:影响与意义
通过前述研究可以看出,战后针对战争犯罪的审判实行的是“双轨制”:主要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负责,次要战犯由各国负责。而从各国相关实践来看,除以色列外,部分国家在论证自身普遍管辖权的合法性的时候,是通过与海盗的类比来确立的。此种类比具有创新性,为以后普遍管辖权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与示范。而从国家实践来看,以色列相关法律的可溯及性,以及美国将普遍管辖权延伸适用于自身参战前的战争犯罪等实践,无疑都非常重要,既有利于有效惩治战争罪犯,终结有罪不罚,又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这些都有利于普遍管辖权的进一步发展。
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初的审判实践(主要是20世纪40年代)而言,以色列的实践无疑特别值得肯定。与其他国家不制定专门法、仅仅通过军事法庭等机制来审判战争罪犯不同,以色列专门制定了能够适用于战争罪犯审判的法律,在普通法框架体系内来展开追诉和审判。事实证明,此种机制既具有可持续性,也非常经济。美国由于欠缺相应的立法,不得不将德米亚纽克引渡给以色列审判即为明证*美国一直到1996年才制定了《战争犯罪法》。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类似法案不同,美国的此法案主要是基于1949年《日内瓦公约》制定的。。英国的后期实践吸取了以色列的经验和美国的教训。
从结果角度来看,在所有针对战争罪犯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国家中,结果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部分国家成功地做出了定罪量刑的判决,确保战争罪犯受到了有效的惩治,而另外一部分国家,要么“半途而废”,要么因技术的原因如证据的不充分等,而最终“功亏一篑”。这也说明,尽管战争犯罪“人人得而诛之”,要有效惩治,除了需要相关国家要有惩治的强烈政治意愿外,还需要配套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在执行中配套的资源,充分的技术支撑。
从影响角度来看,国家针对战争犯罪的普遍管辖实践不仅对后续的相关国际公约的制定提供了“国家实践”的基础,而且,对于后续的国际刑事法庭的相关实践和国家实践而言,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规制战争犯罪的公约即1949年日内瓦公约体系将普遍管辖权作为共同条款规定进了公约之中*如《日内瓦第一公约》第49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50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9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6条。,另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包括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等国际法庭,都可以从相关国家的普遍管辖实践中借鉴适当的“营养”*Requel Cross,The Relevance of the Eichmann,Barbie,and Finta Trials for the ICTR,2003,参见网页:http://www.nesl.edu/userfiles/file/wcmemos/2003/cross.pdf ,2015年6月16日最后访问。。而从后续国家实践角度来看,二战之后国家在战争罪犯审判领域的普遍管辖实践这一“星星之火”,在冷战终结之后,随着国家普遍管辖实践的“突飞猛进”,终成“燎原”之势。
而从中国角度来看,对于战争犯罪的普遍管辖问题,中国目前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方面,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国内相关的研究基本上忽视了二战后国际社会的前述相关实践*目前国内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有朱利江的相关著作。参见朱利江:《对国内战争罪的普遍管辖与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但即使在此著作中,也很少涉及到二战后有关战争罪的普遍管辖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于2010年4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中国关于‘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问题的评论和信息”中,中国认为只存在针对海盗行为的普遍管辖权*参见:“中国关于'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问题的评论和信息”(系外交部2010年9月15日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官方文件)的第3~4段,来源参见网页:http://www.un.org/en/ga/sixth/65/ScopeAppUniJuri_StatesComments/China.pdf,2015年6月20日最后访问。;在第67届联大六委有关此议题的发言中,中国与会代表进一步强调,即使国家要行使普遍管辖权,也要遵循属地等管辖权的优先性,并应尊重国际法上的豁免规则*参见中国代表任晓霞在第67届联大六委关于“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议题的发言,参见网页:http://www.fmprc.gov.cn/ce/ceun/chn/zgylhg/flyty/ldlwjh/t980874.htm,2015年6月16日最后访问。。中国与会代表的上述意见明显忽视了二战后各国有关战犯审判的普遍管辖实践。此种忽视,既不利于维护和强化战后世界秩序,也不利于利用之来推动战败国正视自身所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考虑到国家实践是推动国际法发展的引擎,国家在二战后针对战犯的有关普遍管辖权实践,一方面有利于普遍管辖权的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还有利于我国应对和处理与日本有关的战争问题,包括历史认识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因此,将来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自身有关普遍管辖权问题的立场。
参考文献:
[1]宋杰(2011).普遍民事管辖的发展与挑战.法学研究,1.
[2]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1).UniversalJurisdiction:TheDutytoEnactandEnforceLegislation,2.
[3]E.Lauterpacht,O.C.(ed.)(1968).InternationalLawRepor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Sir Elihu Lauterpacht,C.J.Greenwood(eds.)(1993).InternationalLawRepor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Sir Elihu Lauterpacht,C.J.Greenwood(eds.)(1994).InternationalLawRepor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Sir Elihu Lauterpacht,C.J.Greenwood(eds.)(1997).InternationalLawRepor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M.CherifBassiouni(1992).CrimesagainstHumanityinInternationalLaw.Leide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
[8]R.John Pritchard (1996).TheGiftofClemencyfollowingBritishWarCrimesTrialsintheFarEast,1946-1948.7 Criminal Law Forum,No.1.
[9]Suzannah Linton(2013).HongKong’sWarCrimesTria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1947).LawReportsofTrialsofWarCriminals,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1]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1948).LawReportsofTrialsofWarCriminals,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2]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1949).LawReportsofTrialsofWarCriminals,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作者地址:宋杰,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Email:ralph_sj2000@163.com 。
■责任编辑:李媛
War Criminals Trial and Universal Jurisdiction:
Practice,Development and Problem
SongJie(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After the World War II,the Allies national courts tried some lower suspect war criminals on the base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directly or indirectly.Although some states decided to prevent further prosecutions with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the revival of prosecutions basing on universal jurisdiction happened in the 1980s, which happened in Israel, Australia, UK and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se states' practice, the issue of excising universal jurisdiction against war criminals is involved with not only the relevant political will but also complicated legal issues which need to be supported by the sophisticated procedures.Prosecutions for war criminals based on universal jurisdiction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political wills and determin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unish war criminals and to end impunity,but also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providing experiences and references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World War II; war crime; punish war criminal; universal jurisdic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FX145)
DOI:10.14086/j.cnki.wujss.2015.05.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