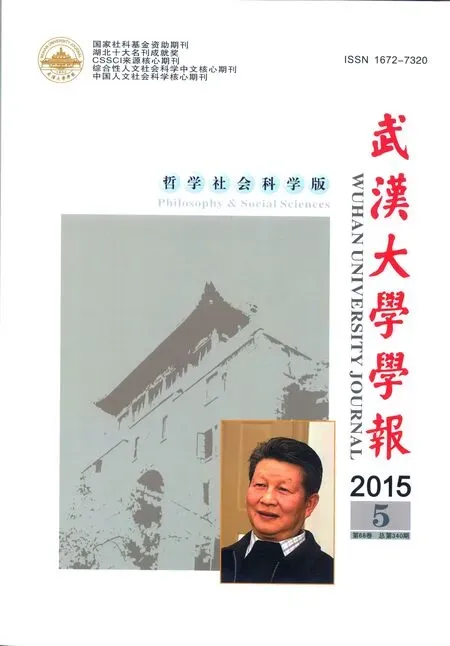战争罪中媒体仇视宣传的责任——纽伦堡后续审判和国际军事法庭三起相关案例之比较
张颖军 刘斯尧

战争罪中媒体仇视宣传的责任
——纽伦堡后续审判和国际军事法庭三起相关案例之比较
张颖军刘斯尧
摘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同盟国组织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两起利用媒体仇视宣传的案件,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对媒体言论的法律规制大体形成于这两个案例。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美国军事法庭的后续审判中对纳粹党新闻领袖奥托·迪特里希的判决几乎被学界所遗忘。面对两个法庭相似罪名的指控,三个案件却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通过展现这两个法庭的判决思路和推理,发现这三起案例对定义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媒体仇视宣传责任意义深刻,促进了国际刑法上间接犯罪责任认定的完善。
关键词:战争法;媒体责任;仇视宣传;纽伦堡后续审判;危害人类罪
2003年12月3日,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1994年卢旺达冲突中涉嫌利用媒体煽动种族仇杀、灭绝和迫害的米勒·科林斯(The Radio Télévision des Mille Collines,RTLM)广播电台创始人费迪南多·纳希马纳(Ferdinand Nahimana)、高级执行官琼·波斯科·巴拉亚戈威拉(Jean-Bosco Barayagwiza)、《康古拉报》(KANGURA)主编哈桑·尼格兹做出判决,判他们因犯下煽动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等而分别被处以终身监禁和35年有期徒刑。这是继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反犹报纸《冲锋队员》的发行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也有人译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参见约瑟夫.E.帕西科:《纽伦堡大审判》,刘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Julius Streicher)判决有罪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首次对媒体工作者进行审判(ICTR Press Release,2003)。这次宣判不仅再次吸引了人们对战争罪中媒体仇视宣传责任的注意,也揭开了70年前对这一问题首次审判的面纱。其实,施特莱彻不是当时唯一受审的媒体从业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下简称“国际军事法庭”)和美国驻德国军政府根据“同盟国管制委员会*同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是1945年8月30日,按照1945年6月5日《苏、英、美、法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和《苏、英、美、法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在德国柏林成立的机构,整体处理接管德国后的主权事项。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27-34页。第十号法令(Control Council Law No.10)”在纽伦堡进行的后续审判(Subsequent Nuremberg Trials,以下简称“后续审判”)*它实际是美国驻德国占领区军政府组建军事法庭,根据同盟国管制委员会10号法令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束后,对直接或间接涉入战争罪的纳粹军事将领、党卫军官员、党卫队特别行动队队员、部长级官员、法官、医生、商人等进行的12场审判,因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场所相同,也被称为纽伦堡后续审判,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或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判(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等。参见Kevin Jon Heller,“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and the Origi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2.目前在战争罪审判研究领域,很多学者也用其指代当时在德国各个占领区内进行的审判。具体参见Gwynne Skinner,“Nuremberg’s Legacy Continues:The Nuremberg Trials’ Influence On Human Rights Litigation in U.S.Courts Under the Alien Tort Statute”. 2008, 71 Alb.L.Rev.321.参见Michael P.Scharf ,“Seizing the ‘Grotian Moment’:Accelerated Form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Fundamental Change”,2010,43 CORNELL INT’L L.J.453.中,还对纳粹宣传部广播司司长汉斯·弗莱彻(Hans Fritzsche)和纳粹党新闻领袖雅各·奥托·迪特里希(Jacob Otto Dietrich,以下简称“迪特里希”)(The Ministries Case,1947:417)分别做出判决。但尽管他们因仇视宣传面临同样的指控,判决却截然不同。施特莱彻被判犯有危害人类罪并处以绞刑(Nuremberg Judgment,1947:295,333),弗莱彻被无罪释放(Nuremberg Judgment,1947:328),而与他同样处于宣传部门领导地位的迪特里希则被判有罪并处7年监禁。笔者通过展现这两个法庭不同的判决思路,比较它们认定仇视宣传行为和归责上的差异,从而发现其对战后国际刑法发展的作用。
一、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思路及推理
(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案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生于1885年,1921年加入纳粹党。1923-1945年间,他创办反犹报刊《冲锋队员报》(Der Stürmer)(Nuremberg Judgment,1947:294)并担任主编至1933年。该报随后成为纳粹宣传机器的核心之一,并最终成为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小报(克劳斯·费舍尔,2007:160)。他的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三部反犹儿童读物,使德国儿童心里埋下了仇恨犹太人的种子。
1.检方的指控
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第一项“破坏和平罪”、第三项“危害人类罪”,检方对施特莱彻提起指控。施特莱彻虽不是纳粹军队成员,也未参与策划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入侵其他国家,但他在煽动灭绝犹太人的宣传中起了关键作用(Randall L.Bytwerk,1983:1)。法庭对其指控的大部分证据来自他的众多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因此他被检察官认定为从犯,应与其他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人一样受到刑事制裁。而且,他在从事这些行为时深知犹太人被屠杀,因此具备主观故意(The Avalon Project,2015)。
2.法庭的判决和推理
第一,破坏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法庭认为,施特莱彻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是希特勒核心集团的顾问,他和纳粹战争政策的制订没有紧密联系,比如,他不曾出席任何希特勒跟手下各级负责人制订决策的重要会议,尽管他也是一个地方长官(Gauleiter)。没有证据证明他对这些决策知情(Nuremberg Judgment,1947:294)。法庭还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持他参与了共同计划或共谋发动侵略战争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1948:427),包括“策划,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See “The Charter of Nuremberg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rticle 6,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ail Published at Nuremberg,Germany,1948,Vol.XXII,p.427.。
法庭在认定有这种共同计划或阴谋的客观要件上,认为:纳粹党及其他潜在人员的目标和目的是和领导人、成员、支持者或纳粹分子有所联系的,该目标和目的是为了以任何可行的方式,包括非法的方式、诉诸武力的威胁、强迫和侵略战争等实现侵略。为煽动其他人加入共同计划或阴谋,他们提出、散播、利用某些极端的信条。因此,纳粹阴谋者对德国的全盘掌控主要是在政治上,第一步是要获得对德国国家机器的控制,第二步是完成掌控,第三步是对这种控制进行整合。可以看出,本案中施特莱彻虽作为报刊杂志的主负责人,但是并没有实际掌控政治上的国家机器,即不在真正纳粹党人的核心计划和决策领导层中,对于他个人的表达及利用媒体身份宣传散播反犹思想的行为,不包含在“共同计划或阴谋”的范围内。因此,法庭判定施特莱彻不构成破坏和平罪。
第二,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危害人类罪是“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管辖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地之国内法则在所不问。”“凡参与犯罪之共同计划或共谋之决定或执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犯者,对于执行此种计划之任何人所实施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国际条约集[1945-1947],1959:97-98)。对此,法庭认为,施特莱彻25年来发布、表达的各种仇恨犹太人的言论、作品以及鼓吹渲染行为煽动了德国人民迫害犹太人。另外,由于《宪章》规定危害人类罪必须发生在“战前或战时”,而施特莱彻煽动种族灭绝和屠杀,正值犹太人在东欧被残杀的最可怕情形下,明显是战争罪中以政治和种族为由构成的迫害,因此,其构成危害人类罪(Nuremberg Judgment,1947:296)。由此可见,在《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与战争相关是危害人类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二)汉斯·弗莱彻(Hans Fritzsche)案
汉斯·弗莱彻生于1900年,曾是著名的电台评论员。1932年9月,他开始从事新闻业;同年,成为帝国政府机构无线新闻服务处负责人。1933年5月1日,该机构被纳粹党整合进第三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弗莱彻因此成为纳粹党党员并在该部任职。1938年12月,成为该部内务新闻司司长;1942年,晋升为部长级领导。1942年11月,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广播司司长和大德意志电台政治组织全权代表(Nuremberg Judgment,1947:326-327)。
1.检方的指控
起诉书指控他犯有三项罪名: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认为他利用自身的地位和影响,散布、传播起诉书所列纳粹的主要政策和思想,特别是宣传反犹措施和对被占地区的无情盘剥,犯有拥护、鼓励和煽动从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The Avalon Project,2015)。
2.法庭的判决和推理
第一, 破坏和平罪。法庭查明,弗莱彻担任内务新闻司司长时,负责监管2300份日报的发行。在履行此职责过程中,他每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将宣传部的指示传达给这些报纸。工作职能上,他归迪特里希领导,而迪特里希又听命于戈贝尔。这些指导意见被冠以“帝国新闻领袖每日纲要”(Daily paroles of the Reich Press Chief)指引着舆论导向。纳粹德国每次侵略行动前都先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弗莱彻领导内务新闻司时,指示新闻机构应如何报道纳粹德国对波西米亚和马拉维亚、波兰、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战争。弗莱彻对制订这些宣传政策没有控制权,只是将迪特里希交给他的指示传达给新闻界。比如,1939年2月波西米亚、马拉维亚被吞并前,他接到迪特里希的命令——要求报道时把报道的焦点注意力放在斯洛伐克寻求独立、其反德政策和布拉格现存政权的政治问题上。
1942年1月,弗莱彻成为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广播司司长。最开始,迪特里希和其他部门领导都是通过广播发挥他们对政策的影响。但是,二战后期,弗莱彻成为唯一在宣传部内负责广播活动的领导。在工作期间,他按照纳粹政权的一般政治政策,制定日常广播“纲要”(paroles)传达给所有帝国宣传办公室。这一工作受帝国外事办广播政治司指导和戈贝尔个人监管。弗莱彻和宣传部其他官员一样,定期出席戈贝尔的日常工作会议。会上,他们被具体指导如何制定日常新闻和宣传政策。后来他的唯一职责甚至就是传递戈贝尔通过电话传达给他的指示。
法庭认为,从弗莱彻在纳粹政权的地位和影响来看,他从未达到参加纳粹策划侵略战争会议的地位;他甚至从未与希特勒有过交谈,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被告知那些会议要采取的决策。因此,他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共同计划或共谋发动侵略战争”罪。
第二, 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起诉书指控弗莱彻犯有煽动和鼓励战争罪,通过虚假新闻报道激起德国民众情绪,从事罪状三和罪状四的暴行。但法庭认为,他的地位和职责还未重要到能参与制订和谋划宣传战的程度。诚然,他是绝对的反犹主义者。比如,他在报道中称战争是由犹太人引起的。但这些言论并未推动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且,没有证据显示他知道犹太人在东欧被屠杀。甚至有两个实例证实,他曾试图阻止反犹报刊《冲锋队员报》的发行,尽管没有成功。
法庭认为,虽然弗莱彻有时报道虚假新闻,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那是假的。比如,在德国U艇沉没事件的报道中,他说雅典附近海域没有德国U艇。这个消息不真实,但他是从德国海军获得的,他当时没有理由相信那不是真实的。对于弗莱彻在新闻报道中发表过的激烈言论,法庭不认为其目的是煽动德国民众对占领区人民实施暴行,也不能据此认定弗莱彻参与了这些罪行。它们的目的更确切地说是激起公众情绪支持希特勒和德国的战争。综上,法庭宣布,弗莱彻无罪,应予释放(Nuremberg Judgment,1947:327-328)。后来,他被西德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法院审判并被判处9年监禁。
二、 纽伦堡后续审判的判决思路和推理
纽伦堡后续审判第11场“对部长的审判” (The Ministers Case)*“对部长的审判”参见:“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Nuremberg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10,Vol.ⅩⅣ,1948, published at Nuremberg,Germany.进行了对纳粹党新闻领袖雅各·奥托·迪特里希的审判。这是第三个媒体仇视宣传的案件。
(一)背景
迪特里希生于1897年,曾担任纳粹党新闻领袖、第三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新闻司司长。1928年,他成为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的主管,并于1929年加入纳粹党。当时纳粹党的主要宣传机构有全国宣传指导处、新闻办公室、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其中,新闻办公室设在慕尼黑,专门负责发布纳粹党全国性活动的消息,并监视党的系统内所有机关报刊的宣传内容(Gregory S.Gordon,2014)。奥托·迪特里希作为新闻发布官,能直接了解希特勒的宣传意图,因此他在党内地位特殊。他还曾建立自己的地方新闻办公室,以全面控制当地的党报宣传。
(二)法庭的判决和推理
起诉书认为迪特里希触犯了八项罪状中的五项:罪状一,破坏和平罪;罪状三,战争罪;罪状四,危害人类罪中的对平民犯下暴行和犯罪;罪状五,危害人类罪中的迫害行为;罪状八,犯罪组织机构成员。但法庭最终判决迪特里希只触犯了罪状五和罪状八。罪状四在法院审判前已被撤销(Gregory S.Gordon,2014)。由于罪状三主要是他处理“英国飞行员在艾森受私刑致死案”(Essen Lynching Case)的措施问题,罪状八是因他在纳粹党的成员身份,与仇视宣传无关,因此,以下仅分析法庭对罪状一和罪状五的判决。
1.罪状一:破坏和平罪
法庭认为,被告迪特里希在德国计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整个期间都是帝国新闻主管和纳粹党新闻领袖,那时他作为随从不断出入希特勒的指挥部。唯一能证明他对这些计划有所了解的是他掌控了德国和政党的新闻媒体,在每次侵略战争之前和发动时都发挥了作用,激起了全德的情绪来支持他们,并由此影响了德国公众的观念。虽然他没有参加希特勒的任何值得关注的会议,但完全有可能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有强烈的心理预见。然而,无论如何,怀疑不能代替证据。因此,依据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法庭认为没有可以认定他在该罪状下有罪的证据,他无罪(Trials of War Criminals,1948:417)。
2.罪状五:危害人类罪中的迫害行为
在罪状五危害人类罪中,法庭对迪特里希的指控主要是基于他的媒体活动和仇恨言论。罪状五的行为形态主要是基于对平民犯下的暴行和罪行,当然其中包含各种不同类别的犯罪行为,而且也包括基于言论行为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在管制委员会第10号法令第二条中,界定了“危害人类罪”:“参与暴行和犯罪,包括……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理由的迫害。”起诉书第39段提出,“被告创建、制定并散播了带煽动性的教义,以此煽动德国人去积极迫害那些‘政治和种族劣群’” (Trials of War Criminals,1948:565-572)。起诉书还提到,“在演讲、文章、新闻稿和其他出版物中,他不断重申这些人是细菌、害虫和劣种人群,应该被消灭”(Trials of War Criminals,1948:565)。
法庭认为迪特里希符合罪状五规定的“迫害行为”,主要是考虑到在屠杀方案中他对德国人民的影响。判决书中认为,这种能激起德国人对犹太人仇恨的言论是由迪特里希利用新闻部门来推动的。这些出版物和期刊指令并不仅是政治上的一种辩论,因为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地表达反犹思想,并且他们并不完全是为了在战争中统一德国人民,他们特定的目的是激起德国人民反对犹太人,给已发生和尚未发生的仇恨行为提供“正当”依据,同时消除任何对种族迫害的“正义性”产生怀疑的可能性。在主观要件上,法庭认为迪特里希是有意实施,因此构成危害人类罪(Trials of War Criminals,1948:576)。
三、 上述两个军事法庭媒体仇视宣传案例之比较
通过比较上述判决可以看出,两个法庭在认定仇视宣传案时存在以下异同:
第一,虽然这三个案件的被告利用媒体仇视宣传的行为被各自指控有反和平罪、战争罪等不同罪状,但两个军事法庭通过论证认为,它只属于危害人类罪。由于那时还出现灭绝种族罪的罪名,像这三个案件被告那样鼓吹、煽动对犹太民族的歧视、灭绝和迫害的都被归于危害人类罪论处。
第二,由于两个军事法庭所依据的法律不同,对于危害人类罪的定义也略有不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依据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规定“危害人类罪,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管辖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地之国内法则在所不问。”(国际条约集[1945-1947],1959:97)
纽伦堡后续审判依据的《管制委员会第10号法令》规定,危害人类罪是 “暴行和罪行,包括但不限于对平民人口犯下的谋杀、灭绝、奴役、驱逐、监禁、酷刑、强奸或其他非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的迫害,无论是否违反罪行实施的国内法律。”(The Allied Control Council,1945:307)相比可见,《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要求危害人类罪在“战前或战时”从事。与战争有关就成为危害人类罪的一个构成要件。在施特莱彻案中,法庭为此颇费功夫地加以论证以说明他符合该罪。而《管制委员会第10号法令》则不再要求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有关,既减少了法庭论证的任务,这也表明“危害人类罪”已经作为一项可以单独成立的罪名,不仅在“战前或战时”,而且还可以在和平时期也可以触犯。
第三,从法庭判决看,纽伦堡后续审判对被告指控的罪名更具体,比如,“迪特里希案”被指控的罪名就包括危害人类罪下的两个罪名:“危害人类罪中的迫害行为”(罪状五)和“危害人类罪中对平民犯下暴行和犯罪”(罪状四)。尽管罪状四在该案审判前已撤销,还是可以看出后续审判所适用的实体法更为细致(Kevin Jon Heller,2014:401) 。
第四,从两个法庭的判决思路来看,在国际军事法庭,直接从事仇视宣传似乎成为认定被告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要件之一。在“汉斯·弗里彻案”中,就是因为指控他直接从事仇视宣传的证据不足,才判决他于“危害人类罪”的罪名无罪。而美占区军事法庭则对这一条似乎没有那么强调,如上所述,虽然迪特里希在演讲、文章、新闻稿和其他出版物中有直接鼓吹、煽动种族优越论、贬低犹太人的论调,但是法庭对他在履行作为宣传部门领导职责时对全国媒体仇视宣传予以审核和批准的行为也认定为危害人类罪中的迫害。说明两个法庭对这一行为的归责原则是不一样的。纽伦堡后续审判依据的《管制委员会十号法令》第2条第2款明确规定,“任何人,不管其国籍或行为时职务为何,具有下列情形的,也视为构成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犯罪:(a)主犯,或(b)任何犯罪行为体中的从犯,或命令,教唆者,或(c)赞同犯罪的,或(d)与犯罪的计划或共同行为体有关联的,或(e)是任何与此犯罪行为有关的犯罪组织或集团的成员的,或(f)赞成第一条第一款的罪行,如果他如此行事时是在德国或其盟国的政治、军事或民间组织中处于高级地位,或在任何国家的财政、工业或经济生活中处于高级地位的。”*Control Council Law No.10,Article Ⅱ.CONL/P (45)53.The Allied Control Council (1945),Vol.Ⅰ,p.307.
这其实就明确将不同地位、可能间接涉入法令所述战争罪、反和平罪、危害人类罪的人都包括进去了。这也是对二战中的德国企业家、银行家、医生、法官、纳粹低层级部门领导等的审判能在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则只规定“凡参与犯上述任何一种犯罪之共同计划或共谋之决定或执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犯者,对于执行此种计划之任何人所实施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国际条约集[1945-1947],1959:97-98)。可以看出,它主要还是利用共谋或计划以及传统的胁从犯理论进行归责,与后续审判相比有一定局限。
第五,两个法庭对于案中被告仇视宣传行为的归责方式不同。国际军事法庭在施特莱彻案中,通过论证,以危害人类罪中谋杀和迫害的从犯对其归责;而纽伦堡后续审判因为有了前面所说的规定,直接将他们利用媒体宣传、煽动仇视犹太人的做法归为危害人类罪中的迫害行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为日后国际刑法上间接犯罪责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四、 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后续审判上述仇视宣传案的判决对完善国际法上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的定义具有重要的意义。纽伦堡审判之后,危害人类罪的界定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以下简称《前南刑庭规约》)、《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以下简称《卢旺达刑庭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中得到了进一步承袭和发展。《前南刑庭规约》特别规定危害人类罪适用于所有性质的武装冲突,不论它们是否具有国际性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做出了一定程度修订,规定危害人类罪在客观攻击上应该具有“广泛或有系统”的特征,而且强调了主观方面“出于民族、政治、人种、种族或宗教原因”的歧视性动机或理由是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一般性要件,改变了之前要求迫害行为的行为人具备歧视性动机的做法(王新,2011:18)。1998年《罗马规约》使危害人类罪与武装冲突彻底脱钩(刘大群,2006:1-34、355),确认攻击行为应该具有“广泛或有系统性”的构成标准,舍弃了之前《卢旺达刑庭规约》将“歧视性理由”作为该罪一般性要件的做法。
第二,虽然纽伦堡审判时尚未出现“灭绝种族罪”罪名,但上述几个案例使立法者开始考虑对如所述被告那样未直接参与屠杀、灭绝和迫害但通过媒体散布、传播、煽动种族歧视和灭绝理念的行为加以明确规定。《前南刑庭规约》和《卢旺达刑庭规约》除了在“个人刑事责任”这一条统一规定“计划、煽动、命令从事公约所述犯罪的,或以其他方式在计划、准备和执行公约所述犯罪的人,都应承担个人刑事责任”*ICTR Statute,Article 6.Se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2010); ICTY Statute,Article 7.Se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009).外,还在“灭绝种族罪”项下专门规定,“共谋实施灭绝种族的、直接、公开煽动灭绝种族的、图谋从事灭绝种族的和灭绝种族罪之共犯都应受到惩处”*ICTR Statute,Article 2(3); ICTY Statute,Article 4(3).Se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009).从而使利用媒体仇视宣传之类的行为可直接被归为犯罪。《罗马规约》虽然没有像它们那样在罪名下直接规定,但在“个人刑事责任”中专门列出一项,规定,“在灭种罪中,直接并公开煽动他人实施灭绝种族的应承担个人刑事责任”*Rome Statute,Article 25,(3),(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2011)。这样做有利于法庭更明确地适用,反映了国际社会打击种族歧视类犯罪的决心和倡导人人享有基本人权的理念。
第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后续审判上述仇视宣传案的判决促进了国际刑法上间接犯罪责任认定的发展与完善。近些年来,国际刑法在追究间接犯罪的责任领域发展很快,比如,追究间接涉入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战争罪等严重国际犯罪的公司、法人责任(张颖军,2011:20)。虽然,此类责任还未纳入国际刑法公约,但一些国家已开始行动。1997年9月,尤纳科公司(Unocal)也因从被认为侵犯公民人权的缅甸政府获得石油开采和管道建设项目,而被诉至美国加州的法院(张颖军,2011:21)。2006年、2007年,两名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做交易的商人在荷兰海牙地区法院被以战争罪共犯(Complicity in war crime)判决有罪(Wim Huisman & Elies van Sliedregt,2010:805)。在处理这些案件时,纽伦堡后续审判追诉商人、媒体人等责任的实践成为被援引的重要判例,这些案例对国际刑法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纽伦堡审判的上述案例对厘清媒体言论的边界也有重要作用。虽然,它们对这方面国际立法的具体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战后逐渐兴起的对媒体言论、在媒体上表达言论,以及利用媒体散布和传播言论的行为进行限制的立法*例如,2003年1月28日,欧洲理事会通过2001年《网络犯罪公约》之《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犯罪化的附加议定书》,将利用计算机系统和网络这类新媒体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刑事化,它规定的四种犯罪行为中就有利用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散布、传播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言论和材料、否定灭绝种族罪和反人道罪等。参见张颖军:《打击网络犯罪中的少数人权利保护—— 〈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犯罪化的附加议定书〉介评》,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24-127页。,或多或少受到了这些战后审判所确立的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不加歧视地享有基本人权的理念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对于国际法上有关言论自由立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龚艳(2011).仇恨言论的法律规制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刘大群(2006).论危害人类罪.武大国际法评论, 1.
[3]克劳斯·费舍尔(2007).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4]王新(2011).危害人类罪在国际刑法中的确认和构成要件.河北法学.4.
[5]张颖军(2011).打击网络犯罪中的少数人权利保护——《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犯罪化的附加议定书》介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6]Gregory S.Gordon(2014).TheForgottenNurembergHateSpeechCase:OttoDietrichandTheFutureofPersecutionLaw, 75 Ohio St.L.J.571.
[7]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2003).Press Release.Three Media Leaders convicted for Genocide,http://www.unictr.org/en/news/three-media-leaders-convicted-genocide.
[8]Law Reports(1947).LawReportsofTrialsofWarCriminals,SelectedandpreparedbytheUNWarCrimesCommission,Vol.Ⅰ.London:Published for the UN War Crimes Commission by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9]Michael Perich(2012),MediaInfluenceInTheGhailaniTrial:HaveWeSeenThisBefore?TheEvergrowingImportanceOfAnIndependentJudiciary,4 Wash.U.Jurisprudence Rev.349.
[10]Nuremberg Judgment(1947).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Judgment and Sentence,October 1,1946,41 Am.J.Int’l L.
[11]Randall L.Bytwerk (1983).JuliusStreicher.New York:Dorset Press.
[12]Randall L.Bytwerk(2001).JuliusStreicher:NaziEditoroftheNotoriousAnti-SemiticNewspaperDerStürmer,New York:Cooper Square Press.
[13]The Avalon Project(2015).Yale Law School.http://avalon.law.yale.edu/.
[14]Wim Huisman & Elies van Sliedregt (2010).Rogue Traders:Dutch Businessmen,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Corporate Complicity,JournalofInternationalCriminalJustice,8.
■作者地址:张颖军,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zyj2161@sina.com。
刘斯尧,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李媛
The Responsibility of Hate Speech unde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ZhangYingjun(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iuSiyao(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wo hate speech cases were jud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MT).At present, researchers thought the legal system about the media was formed from the two cases. However, after the judgments, the U.S. military court has dealed with another case which was in regard to the news leder of Nazi whose name was Otto Dietrich. Although the same charges against the defendants,the tribunals issued totally different judgments:th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onviction of Nazi newspaper editor Julius Streicher and the acquittal on the same charge of Third Reich Radio Division Chief Hans Fritzsche by IMT,whereas the Reich Press Chief Otto Dietrich,the similar status with the latter,was convict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harged language did not directly call for violence. Those three cases have significant meaning to defin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crimes of genocide,responsibilities of hate speeches.They have promte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by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consequential crime.
Key words:law of war; media responsibility; hate speech; nuremberg subsequent trial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820014)
DOI:10.14086/j.cnki.wujss.2015.05.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