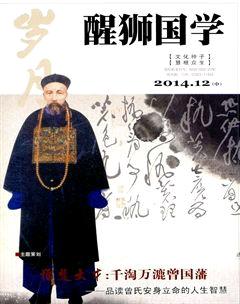文化霸权与文明衰落(六)
孙皓晖
儒家学派有若干一以贯之的精神,我称之为儒家的学派性格。
迂阔之气
迂阔之气,大约是儒家性格中唯一有着些许可爱之处的缺失。
迂阔者,绕远而不切实际也。儒家蔑视任何民生技能,蔑视任何形式的劳动,在所有学派中,独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殊荣。见诸政治实践,入仕多居“清要”之职,对需要专业技能的领域涉足极少。譬如兵事,譬如工程,譬如经济,譬如行法,等等,少见儒家身影。喜欢做官,却不喜欢做事,尤其不喜欢做那种既辛苦又专业的苦差事,美其名曰“君子论道不计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执着之处,只在专一的扫天下而不扫庭院,只在专一的坐而论道,最热衷于担当道德评判角色。
此风流播后世,便有了一班“清流”儒家,以做官不做事为名士作派,终日玄谈,在职酗酒,观赏性事,竞赛颓废;其种种作为,直比当时腐败的社会更腐败,实在令人齿冷。儒家迂阔处,还在于议政议事之言论,多大而无当。此风在原生态时期,以孟子为甚,雄辩滔滔云山雾罩,似乎有着某种精神指向,却不知究竟要你做甚。“笔下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之评,可谓传神。凡此种种迂阔处,若仅仅是个人作派,自是无可无不可。然则,儒家却将这种迂阔之风,带进了庙堂官署,带进了学堂书房;不敬业,不成事,不务实学,不通民生;酿成官场流风,酿成治学恶习,沾沾自喜,不以为非,实在是中国文明变形之一大奇观,叫人不敢恭维。
偏执习性
偏执习性,儒家又一性格缺失。
儒家偏执,基本点在三:一、咬定自家不放松,绝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另外活法。二、不容纳其他任何学派的任何主张,绝不相信自家经书之外还有真理。你说山外有山吗,人上有人吗,扯淡,儒家理论绝对天下第一!三、对其他学派恶意攻讦,人身伤害,其用语之刻毒天下仅见。
孔子骂人很少,稍好,大约生平只骂过一件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直骂陶殉,实骂人殉。此等事该骂,不能算作孔子缺点。但是,孔子此骂,瞄准了“无后”,却定下了儒家骂人定式——人身攻击,直捣传宗接代。此种秉性,以孟子为最,骂论敌刻毒异常;骂墨子,是“兼爱无父,禽兽行”;骂杨朱学派,是“无君,禽兽行”;骂纵横家,是“妾妇之道”。近见网络文章,有人将孟子称为“战国职业骂客”,比较实在。自孟子开始,“衣冠禽兽”便成了儒家恒久的骂人经典语汇。儒家动辄口诛笔伐,毒骂入骨,实在是一种阴暗心理、恶劣秉性。用语武断的指斥性评判,孟子更是多见。一则典型例子是:古文献记载武王伐纣的战争很残酷,有“血流漂杵”四个字;孟子偏不信,昂昂然宣称:“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能血流漂杵!”指示弟子当即删去了古文献的这一句。
如此武断偏执,千古之下,无出其右。
论事诛心
论事诛心,是儒家又一性格缺失。
儒家论人论事,有一个可怕的习惯——动辄诛心。
什么是诛心?不问行为言论之本身正确与否,只专一地纠缠行为动机,以求心罪。不是看你如何做事,而是看你如何想法,这就是论事诛心。此法成为一种杀人方略,有学者考证认为:出于战国时期的《公羊春秋》,成于董仲舒的种种论证。无论其演变如何,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以“道”定罪的路子。所谓“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正是儒家“诛心”套路的自我表白。
儒家以《春秋》立起的政治标尺,不是行为法度,而是道义标尺、教义标尺、心理标尺。由诛心之法,衍生出儒家攻讦政敌、论敌的一个威力无穷的非常规武器——“名教罪人”。你可以没有犯法,但你完全可能因为某句话某件事,而被认定为“名教罪人”。原因无他,只是“其心有异”。
此风传承流播,儒家大得其手,非但将有形之敌统统打倒,更将无形之敌也置于死地。后世之宋明理学更甚,非但要“存天理,灭人欲”,还要破“山中贼”,更破“心中贼”。如此汹汹诛心,堪问灵魂,天下孰能不诚惶诚恐?孰能不臣服儒家?
最是记仇
记仇,是儒家的又一性格缺失。
在所有的先秦学派中,儒家是最记仇的一家。但有歧见,殷殷在心,一有机会,便新账老账一起算,绝不手软。这种性格,与儒家提倡的“恕道”很不相应,使人难以相信。但是,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一个孜孜提倡“恕道”的学派,事实上却是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学派。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与几乎所有的学派,都因主张不同而产生过龃龉。期间,除了论战中的观念批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揪住儒家不放。儒家却是耿耿于怀,念兹在兹,一遇机会,便以“史家”秉性,将论敌种种时期的言词作为清算一通,而后再做定性式的人身攻击。读儒家经书,每遇此等攻击之辞,不用说,便是儒家在发泄仇恨。
若仅仅如此,还不能说明儒家记仇。
事实为据
儒家记仇,积成秉性,有事实为依据。
基本事实一,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被无情遗弃,所以,对生身时代仇恨极深。举凡儒家修史,“自周以降,风气大坏”之类的词句,比比皆是。司马迁的《史记》稍好,但也是否定春秋战国,以儒家观念做史家评判的。《汉书》最鲜明,大凡直接表现修史者观念的领域通论,诸如《刑法志》《食货志》《礼乐志》《律历志》《郊祀志》等,无不先狠狠赞颂一通上古三代,紧接着便是一句必然的转折定性——“周室既衰”,春秋时代如何如何坏;“陵夷至于战国”,更是如何如何坏;连番指斥两大时代,然后又一转折,说到“汉兴”之后如何好,再变为连篇累牍的颂词。如此三段论法,已经成为定式,实在是有趣得紧。显然,在儒家眼里,所有的时代中,惟春秋战国最不是东西!
基本事实二,儒家在秦帝国时期大遭“压制迫害”,从此对秦帝国永远地咬牙切齿,不由分说一言以蔽之——暴政暴秦!两汉之后的儒家,干脆只管骂秦,连论证都懒得做了。说儒家患有“秦过敏症”,似乎不为过分。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必然要镇压复辟势力。事情起因,在于儒家自己不守秦法,伙同六国贵族大肆散布种种流言,从而获罪,被坑杀了寥寥几人(被坑杀者绝大多数是方士)。纵然冤枉,两千余年之后,竟仍然不能释怀,一概骂倒秦帝国,也是绝无仅有了。除了“记仇成癖”,不知道还能有何种解释。
基本事实三,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善为人敌,几乎被天下学派孤立。一旦得势,儒家立即以“独尊”平台为条件,全力排斥百家经典的流传。至近代梁启超时期,《墨子》文本已经难以寻觅,隐藏到道家炼丹术之类的书里去了。一个学派“独尊”,在春秋战国时代,无异于痴人说梦,任何学派都不可能有如此狼子野心。所以,西汉时期的其他任何学派,都没有提出如此狂妄、如此荒谬的主张。唯独儒家,不但要说,还要做。这便是儒家,为图复仇,敢与天下作对,敢与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文明成就作对,破罐子猛摔,以求出人头地,唯求复仇为快。
其心之野,其图之大,两千年之后,尤令人乍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