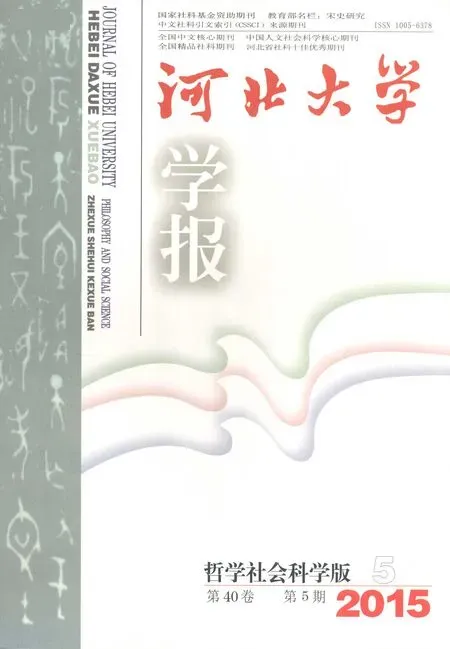20世纪以来回族小说中的少年形象
王继霞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20世纪以来回族小说中的少年形象
王继霞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少年形象是凝聚着回族深刻历史印记和原初生活体验的重要文学典型。梳理了其自20世纪以来的历时演变,并重点分析了民国、新时期、新世纪等历史时段中该形象的不同成长际遇和精神诉求,认为它们反映了成长主体与民族文化共同体间情感密度的变动以及相应引发的精神重构,是20世纪回族社会现代转型的精神缩影。在此基础上对该形象价值进行反思,指出其审美创新、人文意蕴等都有待挖掘提升。
回族少年形象;孕育发展;精神流变;价值反思
一、回族少年形象的孕育发展
少年形象是回族文学重要典型之一,凝聚着回族深刻的历史印记和原初的生活体验,具有独特民族性审美价值和丰富思想意蕴。它较早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回族报刊中。1906-1949 年间回族知识分子在京津沪滇等城市创办了200多种回族报刊,构成回族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传播媒介。它们围绕着族教振兴的核心使命刊载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呈现出超越传统私人话语、广涉回族社会各个方面的民族生存文化图。许多浸润着回族时代印记和心理特质的少年形象就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叙事类作品——现代回族小说的雏形——之中。滞留在清真寺中的苦闷的宏志、面向社会彷徨无措的彬哥、在家庭不幸中不能自拔的可怜生等①宏志系文所著同名短篇小说《宏志》(《晨熹旬刊》1935年第一卷第十二、十三、十四号合刊)主人公;彬哥系红霞所著短篇小说《新路》(《月华周报》 1948年8月1日第27期第三版)主人公;可怜生系书庵所著短篇小说《不回来了》(《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6年第一卷第六期)主人公。,从不同层面实录性地呈现了20世纪初期回族闭塞贫弱、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以及这一代少年忧心忡忡充满无助之感的成长之痛。
另一方面,报刊文学社会工具性的价值原点和现代回族文学初创期的萌芽特质也决定了这些形象在思想上偏于成人化、在艺术上相对稚嫩单薄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歌颂新生政党、赞美社会主义新生活一度成为文学核心甚至是唯一的使命,回族文学亦汇入时代大潮。
1980年度以来,在新的文艺政策民族政策感召下,在新的时代生活语境中,这种创作局面才得到根本性改变。许多回族作家开始将注意力投射到本民族身上,在抚慰伤痕、反思历史、憧憬变革的同时,他们努力呈现着回族——这个有着自己一定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回族少年形象于此开始走入我们视野。在红色风暴中精神迷失的哈桑、热情追问着民族历史与未来的马力、面对传统压力执着向学的木撒等,这些新时代的少年带着各自的“念想”奔向青春①哈桑系王瑞康所著短篇小说《回回村纪事·高高的宣礼楼》(《新月集》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5.8)主人公;马力系王延辉所著短篇小说《出幼》(《中国神话》济南:明天出版社,1994.3)主人公;木撒系马治中所著短篇小说《三代人》(《回族小说散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昌吉回族自治州文联回族文学编选组编,1984.7)主人公。。相较而言,本时期该形象的塑造成熟许多,形式上由简单的叙事类报刊篇章走向结构完整的短篇小说;内容上也趋于饱满,主人公不再止于对时事事务的空泛感怀,而是在现实矛盾或变故的重重考验中经历螺旋式上升的成长过程,如王瑞康在“拆毁宣礼楼—内心纠结—重建宣礼楼—心灵重获平静”的情节变动中完成了哈桑形象,传达了文革境遇中一代回族少年的成长诉求。这种视域的确定使得该形象更具有成长期少年的精神特质,相应文本主题意蕴也更为凝炼丰厚。
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日益开放,日常生活合法性范畴不断扩大,宏大国家话语阐释和时代主潮抒写不再成为焦点,文学命题日渐多元。回族少年形象塑造获得纵深突破,数量增加、视角扩大。既往立足特定社会背景、以族裔化视角为中心对少年予以关照的固定模式开始被打破,逐渐出现了从自我、他者、家庭、族群、乡村、城市等多重生活空间对对象物质、精神层面的各种显性或隐性成长的书写。可以说本时期少年形象在精神浓度、审美意蕴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是当代回族文学发展的重要收获之一。
总之,回族少年形象自20世纪初回族报刊文学兴起时即开始孕育,历经一百多年文学实践以小说为主要形式不断得以丰赡发展。相较而言,民国时代、建国前三十年时期,该形象更多是关于族教、国家等宏大主题的具象投射,相应族裔化、社会化色彩浓厚一些,而个性化不足;加之艺术手法也较为有限,人物总体不够丰满立体。新时期以来,创作视角扩大、艺术手法更新,诸多关涉少年精神世界的内容都被纳入作者笔下,巧妙运营形成一个个带着特定时代气息、生活含量、民族韵味的文学典型。
二、回族少年形象的精神流变
20世纪回族经历了艰难的现代转型,从闭塞濒危之境逐渐走出并不断融入主流获得发展,少年也与本民族一道共同成长,走过从压抑迷茫到求索反思的精神之旅。依托这一巨型社会背景,回族小说集中刻画了解放前、新时期、新世纪三个历史时段中的少年形象,通过他们不同的精神诉求传达出其与民族文化共同体间情感密度的变动以及相应引发的精神重构,折射出回族在现代进程中与各种外在力量纠葛、抗争的心路历程。
(一)解放前:情系国教 心忧未来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回族新文化运动中,少年群体——这一未来回族人的希望所在——受到广泛关注。他们的教育现状、职业选择、精神建构等都成为回族社会的时事热点纳入知识精英的视野。于此,一些浸润着民族特质与时代印记的少年形象就在报刊文学中应运而生。
小说《宏志》以回族日常清真寺生活为主要场景,塑造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回族少年形象。他与父亲相依为命,生活贫困不堪、备受嘲讽。这种境遇令他常常苦恼抱怨道:“唉,安拉!这是从何说起呢?像我们这样的苦痛,是已经够人受的了,又怎堪不停的再递增呢?”而父亲则以“认定然”的伊斯兰信仰为支撑反复劝说:“这正是主的赐悯,这是你一生事业的成功之路……我们只有本着真主赐予我们的能力去换饭吃,我们决不能作寄生虫去仰仗于人。”在宗教的慰藉中少年宏志逐渐平复了内心,和父亲一道“随着阿訇的喊声都静静的向寺中走去”“静待着真主的公道和人世公理的到临”[1]。
《诱惑》《新路》等作品则把镜头从清真寺中拉出,关注少年步入主流社会时的精神困惑。《诱惑》中的主人公面对职业选择时内心非常纠结,是按照族内传统职业定位做一个献身族教的宗教职业者,还是投身社会革命做一个时代弄潮儿呢?他反复思量难以抉择。“安拉呀!你相助我这脆弱的心吧”[2],这无助的呼喊道出当时许多即将步入社会的少年内心的迷茫。《新路》描写了“我”和“彬哥”等回族少年因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得不到理解尊重、理想难以实现的现实苦闷。“我用眼睛在追寻人生的光明,但得到的却是黑暗与恐怖,强烈的刺激使我这颗年青而有活力的心未老先衰”[3],这些独白让我们看到回族少年举步维艰的生活困境。
民国少年生逢国势动荡族教濒危之际,不断遭遇启蒙、革命等社会浪潮的冲击以及诸如经济滑坡、教育滞后、宗教衰颓、话语权缺失等关涉族教存亡命题的逼迫,于此迅速成长裂变。宏志在宗教慰藉中选择了沉默隐忍、彬哥在主流质疑时表现得焦灼痛苦,这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20世纪初始狂飙突进的现代文化理念对于回族——这个长期被置于边缘的、衰颓滞后的少数民族而言,只是一种模糊的碎片式存在,它激发并加剧着这个群体的现实焦虑感。而与此同时,传统民族认同意识虽然备受冲击,却依然顽强存在并很大程度上主宰着回族的思想行为。这使得对族教家国现状与未来的忧虑成为了民国少年蛰伏于心的成长之痛,影响着他们对外界的认知和抉择。报刊文学中该形象呈现出的如行将脱壳的雏鸡一般,不断张望探求外部世界的身影,是这一心理的投射,一定意义上浓缩着回族社会逐步走出闭塞面向主流的精神历程。
(二)新时期:追问历史 重构自我
19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全新发展。少年形象,相较于前者,这一代人没有了贫穷困厄境遇的挤压,他们和许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一样,对时代和生活充满激情与憧憬。然而这种共鸣并不能彻底消除他们精神深处潜在的隐痛,在时代主潮的起伏冲击之外,他们还承受着多重文化抉择、身份认同等新的焦虑,这成为其特有的成长之痛。
《高高的宣礼楼》中的哈桑是一个在红色风暴中迷失自我的回族少年。他与许多回族孩子一样,自幼在“祖习、风俗、自性”的形式中接受着基本的伊斯兰教文化熏陶,在情感和信仰上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坚守民族立场,以异于“常态”的文化身份行走在世界中,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伴随在这一代少年的成长之旅中,令他们困惑不已。王延辉笔下的马力,使少年的求索就具有了为民族代言、为自我明证的双重意味,个体成长与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自我确认紧密联系起来。
相较于第一代少年置身族教中迷茫地观望外界、踟蹰不已,这一代人已经大大走出边缘,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家庭与寺坊结构成的较稳定的生活小环境与全新政权领导下的社会大环境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意识到必须在强烈的社会位移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于此,精神上求索定位的诉求更为急切。
(三)新世纪:世俗来袭 心无所依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涌动不息,道德滑坡、信仰衰颓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马金莲笔下的舍木,不愿忍受贫瘠闭塞的乡村生活,不愿听命或念经或读书或务农的生活安排,瞒着老父“从穷山恶水的地方逃出去”南下打工。在深圳这个“奢华富裕”光怪陆离的城市里,“他把自己弄丢了”,就像“是一滴水,掉进这个城市就被淹没了”[4]。卖血攒钱的日子最终击垮了舍木的健康,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黑心蓝肺》中的少年,原本过着平静温馨的生活,不想富家子弟的骄纵妄为破坏了这一切,父亲为此奄奄一息,母亲含冤奔走求告无门。冰冷的现实境遇将希望一点一点被碾碎,最终伴随着“我想看看你的心是不是黑色的”愤怒呼喊,少年走上手刃仇人以暴制暴的复仇之路。消费主义浪潮中社会道德失范、传统信仰衰颓带给少年尖锐的成长体验。
这些奔走在世俗大潮中的少年们,与传统的乡土、信仰越来越远,精神悬浮,青春破碎,在物欲、权益、不公、交换的纠缠中越陷越深,活在当下活在现实中日益成为他们的人生轴心。
从宏志的彷徨到马力的追问、舍木的抉择,回族少年的精神之旅充盈着成长的现代性,在与外在影响相对抗较量的过程中,他们或回归于某种传统信念、或迈入新的被感召的轨道,于此个人叙事与民族叙事相互交织,回族社会在20世纪现代转型重要节点上平衡自我、民族、国家的多重召唤,重构现代意识的复杂精神裂变与重构得以动态性具象呈现。
三、回族少年形象的价值反思
少年是孕育于回族生活深处、浸润着该民族独特文化气息和原初生活印迹的一个艺术典型,具有重要审美价值。
它自20世纪初期回族现代小说兴起之时孕育,从最初的横截面式的简笔勾勒到以短篇小说为载体的多维度细致摹绘,审美意蕴不断提升。例如同样是描写学龄少年的生活,早期报刊文学作品往往止于主人公对积贫积弱生活际遇的伤感直白的述说;而当代小说创作则尝试从客观自然生态、具体人文语境、个体经历际遇、心性气质等多种角度展开对人物精神世界的阐述。如古原的《白盖头》就细腻绘制了少年的生存氛围:空旷荒僻的乡野、捡拾草木的光阴、咩咩叫着的小羊、衰老贫弱的奶奶。这些共同传达出一个寂寞失语孤独无助的精神世界,它隐含的不仅是少年个体成长的痛楚,还有诸如生命、宇宙、孤独、无力等超越时空困扰人类的永恒精神命题。于此,为了缓冲叙事张力、抚慰少年心灵,作者精心设置了一个深具民族文化意蕴的、戴着白色盖头的老人,作为少年成长的精神范导者,引领他完成自我建构。小说中“戴着白色盖头的老人”成为一幅“赏心悦目”“洁净”“高贵”的画面,定格在少年视线中,消减着他的无助与孤寂。这种独特范导者(如清真寺、盖头、老人、牛、羊等)的设置,在其他少年形象塑造中也常见到,它们传达出创作者对民族文化的希望、憧憬、再造、想象,使得这一文学典型浸润着民族文化的诗性美,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创造。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形象的塑造仍有极大提升空间。目前尚未出现以此为核心、在主流视域内也生成广泛影响的作品。创作主体对该群体关注度的不足、短篇小说容量的有限等都亟待打破。事实上,作为行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未来回族人的代表,少年的精神世界尤为值得关注。他们面对的成长环境日益复杂,遭遇的精神纠葛与成长话题也更为多样,它可能表征在衣食住行和思维情感的方方面面,融个性、民族性、地域性乃至世界性等多种特质于一体,这些深层理性都有待于创作者深入体察与挖掘,为此这一形象也将有望在更深广的层面上产生价值。
童庆炳先生谈到当代文学价值建构时,主张既要重视“历史理性”,更要强调“人文关怀”[5]。就少年形象而言,它一定程度上浓缩着回族社会20世纪现代转型的精神缩影,其历史认知价值不容忽视。建国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必要的文化整合与思想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稳定团结的社会新格局的建构。在今天全球化的现代转型背景下,深入阐释和有效运用各民族适合时代、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进步文化资源,无疑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的世界竞争力。
[1]文.宏志[J].晨熹旬刊,1935,1(12-14):20-22.
[2]马湘.诱惑[J].成师月刊,1934,1(1):10-13.
[3]红霞.新路[N].月华周报,1948-08-01.
[4]马金莲.孔雀菜[J].回族文学,2011(6):4-15.
[5]童庆炳.现代诗学问题十讲[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148.
【责任编辑 王雅坤】
On the Teenagers Images in Hui Novels of the 20th Century
WANG Ji-xia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30, China)
Muslim teenagers images are the important literature typical examples which embody profound mark of history and original life experien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teenagers images from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New Age, New Century have been analyzed on their different growth encounters and spiritual aspirations, and the results have been found that they reflect the emotional density changes and corresponding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s and the ethnic cultural community, therefore they are the spirit microcosm of Muslim society transformation towards the modern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on the basis of introspection of its image value that its aesthetic innovation, cultural implication etc. need to be excavated and improved.
Hui teenagers imag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spirit evolution; value introspection
2015-04-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回族报刊文学价值研究:1906 ~1949》(13XZW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回族家族文学研究》(11CZW076) 作者简介:王继霞(1972-),女,内蒙古包头人,回族,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回族文化与文学。
I206
A
1005-6378(2015)05-0074-04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