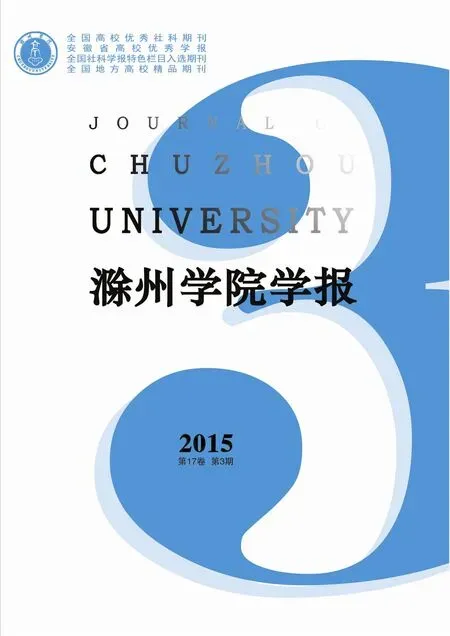论叶适的散文观
陈光锐
一、“文欲肆”的文学内涵
叶适曾经说过:“经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1]235“文欲肆”的“肆”可以诠释为汪洋恣肆、无拘无束之意,这种创作风范是有纵横家之风的,但是叶适与战国纵横家毕竟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汲取的是战国策士行文的雄肆辨丽,坚守的却是封建士大夫的忠君爱国的政治操守,他在为李焘所作的《巽岩集序》中写道:
自有文字以来,名公数十,大抵以笔势纵放、凌厉驰骋为极工,风霆怒而江河流,六骥调而八音和,春辉秋明而海澄岳静也。高者自能,余则勉而效之矣。虽然,此韩愈所谓下逮庄、骚,其上无是也。观公大篇详而正,短语简而法,初未尝藻黼琢镂,以媚俗为意;曾点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声色臭味自怡悦也。[1]210
我们可以说叶适对散文史上“以笔势纵放、凌厉驰骋为极工”的数十名公并非不予称赏,但是他认为这种文风只能是和《庄子》、《离骚》相提并论,还不可以说是达到了庄、骚以前的境界,有才华的高明作者能够不期然而至此种格调,而那些才不及此,而仅能勉强模仿的就更不值一提了。叶适对《庄子》、《离骚》的态度有相同之处,他说过“庄周者,不得志于当世而放意于狂言,湛浊一世而思以寄之,是以至此。其怨愤之切,所以异于屈原者鲜矣”[1]712,可见叶适从思想上将《庄子》和《离骚》归为一类,两者的风格都是以怨愤为主,怨愤之情发为词章,势必难有平和之调,叶适认为这不能算作文章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与《尚书》还隔着一层,至于那些强为模拟的更是“以媚俗为意”。叶适的观点明显是以理学价值为尺度的判断标准,实际上庄子和屈原的怨愤是遭受不公平对待时必然会产生的情绪、情感,而《庄子》和《离骚》正是此种情感宣泄极具感染力的文学表达,叶适对此不是不了解,他说《庄子》在当时和后世都不乏“悦之者”,而喜欢它的原因之一就是“好文者资其辞”。[1]712他承认了《庄子》和《离骚》的文词的艺术魅力,他只是不认同《庄子》和《离骚》用怨愤之辞表达发自心灵的怒吼。他真正心仪的是“曾点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声色臭味自怡悦也”的文章格调。他的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试图用儒家温柔敦厚的文艺思想作为感化庶民的有效手段,认为一切的不和谐、不公平都可以用礼乐教化来安抚、熨平,不希望用战鼓和烈酒来宣泄,所以他欣赏的“详而正,简而法”的文章。其二,出于强调文章的教化功用,叶适反对“以声色臭味自怡悦”的创作动因,过分突出文章社会伦理责任,弱化文学抒情的个性化、私人化,这样一来,醇酒、妇人、隐衷、私情便都成为写作文章的禁忌。他的弟子吴子良就说过:“自古文字如韩、欧、苏,犹间有无益之言,如说酒、说妇人,或谐谑之类。惟水心先生篇篇法言,句句庄重”[2]560。
至此,我们认为叶适“文欲肆”的 “肆”不能理解为像战国纵横之士为了博取名利而准的无一、惟利是求的任意发挥,也不是对不公平社会秩序的直露无隐的批判,也不能理解为对放肆、无拘束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记述,这里的“肆”大概只能理解为行文表达的顺畅、全面、充分,而不是思想、内容的放肆不羁。由此可见叶适文学视野的宽度是有限的,他对前代和当时文人的散文批评中无不带着这样的烙印。
二、对宋代散文议论化倾向的肯定
“肆”的风格特征主要与议论文体相适应,叶适重议论、好议论,这不是他一人的偏爱,是整个宋代的时尚使然,叶适则继承北宋古文经世致用的风气,将历史得失与本朝时事紧密结合,自成一家。所以,叶适所谓“文欲肆”主要是针对议论文体而言,而他对前代和有宋一代的散文,最为关注的是议论文章,他认为议论是古已有之的散文表达方法:
叙诸论,舜、禹、皋、陶辨析名理,伊、傅、周、召继之,《典》、《诰》所载,论事之始也,至孔、孟折衷大义,无遗憾矣。春秋时,管仲、晏子、子产、叔向、左氏善为论,汉人贾谊、司马迁、刘向、杨雄、班固善为论,后千余年,无有及者,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起,不能仿佛也。盖道无偏倚,惟精卓简至者独造;词必枝叶,非衍畅条达者难工;此后世所以不逮古人也。
独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千百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来,虽理有未精,而词之所至者莫或过焉,盖古今议论之杰也。[3]744
叶适指出,论事之文肇始于《尚书》中的《典》《诰》,这是议论文章的最早传统。孔子和孟子的议论风旨已经达到了无遗憾的高度,而议论散文发展的最高峰似乎是在两汉时期,叶适曾经指摘过《史记》和《汉书》的史学价值,但是他也感受到《史记》“辨丽奇伟”的艺术特征,其中的“辨”当就是指议论而言,叶适认为后世议论文不能企及两汉,更遑论两汉以前。叶适推崇的议论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有何特点呢?即“盖道无偏倚,惟精卓简至者独造;词必枝叶,非衍畅条达者难工”,首先议论必须合“道”,必须能够精卓简至者方能到达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这是要求议论内容的正当不颇;其次,议论文章还必须讲求词章安排,所谓“词必枝叶”,是说必须在合“道”或者说合乎义理的前提下,充分拓开思路,运用逻辑推演,调动语词意象,合理安排条理,即“非衍畅条达者难工”。这是要求论说者能够对一个问题穷尽其理,并且论说畅达有致,不留余地。在叶适看来,北宋古文运动的大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距离这样的要求尚有距离,能够做到的唯有苏轼一人而已。以理学家的标准衡量苏轼的“道”,当然不尽人意,所谓“理有未精”是也,但是苏轼纵横捭阖、架虚行危的论说艺术着实让叶适钦羡,他虽奉欧阳修“为本朝议论之宗”,但更称誉苏轼为“古今议论之杰”,把苏轼放在整个的散文史上去评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叶适重视文章的写作技巧和表达艺术,对议论文章“肆”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作者不仅合道,更要合乎艺术规律,才能创作出让“读者皆知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来”的议论文。
“肆”作为叶适对议论散文的艺术追求,其表现为文气流畅,辨说详博,这是宋学议论精神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在论说文体创作中的展现,而且此种议论之风还超出议论文体的范畴,影响到其他原本不主议论的文体之中,比如本以叙事为要的记体散文,叶适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流变,并且认为这是宋人对散文文体的创变之举:
韩愈以来,相承以碑志序记为文章家大典册,而记,虽愈及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变其态,如《吉州学》、《丰乐亭》、《拟岘台》、《道州山亭》、《信州兴造》、《桂州新城》,后鲜过之矣。若《超然台》、《放鹤亭》《筼筜偃竹》、《石钟山》,奔放四出,其锋不可挡,又关纽绳约之不能齐,而欧、曾不逮也。[3]733
叶适认为欧、曾、王、苏尽变韩、柳记体散文的常态,是说宋代文人破体为文,在叙事之文中多发议论,记体散文的议论化是宋人重议论时代风尚浸染的自然结果。在叶适看来,韩愈、柳宗元的记体文从题材到气度都未免显得过于窘涩,他认为记体文本来也可以像议论文那样大开大合,挥洒自如,像苏轼的记体文那样“奔放四出,其锋不可当,又关纽绳约之不能齐”,这与议论文追求“肆”的艺术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上文提到的欧阳修的《丰乐亭记》,本来是一篇平常的亭台记游之文,但是欧阳修却能“作记游文,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阔大”。[4]243再如苏轼《超然台记》,文首即以大段议论开篇,纵论忧乐、福祸之辨,于筑台始末反而轻描淡写。宋代作家突破了韩愈、柳宗元创立的叙事为主的记体文的体裁束缚,将议论合理有机地穿插于叙事之中,有时甚至喧宾夺主,主要以议论行文。
众所周知,两汉以后,唐宋散文可谓双峰并峙,但是在叶适的心目中,宋代散文还是高出唐文一筹。他没有否认韩愈、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领袖的开创之功。认同古文由韩愈复振的说法,还说过“后世惟一韩愈号能追三代之文,其词或仿佛似之”[3]79的话,虽然对唐代古文运动的业绩也能够给予冷静、客观的估断,但是他更主张宋朝散文克服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弊端,对元祐诸子尤其赞叹有加,其《播芳集序》云:
近世文学视古为盛,而议论于今犹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价,岂曰惧天下之议而使之无传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备载而无遗,则泛然而无统;若曰各因其人而为之去取,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尤不可以列论。于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择其意趣之高远,词藻之佳丽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广其传,盖使天下后世,皆得以玩赏而不容瑕疵云。[1]277
序文开头一段议论是这样说的:“昔人谓‘苏明允不工于诗,欧阳永叔不工于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句,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此数公者,皆以文字显名于世,而人犹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难也。夫作文之难,固本于人才之不能纯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不能去取抉择,兼收备载,所以致议者之纷纷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长,则数公之文当不容议矣。”由此可知,叶适《播芳集》所选均为北宋以来散文名家之作,而之所以编选此集,就是因为叶适认为“近世文学视古为盛,而议论于今犹未平”,这里既有对本朝文章成就和价值的自信,也对一些尊古陋今的文学观表示了不满。此处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叶适遴选散文篇章的标准:“择其意趣之高远,词藻之佳丽者而集之”,意趣高远指思想内容,词藻之佳丽则是专指艺术手法,明确表示讲求文章词藻的“佳丽”,这是叶适对散文文学性的公开认可和追求,在理学文艺观主导的南宋时期尤值得赞赏。而且其编选目的也耐人寻味:“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广其传,盖使天下后世,皆得以玩赏而不容瑕疵云。”他希望借此集扩大北宋散文的文学影响,流传于天下后世,他还认为这样意趣高远、词藻佳丽的文学散文应该成为人们“赏玩”的佳作,“赏玩”一词强调的似乎不再是以文传道,而是承认了文学本身就应该具备的愉悦功能。
三、对宋四六文的评价
宋代四六,渊源于南北朝时期的骈文,经历唐、五代,其好典故、重骈俪的体制特点没有大的变化,宋初的杨亿、刘筠等人祖述李商隐骈文的精工华美,文如其诗,掀起又一波骈文创作的高潮。古文运动的先驱石介在《怪说》一文蔑称其文:“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5]290,欧阳修和三苏虽然以倡导散体古文为主,但是他们对骈文态度不像石介这样偏激,而是尝试运古文之法于骈文创作之中,并且取得了成功,形成一种融合骈散的新体骈文,这就是宋四六。
叶适对宋四六对前代骈文的承续和演变过程有过比较准确的记述,他说:“徐陵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传写成诵,被之华夷,家藏其本,遂为南北所宗,陆机任昉不能代也。自唐及本朝庆历以前,皆用其体,变灭不尽者,犹为四六,朝廷制命既遵行之,不复可改矣。”[3]488所说庆历之前,即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尚未兴起之时,叶适还揭示了四六文在宋代与古文并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廷制命遵行之”,北宋王安石科举罢词赋,后来朝廷以为朝廷官事文书还是以四六行文为宜,于是特设词科,专试四六。《文献通考·卷三十三·选举考六》:“三省言唐世随事设科,其名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诸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阙,……(绍圣)二年诏立宏词科,……所试者章表、露布、檄书用四六。”[6]315词科试四六应用之文,因而应举士子多用力摩习,叶适以为词科试四六是科举的弊端之一,其《外稿·宏词》篇云:
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1]803
作为对科举利弊的探讨,叶适的观点自有道理,尤其当四六风行成为一种科场风气,流于模拟因袭,借以博取高官美仕并进而形成一种华而不实的词科习气的时候。但是四六文本身的美学价值也是不容视而不见的,特别是在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大家对之进行了散文化的改造之后,四六文的表现力得到强化,用典不再追求“巧密”,语言趋向通顺自然。宋人自己已经认识到四六文创作与古文之间有消息相通的一面,叶适批评四六为无用之文,不过他在现实的生活中并非不作四六文,他对欧阳修等古文大家运散入骈的创新之举称许有加,并且主动学习,其四六风格绝似欧阳修,《荆溪林下偶谈》记云:“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水心与筼窗论四六,筼窗云:‘欧做得五六分,苏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欧更与饶一两分可也。’水心见筼窗四六数篇,如《代谢希孟上钱相》之类。深叹赏之”[2]555,这里显然是将欧阳修的四六文成就列为本朝第一,苏轼、王安石紧随其后,这也是承认了古文和四六之间并非如石介那样势同水火,因为科举时代的文人应进士、制举、词科等,都难免要研习四六,欧、苏、王等人自难免俗,只是此数人能够融通骈散,创为新体。除吴子良的赞语而外,叶适的四六文的成就还受到黄震的夸奖,他在评价叶适主要以四六行文的“表”“启”文时说道:“文平意顺,水心大手笔也。四六语如此,近世雕镂自以为工者何如也?”[2]85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水心集提要》评价说:“适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7]2462作为南宋中后期的散文大家,其理学家的道德操守和政治抱负影响他对散文文学性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判断,但是他重文、擅文,主动继承了宋代散文经世致用的传统,议论风发,这是与一般的理学家轻文、弃文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1] 叶适著,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清)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3.
[5]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90.
[6]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5.
[7]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2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