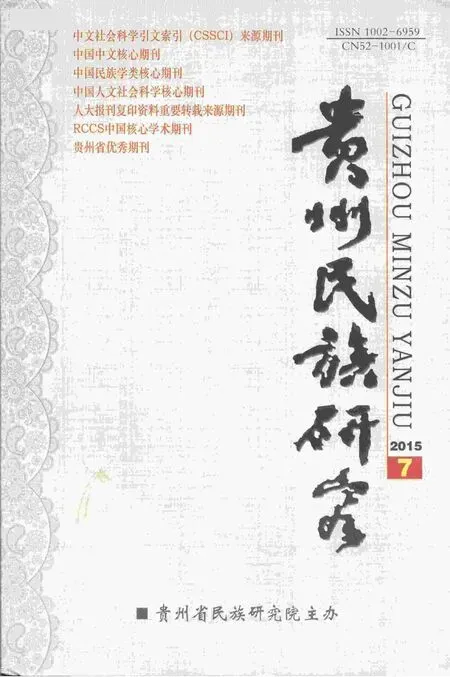试论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
李 晶
(西安文理学院 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多民族的历史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尽管如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却始终难以获得应有的地位,始终处于中国文学的边缘。特别是中国进入近现代历史之后,中国文学领域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甚至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由此,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遭受三重话语霸权的排挤表现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突出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理性的认识和思维,同时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多民族文学研究,对话语霸权现象展开强烈批判,强调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不同民族文化要互相影响、互相融合,这样才能使中国民族文学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而我们的民族文学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一、少数民族文学分析
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悠久,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神话传说、民俗故事、叙事诗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并没有书面形式,而是口头流传,但这并不能夺去少数民族文学的璀璨光芒。不少作品还被翻译成汉文字出现在中国经典的文学作品之中。比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当时各民族流传诗歌的作品。虽然当时的汉民族尚未形成,并没有少数民族的概念。但是从当今的视角来看,很多少数民族的先祖正是当时分布各地的居民。比如湖南湘西土家族在婚礼之前的告祖仪式上,还要演奏诗经音乐,所唱歌词恰恰是《诗经》中的《关雎》、《桃夭》之章,而且歌词与《诗经》相同,这种遗风说明《诗经》与古代少数民族的渊源关系。
虽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是相对于汉民族而言在影响力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就是文学的霸语权。因为相比汉民族,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存在差距,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学等社会的各个方面长期以来都是汉民族占据主导地位。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集中,我们很少发现少数民族的作品,这是因为历代很少有学者对于少数民族的作品进行研究或者收录自己编纂的作品集中,这也恰恰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多重话语霸权下影响力不足的最有力说明。[1]
二、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
西方话语霸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因为超过一半的文学史都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上。[2]当代文学这种特定时期下的言说方式原本反映现当代文学生存经验,同时还应该体现现当代生存背景的独特性,可是现当代文学处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压迫之下,在反映本民族生存经验的过程中表现得不够出色,出现现当代文学的失语现象。[3]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逐渐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评价标准各不相同,同时还立足于中国文人的生存经验,逐渐发展成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阐释体系。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经验恰恰可以通过这种阐释体系体现出来,如《文心雕龙》、《诗品》、《文赋》等都能够出色地承担起反映中华民族独特生存经验的重任。可是,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文化便陷入了西方文化强势压迫的不利条件,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文学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出现了失语现象,而它阐述生存经验的功能也很快消失,事实上,这种现象非常不正常。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逐渐向着西方的方向发展,文学生存机制本身具有的连续性不能采取强制手段人为隔断,否则只能使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忠实追随者,失去言说本民族独特生存经验的功能。处于这样一种不利条件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价体系必然不能很好地传承中国传统文论的独特特征,而中国文论也就难以依照自己的标准对世界文论体系做出评判。[4]
现当代中国文学体系处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霸权之下,属于中国文学体系的少数民族文学自然也难逃西方话语霸权的压迫,这主要通过处于西方文学评价体系下的少数民族文学评价一直努力为自己争取合法化身份体现出来。少数民族文学处于被压迫的形势下,已经濒临生存的边缘,但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学有自身的独特生存机制,因而也应该具有自身独特的评价标准。可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直没有形成这种独特性,而是紧随西方文学之后,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史就是这一现象的突出表现,如《白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史》、《藏族文学史简编》、《少数民族文学》等,以上提到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无论是在评价标准上,还是在结构体系上都体现了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追随,而且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史无不采用了西方话语来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反映出西方话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巨大冲击,而少数民族文学也在与西方话语的碰撞中失去自己的独特性。
三、汉语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不但面临西方话语压迫,而且也面临着汉语话语霸权的巨大冲击,现代学者王国维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中国史诗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他同时也认为,中国尽管是一个古文学大国,可是却没有一部史诗可以与西方史诗相媲美,胡适也持类似观点。[5]可是,少数民族地区却不乏优秀的史诗,即使我们依据西方史诗标准进行衡量,它们也仍然毫无疑问被划入史诗的范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乌古斯传》、《格萨尔王传》,此外还有《江格尔》等。不管是《格萨尔王传》还是《乌古斯传》都应该划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行列,可是中国文学史却并没有为这些作品提供应有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中国不存在史诗的结论,这也是汉语话语霸权的最根本体现。
另外,处于汉文化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文献存在非常明显的失落感,而语言失落是其最突出的表现。[6]中华民族是由多种少数民族组合在一起的大家庭,民族之间通过各自的语言进行区别,因此中华民族的语言应该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应该采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并且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所以对少数民族文学展开研究必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切入,而且语言也必定会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项必备条件。如果将某一种少数民族文化转换成另一种民族文化,需要用到翻译,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敕勒歌》就是一首鲜卑族民族诗歌,后才被翻译成汉族诗歌,虽然我们所见到的《敕勒歌》新形式仍然带有少数民族文化色彩,比如诗句与诗句之间长短不齐,可是鲜卑语已经消失,这首诗歌真实的原始风貌是怎样的,我们并不能深入考究。由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汉族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经常会出现互相翻译的情况,因此不同文化的碰撞应该首先表现为语言的碰撞或者思维的碰撞。由此,语言问题表现出一种新的含义,也就是汉族语言的话语霸权地位。[7]
正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存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没能保存下来,这不但造成了如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而且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史被汉族文学史一统天下,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中国的文学史观念来源于西方,它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地交流与碰撞中出现的。重新书写文学史的过程实质是重新整合本民族文学史的过程,它不仅需要重新对传统文学进行归纳和整理,也需要当今研究者针对传统文学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也恰恰因为如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才会出现这种非正常化状态,使如今的文学史研究变得残缺不全。虽然上文也列举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却并不能同汉族文学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应得的地位,似乎中华民族文学史自诞生的第一天就就没有为少数民族文学准备位置。因为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所以很多文学研究者总是习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汉族文学上,导致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很少。
四、精英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必然会出现碰撞、融合,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8],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结果必须依靠精英知识分子才能向外传播,而大部分的精英知识分子都来自汉族。虽然也存在一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比如人民艺术家——老舍,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精英知识分子基本都已经被汉化,也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被汉族文化所同化,无论是西方话语霸权还是汉语话语霸权,都必须通过精英知识分子来实现。由于精英话语霸权的存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长期处于不入流地位,它直接导致了文学研究者忽视少数民族文学的现象出现,使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直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因而,少数民族作品也很少得以向外传播和发展,在国外的影响力远远低于汉族文学。
精英意识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夷夏之辨;二是雅俗之分。纵观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尽管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夷夏有别”以及“夷夏一家”的说法,但不管这些观念在什么时间流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种歧视观念。通常情况下,“夷夏一家”观念流行的时期恰恰是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权时期,而这种观点反映了少数民族希望取得合法地位的想法。可是,汉族却流行着“五胡乱华”的错误观念,所以“夷夏有别”观念是汉族文化话语霸权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压制的反映。事实上,这一观念反映出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汉族政权认为自己建立的政权才是正统的,而少数民族尚未开化,野蛮、落后,因此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政权不具备合法性。雅俗之分的观点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雅俗之分就是对“夷夏之分”的反映,“夷”就是“俗”,“夏”就是“雅”,“雅”是历代文人一直追求的境界。无论是“夷夏之辨”还是“雅俗之分”,共同束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使其长期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而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优秀代表,如《格萨尔王传》、《乌古斯传》等一直处于汉族文学的压迫之下。关于这一点,现代文学研究中尤为突出,新文学自出现的第一天起就被赋予了强烈的精英意识,而中国的新文学更是一直没有停止过雅俗之争。
新文学出现之后,首先要为自己争取一个合法的地位,而一直被人们看做俗文学代表的“新鸳鸯蝴蝶派”便成为了第一个目标。如果以市民的角度来评价“新鸳鸯蝴蝶派”,它是一种真实的市民生活反映,能够体现现代市民生活的情趣,因而能够被广大市民所认可,与市民审美情趣相符合,并且中国新文学在成立之初也引入了西方市民文学,周作人、林语堂都曾经借鉴过。新文学需要将一切休闲的文学、带有封建性的文学列入打击的范围,所以“新鸳鸯蝴蝶派”被强行划入非法的范围,可是“新鸳鸯蝴蝶派”在市民中间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仍然受到广大市民的热捧。正是因为如此,王德威发表观点说,中国新文学从晚清时候起才开始具备现代性,而“新鸳鸯蝴蝶派”是俗文学开始的标志。无论中国新文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具有现代性,“新鸳鸯蝴蝶派”一直处于精英知识分子的操控之下是毫无疑问的,而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和发展命运更是不言而喻。
另外,少数民族文学处于精英话语霸权之下还通过旁观者猎奇的眼光反映出来,这种旁观者的眼光非但不能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甚至有可能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造成偏差。[9]汉族通常以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待少数民族,汉族人民对“敖包相会”的理解就非常典型。通常,提到敖包,汉人更容易想到美丽的蒙古姑娘同自己心爱的人相会的场景,很自然以为敖包是青年男女约会的地方,这其实是对敖包的一种错误理解。[10]在古代,敖包是一种圆形建筑物,是由石块、泥土以及柳条等堆积而成,一般建在明显的地方,如路口、湖畔、山顶等,主要用来供奉神灵,逐渐才发展成为人们集会放松的地方。所以,汉人们想当然以为敖包是青年男女约会的场所是不正确的,这种错误认识直接反映出汉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观赏的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带着一种民族偏见去看待少数民族文学,这直接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处于被精英知识分子控制的话语霸权之下,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
结语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每一次民族融合之后都会随后出现文学的繁荣,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融合,文学自觉性产生,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新的文体,而那时候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盛唐时期也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不仅政治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而且文学也欣欣向荣,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巅峰时期。另外,汉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如此繁荣的景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汉族文学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先进成分,如元代戏曲非常繁荣就能证明这一点。所以说,要想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透彻的研究并推广,一方面要遏制西方和汉民族文化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还要破除类似的精英文化霸权话语。繁荣的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一种补充,既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又能加快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脚步,无论从理论方面来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它对于中国文学话语的重建都意义非凡。
[1]姚新勇.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的反思[J].民族文学研究,2004,(02):20-21
[2]梁庭望.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2):28-29
[3]李晓峰.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J].民族文学研究,2007,(02):15-16
[4]徐其超.文学史观与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地位的缺失和构建[J].民族文学研究,2009,(05):44-45.
[5]席 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述”问题[J].民族文学研究,2011,(04):31-32.
[6]李 菲.民族文学与民族志——文学人类学批评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J].民族文学研究,2009,(08):67-68.
[7]李晓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J].民族文学研究,2003,(02):35-36.
[8]杨建军,陈 芬.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9):19-20.
[9]罗庆春,刘兴禄.“文化混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构成论[J].民族文学研究,2006,(02):45-46.
[10]曹顺庆.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2005,(03):8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