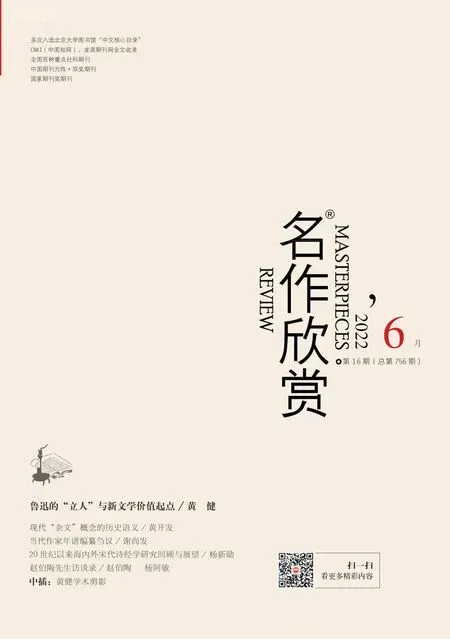喧嚣和沉静的冰火两重天
——论新世纪中国公共领域与文学公共性
北京 江涛
喧嚣和沉静的冰火两重天
——论新世纪中国公共领域与文学公共性
北京 江涛
中国当下的公共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公共领域的异军突起。但网络公共领域由于深受着消费主义思潮的引诱与侵蚀,发展并不完善。此外,式微的当下文学以书写日常、关注日常的姿态也参与了对公共领域的渗透。面对沉静的文学公共性,我们应保证文学的多元性,在文学与网络的双重发展中,尽可能地给予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努力重建符合这个时代的新的公共关怀。
公共领域 文学公共性 网络公共性
自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问世以来,“公共领域”就成了学术界炙手可热的问题,大量的专家学者将哈氏的理论通过“拿来主义”横向移植到中国本土,而笔者认为,如果将哈氏的理论用来丈量新世纪以后的中国现实,则会有失语的可能性。哈贝马斯时代,他并没有预见一种叫作“网络媒介”的事物会在若干年以后的中国乃至世界成为了人类学习、生活和交往的重要工具,他所预料的结构转型也不过是终止于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媒介时代,而在新世纪以后的中国乃至全球,公共领域的结构再次发生转型。那么“公共领域”的本体论则难免出现失语,同时,文学公共领域也将随之发生质变,它从公共领域的“前身”和“雏形”,与其分道扬镳,被取代,甚至消失,文学进入了私人场域。那么问题来了:文学的公共性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它是否存在重建的可能?这值得深究。
公共领域的新天地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①如果将公共领域的概念简单化,可以理解为公共领域是一个所有人平等沟通和交往,提出公共意见的场域。在西方,公共领域出现过几次结构转型,从古希腊公共领域到中世纪代表型公共领域再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以及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文化消费的公共领域(伪公共领域),它的内在机制发生了数次改朝换代。只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代,是以文学公共领域为“前身”和“雏形”的,所以从它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以“国家”和“社会”分离为基础而不全是依托文学公共领域的繁荣抑或消失而说明。
哈贝马斯说:“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②他的理由有如下几点:对文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禁戒,批判转移为消费;社交讨论让位于无须承担责任的“集体活动”,而“集体活动”因没有公众私人性而无法形成公众;以广播、电影和电视为主的大众媒体是一种被扭曲的交往,它们日趋消弭读者和出版物之间的必要距离,而这个必要距离正是实现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所以20世纪当大众文化盛行之际,文化批判便成了文化消费,媒介成为了单向度的灌输,无法形成平等的交往,于是哈贝马斯断定,公共领域被取而代之。
但哈贝马斯在晚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再版序言时写道:“当时,我过分消极地批判了大众的抵制能力和判断潜能,这一多元大众的文化习惯从其阶级局限性摆脱出来,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因而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文化和政治之间新的紧密关系’同样也模糊不清,它不仅吸收了娱乐成分,而且,判断标准本身也随之改变了。”③从哈贝马斯的这段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政治公众到私人公众、文化批判到文化消费这一发展脉络的反省式思考,毕竟他曾经的判断有简单化的倾向。我想,哈贝马斯的这段话更适用于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公共领域。
首先从公共领域的本体论来看,赵勇认为,应把公共领域看作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中间地带,“这一地带由私人领域生发而成,又可通过公共舆论抵达公共权力领域”④。所以公共领域的最大功能便是批判。哈贝马斯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区分为“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前者的文化机制主要有沙龙、咖啡馆、读书会、博物馆以及报刊、书店等,讨论的是文学艺术,“围绕着文学和艺术作品所展开的批评很快就扩大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⑤,于是政治公共领域便形成,二者共同组成了公共领域。新世纪以后,公共领域的内在结构再次转型,其机制不再依托文学公共领域,而是以网络媒介为平台。
网络媒介具有前所未有异常强大的包容性,它归根结底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公共空间,它的主体除了是普通公众之外,还可能混合着权力阶层,以及他们所雇佣的“水军”。他们的现实身份是隐藏的,他们的讨论更像是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他们所针对的对象,可以是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历史知识,但更多的是大众文化、热点事件、政治经济、生活现状等,是对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所涉及的对象的整体性容纳。当然,除了继承公共领域的批判性特点之外,也融合了伪公共领域的文化消费特点和娱乐功能。因此,它所抵达的也就会有两个领域,最常见的便是私人领域。因为网络公共领域除了是平等交往的平台之外也是文化传播的平台,它呈现了双重特性,以下是它与19世纪以前西方公共领域特性的对比: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文学艺术→书刊→私人领域(阅读)→公共领域
网络公共领域:文学艺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浏览)→公共领域
作为前者文化机制的咖啡馆、沙龙和宴会等不具备承载作品发行、传播的功能,而网络公共领域本身就具备了这一功能,作者可以通过把自己的文艺作品上传到网络上从而让更多的受众浏览阅读,这是它的超强开放功能之一。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也便具备了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的特性。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经常是在同一社会环境中展开,且无须通过讨论继续下去,如大家一起看电影、听广播和看电视等,它消除了私人领域的空间,但网络却能保留这一空间,人们几乎都是在与外界隔离的家庭私人领域的空间中进行网上阅读。但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民众只是利用网络这一公共领域进行文化的接收活动,也就是只完成了文学艺术到公共领域再到私人领域的步骤,并没有再回到公共领域上发表自己的私人意见,更不可能参与讨论和形成公共意见。他们把网络公共领域当成了曾经的书本和报纸,后来的电视或电影,只是单纯地利用了它的载体功能,结果也便只能最终抵达私人领域而不能重返公共领域,那么它也便失去了公共领域的交往意义而成为了酷似于大众媒体的单向度灌输。
其次,网络公共领域也能如文学公共领域一样抵达政治公共领域且更直接和全面,从而形成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分庭抗礼的局面。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信息。在过去,信息总是受制于权力领域的垄断而带有等级色彩;而如今,正如梅罗维茨所说的:“群体身份、社会化的程度和等级制度的级别之间的传统区别是建立在印刷媒介所形成的孤立场景基础之上的,从这种程度上看,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会模糊这些区别。”⑥人人都有着话语权,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大众,大家各抒己见,发表着各自的看法,形成了一种公众舆论。这种公众舆论有批判,也有面对批判的再批判,并且还引发了权力机构对于公众舆论的回应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便显示了网络公共领域更为强大的实力与力量。
所以在新世纪以后的中国,网络公共领域俨然代替了文学公共领域,成为了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和“雏形”,但它本身却又要比文学公共领域更为复杂和多变。
文学公共领域的新特征
前文说过,网络公共领域包含了文学公共领域的特性。当文学公共领域从传统的研讨会、课堂、文学沙龙等移植到互联网上时,便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首先是参与讨论的主体身份变得更庞杂。除了许多作家、评论家、专业读者会在网络上开通博客或者接受网媒的访问,发表自己对文学较专业的看法和见解之外,也会有一些业余读者、媒体评论员在网上发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精英文学的网络讨论稍显冷淡,通俗文学方面,参与互联网讨论的人却济济一堂,撑起了文学公共领域的喧嚣之势。但这种看似喧嚣的讨论却只是一种被阉割的文学批评,它缺少的是一种真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批判意识,更多的还是一种狂欢式的娱乐化表现。
其次,网民们对文学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对文学事件隔岸观火的心态。如当年的顾彬事件,“民心来得如此快如此汹涌。还没等专家们作家们做出反应,网上已经是一片拥护之声。《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查了一下百度,发现相关链接达到了二十一万个,这个反响是太大了”⑦。大量的网民纷纷不断地发表着惊世之语,批评着脆弱无助的当代文学。而这种批判不是出于理性,更多的是一种跟风和瞎起哄。“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扩大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范围,因为它使象征形式能传输到时间与空间上分散的、广大的潜在受众”⑧,文学公共领域受网络开放式的特性影响,又缺乏必要的价值导向和控制,总有滑向媚俗化的倾向。如当年的“唱胜党”与“唱衰党”的争论,可以对照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双方从一开始的理性争辩渐渐走向了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只是后者的影响范围始终局限在学术界,而前者则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娱乐功能被更多圈外人士关注和调侃。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公共领域的精英意识退化,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与侵蚀,文学已经出现了日薄西山的倾向。当它转移到网络平台后,似乎瞬间被点燃,呈现出喧嚣之势,但那不过是一种娱乐式的“虚胖”,掩盖不住“犬儒主义式批评”⑨的内在骨髓。
沉静的文学公共性
网络公共领域的喧嚣并不能复现文学公共性的繁荣,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极有可能加速导致文学公共性的彻底沉静。自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长达数十载的契约解约以来,被政治意识形态和商业意识形态放逐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只能回到文学艺术的象牙塔中舔舐自己没落的心灵,文学便彻底边缘化,只是,重建文学公共性的耳语却一直生生不息。
赵勇对于文学公共性有过这样的定义:“所谓的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⑩他认为文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喧嚣和骚动后,90年代以来文学趋于平静,作家大多远离现实,关注私人生活。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文学缺少了“现实干预性和批判性,走向去政治化”,文学批判被文学消费取缔。只是笔者有一个疑问:文学除了批判就一定走向消费吗?文学的去政治化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诉求?
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政治性。汪晖在他的经典著作《去政治化的政治》中说:“‘去政治化’是一种特定形式,它没有也不可能取消政治关系,而是用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表达和建构特定支配的方式。”⑪中国当代文学的“去政治化”不光是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共振,也跟自身的历史语境有关。文学的“向内转”从20世纪80年代就有征兆。曾经的中国存在一种强硬的“政治化的政治”,那么摆脱这种“政治”的“去政治化”便势在必行。所以直至今日,有很大一部分文学从宏大叙事中逃离,它们关注日常,走进了私人的象牙塔里,甚至摆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姿态,这种“去”同样是一种另类的政治诉求。
那么这种日常的、私人的、内在的政治诉求又如何能成为公共性进入公共领域呢?南帆以阿伦特的理论为依据做出了回答:“文学不是日常生活的单纯记录,文学是探索、分析、搜集和汇聚日常生活之中足以酿成重大历史事变的能量;文学所拥有的心理动员进而使这些能量扩散至公共领域。”⑫因此,南帆认为文学书写日常是积蓄变革能量的必经之路,同样能抵达公共领域。
当文学的现实批判转向日常认同时,就必须要像贴标签一样贴上消费品的身份证明吗?陈世骧早在6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沈从文认为他的文章只是为了吟唱和抒情而存在,莫不是沈从文的文学也成了文学消费品?文学本身就是艺术的门类,天生就与审美有不解之缘,《文心雕龙·明诗》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学对日常人生的感觉、体悟,能形成一种审美欢愉给人以心灵的净化和共鸣。这与消费主义关系不大,反而是与古典美学的隔空对接。
那么面对如此沉静的文学公共性,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还该提倡什么?阿伦特曾指出,“公共”指的是世界本身,“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⑬,文学的公共性也便是世界本身,是“无数的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所以批判世界或是认同世界,都是文学公共性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哲学认为“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强硬的政治化之后必然是去政治化的出现,就像利奥塔预言的那样,宏大叙事之后便是小叙事的登场,而我们应该保证的是文学的多元性,在以批判为主的时代就应该号召贴近生活、抒发人性的灵性文学;反之亦然,我们需要的不光是鲁迅、茅盾、老舍那种毒辣或是温情的批判与人道主义同情,同时也需要沈从文、周作人、废名的浪漫与闲适,我想只有他们的同时存在,才能满足这一时代的公共文学性的健全。
结语
回到中国当下的公共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公共领域的异军突起,它所造成的公共影响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同陈思和的“民间”一样,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公共领域。我们也应该保持理性的认识去看待它的发展,并尽可能地给予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努力重建符合这个时代的新的公共关怀。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阶段性成果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转引自汪晖、陈燕谷主编的《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版,第125页。
②③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第17页,第38页。
④⑩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和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⑥约比亚·美罗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⑦平心:《试探顾彬事件的几个“看点”》,德国之声中文网站,2006年12月24日。
⑧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⑨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⑪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0页。
⑫南帆:《文学公共性:抒情、小说、后现代》,《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
⑬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作 者: 江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