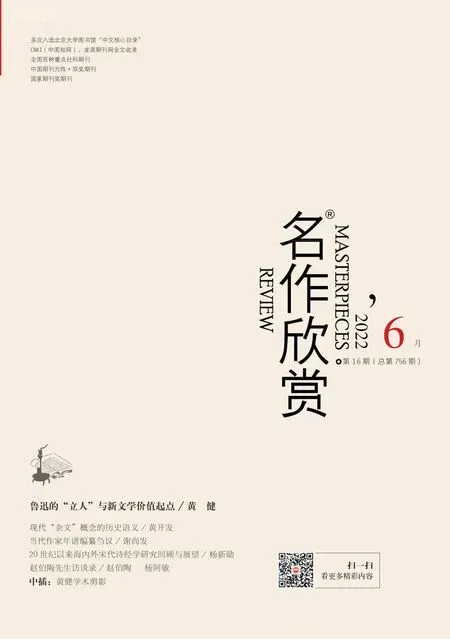简练、优雅与地方性
——论张庆国的小说语言
云南 周明全
简练、优雅与地方性
——论张庆国的小说语言
云南 周明全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作者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也是作品的内容,小说中涉及的生活事件,跟作家采用的语言形式同为一体,不可分割。在这种语言观的认识之下,作者对同乡作家张庆国的语言进行分析,指出张庆国的小说语言具有简练、优雅和地方性三方面特征。
张庆国 简练 优雅 地方性
区域文学·第十辑
张国庆是我们云南的作家,人老实,不张扬,创作三十余年,步步向上,发表了近四百万字作品。他的小说大部分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花城》等国内重要文学杂志,被选刊多次转载,还入选过年度选本和“中国小说排行榜”,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张庆国的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语言。当代绝大多数作家,不重视语言,放弃对语言的精致追求,使得小说越来越粗糙。当代文学整体来说对语言重视得不够。语言之于文学,不是外壳,而是灵魂。张庆国在为云南作家们讲课时,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说,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只为读者提供思想暗示,不提供实物。一匹马,画家的办法是画出来让人看见;音乐家的办法是让人听到马蹄声;作家的办法是用文字告诉读者有一匹马,读者看不到也听不见,只能根据语言文字的暗示,去想象一匹马。所以,作家的语言处理不好,写作就会失效。
早在2011年,著名批评家贺绍俊就撰文呼吁,当务之急是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的优雅语言。他指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正面对语言这道坎,迈过这道坎,也许就风光无限。在贺绍俊看来,文学语言不同于思想语言,不同于实用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文学语言是用来承载民族精神内涵和永恒精神价值的,因此,语言问题并不是一个形式问题,建立起优雅的文学语言,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得以发展和突破的关键,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关键。①
缺乏语言功夫,再好的主题、再深刻的思想也没有承载支架。严峻的事实是,语言的浅薄和粗俗化,已使近年的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变得平庸,很多作家直奔主题,文本干瘪无力。语言是小说存在的家园。汪曾祺作为当代较有影响的小说家,历来重视语言,小说成就颇高。他曾说:“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②
在我的视野中,老村、金宇澄、李洱、张庆国等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有自觉的语言意识,而且有相应的准备。我说的准备,是经年累月的对语言的琢磨提炼,也就是说,作家应该先找到适合自己表述的语言,再去找故事、人物。但现在的作家,大多数先从故事和人物入手,忽视了语言准备。语言过剩和语言紧缺并存,是当下中国文学的危机之一。
在一次访谈中,张庆国透露了自己对语言的长期准备过程,他说:“中学时我一度疯狂迷上遣词造句的研究,那时我做的最多的事是查词典,在家里找到一本‘破四旧’遗漏的老式‘四角号码’词典,里面的旧式词汇很多,我觉得太丰富了,太好了。所以我最初的语言训练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很早就开始了。”③作家老村的语言把握也颇为到位,他写作《骚土》前,就已经天天看《辞海》,搜罗陕西语系中的古字、古词。《骚土》使用《辞海》中的词汇也就百十来个,但这百十来个经历岁月淘洗的词,像盖木头房子使用的铆钉,使《骚土》站住了,具有了稳定性、经典性,继承了传统中国小说的精髓。
张庆国小说语言的第一个特征是简练,单刀直入,这是他多年训练和追求的结果。他在早期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于《花城》的中篇小说《巴町神歌》(1991年第5期),所用的语言是较为繁复的。语言由繁复转向简练,说明张庆国的文学观点发生了变化,从青年时期的先锋派学习,改变为另取一套的镇定自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庆国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正逢中国的先锋小说探索风起云涌。他的写作经历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风行同步,正如他在相关文章中自我介绍的那样,西方现代派文学为他所钟爱,从卡夫卡到马尔克斯他都很熟悉。但熟悉是一回事,真正运用是另一回事。张庆国在2009年发表于《山西文学》的一篇读外国小说的随笔中对自己的那段文学经历进行了检讨,认为早年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作家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只欣赏语言的壳,未能准确领会语言的魂。④
语言不只是形式,也是作品的内容,小说中涉及的生活事件,跟作家采用的语言形式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作家对人生有所理解,发现了主题,就会寻找相应的语言形式。早期张庆国的小说有先锋实验色彩,语言繁复,是因为他喜欢西方现代派小说新的语言表达形式,他用那种语言形式描述了人生的神秘,却不太明白外国作家为什么那样写,不清楚那种新锐语言后面的西方文化背景及其精神意义。他的语言繁复,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思想在迷茫地绕圈子。
这不只是张庆国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通病。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寻找新的出路,青年作家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花样翻新的技巧有所迷恋,剥了其语言的壳,穿到自己身上。他们只能这样做,但这样做是不得体的,语言不是作品的外衣,是重要内容。西方现代派文学选择的语言形式,出于他们自身的处境和由此产生的作品。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之后,面对“上帝已死”的孤独和恐慌,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巴尔扎克式的外部写实传统,无法解决西方人巨大的内心困扰,于是催生出他们的新思考及文学形式的现代性突破,并产生了相应的文学语言。
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以后大踏步前进,同样面临传统革命文学不再适应历史转变后的中国经验的困扰,但这个困扰跟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文化相去甚远。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物质困难、精神贫乏、思想空洞。思想空洞导致我们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也找不到解决自身问题的答案,因为西方作家的写作只能解释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借用他们的语言,为自己的作品暂时取暖。
正如张庆国后来著文所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外国有外国的问题,乌鸦解决乌鸦的麻烦,老鼠享受老鼠的欢乐。中国作家写爱情,也许为的是表达生的喜悦;外国作家写爱情,可能恰恰是解释死的无奈。”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作家,很难有这种认识深度,只为读到崭新的语言而惊喜,当他们用那种语言创作自己的中国生活小说时,难免徘徊迷茫。
后来,张庆国的小说语言倾向简练明确,直截了当,是因为对世界看得清楚了,心里有了底,就能找到恰如其分的语言来表达。当西方现代派文学成为常识,融会在中国作家的生活观察中,融会在作家的中国方式表达中时,张庆国也清楚地找到了自己想要描绘的人生,以及相应的语言方式。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写,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及其命运有明确认识,对安排出的相应情节心中有数,语言方式就很果断,直接挑明,一针见血。
张庆国的这个语言特色,最为鲜明地体现在其最新发表的小说《马厩之夜》(《人民文学》2014年第3期)中。这部中篇小说讲的是老故事,叙事方法却很新颖,人生认识独特而明确。小说中的桃花村,在日本人的威逼下,把村里的几个女孩送给日军做慰安妇,战后为隐瞒羞耻,引出了更大混乱。如此复杂的伦理故事,张庆国在小说开头,表达得简练有力:
我母亲六岁那年,被赵木匠从缅甸领回来。原来她有一个印度人的名字……她跟着赵木匠走进桃花村时,连中国话也不会说,对赵木匠要把自己养大做儿媳的事不懂,也没有兴趣搞懂,只想再活几年,活厌烦了就上吊,去找早就死去的印度父亲。
短短数十字,就把小说中的几个叙述者摆了出来,也把人物国籍与身份的混乱摆出来了,同时亮出其生死态度。多个叙述者,是因为主人公人生的紊乱和隐瞒;国籍和身份的混乱出于时代混乱,生死未知,来自于战争危险。这么简短的篇幅中信息容量很大,令人赞叹。
简练的语言容量最大,也最有力。金圣叹就曾感慨道:“不会用笔者,一笔只作一笔用,会用笔者,一笔作百十笔用。”⑥莫言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师,但他的小说语言是很不节制的,肆意汪洋,少了韵味,多了泥沙俱下的土味。张庆国不同,他的语言谨慎用心,有很多玄机。在他的中篇小说《钥匙的惊慌》(《十月》1995年第4期)中,迷茫时代中的恍惚人物李正,为家里准备做防盗笼的事,心乱如麻,无所适从。价格高了不行,便宜也不行;安装怕麻烦,不安装又恐慌。他最后决定做防盗笼,交付定金,制作人老田却失踪了,他受到了致命一击。这里,张庆国只用一个短句,就把李正的心态写了出来:“没有老田,小店已经在昆明城的早晨死去。”“早晨”充满希望,但“早晨”后面的“死”字,写尽了李正的万念俱灰。
语言的优雅,是张庆国小说的第二个特征。
这个特色,也许跟作者个人的出身有些联系。我和张庆国有个对话,他介绍说,自己出身书香世家,直到父亲那一代,家族也全部是大学生,他奶奶的女佣“文革”开始那年才被辞退。我知道他自小阅读《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著作,其小说语言,早在传统文化的感染中养出了优雅的风度。
张庆国的小说《黑暗的火车》(《十月》2000年第2期),就体现了语言优雅的特点。雾、火车的摇晃、目光的潮湿、夜色的疑惑、房间中的慌乱、床上的凹印等,众多俯拾即是的优美短句,使得《黑暗的火车》色香味俱全,醇厚,很有嚼头,层层推进,让火车驶入读者内心,回味无穷。
优雅来自恬淡,以及对事物细微的体察。在小说《如鬼》(《钟山》2011年第4期)中,张庆国写鸽子,表现出细微而深刻的洞察力。
那些神奇可爱的鸟,羽毛光滑,眼睛明亮,骄傲优雅而相亲相爱。公鸽向母鸽求爱,是那样彬彬有礼,不慌不忙。它绕着母鸽点头,一遍一遍地点,用力点,深深地点,乞求它赐给自己爱情。母鸽不同意,表情冷淡,它就再努力,咕咕咕地唱歌,我认为是唱歌。父亲说,不是唱歌,它是在念情诗。
张庆国的语言优雅,还来自于他对比喻的应用和掌控。在小说《桃花灿烂》(《人民文学》2003年第12期)中,张庆国将街上的乘客比喻成豆子,形象且特别有味。他写道:“散落在街上的乘客是大豆、小豆,虫吃过的豆子和金豆,开着出租车满城拣豆子。”小说《水镇蝴蝶飞舞》(《花城》1996年第2期),更能体现出这方面的特色。这部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写得仓皇迷离,纯净唯美。江边的小镇,神秘的纸花店,寂寞的招待所,黄昏中飞舞的金属蝴蝶,琴师与美女,医生和杀手,惟妙惟肖,读来恍然若梦。
在小说《如鬼》中,张庆国写道:“关于二叔的传说,像树上落下的鸟窝,干枯散乱,轻飘飘的一点重量也没有。”在小说《如风》(《芳草》2011年第1期)中,张庆国把警察陈刚比喻成猎狗,将马局长比喻成狡猾的野猪。明喻、暗喻、隐喻交叉,巧妙运用,有绅士品质,机智俏皮。
张庆国语言的机智俏皮,跟其他作家有明显区别。文学语言不是俏皮话,语言的力量不体现在表面的花哨,表面的俏皮话只是小水花,张庆国的机智是大海本身,出于其对生活和艺术的独特理解,跟小说内容融为一体。这让我想起了作家刘震云的小说。刘震云的小说中也有很多看似精彩的俏皮话,但他的俏皮话大多是为俏皮而俏皮,与叙述主体游离,未能融入小说的整体语境,来路不明。
此外,反讽与幽默,语言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也是张庆国语言的特征。张庆国常把严峻的事件轻描淡写,把痛苦表述得不以为然,把惨烈的现实描绘得虚幻神秘。他的词语研究非常细致,语言中很少虚词,大量使用动词、名词,大量做形象比喻与具体描绘,很少抽象表述。
作为生活在云南这块神性土地上的作家,张庆国还对语言的地方性挖掘很重视。地方性是现代性的一种,做到更高意义的地方性表达,才能言之有物,体现最实在的世界性。刘恪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中说:“我特别相信语言是地方性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诞生于某一个地方,由那一个地方赐予他语言,及一种语言的情感、地方性知识、个人所拥有的地方语言经验与表达方式。”刘恪相信,只有地方性的语言才是最独特个性的语言表达。⑦
张庆国的小说中,很早就出现了大量昆明及云南的地理名称,他在多年前就对小说的地方性表达做出尝试,力求运用差异化的地方知识,写出特殊人生,实现文学的创造力。中国文学的普通话写作,抹平了地域差异,把不同地域间特有的文化资源、传承、习俗等烙印消灭殆尽,十分可惜。但是,只注重地域差异,不研究交流的有效,也会造成重大遗憾。众多中国作家对此已有认识,正开展各种探索,张庆国便是其中之一。云南文化种类繁多,体现出多种多样的差异性,艺术资源很丰富,作家只有用心琢磨,才可以写出体现神性的大作品。
作为云南最优秀的小说家,张庆国应该再做努力,继续深入民间,淘洗出云南最有文化魅力、最有地域特色的词汇,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①贺绍俊:《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的优雅语言》,《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
②汪曾祺:《关于小说的语言》,《小说选刊》1988年第4期。
③贾薇:《文学只是一种消遣——与作家张庆国对话》,http://blog.sina.com.cn/s/log_5672e40d0100ij56. html.
④⑤张庆国:《冬天的树和树上暴露的鸟巢》,《山西文学》2009年第5期。
⑥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转引自叶郎《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⑦刘恪:《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作 者: 周明全,青年批评家,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