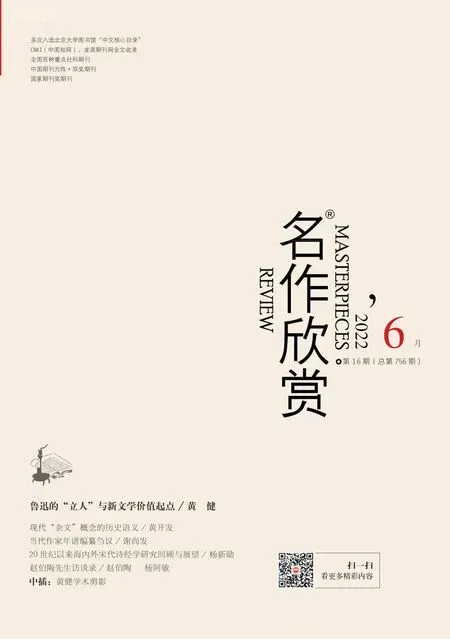一种有厚重感和方向感的写作
——读范稳长篇《吾血吾土》
江苏 陈林
一种有厚重感和方向感的写作
——读范稳长篇《吾血吾土》
江苏 陈林
范稳是一位把写作当信仰的作家,他的作品显示出对史诗品格的追求。其新作《吾血吾土》延续作者一贯的风格追求,揭示了作者试图以新颖的形式和饱含激情的笔墨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并呈现出那些被遗忘在历史缝隙里的民族英雄形象,以重塑我们对历史以及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记忆和思考,因此,不失为一种有厚重感和方向感的写作。
范稳 《吾血吾土》 厚重感 方向感
范稳的写作是一种有厚重感和方向感的写作。从他的成名作《水乳大地》,到后来的《悲悯大地》《大地雅歌》《碧色寨》和《吾血吾土》,尽管在题材、主题、结构、艺术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无一不显示出作者对史诗品格的追求。扎根在雄浑、苍劲的云南高原之上,范稳似乎对某种大写意、大境界的东西非常着迷,所以,在“藏地三部曲”中,每一部都以承载万物、生养万物的“大地”命名。在《水乳大地》中,藏地独有的文化、宗教、信仰之间的相互砥砺、融合成为小说的主题。《悲悯大地》通过讲述一个藏人走向神性世界的艰难历程,诠释了宗教的超拔精神对大地及其生养者的浸淫和滋养。《大地雅歌》在与《圣经》等文本的互文性关联中,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最朴素而高贵的爱情的讴歌。2009年,在完成了《大地雅歌》之后,范稳面临着在题材上突破和超越的困难。一次到滇南的采访,让他有机会探访滇越铁路并找到新的写作契机。在做足了范稳式写作所必备的案头工作和采风工作之后,2010年底,他完成了《碧色寨》。小说讲述了一条铁路由盛到衰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的命运。
2014年9月底,范稳的新作《吾血吾土》上架。小说以一个远征军老兵的命运为线索,时间跨越了上世纪30年代末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作者以大量的史料和田野调查为基础,以新颖的形式和饱含激情的笔墨试图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并呈现出那些被遗忘在历史缝隙里的民族英雄形象,以重塑我们对历史以及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记忆和思考。
在宏大叙事遭遇挑战,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语境中,范稳的写作从不失其厚重。从“藏地三部曲”到《吾血吾土》,他从不回避文化、宗教、历史等重大题材。另外,范稳是一个对世界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且把写作当信仰的作家。在《吾血吾土》的后记里,他说这部小说的写作“并不是要超越或突破什么,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对当下的犬儒主义者来说,活着并不需要被证明;而对一个对真理和信仰尚有追求和担当的人而言,活着则必须被证明,活着即证明活着。
历史叙述与“失败的形式”
《吾血吾土》中历史叙事的形式颇为值得注意。小说以“卷宗”的形式铺开,总共由五部分组成,前四卷是以不同的名义分别做出的四次“交代”。在小说中,“交代材料”“思想汇报”“刑事裁定书”等,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要形式。显然,这种形式是失败的。然而,借用詹明信的说法,正是这种“形式的失败,而非老卢卡奇意义上的成功,可以成为导向某种社会意义和社会真实的线索”①。
在这种“失败的形式”中,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和诸多预设前提,人物的历史叙述受到了权力、叙述框架和言说方式的限制,不可能呈现它的真实面貌。例如,“附件4:刑事裁定书”中的叙事,在革命/反革命、共产党/国民党等概念的二元设置中,一个民族英雄鲜活饱满的历史被遮蔽、歪曲、改写。为了掩盖参加过内战的事实,赵广陵必须隐藏起他在西南联大、黄埔军校的读书生涯,以及加入远征军的抗日经历,而只能靠编织谎言来填补这些空缺。谎言成了某种历史书写的重要材料。
在被扭曲的、残缺的、破碎的叙述中,重要的不是能够从中捕捉到人物被割裂的、被给定的、线性化的历史内容,而是从中看到历史是如何在叙述中被遮蔽、扭曲和遗忘,以及这种历史叙述自身的历史——制造谎言的历史。通过展示历史谎言的生产机制和生产过程,小说从反面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
健忘症与身份政治
记忆是历史的基础,记忆的健忘症必然导致历史的贫血症或坏血症。失去记忆,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也必将失去理解自我和确立自我的依据和能力。只有记忆,才能使人的意识获得连续性,进而获得自我的同一性。如果我们不同意弗洛伊德等人对记忆的生理学、心理学阐释,将人视作“孤立的存在”,而像哈布瓦赫那样,引入人和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认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那么不难看到,《吾血吾土》中造成健忘症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社会权力。
在权力的压迫下,记忆被迫遗忘。由于“告密者”“人民管制”“洗澡”的存在,以及各种暴力形式的压制,记忆像黑暗中的嫩芽逐渐枯萎。在与权力的角逐中,与生俱来的健忘本能被激发,如茨威格所言:“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种本能会使我们不由自主地避开事实真相——因为事实真相就像墨杜萨的脸,又迷人又可怕。”②与墨杜萨一样,昔日英俊潇洒的赵广陵,在救亡图存的战役中被战火烧毁了脸,然而他必须遮掩这一事实,使“人不见其往昔真面目”,因为真面目迷人而可怕。
自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赵广陵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中寻求生存,忍受身陷囹圄之罪、妻离子散之苦、家破人亡之痛,他不断检讨、反省、自我批判,要活着,就不能去触摸那可怕的真相。人们看到的是赵广陵被烧毁后的脸,而他的真相,同时作为历史真相的隐喻,则被遮遮掩掩,难以知晓。
小说中,身份的政治化是当时社会施暴的重要方式。
毫无疑问,身份有其社会属性,但当它被某种单一的、扭曲的政治属性所取代时,就可能变成一个魔鬼般让人心惊胆战的东西。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劳改犯……所有这些身份符号都曾被强置到赵广陵身上。它们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甚至是凭空生造的。
在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中,政治风向标的晦暗不明让“赵广陵们”无所适从。他们要敏锐地把握到时局的变化并据此调整、出示自己的身份,更准确地说是隐藏它们。为逃避政治迫害,他只能不断更换名字,因为每个名字都和一系列性命攸关的政治密码关联在一起。更名确切地说是除名——将其名字从生者之列中除去。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它让你活着,却等同于死去。面对权力的迫害,良知让他与遗忘做斗争,政治则让他与记忆做斗争,他难免要分裂,要产生身份危机。在接受问话时,赵广陵因为一个人称代词“你们”而激动不已。人称代词表面的指代意义背后,也关涉身份政治和认同的问题,只有在表述中才能获得认同。“人称代词不仅表示我们自身的地位和同其他参与谈话者的关系,而且还好似一面反映社会关系系统的微型镜。”③
后革命时代的记忆焦虑
赫尔岑说过:“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利季娅接着写道:“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④庆幸的是,老兵终于等到可以开口的机会,可以用话语去穿透、修复、填补历史的黑洞。可是,如小说后记中所说:“从被迫性遗忘到自然性遗忘,前者是被政治打败的遗忘,后者是被时间战胜的遗忘,这个过程多么令人触目惊心。”记忆被围追堵截,先是社会机器的碾磨,后是自然风沙的湮灭。事实上,记忆在后革命时代的遭遇要比这复杂得多。
丹尼尔·贝尔曾用“革命的第二天”描述了后革命时代可能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⑤这暗示了后革命时代资本化和官僚化对“道德理想”的蚕食,在《吾血吾土》中,即是对记忆的蚕食。
随着死亡的临近以及老兵们的“凋零”,记忆必须以符号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为此,赵广陵走遍战场的每一个角落,搜寻战场遗物。这些遗物是实物性的,更是战场和历史的符号呈现。当亲历者纷纷“凋零”之后,这些遗物开始说话,讲述着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它们从来就不只是将士手边唾手可得的工具。从血迹斑斑到锈迹斑斑,从锃亮完整到支离残碎,它们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和岁月的风化,浓缩着枪林弹雨中的爱恨情仇,凝聚着所有的荣与辱、喜悦与辛酸、悲壮与恐惧。珍藏它们,不啻是珍藏一份记忆。然而,在捍卫记忆的战争中,从来不乏背叛者。
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历史符号的商品化构成了对记忆的威胁。在利益的诱惑下,赵广陵的侄孙赵厚明不知羞耻地将二爷收藏的日本113连队军旗残片出卖给日本老兵秋吉夫三,到后来,甚至一大半收藏品都被偷偷变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记忆如何被出卖,历史如何被亵渎。可是在今天,谁知道有多少个赵厚明呢?对赵厚明做简单的道德判断还不够,更让人忧心的是,老兵们的共同语码在赵厚明们那儿已经失效。他们不再能领会历史的意义。
官僚化是斩断记忆的另一把利剑。赵广陵平反后,已是风烛残年,贫病交加。让人痛心的是,他儿子见到他时,官腔十足,根本不承认他的父亲身份,一心想奔赴威风八面的官场。老父亲这个记忆的载体和化身在这里被打入冷宫。冷漠是后革命时代践踏记忆的又一种方式。
在资本与官僚的夹击下,记忆落荒而逃。路在何方?
历史真相与“想象的共同体”
在后记中,范稳透露了他“试图用一个人的命运来还原某段历史”的愿望,为此,他采访了二十多位老兵,搜集整理了五十多个老兵的人生档案,参加中国抗日远征军“忠魂归国”的公益活动,并亲赴日本了解情况,以“尊重史实的态度”展开书写活动。然而,在东京的见闻让范稳警醒:“一段历史,永远有两种以上的诠释。”⑥倘若历史永远有不同的诠释,那么历史的真相在哪儿?难道我们只能让语词在历史诡异的面孔上打滑,而终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困境?范稳这是在自我解构吗?对此,小说中一个颇有寓意的场景值得回味和思索,那就是为抗日英雄廖志宏迁坟。
为了能让“忠魂归国”,赵广陵克服了重重阻碍,费尽周折来到缅甸境内为廖志宏迁坟。遗憾的是:“什么也挖不到了,蚂蚁把什么都吃光了。”这个句子既是实写,又寓意深刻——我们是否也像赵广陵一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挖开历史的真相,而它早已被“吃光了”?如果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派小说,那么到这里可能戛然而止,撕开历史荒诞的面孔,让读者在它的逼视下产生震惊、不安、恐惧、虚无;而范稳并未就此打住。
尽管范稳意识到历史总会有不同的阐释,但并不意味着历史的阐释可以信马由缰、为所欲为。历史依然有它的真实,这种真实无法依傍于纯粹客观的判断,而只能是一种伦理学和美学的判断。在范稳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召唤中,我们听到了伦理的呼声。这是他历史叙事的落脚点。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⑦。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不是凭空虚构的,也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工具,它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而与一种历史文化变迁和文化心理结构相关联。民族的自我认同,在语言、文化、象征中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追求实际上是人类寻找故乡的根本境况。这大概就是范稳不吝笔墨去塑造一群知识分子,不断强调文脉之重要性的原因。
所以,尽管历史的真相可能像廖志宏的尸体一样被“吃光了”,但并不妨碍我们迎接“忠魂归国”;我们并不知道每一位烈士的名字,但并不妨碍我们造纪念碑和墓园,并致以满怀深情的敬意。在赵广陵为廖志宏吟诵的《招魂》中,我们不仅因洞见了历史的真相而动容,更因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出自叙事伦理的震撼力而潸然泪下。赵广陵为烈士招魂,让死者魂归故里,更是在召回人类的良知。
历史在范稳这里有它的底线,英魂借此得以安息。
①〔美〕詹明信:《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页。
②〔奥〕茨威格:《健忘的悲哀》,樊修章译,见《回归自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③〔苏〕伊·谢·科恩:《自我论》,佟景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18页。
④蓝英年:《记忆是无法铲除的》,见〔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蓝英年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⑤〔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
⑥范稳:《拒绝遗忘》,见《吾血吾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63页。
⑦〔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本),吾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作 者: 陈林,苏州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