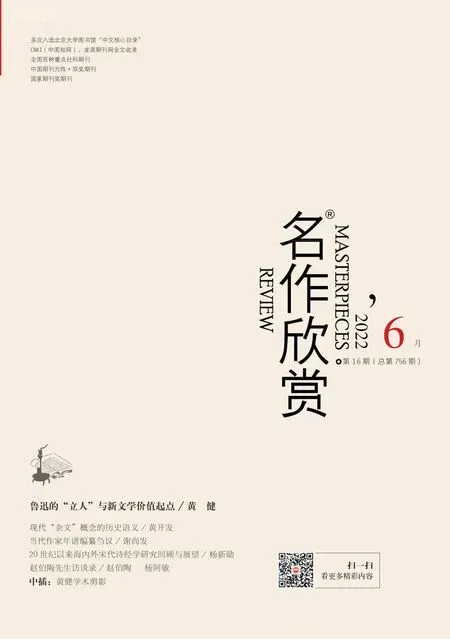若泽·萨拉马戈《双生》:小说的“反常识”和“常识”
广东 林培源
若泽·萨拉马戈《双生》:小说的“反常识”和“常识”
广东 林培源
本文是作家林培源对若泽·萨拉马戈的小说《双生》的解读。作者认为,《双生》是一部人类存在境况的隐喻,萨拉马戈呈现的,是不可能中的可能。小说以“反常识”建构“常识”:日常生活逻辑的常识、小说叙事的常识以及人类存在境况的常识。
若泽·萨拉马戈 《双生》 反常识 常识
死了的不能复生,而活着的人要从那天开始死去。
——若泽·萨拉马戈:《双生》
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的《双生》(O Homem Duplicado,英译:The Double,2002),就像一头巨象。当读者读到最后一个句子时,这头巨象抬起了双脚,朝着一个“原初目标”狂奔起来,任何拦在它面前的人和物,都将被这头狂奔的动物击倒。为什么说是“原初目标”?大概只有读到小说的最后一个句子,这部杰作的真实面目才会显露出来,你才会明白,什么是“original target”(原初目标)。萨拉马戈就像一个引诱者、一个冒犯者,他不仅引诱读者踏入故事的冒险之旅,也引诱作为叙事者和作者的自己陷入一场疯狂的叙事循环中。
小说的叙事始于这样一句话:“这个刚刚走进店里来租录像带的男人,身份证上有个独特的名字,时间侵占流动它的古典风味——他名叫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黄茜的译笔如此流畅,以至于读的过程中,你似乎嗅不到一丝“翻译腔”的味道)正是这句话,开启了一个充满悖论和挑战的故事;而小说的结尾,还是这一位阿丰索:“他换了衣服,干净的衬衫、领带、外套、最好的鞋子,他将手枪插在腰带上,走了出去。”你可以看到,萨拉马戈创造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复制人的故事”,就在主人公阿丰索(年轻的、三十八岁的阿丰索)一连串的动作中,完成了叙述的不闭合之圆。
《双生》出版时,萨拉马戈已逾八十高龄。对一个高产且充满创造性的小说家来说,写这样一部带有黑色电影性质的小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复制人的故事”有悬念、张力、仇恨和“谋杀”),类似“智性”的游戏,甚至可以说是种知识的炫耀。整部小说的“内核”——如果小说有一个内核的话,就像帕慕克《天真的与感伤的小说家》中反复提及的“中心”——起源于一次偶然的发现:阿丰索在庸常的时日里,走进一家店,租下一盒电影录像带(片名充满了隐喻:《捷足未必先登》),却在看完电影躺下之后猛然发现,电影中扮演旅馆接待员的那个人,和他一模一样。如果用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著名概念来说,这是戏剧里的“发现”,而发现之后,还需“突转”,如此,戏剧的整一性才能呈现出来,就像水落尽,石头出。阿丰索的发现,带有震怒、怀疑和好奇,这些驳杂的情绪是叙事走向诡谲和引人入胜的原动力,于是,萨拉马戈的叙事列车开动了。小说的前五分之一,萨拉马戈写的是“寻找”,他就像一个耐心的、充满理性分析的侦探,将推理和甄别的能力赋予阿丰索(一个历史教师),让阿丰索带着强烈的好奇去探求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陌生人的名字乃至地址。于是,有相当长的篇幅(中译本前八十三页),萨拉马戈使用了“重复”的手法:阿丰索租下同一家制片公司的大量录像带,回家观看,他根据重复出现的演员名单进行筛选、排除,最后,终于在《舞台女神》这部电影中,发现了那个和他在生理上长得一样的演员的名字: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克拉拉是艺名,真实姓名为:安东尼奥·克拉罗)。
于是,故事饶有趣味的地方就从这里上升为人类存在境况的隐喻。萨拉马戈呈现的,是不可能中的可能,他的小说,是从“无”到“无”,就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存在过,又被蚂蚁吞噬,最终消失在拉丁美洲大地的“马孔多”一样。这里,有一个词语必须引起重视,这个词语不是别的,正是“常识”。萨拉马戈在《双生》中不厌其烦地和读者、叙事者(阿丰索)乃至自己谈论“常识”。我所理解的常识,在小说语境中,有三层涵义:
第一层,日常生活逻辑的常识,即,这世上不可能存在一个和我们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不论从生理上还是精神上,都不存在,就如不存在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萨拉马戈通过对这个常识的反动,撩动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否定之否定中,整部小说的地基就此夯实,任凭你如何摇晃,建立起来的钢筋水泥建筑,将屹立不倒。
第二层,小说叙事的常识。这里涉及叙事逻辑的问题,小说叙事逻辑遵循“虚构的真实”这一原则,即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提到的“说服力”。萨拉马戈轻易地就将这个难题解决了,他将半限制性视角(阿丰索)和全知视角(“我们”)交叉混用。阿丰索的视角容易理解,“我们”就显得暧昧模糊了——这不得不令人想起《包法利夫人》伟大的开篇:“我们在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人物的行动、心理和情感,在阿丰索身上分毫不差地呈现出来。例如,阿丰索发现存在另一个“分身”之后,萨拉马戈写道:“我真的是一个错误吗?他问自己,假设我确实是的,一个人知道了自己是个错误,还有什么意义呢,后果又如何呢。一阵惊惧迅速窜过他的脊柱。”身为历史教师的阿丰索,被这个发现击垮了,历史加诸他身上的常识和认知,就此崩落,而常识的崩落,却建立起叙事的“常识”。
第三层,人类存在境况。萨拉马戈打破常识又重构的过程,类似借尸还魂,用的是存在主义的手法;换句话说,阿丰索陷入的发现分身、复制者的这出荒诞的“境遇剧”(萨特式的“境遇剧”)不单是他个人的,还是人类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就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为一个“潜文本”被后世的许多文本所指涉那样,萨拉马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原初文本”。这部小说最伟大的创造在于,他用“反常识”构建“常识”。当这个认识论层面的彻底扭转抵达之后,叙述的难度一下子提高了——
萨拉马戈探究的问题,在阿丰索“发现”之后,才刚冒出头,接着,是必须拧紧不放松的“突转”(并且不止一个突转,小说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每一个突转,都是致命的):阿丰索找到了他的“复制人”,他的双生人——安东尼奥·克拉罗,一个二三线配角演员。这样,通过“发现”和“突转”,萨拉马戈反常识的叙事常识就建立了,故事的可信度和虚构的逻辑,就像精准无比的齿轮,咬在了一起,并且推动叙事的下一轮疯狂运转。萨拉马戈的笔法,不是博尔赫斯式的迷宫,也不是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他只属于他自己。《双生》的腰封上,赫然印着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德国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话:“我们时代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实体的丧失持续不停,无法挽回。”这句话恰如其分,可以成为整部小说的“哲学注脚”。阿丰索在小说中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实体的丧失持续不停,无法挽回”,最终,阿丰索只能借用安东尼奥·克拉罗的身份活下去——“死了的不能复生,而活着的人要从那天开始死去。”
小说越到结尾,悲怆的气息越浓厚,悲剧性像暗无边界的夜色弥漫过来。阿丰索的懦弱、怨恨和报复,最终让位于一个终极性的难题:如果你寄存的“实体”(对阿丰索来说,是他和安东尼奥·克拉罗互换的身份)倾覆了,真实的你将如何存在?萨拉马戈并没有软弱,他残忍地揭开存在的伤疤,阿丰索的哭泣和颤抖,以及最后被命运压着盗用了安东尼奥·克拉罗的身份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阿丰索最严重的惩罚。真实的安东尼奥·克拉罗也是出于报复,提出以和阿丰索未婚妻玛利亚·达·帕斯过夜作为威胁,于是,原本平衡的四人结构(阿丰索-玛利亚/克拉罗-埃莱娜)被打破了。
故事以玛利亚和克拉罗的车祸结束,而在结束时,原本被真相排除在外的玛利亚也知情了。小说的悲剧性正在于此——无辜者成了人性懦弱和仇恨的牺牲品。作为负罪者的阿丰索,注定要像西绪弗斯一样,背着死者(安东尼奥·克拉罗)身份铸成的巨石活下去。萨拉马戈揭示了身份的互换、错位,但最终这把利刃,刺中的是每个个体柔软不堪的灵魂。
和萨特用文学来注解其存在主义哲学迥然不同,萨拉马戈的小说巧妙地躲开了成为哲学注脚的噩运,他让哲学反过来成为文学的注脚。这是萨拉马戈的高明。他创造的阿丰索属于他一个人,同时也属于所有人。他写的是“可能的历史”,和奥威尔的《1984》一样,最终会成为映射人类命运的预言。
这就是小说的迷人之处,它诞生于一个令人震颤的意念,柏拉图式的“迷狂”,最终,借助语言符号的载体,涉及了一个人类生命哲学的隐秘主题:有与无。一如老子那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萨拉马戈《双生》的存在根基,也是小说能超越语言界限、直抵人心的秘密所在。伟大的小说,就如同一面多棱镜,它反照太阳的光芒,不管你从哪一面注视,反射到视网膜中的那片阳光,本身已经取代了阳光,成为其自身。
2014年3月21日完稿
2015年4月13日修改
作 者: 林培源,青年作家。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已出版短篇小说集《第三条河岸》《钻石与灰烬》等六部。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