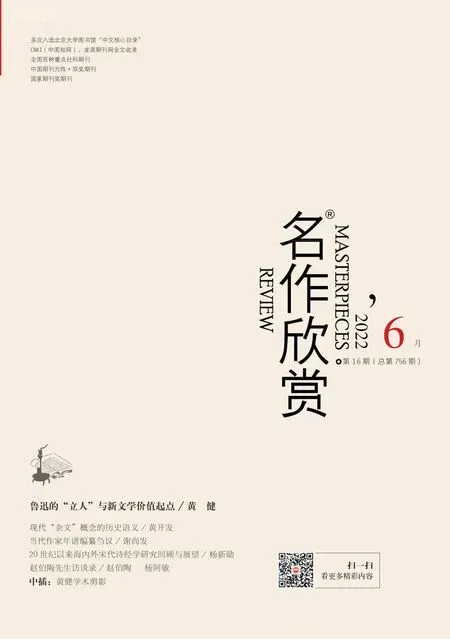拒斥、融入与抽离
——网络时代:我的“部落化”生活
北京 李天豪
拒斥、融入与抽离
——网络时代:我的“部落化”生活
北京 李天豪
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受到印刷术深刻影响的一个人,其影响之深,可谓深入骨髓、渗透灵魂,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即便作为一个“90后”,作为一个新媒体取代纸质媒介的过渡时期的“历史中间物”,我更像是媒介革命的前代“遗少”,固守着某些可能迂腐陈旧、笨拙可笑、不合时宜的习惯。我坚持用纸本书阅读,认为电子书只配做厕所读物;一直拒绝参与网络虚拟社交,直到大学上了一学期才真正拥有自己的第一个QQ号,而当时“人人”已经后来居上,风靡校园;甚至写论文和搞创作都必须用黑色的签字笔在白净的笔记本上写好了再誊抄到word文档上,否则面对电脑就会大脑空空,毫无思路。我一直不明白过去的我为什么会如此抵制网络入侵我的生活,现在想来,这可能是一种对自己早已适应了的感到舒适惬意的生活方式的固守。我虽然在拒绝改变的时候没有经过理性深入地思考,但已经隐隐意识到:这是一次彻底的毫不留情的改变,它会摧毁我过去的交友方式、思考方式,它会使我坚信的某种想法坍塌,使我感到安全与舒适的圈子瓦解。所以,我拒斥网络,像拒斥某种试图侵袭进入我生活的洪水猛兽。我是那么懒那么顽固的一个人,只想在自己的舒适地带经营自我。我奉行最传统最正常不过的价值观,把那些光怪陆离、奇形怪状的各色人等关在电脑之外,不要那些喧哗聒噪的声音告诉我我有多out(落后)。
可是,固步自封带来的一定是无知落后(这句是真心话,别笑)。慢慢地,我发现自己愈来愈不能理解和接受我身处的这个时代,它裹挟着瞬息万变的讯息和斑斓诡异的事实汹涌袭来,所有不能参与这场众声喧哗的狂欢的人类都像是被放逐在空旷无人的荒原,茕茕孑立。当我在听学术讲座的时候,尤其是当我的同龄人我的同学们就当下的时事热点和社会现象向主讲者发问的时候,我更加深刻地感觉到我与某种话语模式的分离。因为拒斥网络,我失去了观照和参与这个社会的资格,我被自己营造的屏障所禁锢,成为这个时代的“多余人”。我因为惧怕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圈子、自己一以贯之的观念而拒斥网络,但恰恰是这种拒斥,让我逐渐与圈子脱节,而我所信仰的那一套在以往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形成的单纯又极端的价值准则,也丝毫不能让我在与世界和他者的参照中给予我些微的安全感与发自内心的力量。我没有勇气继续供奉,我的供奉更像是一种抱残守缺。我急需将其打碎、重塑。就像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中的一句台词:“你连世界都没观过,哪来的世界观?”这句话的高逼格(引申为能力与档次)说法或许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中所言:“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于是,我打开了电脑,换上了智能手机,准备开启一个新的世界。是的,我有意把这种改变变得仪式化,像是与往日狭隘闭塞的自己作别。我开始用博客,发博文,分享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我开始养成每日浏览新闻的习惯,知晓日益平面化的世界彼端的一切;我开始习惯每天刷朋友圈,在这种媒介中维系和平衡我与朋友的关系;我渐渐学着在微博、微信上获取信息,在犄角旮旯和边边角角获得一种碎片化阅读体验;我开始在豆瓣上结交志趣相投的人,突破自己由线性人生所造成的交友的局限。
但同时,我对新媒体的使用也抱着一种审慎抽离的心态。深知碎片化的阅读无法获得系统性、体系性的知识架构,大部头书本的阅读还不能放弃治疗;朋友圈发状态要适可而止,谨防自己晒幸福(无恩爱可秀)的心态养成,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生活的质量建立在点赞的人数之上,这是一种最要不得的媚俗心态;网络上的交友更要谨慎适度,意识到二次元世界与三次元世界的不同,如果我们彼此在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虚拟空间里因为抽象化符号化了的自我而互相欣赏,那么,就不要让这种志同道合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幻灭。麦克卢汉不是早就提醒我们了吗?不要陷入使用媒介的自恋性麻木之中,要清醒,要理智,要冷静。
网络时代是不可阻挡的,只有投身其中才能称其为一个真实鲜活、还在参与这个世界的人,但只有在纷繁复杂、众声喧哗中抽身其外,才不会成为一个扁平而失去内核的人。这一进一出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在吐纳信息、彼此参照中都变得更丰富更完善。二次元热闹归热闹,我们还是要在三次元的世界里学着怎么做好那个“我”。
作 者: 李天豪,北京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