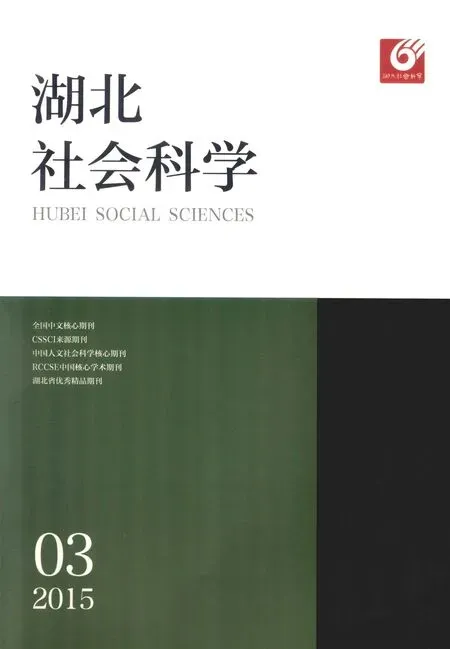论《坛经》的“即心即佛”
江 澜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0)
一、何为佛?
“佛”一词源于古印度梵文“Buddha”,本义为“觉者”,即觉悟了真理的智者。在早期印度佛教中,“佛”特指佛陀,即释迦摩尼这个人,他是人间的觉者,是佛教的教主与导师。而且佛也只有一个,凡夫可以通过不懈的多次地的修行达至阿罗汉果位(此果位标志常人的最后解脱),但阿罗汉不是佛,也不能升至成佛。对于佛身的看法,早期小乘佛教认为佛只有生身这一身,生身即肉身,而肉身可灭,并不永恒存在。后来释迦摩尼佛灭度以后,部派佛教出于对他的敬仰与怀念,提出了佛二身说,即肉身和法身,法身特指脱尽烦恼的无漏身。[1](p135)
两汉魏晋时期,佛教依附在儒道玄学的基础上而开始在中国传播,因此对佛经的解释明显烙有中国思想的印迹,认为“佛”就是儒家的帝王、周孔以及道家的神仙,并将佛学混杂于黄老玄学。但随着佛教翻译水平的提高和理解的深入,“佛”一词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用“佛”泛指一切觉行圆满者,因此除释迦摩尼佛之外,在佛陀跋陀罗所译的《观佛三昧海经》中首次出现了东方妙喜世界的阿閦佛、南方欢喜世界的宝相佛、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北方莲华庄严世界的微妙声佛所谓四方四佛。[2](p166)从时间的角度有代表过去的燃灯佛、代表现在的释迦摩尼佛、以及代表未来的弥勒佛。同时,佛陀本人也被神化,比如传说他是菩萨入胎作白象形,从母右腋出生,并身紫金色,落地能言,有七宝盖,与佛一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此佛陀的人格已经被完全神格化,偶像化,其对人间的作用类同于西方能救世的上帝。大乘佛教还主张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有情世界都可以通过修菩萨行的六度而成佛。此外,对于佛身的看法,也由之前小乘的一身二身发展为三身:法身、化身、报身。其中法身是佛依靠自然天成的本性所得的自性身,化身是佛为了教化众生,变现的各种人格身,报身是佛陀经无量的德福和智慧产生的果报身。
纵观小乘与大乘诸佛教教派,两者都有将佛及佛身外在化和偶像化的倾向,致使民间也由对佛的信仰变成了对佛的崇拜。但不论是小乘佛教中特定的某个觉悟者,还是大乘佛教中的众多觉悟者,“佛”的核心意义都脱离不了“觉悟”二字。学者方立天将“觉”分为三义: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1](p134)自觉是指自己觉悟宇宙真理并了脱生死,觉他是指使众生觉悟、解脱。觉行圆满是指闻思修证的合一,它们是凡夫走完成佛道路的标志。这当然是佛教中对“觉”的一种通行解释,但对慧能来说,觉悟根本只在于自觉,而非关其他,正所谓“自性觉即是佛”。
但慧能之“佛”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佛”一词在《坛经》文本中出现200余次,共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作为修饰词使用,如:佛性、佛道、佛法、佛地位、佛境界等,另一种是作为名词单独使用。单独使用的“佛”的含义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指觉悟者,如“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指成为具有佛性之人;二是指觉悟本身,如“自性觉,即是佛”、“即心即佛”等,这里的“佛”是指觉悟的佛性,而这一种正是《坛经》阐释的重点。慧能强调“佛”不是人之外作为偶像的神,而只是人本来拥有的自性本心,所以慧能直说,“只汝自心,更无别佛。”另外,对于佛身,慧能也有创造性的解释,他将传统的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归为自性三身佛,亦即人心灵的三种变化形态:清净法身佛、千百亿化身佛和圆满报身佛。
第一,清净法身佛是人本来具有的自性、自心。与一般佛教相同,慧能认为法身本来清净无碍并涵蕴万法,但不同的是,慧能将法身视为人内在的自性,而非作为外在偶像佛的法身,但人的自性容易被欲念所遮蔽,所以需要去念去避而使自性彰显。
第二,千百亿化身佛是自性的变化。在一般佛教中,化身佛指佛为化度众生而随任方便显示出的种种不同法相。但慧能抛弃了这种常规看法,他认为万法的种种变化都来自于心念思量,报身佛就是人随心念变化所呈现的不同状态。“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可见,法有善有恶,但心要去善扬恶,最后超出善恶。超出善恶的心就是自性,自性的随任变化就是化身佛。
第三,圆满报身佛是自性的实现。在慧能看来,报身佛不是佛通过修行达到的相好庄严的回报,而是如同去除遮蔽的灯光,自性显示出了无善无恶、圆融不二的本来面貌,人自性的圆满实现就是报身佛。慧能所认为这三种佛身均由人的心灵变化而出,佛乃是个体心灵对自身本性的直接了悟。
二、何为禅?
对于禅宗,我们更需要理解什么是禅?在日常语义中,“禅”常与一些词搭配成为一些流行说法,比如有“口头禅”,其意指某人口中频率使用很高的词,也指人对某事光说不练,将禅作为修饰词的用法也层出不穷,如禅茶、禅诗、禅话、禅画等;此外还有从禅宗故事中流传下来的词,如“野狐禅”,引申指人走旁门左道,不行正道,又如“一指禅”现专指少林寺的一门武术功夫等等。那么“禅”在佛教中的本义是什么呢?“禅”是梵文“禅那”的简称,意思是“思维修”或“静虑”,这是指人的心灵处于安宁和清明觉知的状态,因此作为佛教的通行修炼方法,“禅”常与“定”相连而被称为“禅定”。但“定”这种修行方法并非为禅宗所专有:在古印度,禅定法于佛教创立前后已在各沙门流行,例如早期印度的耆那教、晚期的瑜伽行派;在中国,儒家也以静定为功夫,如《大学》一书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3](p3)其中“定”成为儒家心性修养的重要途径,道家的练内丹及静坐也与禅定有着深刻的相似性,另外西方天主教的静坐、穆斯林的祷告也都具有禅定的意味。但禅定却只在佛教中形成了主题并凸显出自身独特的意义,《大智度论》卷二八:“四禅亦名禅,亦名定,亦名三昧。除四禅,诸余定亦名定,亦名三昧,不名为禅。”[4](p24)可见,禅定与一般的静定是有区别的:静定的目的是调息调心以达到身心的合一,比如瑜伽和道家,而禅定的目的是使人获得大智慧而了脱生死。另外在佛教中,禅与定也有区别,禅是思维修,是内观,而定是摄心使其不散乱。因此,“禅”涵摄观而发慧,“定”连接止而息念,即止观双运。小乘古典禅法将在色界天称为“禅”,在无色界称为“定”,并把“四禅”、“四无色定”和“灭心定”合为九种禅定,四禅分别是: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①初禅以“寻”、“伺”为思维形式;二禅以“内等净”为思维形式;三禅以“行舍”、“正念”、“正知”为思维形式,四禅以“舍清净”、“念清净”为思维形式。四无色界定分别是: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1](p732)由此而来的各种禅观法也层出不穷:如华严宗的十玄门法界观、密宗的白骨观、本尊观以及净土宗的十六观,包括日落观、水观、地观、宝树观等等。此外还有《禅经修行方便》所提到的五种基本禅观法:不净观、慈悲观、十二因缘观、界分别观、数息观。[4](p42)这些禅观法都是各宗各派用于修行禅定的方便之门,其目的都是引导人放弃对世间一切法相的执迷而了生脱死。
禅定于佛教修行如此重要,以至于一般人们都会将禅直接理解为禅定,但慧能认为禅的本意并不是禅定,更不是静坐,它只是由心灵觉悟而获得的智慧。根据这一点,慧能赋予了“坐禅”以新的内涵:“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处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这里的“坐”不是指常规静坐的行为,而是指心在一切境中不起妄念,它直接相关于心灵的修炼而非只是身体的修炼,“坐”的目的在于修“止”,修“止”而后能内见自性本心。另外,对于何为“禅定”慧能也有新的解释:“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这里的“定”特指保持心灵的澄静,慧能将“坐禅”与“禅定”赋予了超越身体的含义,而直接与心相关联,且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通达禅。慧能说:“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如此一来,禅就是“见性”,就是佛性智慧的最高证悟。由此,禅宗之禅作为智慧之禅规定了禅定,也规定了人在生活世界中应行走的道路。那么,慧能所说的智慧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第一,它与日常智慧相区分。
日常智慧如黑厚学的处事智慧,民间谚语,孺子家训等等,它们相关于人的生活本身,是关于生活世界的实用智慧,属于机智和聪明,其作用是局部和短暂的。禅宗的智慧却是对世界和人存在的根源性观照,能带给人以解脱与大自在,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
第二,它与早期佛教智慧相区分。
在早期佛教中,智慧里包含了“神通”的内容。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家僧团中表现最为突出,如佛图澄、玄高等高僧就是因为显示了神通和法力,而被统治者尊为帝师。汤用彤先生提出:“汉魏禅家,盖均着重神通。疑此亦受道家成仙说之影响也。”[5](p15)此外藏密所持的手印与咒语也有类似作用,他们认为通过修持,人可以获得五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和宿命通。这些都使佛的般若智慧具有了神秘色彩。而慧能却不谈神通,他认为般若智慧就在日常生活中,它并不神秘,也不遥远,“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净土、道场就在心中,修行人应不离世间觉。慧能甚至还把佛弟子的行为准则和儒家伦理道德相结合,形成了特色化的禅宗智慧:“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第三,它与一般的中国佛教相区分。
中国化的佛教除了禅宗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天台宗、唯识宗、净土宗与华严宗。天台宗注重三止三观的修息功夫,以此去体悟事物即空即假即中,亦即圆融三谛;唯识宗注重对人八大心识的细微分析,并力图通过修持而达至转识成智;净土宗注重对“阿弥陀佛”四字真言的诵持,心系一缘以往生净土;华严宗则显示了觉悟者已经领悟的如来藏清净体。而慧能在佛理上去芜取精,对之加以最大程度的简化和明晰化,将成佛之路创造性的直接归结于对本心的觉悟,在这个意义上,禅宗甚至被称为“心宗”,但慧能的“心”如何解释呢?
三、何为心?
“心”,首先,在现代汉语中意指人生理肉体的心,即“心脏”这一器官,它是身体性而非精神性的;其次,在日常语义中,“心”一指心理感受,即心情,二指“念头”、“欲念”,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它不诉诸形体,但自己可以感受得到。比如“虔诚心”、“喜悦心”、“嫉妒心”等等。三指“精华”、“要害”,如讨论某“中心”议题;再次,在佛教的语境中,“心”既不是指可观察的肉体心脏,也不是“念头”与“欲念”,《般若波罗蜜心经》的“心”可理解为“要害”与“精华”。另外,唯识宗将“心”理解为“心识”。“识”即“意识”,是指人的心理与精神活动。他们对于“意识”展开了最为清晰的讨论,此宗依据《解深密经》以及《瑜伽师地论》两部经典认为:人有八识,前六识依次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需要有对象才能发生,如在睡眠和休克状态,这六识就无法起作用。第七识是末那识,它是“恒审思量”,其职能是肯定有“我”,它是无明的源泉。第七识能熏染第八识阿赖耶识形成所谓的“种子”。而第八识阿赖耶识是人的清静本体,它能够保持前七识的前后连续性和精神各部机能的统一,它不但贯彻人的一生,而且也是轮回的主体,也就是不死的灵魂,但因第七识的熏染,人的第八识通常并不清静,只有把污染的阿赖耶识转变为清净阿赖耶,才是成佛的唯一途径。[6](p118-119)将污染的识转变为清净智慧,这就是转识成智。
与唯识宗一样,慧能也主张“心”对于成佛的重要性,但他没有将“心”与“识”连用,而是将“心”与“性”相接。“心”字在《坛经》中共出现254次,基本可以归纳为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日常语义的“欲念”,可理解为染着心,如“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二是指自性,亦即清净心,如“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可见,心具有可净可染的性质。那么作为清净的“心”与“性”是什么关系呢?慧能认为“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这里,心是性的居所,性是心的主宰,心与性无法分离。彭富春先生认为“一般而论,性与心是不同的,性是存在的规定,心是人的规定。但禅宗所理解的性与心是同一的。……禅宗的革命性在于,它不仅将佛的佛性理解为人的自性,而且将人的自性解释为人的本心。”[7](p200)在《坛经》文本中,当“心”在自性这个意义上使用时,慧能往往使用“自心”、“本心”的称谓,当然也将其经常简称为“心”。“心”在此成了人存在的最高规定,“心”、“自性”被慧能描述为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和能生万法。
所谓“本自清净”是指自心没有被无明所熏染,无滞无住,空明清朗;所谓“本不生灭”是指人心的实相不是如有为法一般具有生灭,因此也无空间与时间上的消亡;所谓“本自具足”是指它自身是圆满无缺憾的,无须外求;所谓“本无动摇”是指它自身居于自身,是宁静纯一的,能保持自身而不与境迁;所谓“能生万法”是指由心的宁静纯一能生出种种世间有为法,即由心生境。这里的“生”不是一种意向性的行为,而是众法与万境对自性的敞开。
但这种本心是否专指人心?并为人所专有呢?
对于究竟谁能成佛的问题,在佛教各部派中一直存在争议。根据前文所述,小乘佛教佛只是释迦摩尼佛一个,因此,除他一人具佛性之外,其余都无佛性。佛教徒通常将世间万物分为有情与无情两类:有生命之物称为有情,无生命之物称为无情。天台宗高僧湛然认为一切无情有情皆有佛性,真如遍在就是佛性遍在,并以此提出了“无情有性”之说。[1](p258)对于此说其他佛教宗派是反对的,如华严宗就提出只有“有情”才有佛性。何为“有情”呢?华严宗认为“有情”是指有情识,其组成要素一个是精神的,是五蕴中的受想行识四蕴;另一个是肉体的,是五蕴中的色蕴。因此“有情”主要指动物(包括人),植物虽然有生命但没有自觉的精神作用,所以不能称为“有情”。而无情识的草木瓦石只具有真如本体的法性,而法性与佛性是有区别的,佛性仅为有情众生所有,法性则为无情识的万物所有,无情识的万物不具有佛性,因而也不能成佛。[1](p269)另外,近代高僧太虚大师认为“有情”狭义来讲包括三界五趣,广义地说还包括三乘圣者而为九法界。[8](p74)具体说来就是凡是未成佛之前的包括下至畜生上至天人、菩萨等都在此列,在此,“有情”排除了无生命之物;唯识宗对“有情”的认识大体同于太虚的说法,但认为“有情”分五种性,其中无有出世功德种性的众生,因断了一切善根而不能成佛,因此有“一阐提之人不能成佛”之说①唯识宗认为一切有情有五种性:声闻种性、独觉种性、如来种性、不定种性和无有出世功德种性。这些种性由阿赖耶识中无漏种子(没有烦恼所污)和有漏种子(为烦恼所污,受到束缚限制)所决定,不可改变。其中第五种无有出世功德种性,又名一阐提,因不信佛法,断绝了善根,所以沉沦生死苦海,永远不能成佛。。与华严宗类似,慧能也提出“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但他认为“有情”主要指人,为何是这样?因为从世界整体来说,人虽是世界中一物性存在者,但却是具有独特意义的存在者。只有人才拥有心灵,其他物如矿物、植物、动物因没有心灵所以没有佛性可言。同时,人一方面具有人性,一方面也具有动物性。动物性主要指人自我保存的本能与各种随之而来的欲望,而人性则主要是指人有心灵,心灵的本性是虚空,心灵拥有如日月般常明的智慧,它使人能观照自己、分析自身、设定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人甚至就是心灵。慧能认为“万法在诸人性中”,佛的智慧只有通过人的修证才能获得,并且人与人之间都具足无差等的佛性,即无论何种出身都可成佛,正所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在此,每个人的本心都为其修行提供了内在根据和可靠保证。
四、心的迷误
人心既然本性清静,那迷误何以产生呢?慧能对于人的迷误有一段精彩的比喻:“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慧能将自性比作清静的天空,迷误比作浮云,认为人要吹散浮云方可见到清朗的天空。
尽管禅宗已指明了心的本性是清净的、不生灭的、本自具足的、本无动摇的、能生万法的,但为什么人多处于迷误之中呢?慧能的回答是:“道须流通,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流通。心若住法,名为自缚。”“滞”、“住”即是产生迷误的根源,人心之所以会“滞”、会“住”,是因为认“假”为“真”,由此产生了导致人无明的三毒:“贪”、“嗔”、“痴”。
第一是“贪”。
“贪”是指贪欲,何为欲?欲,欲望即需求。何为贪?超过了正常的边界就是贪,首先,“需求”具有意志性、指向性,它是促使人发起行动的启动键,所谓生命不息,欲望不止;其次,“需求”意味着对某物的缺失,对于人来说,低级需求如饮食男女,高级需求如获得幸福和成功等等,这些需求一方面是人对自身的保存,一方面是人对自身的实现;最后,需求与情感相连,即所欲的是否实现或实现程度如何,都会引起人情感的变化,或喜或悲,或惊或怒。从本性来讲,欲望没有好与坏,只有强与弱,但强与弱也有其边界,过了强的边界,欲望就是非常态的欲望,这就是佛教中所要戒除的“贪欲”,过了弱的边界,欲望不能保存其自身,人也会走向消亡。另外,欲望除了有其深度上的边界,也有其广度上的边界,慧能认为“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这是指人的性情像浮云一样游移不定,人们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拥有了杂多而无常的欲望,但每个欲望都还没来得及被认识和理解就被冲走和遗忘,以至于每个体验都浅尝即止而无法达到深刻,在此状态下人只会感觉到忙碌的空虚、无聊与情感上的忧愁焦虑,智慧就在过界欲念的遮掩下隐蔽了自身。
第二是“嗔”。
“嗔”是指嗔恨,“嗔”主要源于分别心,分别心是指对好坏优劣多少等的区分,区分来源于人生来而具有自我保存的意愿,因此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人人都希望享有最好的而不是最差的,对好的事物人人也都希望享有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这种好与坏的评判标准往往来自于社会长久以来的约定俗成,也是佛教常说的“习气”,人们因此很难跳出此樊笼。嗔恨是在其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所引发的情感,这种情感具有受动性、对象性,即人的喜与怒不是源自于人自身而是来自于他人或他物,这种情感所导致的行为就是要去打击或消灭某物或某人,这只能引导人走向极端的自我,甚至自身的毁灭,这是人性之恶。
第三是“痴”。
“痴”是指错误、虚妄的认识,是无知或误知。“知”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知道,二是知识。道是真理,知道就是领悟并体验到了关于世间万物存在的真理,即真知。而知识从广义上来说,是指人类在实践生活中所积累的一切智力成果,它包括经验与理念两个层面。①斯宾诺莎把知识分为三类:一是建立在感官知觉上的经验和意见,这类知识是模糊不定的。二是清晰明确的观念和理性知识,这类知识是充分可知的。三是由直觉而来的知识,他把第三种知识看做是最高的知识。(梯利:《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37,338页。)这里的直觉知识与以上两种知识的区别在于:它既不是零碎局部的感觉经验也不是科学逻辑的推理与演绎,这种知识根源于整体的直观。铃木大拙认为禅所要唤醒的正是第三类知识,他认为这类知识与其说是渗透到了一切存在的根基,不如说它是从我们存在的深处喷涌而出的。(铃木大拙,张石译.铃木大拙说禅[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第91页。)而本文所探讨的知识主要指前两类知识。知识不等于真知,但也不能说是假知。知识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服务,它具有工具性和无常性。从佛教观点来看,知识是“有”不是“无”,但是“假”而非“真”,所以不应一味执着。相反,人能智慧而幸福生活乃是由于有真知,真知不是工具而是目的。但真知如何得到?对于佛教来说,真知是智慧,是人的内在觉悟。这样就导致了人们对内在真知与外在知识的两种矛盾看法:一是因为知识能拓展人的未知领域,在对客体的规律研究过程中,人们可以逐步的接近真理,所以认为知识是人获取真知最重要的途径,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二是因为知识是外在的,而真知只源于内在的觉悟,因此知识是人们求道成佛路上的障碍。前者把知识视为一切智慧的源泉,甚至将学知识等同于修智慧,后者把知识与智慧相对立,将无知当大知,曲解了“不向外求”之意。其实这两种关于知识的见解看起来截然相反但都通向“愚痴”。如同欲望一样,知识本身没有善恶好坏之分,只有多与少,它具有工具价值而非目的。作为工具,知识既可以利益人也可以损伤人,对于知识的过度追求能让人成为知识的奴隶和传播知识的工具。人应如何与知识相处?使知识接受智慧的指引和划界,即明白哪些是必须知道的,哪些是不需要知道的,或哪些是可以了解的,从而朝向智慧的目标前进。有关知识,慧能在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时,提到了第五香“解脱知见香”,他说:“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慧能在此十分切中的指出了人在净心之后还需要增加自己的见识,即通过广学多闻,掌握外在事物的诸多法则,磨炼自己的慧心,增加自身定力与洞察力,让智慧在对具体事物的理解与实践中去得到提升,使觉悟不离世间。
综上,由于贪嗔痴的存在,人本有的智慧在现实中常被迷误所遮蔽,但这迷误的发生是必然的吗?抑或偶然?对于“入迷”,铃木大拙有一精辟的论述:“入迷是人最大的特权。如果没有这些,那就是动物或神。”[9](p32)这指出了人生在世必然受到世俗成见和各种妄念的熏染,凡成圣成佛之人无不是在迷误中觉悟成道,没有迷误就没有觉悟。
五、即心即佛
在慧能看来,无论迷误或是觉悟都只相关于人心,正所谓“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这样看来,人心既可以愚也可以智,因此心与佛并不天然对等,唯有开悟的心才是佛,因此“即心即佛”,确切说来应是悟心即佛,而开悟发生在一念之间,由此,成佛成为了每个人此时此地的事情,它直接表现为心灵的瞬间觉悟。那么人心该如何消除迷误?慧能提出了无念、无相及无住的修行之路,这形成了慧能思想中最具特色的表述方式。首先,“无”要理解为否定,具体说来是对人“拥有”的种种念头名相的否定,因为这种生活常态遮蔽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本性,所以否定就是去蔽;其次,“无”在否定中也包含了肯定,去蔽的同时也是对人本性的显现。具体分别表述为:“无念”不是指一念全无,而是“真如念”。一方面,真如不是无心灵的,而是有心灵的,它不是一片顽空;另一方面,念不是杂念,而是纯念,正念。如此正念相续就是无念。“无相”不是否认一切物质现象,而是对物质现象不做无谓的分别取舍,以保持心的清净无妄。“无住”是指对事相层面的“念”与“相”都不要执著,心不住法,道即流通。如果说“无念”与“无相”是对心的否定的话,无相主要是对境的否定[7](p205)。再次,“无”还要理解为悖论之“无”,即它否定的事物也是它所必须依赖的。“无”不是通过远离一切现实生活世界来实现的,相反,“无”恰恰只有在一切现实中才可能实现。由此,无念表述为“于念而离念”,无相表述为“于相而离相”,“于”可理解为进入其中,“离”意味着保持距离,其整体含义是指人在专心致志的心境中让事物的发展顺其自然。“于”和“离”在此同时起作用,不可偏执一端,可见,慧能对“无”的主张中还包含了中道的智慧。何为中道?“道”可解释为方法道路,那么“中”作何解?印顺对“中”的解释是:“中是正确真实,离颠倒戏论而不落空有的二边。”[10](p4)值得注意的是这二边不是简单的对立,它们是保持事物不发生质变的两个端点,事物的“法”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端,当然也不是由两边的综合而形成的第三者,“法”存在于两点之间形成的张力之中。这种不二法门可以克服人们看待事物非此即彼的片面性,慧能在经中最后部分提出破解一切迷妄的“三十六对法”①三十六对法包括无情五对、法相语言十二对、自性起用十九对,共三十六对法,参见《付嘱品第十》。,即可看作是对中道之义的生动注解。最后,“无”对自身也进行了否定,“无念”成了“无无念”,“无相”成了“无无相”,“无住”成了“无无住”,任何有为法都需要被彻底否定,即人在一切行住坐卧中要从容而无所留滞,做到“住无住”、“念无念”、“相无相”,回归到心的本源“净”,以达至随机应变,事前不为成法所拘,事后不留一法可循。
第一戒。
“非”是指分别心,它专指心的各种妄念与执着。尽管就心的真如本性而言,它是清净体,且恒常不染,但在事相层面上“分别心”还是必要的。因为事情无时不在二元转化之中,人需要有分别心进行二相的区分,慧能也说要“能善分别诸法相”,即运用一切感官与智力对事物诸多法则进行清明透彻的观察,然后甄别、判断和取舍,这种选择就是分别决断;其次,慧能还告诉我们“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这都是指在对世间诸多法相并作出判断取舍之后,还要时时归摄到本来清净的自性中来,不要对分别起执著心而遮蔽了自性。“戒”在此即摄杂心规定。
另外,慧能提出了无相三皈依戒,即人只需归依自性三宝,而无需有外在的教律仪轨作为戒律,并将传统的佛、法、僧三宝内化为人心灵的觉、正、净自性三宝,最后以自“觉”为师,主张自性自度。由此,种种外在的戒律清规作为外相被完全清除,慧能将人对自己内心的检视和依归视为唯一的觉悟之路。
第二定。
“心地无乱自性定”,“定”来自无纷扰无分别的心,慧能将定与慧视为体用关系,并将其形象的比作灯与光:“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由此可知,定不由慧起,慧不由定生,两者要么同时存在要么同时消失。“定”在日常含义中主要指“安定”、“稳定”,是指事物某刻的状态。但在《坛经》文本中“定”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首先“定”的时间具有长久性,即恒定、保持等意;其次“定”的面积很广,即所谓“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这种“定”遍及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再次“定”的层次很深,“一行三昧”也意味着这种“定”已深入到事物的内核,只有在即常即广又深的“定”中才可能让犹如灯的光——“慧”发出来。最后慧能还指出“定”并非空定,而是持守“正念”的定。接着,慧能还对“定”中的“不动”做出了精辟的阐释:“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不动”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无情之物的“不动”。情指心灵,这种无情无心灵之物的“不动”在慧能看来是一种死寂,是空洞和无意义的,人不可仿效;二是有情之人的“不动”。这种“不动”与“动”须臾不离,此“动”是指人意识的日常状态,人的意识无时无刻的处于“念念相续”的状态之中,所以是“动”。与此相连的“不动”属于“第一义”本心的不动,此“不动”指心的本来面目,本心因为没有对“念念相续”的意识有任何沾染与执着,它不被物转,不随境迁,所以是“不动”。但这个“不动”中又蕴含诸“动”,它富有生机并随顺化生出万法,由此,本心的清净无妄使人居于自身并通达了万物,如此理解的动中之定才为真定。
第三慧。
“心地无痴自性慧”,“痴”意味着“愚”与“迷”,无痴则慧,但慧如何获得呢?对于大乘佛教而言,“慧”要通过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来修持,其中,布施在六度中居首位,这当然体现了大乘佛教的菩萨救度情怀,但慧能认为修慧比修福更重要,他认为建寺供养等修福的举措不能代替修道(修慧),并告诫人们“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慧能认为“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他始终将人对本心的觉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同时,在大乘佛教的不少经典中,成佛之路被描述的异常艰难,要发大誓愿经无量劫,累积六个十阶次功德才得圆满,但慧能指出“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这意味着人要成佛,并不需要累世的漫长修行,成佛是人以不二智慧冥契不可分的真理而豁然贯通的顿悟,而这种顿悟的发生就在一念之间。当然顿悟的发生少不了前期渐修的铺垫,但这也无疑增强了人学佛的信心。
由此看来,无论是无念无住无相或是戒定慧的修行之路,都被慧能归结到修“心”一途,明心就是觉悟本性,如此的觉悟就是成佛。
[1]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王国轩,译,注.大学 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5]孙尚杨.汤用彤选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6]杜继文.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7]彭富春.论中国的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8]太虚.佛学常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日]铃木大拙.铃木大拙说禅[M].张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0]释印顺.中观论颂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