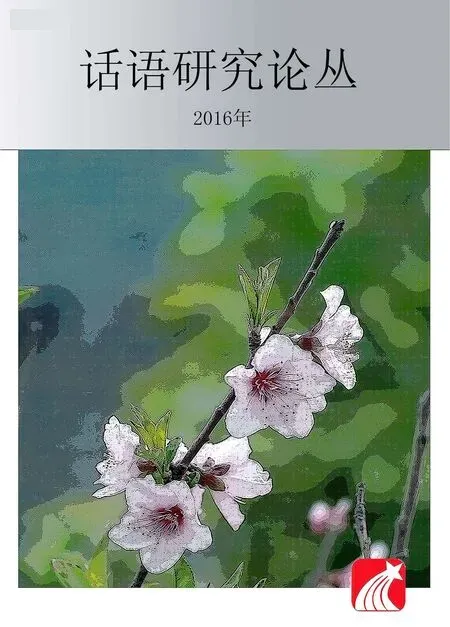象征和权力——哈葛德小说She的性别话语关键词分析
◎ 潘红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省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论文
象征和权力——哈葛德小说She的性别话语分析*
◎ 潘红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省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英国通俗作家哈葛德的小说She以独特的话语方式,再现和建构了英国维多利亚末期男女性别意识和社会权力的关系。本文追溯小说She的历史语境,以批评话语分析为视角,对小说文本中指涉女性力量的“蛇”“面纱”“她”“白色”“厌女症”和“母权”等
及其深层话语意义进行阐释,揭示小说话语所指向的男权意识和性别伦理,探究小说话语与19世纪末英国社会权力结构及意识形态的关系。
哈葛德;小说She;性别话语;女权;性别秩序
1.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哈葛德小说She
1886年10月2日至1887年1月8日,通俗作家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小说She在其时发行量超过《泰晤士报》(Pascal,2007)的英国《插图杂志》(The Graphic)上连载(第34—35卷,879—893册),受到读者热烈追捧,随即出单行本,仅1887年一年内就连续出版7个版本,之后又一版再版,直至今日从未绝版;这部小说被翻译为44种语言(包括1个世界语版本),被拍成14部电影,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小说塑造的阿霞女王——“不可违抗之她”(She-who-must-be-obeyed)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熟知,成为“霸道残忍女性”的代名词:近年BBC热播的电视剧《法庭上的鲁波尔》(Rumpole of the Bailey)就用“She-who-must-be-obeyed”来指代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女人。
小说She的情节十分奇特:剑桥大学教授Holly的同事临终前将幼子Leo和记载着家族史的陶片托付给他,陶片文字记载:祭师凯利克雷特违抗祭师不能结婚的誓约,和埃及公主私奔非洲,遇船难被土著救起,统治土著的是白人女王阿霞。阿霞向凯利克雷特示爱遭拒,出于嫉妒和占有欲把他杀死,公主逃脱后将此事记于陶片代代相传,希望后人为她报仇。Leo长大后跟教授到非洲寻宝,见到了传说中浴火永生的阿霞。阿霞苦守恋人尸体二千多年等其转世复生。而Leo正是凯利克雷特转世,阿霞为和他长相厮守,带他去沐永生之火。但当阿霞再次踏入火柱,却迅速萎缩返祖,阿霞临死前让Leo等她转世再生。
文学话语是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语言实践。小说,作为对社会生活一种审美化的言说方式,在其虚拟的话语世界里展现社会真实,再现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知识体系和权力运作方式。因此,小说话语蕴含了复杂的社会规约和权力意识,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伊格尔顿,1987:25)对文学话语的分析,就是对包孕着社会关系、权力结构的社会存在进行分析和批评,以揭示文学话语中隐含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意义。同时,话语对社会现实具有支配力量。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也体现着权力运作的效应:文学在书写社会现实之同时,以其文本审美话语中蕴含的支配力量,诉诸于人们的情感,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行为,进而以文学话语所衍生的社会权力参与社会实践,参与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建构,构筑新的社会秩序。
哈氏小说She以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历险故事,再现并建构了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社会关于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的社会规约,凸显了作者对当时英国社会性别秩序的焦虑和审视。19世纪后期的英国,正是社会变革、价值观念发生巨变的时代:工业化让女性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生活,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改变了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女性角色由传统的“家庭天使”(angel of the house)转向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new woman),冲击了一贯由男性主宰的社会秩序,女权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哈氏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再现了英国社会巨变时代,女性社会角色变化所带来的男性焦虑,展现了男性通过行使话语权为女性再度定位,并证明自身性别身份和社会权力的话语实践,折射出这一历史节点上,男性作者对性别意识和社会秩序的探索。
话语蕴含的权力关系规约着某种社会秩序,即不同群体在社会中的主体身份、社会地位和群体认同。“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王治柯,1999:159)社会意识中对于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界定反映出社会对男女性别身份和地位的认知,折射出话语权力的隐蔽存在。在话语与社会互为建构的过程中,权力关系作用其中,但“语篇与权力的关系在语篇中非常隐晦”(田海龙,2009:88),文学话语的社会影响不是直接的权力运作,而是间接地通过引发人们的情感和思想变化,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文学话语的权力运作潜藏在文本的深层,隐含在文本话语的背后。
“语篇参与社会实践、再现社会事实和构建社会关系的三个社会功能与其实施这些功能的社会语境不可分离。”(田海龙,2009:127)因此,只有将文学话语与其社会历史语境结合起来,捕捉话语深层的权力关系,才能展示文学话语对社会规约的反映和阐释,才能揭示文学话语对社会现实的支配力量、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力量。本文旨在分析哈氏小说She文本中同现的指涉女性力量的“面纱”“蛇”“她”“白色”“厌女症”和“母权”等关键词,探究小说文本所蕴含的深层话语意义,揭示小说所展现的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男女性别意识中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
2.“蛇”和“面纱”的隐喻:美杜莎、夏娃、莎乐美和女性力量
小说女主角阿霞(Ayesha)是统治非洲土著的白人女王,她沐长生之火而永生不死。阿霞美伦绝艳又暴戾残忍,她的美貌令人难以抗拒,她的残忍让人闻风丧胆,被称为“不可违抗之她”(She-who-must-be-obeyed),简称为“女王”(Hiya)或“她”(She)。两千多年来,阿霞为等待情人转世再生,生活在一座死火山下的墓穴(catacombs)之中,伴随她的除了由她通过人种生育控制而成为哑巴的女奴,只有她保存了两千多年的情人凯利克雷特的僵尸。
小说对阿霞出场的叙事安排耐人寻味:小说共28章,女主角阿霞到第12章才蒙着面纱出场,第13章才揭开面纱展露出令人晕眩的美艳容貌。小说从第3章至第11章刻意渲染了阿霞美貌和残忍的种种传说,营造出一种对阿霞既恐惧又期待的叙事氛围。阿霞的出场伴随着“面纱”和“蛇”的意象,隐含着强烈的指涉意义:蒙着“面纱”的阿霞,身姿“如毒蛇般”柔滑轻盈,腰间缠绕着一条金子打造的双头蛇皮带(a double-headed snake of solid gold)。小说中5次描述、回指这条双头蛇皮带,指向西方文学中邪恶女性的原始形象——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美杜莎(Medusa)。美杜莎以美貌勾引海神波塞冬和她在雅典娜神庙交合,辱没了处女神雅典娜的贞洁,雅典娜为惩罚她,把她的头发变成一条条毒蛇,美杜莎从此成为邪恶丑陋的怪物,任何直视她双眼的人都会变成石像。小说中的阿霞美艳无比,任何直面其美貌的男性都会失去理智、为之疯狂。“蛇”不仅邪恶凶残,也寓意着缠绕不绝的“情欲”,影射了美艳女性的邪恶魔力:女性对男性的色诱成为诱导男性走向毁灭的致命力量。因此,当男主角Holly首次看到揭开面纱的阿霞,阿霞的惊人之艳让他感到阿霞是邪恶和灾祸的化身(Haggard,1991:155)。阿霞当着前世情人Leo的面用巫术杀死了他的土著妻子,在她的尸体旁亲吻Leo,并让他当场向自己示爱,被阿霞美貌冲昏头脑的Leo则言听计从。美艳的阿霞有着强大的魔力,使男性即时失去血性、失去尊严,堕落成不为道德所约束的野性动物。
小说中的“蛇”“夏娃”等词语把阿霞王国指向《圣经》中的伊甸园:当阿霞退去衣饰沐浴长生之火时,她仿佛是赤身裸体的夏娃站在亚当面前(Haggard,1991:291)。小说中有14处用“蛇”(snake,serpent)来描述阿霞的装扮和举止,当阿霞认出Leo是她前世情人凯利克雷特的转世时,甚至兴奋得像“蛇”一般发出嘶嘶的声音。小说中复现的“蛇”意象,也引发对西方文化中原始女性形象夏娃的联想:伊甸园里的夏娃听从化身为蛇的撒旦的谗言,违抗上帝旨意偷食禁果,并诱惑亚当食用,成为违背神旨、臣服于邪恶、导致人类堕落的致命原因,人类由此世代背负原罪。上帝将两人逐出伊甸园,让他们到人间繁衍生息,并规定了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亚当须以汗水谋生、劳作终生,而夏娃则要承受怀胎生育的苦楚,并屈从于丈夫的主宰。伊甸园的失落成为男女承担不同性别角色和职责义务的起点,也是西方传统夫妻关系的最原始界定。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隐喻了男性对女性的主宰:上帝先用泥土创造了亚当,让亚当成为伊甸园的统治者和主宰者,而夏娃则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夏娃附属于亚当,上帝赋予男性对女性的主宰权柄。小说中的阿霞是引诱男性堕落、导致最后失去伊甸园的夏娃。
美艳绝伦的阿霞终日以纱蒙面,“面纱”(veil)成为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方文化中的女性面纱意味纷杂,有着截然相反的寓意:虽然新娘面纱象征纯洁、贵族面纱象征谦逊、修女面纱象征虔诚,但面纱也负载着欲望和淫荡的寓意。小说对阿霞女王纯种阿拉伯血统的强调、对阿霞“面纱”的高频复指(全文本28次)以及阿霞得不到凯利克雷特而将他杀死等情节,指涉了《圣经》中莎乐美(Salome)的故事(Matthew 14:1-12,Mark 6:21-29):先知约翰指责埃及王希律娶其兄之妻希罗底不道德,令希罗底深感羞辱和怨恨,希罗底请求希律王杀死约翰却未能成功。希律王请希罗底之女——美丽的莎乐美为他跳舞,并答应满足她提出的任何要求,莎乐美便尊从母亲意愿,要求杀死约翰。莎乐美之舞魅惑了希律王,让他信守诺言,派人取来了约翰的头颅。因此,在西方文化中,莎乐美及其“七层纱之舞”(Dance of the Seven Veils)逐渐演变为“妖妇”和“魅惑”的象征。哈氏笔下的阿霞有着同样的魅惑力和残忍计谋:她无法得到已经娶妻的凯利克雷特,她宁可毁灭他也不让别人得到,于是阿霞杀死了凯利克雷特并将其死尸保存在自己生活的墓穴之中。
“面纱”有着遮蔽性和揭示性双重的吊诡寓意:“面纱”以其遮蔽性指向其背后的真实性。阿霞的“面纱”掩盖了她的美艳,让阿霞更加神秘魅惑,也隐喻了面纱背后的真实:女性力量的祸害及其带来的毁灭和死亡。小说中失落的科尔文明崇拜真理女神,在古城废墟上,玉石雕塑的裸体真理女神洁白无瑕、双翅半展、薄纱遮面,塑像座基上的古老铭文揭示了科尔人对真理的认知:尽管真理女神召唤人们揭开其面纱,但几千年来人们追寻真理却难识其貌,真理的真正面目唯有在死亡中才能得以揭示。当阿霞再次迈入火柱以求不老之术时,却立即返祖而亡。在永生之火柱中赤身裸体的阿霞,不仅照应了伊甸园里的夏娃,也呼应了前文真理女神的隐喻:只有死亡才能揭开真理的面纱(By Death only can thy veil be drawn,oh Truth!)。
“进入男性话语的女性,是一种双重存在:既可以激发男人的审美情感,又容易引起男人的拒斥心理;既使男人萌生爱恋之心,又使男人产生鄙薄之念。”(谭学纯,2001:23)从阿霞形象的刻画,到对希腊神话里的美杜莎、《圣经》里的夏娃和莎乐美的隐含指涉,小说话语透露出将女性之美视作“祸害”的性别偏见,男性意识中的性别规约通过历史的互文得以强化,文本叙事钩织出的强势男权意识跃然纸上,指向男权中心主义的社会等级秩序。
3.“她”和“白色”的指向:女王、女权和失去亚当的伊甸园
小说书名She奇特且意味深长。“She”是女主角阿霞外号“不可抗拒之她”的简称,哈氏女儿在哈氏传记中曾对这一称呼作过解释:哈氏儿时,保姆常常用一个布玩偶恐吓他,这个被称作“不可抗拒之她”(She-who-must-be-obeyed)的玩偶威力无比,成为他儿时惧怕的对象(Lilias Haggard,1951:28)。阿霞女王因美貌和暴戾成为传奇,令非洲土著闻名丧胆,小说书名大写的“她”(She)隐含了阿霞女王无处不在的威慑力和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恐怖阴影。
哈氏写作这一小说的最初动因是为了展示“不朽女性的不朽爱情”(Haggard,1926: 245)。阿霞女王奇特的爱情故事,成为哈氏实现这一愿望的载体。阿霞以其暴戾残忍统治非洲两千多年,也以其缠绵欲望,在地下墓穴生活两千多年等待恋人转世再生。
阿霞的美艳“不可抗拒”。小说男主角——剑桥大学教授Holly对女性有着强烈的偏见和厌恶(misogynist),他首次去见阿霞时,决计要拒绝向这个异域女王行礼,但当他见到阿霞,却震慑于她的绝世之美,当即跪倒在阿霞脚下。而代表着男性之美的Leo见到阿霞,神魂颠倒,当即丧失善良,臣服于她的种种邪恶意愿。阿霞所表征的女性力量不仅来自她无与伦比的女性诱惑,也来自她的神秘巫术和残忍手段,更来自于她的聪颖睿智和无所不能:阿霞智慧过人、通古识今,她富有语言天赋,能说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英语,通读心术,能远视千里,能行医疗伤、起死回生,还通巫术,会用意念杀人。阿霞所掌握的先进科学知识赋予她更为威严的权力:她保存恋人尸体两千多年,当确认恋人已转世重生,便用硫酸化掉尸体;她还通过人种控制,让一代又一代伺候她的黑人女奴成为驯服的哑巴。按照福柯的理论,知识所及之处即为权力涉足之地:“知识不但能够增强人类的能力和进步,而且也能用来支配他人、限制他人的权力。”(福柯,1997:271)阿霞形象表征了前所未有的女权力量。
实际上,“阿霞”(Ayesha)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哈氏在小说中专门注明其读音为“Assha”(阿霞)(Haggard,1991:149),而且说明她是纯种血统的阿拉伯人,这些都指向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阿霞”这个阿拉伯名字,正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一个妻子的名字。在穆罕默德的众多妻子中,聪颖美丽的阿霞知识渊博,是伊斯兰女性的典范。穆罕默德死后,她成为理解穆罕默德思想的可靠来源,对伊斯兰教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她还参与国家政治和立法辩论,创办了第一个穆斯林妇女学校。因此,哈氏笔下的阿霞是美和恶的集合体:她既聪明美丽又残忍邪恶,既是有着坚贞不渝爱情的美丽女子,又是杀人不见血的恶魔女王。小说塑造的这样一个“她”(She),指涉了女性人格中美与丑的双重存在。
有着阿拉伯族血统的阿霞是白种人。小说中“白色”(white)一词的出现率很高,全文共出现112次,其中38处专门描写阿霞女王:描写阿霞肤色之“白”有21处,服饰之“白”17处;另有2处用snowy描述阿霞之“白”。在当时被欧洲人称为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的非洲,“白色”显得尤为醒目,与小说中出现的83处“黑暗”(dark)形成一种对照,指涉“黑暗大陆”上白人和黑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一些学者(Tabachnick,2013;Vivan,2000; Fischer 2007;Ugor,2006)认为,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这一书名借用了哈氏小说She中的词语“heart of the darkness”:在小说She中,哈氏用heart of the darkness来指非洲腹地层层叠叠的黑暗山峦(Haggard,1991:273)。“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上醒目的“白色”不言而喻地确立起一种政治权力关系,指向“白人”对非洲土著的殖民统治。小说She出版的1887年,正值大英帝国举国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也是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鼎盛时期。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铁腕统治下,英国经济强盛、文化繁荣,并将其触角伸向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黑暗大陆”非洲,英国使用一切手段扩张领土,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成为“日不落”的帝国时代。统治非洲的阿霞还有着征服英国、成为英国女王的野心。由此,读者不难从白人女王阿霞统治黑暗非洲的故事中,捕捉到对维多利亚女王和大英帝国的影射,赋予了小说性别政治的寓意。政治体现权力结构和关系,长期以来,男女两性关系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即男性统治女性。这种权力结构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米利特,1999)。哈氏作为处于权力结构中心的男性作家,面对维多利亚时代日益强大的女权,感受到了男性霸权的认同危机,以小说话语探索性别秩序、参与社会权力话语的建构。
小说中的阿霞生活在一座死火山下的墓穴之中,伴随她的除了由她通过人种控制而成为哑巴的女奴,只有她保存了两千多年的情人的僵尸。阿霞的世界是一个孤独、封闭的女性世界,阿霞统治的世界是失去了亚当的伊甸园。在这个世界里,阿霞是无人不从的女王,见到她的每一个男性都为她的美艳和魅惑所臣服,连一向拒斥女性的剑桥大学教授也不例外。两千多年来,白人女王阿霞操纵权柄统治着这个黑暗大陆,建立起一个主奴有序的独立王国。在这个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王国里,阿霞以残忍的铁腕逻辑主宰一切,她的喜好就是律法,她的意愿就是真理:“别跟我谈什么我的臣民,这些奴隶不是我的什么臣民,他们只是受我差遣的狗奴才,在我得以解脱之前臣服于我。”(Haggard,1991:153)阿霞女王暴戾残忍,对黑人土著无端杀戮,以绝对的威慑力将其王国推入丧绝人伦的野蛮之中。阿霞还幻想着将来走出非洲去英国当女王,和转世情人Leo一起统治英国。阿霞的王国是失去亚当、失去男性主宰、任由她为所欲为的“伊甸园”,亚当的缺位喻指着上帝排定的男女性别秩序遭到了破坏,女性失去约束和管制,世界失去秩序。
因此,阿霞——“不可抗拒的她”(She-who-must-be-obeyed)表征了获得权力的女性威力。哈氏以女性第三人称单数She为小说题目,其多重寓意也在此体现:“她”(She)特指阿霞女王,蕴含了令人胆战的女权力量;“她”(She)泛指维多利亚末期涌现的颠覆男性霸权的新女性;“她”(She)也指涉了整个女性群体——当女性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男性的强势生存受到挑战,男性需要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存在意义重新进行界定和规约。
文学文本记录了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轨迹,而从文学话语中剖析隐含其中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思想意识动因,可以展示这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现状和社会风貌。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工业发展、殖民扩张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社会道德和伦理关系,女权成为维多利亚社会的关注焦点,男性带着焦虑寻求自我身份和权力确认,探求英国社会转型期的男女性别伦理和社会秩序。
4.“厌女症”和“母权”的背后:“新女性”、女权焦虑和社会转型的性别秩序
男权统治下的女性角色是“家庭天使”,婚姻是她们的最后归宿,女性地位卑微,只能以沉默和顺从来接受命运的安排、以忍让和牺牲赢得丈夫的认可。工业革命使女性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维多利亚晚期,英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New Woman),她们反抗父权压制,向往自由平等,追求人格独立,为争取在教育、经济、爱情、法律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不懈抗争。然而,女性对命运的抗争,招致男权社会对女性更大的歧视和偏见,维多利亚后期的“厌女情绪”(misogyny)也愈加强烈。
小说男主角——剑桥大学教授 Holly及其养子 Leo都表明自己厌恶女性(misogynistic):Holly不允许雇女佣来照料养子Leo,Leo成年后也对女性避而远之,可一旦面对阿霞,他们却都无法抗拒其魅力,甘心服从其残忍意愿。“厌女”情绪将男女两性置于对立位置,隐含了男权体制下男性权力话语对女性的歧视和压制。男权意识将男性置于社会主宰的地位,男性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由此而来的男性话语权规定了女性的角色、掌控着女性的命运。男权意识中的女性,正如美杜莎、夏娃和莎乐美,只是激发男性欲望、诱惑男性、导致男性走向毁灭的邪恶力量。
反观英国维多利亚社会,“厌女”有其深刻的历史诱因:面对女权的兴起,男性对女性的排斥和厌恶成为男性极度自我保护、维持自身优越的一种手段。至哈氏小说She发表的1887年,英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女性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857年通过的《婚姻法案》(The Matrimonial CausesAct)首次取消了宗教法庭对离婚案件的管辖权,允许世俗民事法庭做出离婚判决,1878年的修正案又赋予女性更大的离婚自由。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Act)标志着英国国家教育制度的确立,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教育法修正对实施义务教育做出了种种规定,初等教育逐渐普及,赋予女性受教育的平等权利。1882年的《已婚女性财产法》(The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赋予已婚妇女获得、拥有或随意处理不动产或个人财产的权利。1886年的《儿童监护人法》(Guardianship of InfantsAct)又赋予女性在丈夫去世后成为儿女单独监护人的权利。这一系列的立法保障了英国女性在教育、婚姻、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权利,推进了女性的独立身份意识,涌现出一批勇于反抗传统价值体系、倡导女权的“新女性”,社会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的评判也发生了变化,女权挑战使男性深感焦虑。
哈氏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回应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小说男主角启程到非洲探险的时间是1881年,这一时间安排并非偶然,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一年,牛津大学考试开始向女生开放,象征着男性特权的知识领域开始崩溃(Showalter,1992:85)。
而传统的政治权力就是男性权力,阿霞女王的统治隐喻着政治权力向女性的转移。但当女性进入传统的男性社会活动空间,男性独霸知识领域的强势意识受到挑战,男性的自我护卫以更为强势的话语得以展示。小说男主角Holly等人踏上非洲大陆,对野性非洲的书写——狮与鳄的厮杀、射杀羚羊、血腥狩猎等场面,潜隐着强烈的男性征服欲望和好斗姿态,指向男性优越以及男权意识中的暴力倾向和强者生存法则。
阿霞统治的非洲土著“阿玛哈格”族群表面看来有着母系社会的特点,女性被看作“生命之源”,她们被免除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着主动选择配偶的权利,但女性行使话语权的所谓“自由”,仍然是在男权的规约之下,族群的首领——制定族群规约的依然是男性,女性实际上只是激发男性欲望和繁衍族群的生育工具。小说中的土著女人个个美丽非凡,她们对于男性是难以抗拒的勾引者(seducer),以美貌将男性引入歧途。族长Billali失去妻子后感到更加幸福,因自己年事已高不再成为女性引诱的对象而如释重负。不仅如此,女色还被看作是一种可以估价出售的商品(Haggard,1991:202)。因此,“阿玛哈格”族群的组织形态依然是男权统治,女性的生活和生命实际上为男性所主宰:尽管男性以更高的姿态迁就她们,但当族群中的年长女性倚老抗衡男权时,她们就惨遭杀戮,为的是维护族群中男女权利的平衡——这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女性作为诱惑和生育机器的男权逻辑。阿霞极端自私、专横暴戾、任意杀戮,影射了极端女权的灾难性后果。
在小说所再现的历史语境下,传统男性霸权和觉醒中的女权意识抗争角逐,成为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社会权力关系的一个冲突焦点。哈氏小说以文学话语预言了女权的最终走向:女权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女性的自我毁灭,正如阿霞在永生火柱中渐渐枯萎死亡。
5.结语
萨义德认为,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有着共谋关系,小说是一种文化形态,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互为成就(萨义德,2003:79-81)。体现文化形态的小说,以文学话语的方式,回应了一个时代的社会规约和思想意识,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小说所书写的社会历史,往往是正史无法企及的,因为小说话语触及的是社会的深层意识和潜在权力关系,指向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虚构的文本蕴含着历史的真实,向读者呈示了历史学家无法企及的社会内涵,正如殷企平所说:“虚构作品向我呈现了时代和生活,呈现了社会风俗和社会变迁,呈现了反映社会特征的服装、娱乐和欢笑,以及不同社会时期的荒谬之处……。即便是最高产的史学家,恐怕也无法向我呈现那么多吧。”(殷企平,2009:198)
哈葛德小说She中的“蛇”“面纱”“她”“白色”“厌女症”“女权”等词,是小说话语网络上指向小说主题的关键节点,更是指向话语所隐含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关键节点。对这些关键词的分析和批评,从一个层面阐释了小说话语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揭示了文学话语对社会的再现和建构功能。文学话语所探求的是人的自我审视,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小说She这一奇特的历险故事提供给读者的,不只是阅读消遣和大众娱乐,而是一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事实和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对人伦道德、社会秩序和生存哲学的深度思考。这是哈氏小说长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也是对这部小说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意义所在。
注释: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项目“哈葛德小说在晚清:话语意义和西方认知”(编号2013BWW01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Fischer,P.2007.The Graphic She:Text and Image in Rider Haggard’s Imperial Romance.Anglia,Journal of English Philology,125:266-287.
Haggard,L.1951.The Cloak that I Left.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
Haggard,R.1926.The Days of My Life:An Autobiography.C.J.Longman(ed.).London: Longmans.
Haggard,R.1991.She.Karlin,Daniel(ed.).Oxford:World’s Classics.
Showalter,E.1992.Sexual Anarchy,Gender and Culture at the Fin de Siècle.London:Virago Press.
Tabachnick,E.S.2013.Two Tales of Gothic Adventure:She and Heart of Darkness.ELT Journal,56:89-200
Ugor,P.2006.Demonizing the African Other,Humanizing the Self:Hollywood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ImperialAdaptations.Atenea,26:131-149.
Vivan,I.2000.Geography,Literature,and the African Territory: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Western Map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erritory in South Af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31:49-70.
[法]福柯,1997,《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凯特·米利特,1999,《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萨义德,2003,《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谭学纯,2001,话语权和话语:两性角色的“在场”姿态,《宁波大学学报》,第4期,22-27页。
[英]特里·伊格尔顿,1987,《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田海龙,2009,《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治柯,1999,《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7,《圣经》(中文和合本,Matthew 14:1-12,Mark 6:21-29)。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
潘红,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院长,福建省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文体学、批评话语分析、翻译研究。
《话语研究论丛》第一辑
2015年
第49-59页
南开大学出版社
Symbol and Power:AKey-wordAnalysis of Gender in the Novel She by Haggard
Pan Hong,Fuzhou University
The novel She by English popular novelist Henry Rider Haggard represents the features of gender politics and power relationship in the late Victorian England,which in turn,serves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values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the time.This article trac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novel and approaches th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By analyzing and interpreting such recurring key words in the novel as“snake”,“veil”,“she”,“white”,“misogyny”,“matriarchy”,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male chauvinism,gender conflicts and ethics hidden in the discourse,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the social power structure and ideology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Victorian England.
H.R.Haggard,the novel She,gender discourse,feminism,gender order
潘虹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350108)闽侯上街大学城学园路2号,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子邮件:panhong3302@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