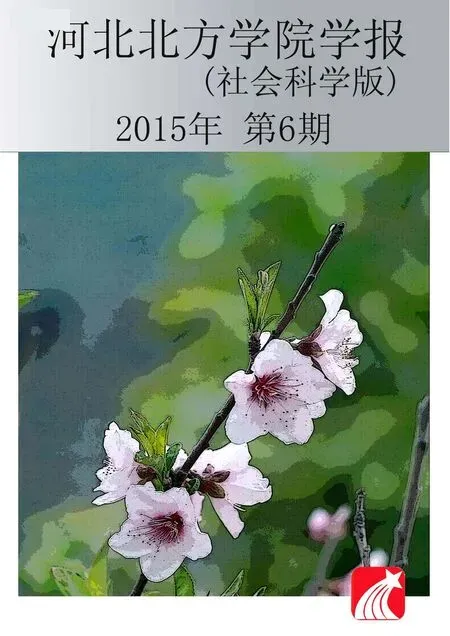《爵士乐》中的花意象研究
张 荣
(宿迁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爵士乐》中的花意象研究
张荣
(宿迁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莫里森善于在小说中使用象征意象来阐释主题,其中“花”意象尤为具有代表性。它们作为情感的承载物被使用,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赋予了小说无与伦比的美感和力量。在《爵士乐》这部小说里,托尼·莫里森创造了花的意象体系:作为核心的木槿花,象征了新黑人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作为陪衬的丁香花和玫瑰花,代表了身份迷茫的新黑人爱情的错乱。
关键词:莫里森;《爵士乐》;花意象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1130.1121.002.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30 11:21
1993年,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凭借小说《宠儿》和《爵士乐》荣膺世界文学桂冠诺贝尔文学奖。莫里森的小说构思缜密,匠心独具,《爵士乐》堪称其作品之最。《爵士乐》这部小说以爵士乐命名,并且将爵士乐本身作为小说的一种叙述策略,以即兴演奏的方式推动并解构小说悲剧的主题,从而构成莫里森特有的行文风格[1]。由于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国内学界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叙事艺术、音乐性及后现代阐释等方面,对其中的意象研究却着墨不多。在莫里森的小说里,意象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些意象内涵丰富,具有独特的个性,从另一个层面展示了小说的魅力。其中,“花”意象尤其具有代表性,往往紧扣主题,起到丰富小说内涵和确定故事基调的作用。譬如《所罗门之歌》中的玫瑰和郁金香,《最蓝的眼睛》里的蒲公英和金盏菊,无一不反映出莫里森作为女性小说家对“花”这一意象的青睐。在《爵士乐》这部小说中,莫里森更是施展非凡的想象力,构建了一套别具一格的“花”意象体系:作为核心的木槿花,作为陪衬的丁香花和玫瑰花。这些姿态万千的“花”伴着独具魅力的黑人爵士乐,貌似散见于书中各个章节,毫无章法可言,实则是巧妙烘托,对小说的主题构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木槿花——身份的探寻
莫里森在多部作品中都运用了象征意象来阐释主题[2]。木槿花在《爵士乐》中出现了5次,是小说的核心,贯穿始终,与小说男主人公乔的命运息息相关。木槿花耐贫瘠、耐旱且生命力强,象征着乔历尽磨难而矢志弥坚的性格。女作家运用意象主义手法,将乔的寻母经历与木槿花这一意象相融合,并借此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男主人公乔于1873年出生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地方,由威廉斯夫妇收养长大。他的养父母给他取了名字,却没有给他姓。他得知亲生父母消失得没有一点痕迹后,便取了痕迹(trace)为姓,穷其一生都在努力探寻自己得以存在的痕迹。年少的乔得知野女人可能是自己的妈妈后,多次在其居处寻找她的踪迹,执着于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他先后进行了3次孤独的寻母,努力想要抓住血缘这一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羁绊。14岁的乔第一次在黄昏中来到据说是母亲居住的洞穴,“木槿树浓密、茂盛而古老。木槿的花朵合上了,等待白天的来临”[3]186。木槿的芬芳如母亲的怀抱,他可以确定母亲在那儿,依稀听到了她的歌声,却看不见她,乔喊出了声,却没有人回应。第一次挫败打击了年少的乔,他选择了逃避,放弃了寻母。后来,白人烧了乔的小屋,他被逐出了家园,为了确认火灾没有危及母亲,他再一次来到母亲的居处,却仍然没有找到她的踪迹。“木槿花开得有他巴掌那么大”[3]187,对木槿树的倾诉影射了乔渴望与母亲对话的心理期待,此时野女人从尚未明确身份的母亲变为乔情感的寄托。第三次寻母,乔已与维奥莱特结婚,“在那棵树的后面,木槿树丛的后面,有一块大石头”[3]193。乔更仔细更深入地寻找母亲的痕迹,他甚至进入那个山洞,但仍然是枉费工夫。这3次寻母失败的经历给乔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挫伤,然而他将这种伤痛深埋心底,即便是朝夕相伴的妻子也无从体察。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黑人迁徙大潮开始。由于留恋南方的生活,还有放不下的寻母情愫,乔仍然在南部农场打工干活。直到1906年一战爆发前夕,贫困的生活与地主的暴力迫使乔和妻子放弃了田野和森林,北上纽约。夫妻俩幻想离开故乡避开痛苦不幸,渴望凭籍辛勤的劳动在大都市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排解失根所带来的致命孤独感。在纽约,乔以兜售化妆品谋生,维奥莱特则以上门为别人做发型为业。置身于喧闹繁华的大都市,他们渐渐迷失了自我,患上了无药可解的忧郁症。20多年生活的折磨使维奥莱特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激情,她精神崩溃,和鸟儿说的话要比和丈夫乔说的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乔试图在一个高中少女多卡丝身上寻求灵魂的新生,和她分享他的寻母经历。乔在对多卡丝的叙述中,不断地强调自己对母爱的渴望及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求而不得。小说第二章中,乔向多卡丝倾诉寻母经历,在回忆中,黄昏中木槿的芬芳似乎一直萦绕在鼻尖,母亲与木槿融为一体,“把手从树叶中间,从白色的花朵中间一下伸过来”[3]38。野女人和木槿花融为一体,母亲的手似乎从一片绿叶白花中伸出来,乔希翼以此证明他是一个有母亲的孩子,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即便这份幸福伴随着耻辱。小说第五章描述了乔生活中的7次重大经历,木槿花再次出现,寻母是乔一生坚持的信念,木槿花从花蕾到巴掌那么大再到繁花似锦暗示了乔的成长,然而母爱缺失造成的遗憾也越来越大。从少年到成年至年届半百,乔对母亲的感情和思念如木槿花从花蕾到绽放一般越发浓厚。读者在层层推进的小说情节中对主人公的心理体验感同身受:渴望、挫败与绝望,失根的虚浮,远离故土的忧伤还有大都市生活的艰辛等,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莫里森采用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叙事风格,“木槿花——母爱”这一意象组合由分散在全书的7个片段组成,没有时间先后顺序,而是通过乔的回忆被重复使用和不断深化,从而缔造了第一主题——身份的探寻。木槿花朝开暮落,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它强韧的生命力恰似母亲的坚贞、永恒和美丽;它的芬芳里蕴含着母爱的味道;它的朴实无华映射出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通读全篇,一朵朵朦胧的木槿花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串联成寻根之歌,莫里森用木槿花意象完成了对小说主人公人生悲剧的寓示。乔从小就被剥夺了母爱,这既是女作家的精巧构思,同时也是那一时代的真实写照。乔的弃儿身份、维奥莱特母亲不堪生活重负而自杀以及多卡丝的父母因种族冲突枉死等恰是同期无数悲惨事件的代表。奴隶制度以及长期以来白人对黑人的压迫导致了这些悲剧,给非裔群体的心灵带来的伤害就像烙在灵魂上的一道巨大伤口,难以愈合。失根导致了黑人悲剧性的命运,母爱的缺失影射了美国黑人对传统文化的疏离,他们所失去的是无法代替和不可或缺的,是友情和爱情都无法填补的缺口。莫里森以史为鉴,用历史观照现实,希望这些故事能够被牢牢地镌刻下来,成为“此在”的存在,而不是被黑人遗忘症所掩盖的“缺席”的存在[4]。
二、丁香花和玫瑰——爱的错乱
爱情,对于乔和维奥莱特来说是相濡以沫,对于乔和多卡丝来说是相互慰籍。维奥莱特是乔的生活伴侣,犹如空气;多卡丝是乔的初恋,恰似丁香。在西方,丁香花象征着“年轻人的纯真无邪,初恋”,“丁香花开的时候”意指气候最好的时候。盛开的丁香散发着一股细细的清香,数不清的小花汇到一起,一簇簇的柔美娇艳,绚丽夺目,正如洋溢的青春。大都市的丁香树为青年男女的爱情“伸展开丁香丛的树枝,让它们低矮得能够遮掩住你”。17岁的多卡丝正处于花一般的年纪,她酷爱流行乐,追求刺激的生活。她认为学习和工作都不是那么重要,最有价值的事莫过于向珍惜自己的人展示自己年轻的身体,而这最好在光线阴暗的丁香树丛下,让爱情、身体与丁香花同时绽开。孤独的乔邂逅了漂亮任性又活泼聪明的多卡丝,犹如吸食鸦片般上了瘾,女孩成了老男人的糖果。这种年轻和甜蜜如春日里的丁香花,焚烧着乔的心,让他忘了20年来扶持前行的妻子,而肆无忌惮地冲进了不道德的爱情漩涡。小说第五章跨越50多年,从乔出生到他枪杀多卡丝,此时丁香花再次出现,与繁茂的木槿花互相交织,勾勒了男主人公不同寻常的一生。木槿花和丁香花暗示男主人公对多卡丝的爱是出于母爱的缺失,多卡丝是乔寻母情结的延伸,她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乔深埋心底关于母亲的回忆。与多卡丝在一起,乔总记起他寻找母亲的经历,与他那疯母亲之间虚无缥缈的交流也在回忆中得以实现。乔只想牢牢地抓住这个女孩,和她分享这个秘密。他在她身上寄托了一种依恋,恰如成年男人对母亲孩童般的依恋。木槿花和丁香花的同时出现,再次折射出母爱的缺失对于非裔群体的伤害,这导致了乔对爱情和婚姻的无能为力,对婚姻的背叛以及对爱情的决绝。
在西方文化中,玫瑰通常是爱情的象征。在《爵士乐》中,少女多卡丝正如一株芬芳的玫瑰花蕾,对年届半百的乔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事实上,乔被这种难以捉摸与鬼使神差的爱情弄得神魂颠倒,既幸福又悲伤,最终在女孩移情别恋后枪杀了她。此时,“玫瑰”被赋予了矛盾性,他们的爱情不再纯粹。“玫瑰”还在维奥莱特的想象中出现:她在得知乔的背叛后,臆想乔可能会给情人买内衣,而内衣上的针脚就像玫瑰花蕾一样。表面上,“玫瑰”是美丽和爱情的象征,然而这种不道德的婚外情却伤害了维奥莱特。
爱情是莫里森小说中的一种媒介,作者巧妙地运用丁香花和玫瑰衬托主题,烘托故事的氛围,推动情节发展,并充分展现出人物的性格。莫里森通过普通黑人的爱情故事,向读者传达出那一代黑人从农村向城市进军过程中的内心世界。失去故土的新黑人在大城市中艰难地生存,生活中充斥着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的冲突与影响。种族压迫和冲突剥夺了他们的母爱,失根的痛苦使他们身份迷茫,精神空虚,传统道德瓦解。他们试图在爱情里寻找出路,以此来弥补母爱的缺失。同时,他们的爱情观也被白人强势文化左右:乔将自己的感情寄予奶黄色皮肤的少女多卡丝;妻子维奥莱特的少女情怀则寄托在外祖母故事中金发白肤的少年格雷身上。由此可见,奴隶制度、种族压迫和白人强势文化给大都市中的新黑人灵魂烙上了烙印,影响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莫里森以她细腻的情感,敏锐的观察,创新的手法和娴熟的写作技巧,悉心撷取各种“花”意象,谱成了一曲爱之歌。她用花来诠释爱,用花来唤起诗意,用花来关注社会问题。莫里森笔下的美国黑人,从南方农村到北方城市,不断地寻找自己的“根”,以期认识自我和确立身份。通过对这些黑人生活状况的书写,莫里森传达了大都市里挣扎的新黑人对传统文化的渴求,揭示了追寻母爱与重建黑人文化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维倩.托尼·莫里森《爵士乐》的音乐性[J].当代外国文学,2009,(3):50-55.
[2]谢群英.简析托尼·莫里森小说中象征意象的运用[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77-79.
[3]莫里森·T.爵士乐[M].潘岳,雷格,译.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6.
[4]荆兴梅,刘剑锋.莫里森作品的历史记忆和身份危机[J].当代外国文学,2011,(1):12-18.
(责任编辑白晨)
Image Research on the Flowers inJazz
ZHANG R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uqian University,Suqian,Jiangsu 223800,China)
Abstract:Toni Morrison is good at using images in her novels,of which the flower image is the most typical.As a carrier of emotion,the flower image contains a profound ideological meaning and also endows the novel with unapproachable beauty and power.In the novel Jazz,Toni Morrison builds the image system of flower.The central image,hibiscus,symbolizes the new black’s exploration of his own identity.The decorative image,rose and lilac,point out the confusion of love because of the lost identity.
Key words:Morrison;Jazz;image of flower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5)06-0052-03
作者简介:张荣(1979-),女,江苏宿迁人,宿迁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和美国女性文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社课题(2015SJD797)
收稿日期:2015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