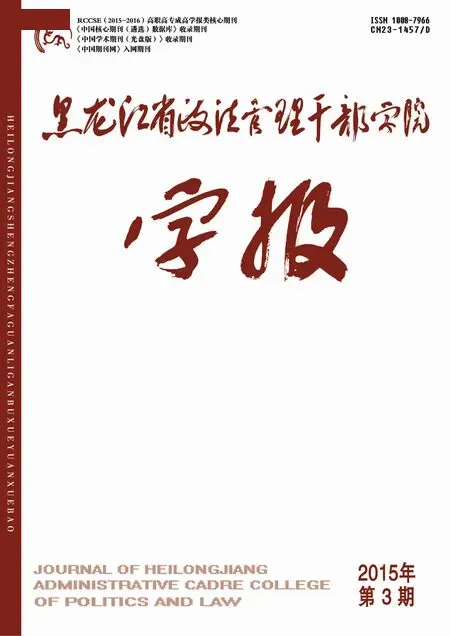对法官遴选中道德考察的反思
司马守卫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134)
“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1]作为社会正义的守门人,人民所期待的法官所应当具备的公正、廉洁、为民的道德品质即被认为是实现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必要前提。人们对法官道德素质的强烈要求使得在法官遴选阶段对法官候选人道德品行的考察成为了提升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一环。通过在遴选时对法官候选人的道德考察,选出具有高尚道德品行的法官,从而避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象的产生,提高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力:这是在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着的发生逻辑。但是,这一逻辑因过于单纯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漏洞和弊端。首要的就是如何对法官候选人进行卓有成效的道德考察的问题,这种考察是否具有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
一、法官遴选中道德考察的困境
从法官遴选机制的各个阶段和各组成要素来看,对法官候选人进行道德考察存在着多重困境。这些困境集中体现在考察标准、考察主体、考察对象、考察方法等各个方面,而且这些困境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关系。
(一)道德标准的困境
学者们普遍主张在法官遴选时对法官候选人进行道德品质的考察,这里对法官候选人进行考察所依据的道德标准既包括在法官行使审判权、进行司法活动时所应遵循的法官职业道德,也包括法官在审判工作之外的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所应遵守的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在世界各国的法官遴选中,道德标准普遍包括职业伦理和个人品行两个方面,其中个人品行又包括普通公民的一般道德素养、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等私人生活领域的道德,它是法官职业道德以外的道德要求,在许多国家,这种不成文的要求对于法官遴选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美国,法官候选人的道德操守,应是令人无可指摘的。在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法官候选人一旦陷入“道德丑闻”,那他将会被排除在法官遴选之外;同时,法官候选人的婚姻状况也会影响到法官的遴选。在日本,从律师中遴选法官时,对其进行考察的实质标准中包含有对个人人格的考核,其中包括对公正性的看法、宽容、忍耐力、慎重、灵活等。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25条规定,法官应当遵守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维护良好的个人声誉。世界各国之所以对法官这一角色施加了如此全面的、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与人们对法官的人性假设具有密切联系,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法官的神圣性是建立在对法官的认知理性和道德人格的彻底认同和无限乐观的基础上的,因为法官不是人而是神,就不会受人的自然局限,也无须外在或内在的约束。这种把法官神圣化的思想在历史上延续甚久”[2]。然而,将如此庞杂、包罗万象的道德标准事无巨细地全都运用到法官遴选上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将上述提到的所有道德标准都适用在具体的法官遴选中,那可能会产生“一官难求”的后果,因为法官毕竟是人,而不是神。
很多学者强调将道德素质作为法官遴选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其前提是将道德标准予以“量化”,如有学者认为:“在遴选法官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候选人的职业伦理道德和个人道德品质的考核,应当明确设定法官品行考核指标体系……尽管职业伦理和道德品行是抽象的,难以量化和考核,但是,只要有科学的考核指标、方法和程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3]“为切实保障司法官队伍的素质,要为司法官品行操守的考核明确设定量化指标体系。”[4]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出在这个前提上,因为道德是无法进行量化的,事实上,所有主张对道德进行量化的学者也都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方案。他们至多给出几个基本的道德词汇,如公正、无私、正派、善良、文明,而这些抽象的词汇并不具有可以在法官遴选时加以适用可操作性。
(二)考察主体的困境
由于道德考察缺乏严格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化标准,也不具有规范的考察程序,致使考察主体在对被考察者进行道德考察时难免伴有随意性的特点,这种随意性极易导致权钱交易、考察行为的形式化等弊病的产生。中国古代选官时就十分注重被选者的道德品行,如秦简《为吏之道》中记载秦代为官“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月龚(恭)敬多让”,这表明秦国以及后来的秦代对官吏的任用条件为:忠君、廉洁、为善、守信、宽厚、平和、恰当等。汉代规定丞相、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县按贤良、孝廉、秀才、明经、明法、文学诸科按名额、按时向朝廷推荐。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年),“诏天下有德孝仁忠义志信者,可以礼召赴阙,不应召者以不敬论”[5]。对于道德品质的考察是无法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进行的,当然,在隋唐以前也不存在科举考试的方法,因此,选任贤德之士的方法主要靠地方官吏的推荐,如汉朝的察举制、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而这种靠个人判断的方式最终都走向了异化的深渊。例如在九品中正制实施的过程中,被推选的主要是大地主阶级和士族的代表,品评不公,“高下任意,荣辱在手”[6],往往偏向士族,压抑寒门。因此,慢慢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从隋唐时期开始,科举制的产生使考察主体变为具有客观性的试题,这才结束了因考察主体判断的主观性而产生的弊端。我国当今现实中的对法官的道德考察也往往由于它的随意性、不确定性、抽象性而导致形式化、品评不公、徇私枉法的严重后果。
(三)考察对象的困境
我国《法官法》规定担任法官的年龄限定在最低年满23岁即可,担任基层、中级、高级、最高法院的法官本科毕业生分别需要2年、2年、3年、3年的法律工作经验,研究生需要1年、1年、2年、2年的法律工作经验。通常的情况是,大学应届毕业生通过公务员考试即进入法院成为书记员或助理审判员,在法院至多工作三年以后即可被选任为法官。这样就会导致的一个后果即是法官候选人普遍的年轻化,他们的道德素质、心智成熟度等心理状态的易变性较大。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青年阶段(20岁至35岁)是各方面都不稳定的时期。被誉为青年心理学之父的斯坦勒鲍鲁将青年期称为“疾风怒涛”的时期,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各种心理观念相互矛盾、心理倾向摇摆不定,经历着人格的多重冲突[7]。对处于这一时期的法官候选人进行道德考察,盖棺定论,“一考定终身”是不合理的,因为法官的德性是一种在法官履行道德原则和规范方面体现出来的比较稳重和持久的个人秉性和气质。而在很多西方国家中,对法官候选人进行道德考察即不存在这方面的担忧,因为作为法官候选人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甚至更大,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在法官遴选时贯彻的是“精英、经验、年长”的原则。在英国,“一个有抱负的出庭律师到55岁才能成为某种法官”[8]。按照日本法律之规定,年满40岁才能担任最高法院法官。1981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年龄为59岁,而他们任职时的平均年龄为46岁。法国普通职最高行政法官必须年满45岁才有资格当选。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其实年龄的要求与其说是一种目的,不如说是一种手段。目的是通过对法官选任年龄的界定拉动对学历、经验、品德、学识、业绩的综合考察。”[9]
(四)考察方式的困境
道德品质是一个人的内在心理状况,不可被直接观察到,任何有关道德品行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推测性的,这就涉及道德考察方式的合理性问题,即通过哪种方式才能正确、合理地判断一个人内在的道德倾向。
第一,关于考察方式的相关规定十分笼统。根据我国《公开选拔初任法官、检察官任职人选暂行办法》规定,公开选拔出任法官,应当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采用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可以采取个别谈话、发放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实地考察、查阅资料、专项调查、同考察对象面谈等方法。这里只是对考察方法进行了简单的列举,却没有具体规定可供考察主体直接采用的操作程序和方法。
第二,个别谈话、发放征求意见表等方式易受被调查者主观偏见的影响。被调查者多凭对法官候选人与自己的亲属关系、私人交情等因素对其作出评价,主观偏见、嫉妒心理、情感偏向、利害关系等不确定因素掺杂其中,使考察结果的可靠性大打折扣。有学者还主张通过社区民众的参与来对法官候选人进行个人品德的考量,但随着我国社会结构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致使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大大减弱。
第三,采取一次性的短期调查不能对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进行准确认定。俗语有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如有的学者主张的:“公务员的内在德行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道德言行才能合理地推导出其道德品行。”[10]所以,仅凭短时间的谈话、调查等考查方式难以得出值得信服的结论。
第四,考察资料的缺乏。有些法官候选人实际从事法律工作时间较短,并没有积累下来多少可以作为道德考察资料的记录。而且我国《法官法》虽然规定了法官候选人需要具有一至三年的法律工作经验,但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解释,这里的“法律工作”包括“从事国家或地方的立法工作,审判、检察工作,公安、国家安全、监狱管理、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党的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府部门中的法制工作等”,很多法官候选人根本没有参加过处理诉讼案件的活动,因而无从对其是否具有法官审理案件时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进行评判。
(五)法官职业道德的追溯力问题
法官职业道德是在法官任职以后,在行使审判权,从事审判活动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很难在一个人职业之前判断他是否具有从事某一职业的道德素养,只有“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从而才能体现出是否具备相关的职业道德。即使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也不能保证从其职业行为中可以准确判断出其是否具备作为一个法官所应当具有的职业道德,因为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法官的职业道德是不尽相同的,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律师为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从事法律活动,体现出明显的对己方当事人的偏向性,而法官则处于中立位置,必须体现出公正性。这样就会导致律师被认为因不具有“公正性”而不具有作为法官的道德素质。
二、反思后的启示
首先,转变过分强调道德考察的态度,否则可能会弄巧成拙。正像有的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对法官的人品和道德素质,虽然强调的多,但在具体如何考核和筛选方面却相对忽视了,尚没有过硬的措施。”[11]在没有健全的道德考察标准、程序、机制的情况下,贸然强调道德考察在法官遴选中的地位和作用,极有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并发问题,例如在道德考察过程中出现的考察者与被考察者之间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因为考察标准的模糊性造成的考察行为的随意性、由于考查方式的不严谨造成的认定结果不可信等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看到的那样:“在实际操作中,对候选人的考核由于缺乏独立的专门考核机构,缺乏科学的考核标准对候选人警醒全面综合审核,使得法官选任中的考核程序流于形式。”[12]
其次以法定的消极考察作为无法进行积极有效的道德考察的弥补。王利明教授曾说:“法官应当具有卫道士的气概和殉道者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3]这里就包含了消极考察的韵味。消极考察是指只要被考察者不存在可能影响其任职后进行公正审判的行为不端的记录,即可在道德考察方面不对被考察者的成功选任设置阻碍。我国《法官法》第10条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或者曾被开除公职的,不得担任法官。《公开选拔出任法官、检察官任职人员暂行办法》第8条比上述规定又增加了“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结案的”人员不得参加初任法官任职人员的公开选拔。上述几条规定既简单明了,又因存在明确的官方档案资料可查而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但是,这里也存在着的一个弊端是尚有很多可能会影响法官任职后的公正裁决的不端行为没有被明确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在法官候选人从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过伪造证据行为的、多次违反法庭纪律的、阻碍案件公正审判的都应当作为考察因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法官遴选道德考察时,是否要将候选人与法官职业无关的“私德”包含进来,例如法官候选人是否要因存在过感情生活上的“出轨”行为或者因存在过“见义不为”的行为,就要剥夺其出任法官的资格。职业道德和一般民众的普通道德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关系。“在利益多元化、价值多样性、身份多重化、国家与社会领域日趋分离的今天,传统文化中基于家国同构、私德本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逻辑,显然缺乏社会现实基础。”[12]因此,在法官遴选过程中,应当将重点放在与公正审理案件有关的法官职业道德上,而不是其私人道德。
最后,强调遴选后的道德建设和道德监督。有学者认为,法官职业需要严苛的入职门槛,同时配以相对宽松的事后管理和监督,而我国现代法官遴选的问题在于入职门槛偏低,事后管理和监督机制却非常严苛。[14]但这种观点预设的前提是设置高门槛的可能性,可以说在法官候选人学历、工作经验、知识水平、审判技能方面都有高门槛的可能性,但是道德的高门槛却难以设置。更现实,也是更为合理的方式毋宁是放低对法官候选人道德考察的标准,待选任之后再进行严格的道德监督和持续的职业伦理道德建设。如此一来,也避免了法官职业道德的追溯力问题。
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公信力的树立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官遴选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遏制法官腐败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其中涉及众多因素。……法官遴选制度只是这一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但却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15]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基于法官遴选各项制度的合理化、法官资格的提升、遴选程序的完善、遴选主体的健全、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等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施行,道德考察会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也会更加公正合理。但在这一切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之前,对待法官遴选中道德考察时的谨慎态度还是必不可少的。
[1]肖扬.当代司法体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
[2]曹刚.论法官的角色伦理[J].伦理学研究,2004,(05).
[3]王琦.外国法官遴选制度的考察与借鉴——以美、英、德、法、日五国法官遴选制度为中心[J].法学论坛,2010,(05).
[4]叶肖华,谢云生,李小伟.论我国司法官选任制度的完善[J].法学杂志,2012,(07).
[5][北齐]魏收魏书前废帝广陵王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王道国.论法官选任标准的完善[J].社会科学论坛,2006,(06).
[8][英]安东尼·桑普森.最新英国剖析[M].唐雪葆,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2.
[9]刘忠.关于法官的选任年龄[J].比较法研究,2003,(03).
[10]李春成.公务员德行考察中的认识误区[J].探索与争鸣,2012,(01).
[11]宋建朝,付向波.探索中国特色的法官遴选制度[J].人民司法,2006,(03).
[12]李立新.我国法官选任制度的问题和改革[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
[13]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51.
[15]甄树青.法官遴选制度比较研究[J].外国法译评,19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