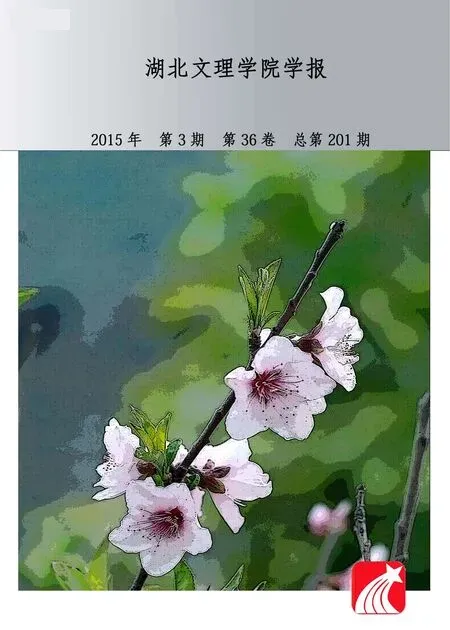试论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的心理结构
唐明生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试论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的心理结构
唐明生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主要表现了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缘由、戏曲题材的来源、戏曲的流通与传播、戏曲发展史等内容。这些内容和戏曲序跋体批评者重视戏曲文学作品的道德内容、强调其社会功用的心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者;心理结构
“所谓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就是通过附于戏曲文献正文前后,并对戏曲文献正文进行说明、议论的文本样式。它是和戏曲目录体批评、戏曲评点体批评、戏曲曲话体批评等并列的一种重要的戏曲批评文体,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一种重要载体。”[1]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伴随着中国古代戏曲文献的出现、发展而逐渐出现和发展起来。在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中,表现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缘由、戏曲题材的来源、戏曲的流通与传播、戏曲发展史等内容构成了戏曲序跋体批评的主要内容。在这些戏曲序跋体批评中,戏曲序跋体批评者的心理结构对上述内容的表达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戏曲序跋体批评的表达史同时也就是戏曲序跋批评者的心理结构展现史,戏曲序跋体批评展现了戏曲序跋体批评者独特的心理结构。
一、戏曲序跋体批评者的心理结构
戏曲序跋作者是文人,同时又是戏曲的爱好者,如果不爱好就谈不上关注戏曲、谈不上去为自己或他人的戏曲作品、戏曲选集、别集去作序。因为爱好,自然对戏曲充满着热烈的情感,渴望着戏曲能被世人认同而享受和传统诗文一样的社会地位。即使是出版商在出版戏曲选集时为了抬高戏曲选集的地位而请人写的或假冒当时的文化名人作的序跋也同样是在关注着戏曲。因为要使出版的戏曲选集、戏曲作品能够得到推介、得到大家的认可,就必须去认真地阅读戏曲,只有认真阅读了才可能写出见真章的评论、推介性文字而得到世人的认可。关注意味着肯定,至少是从心里上在暗暗的肯定。这中间虽然也不可避免会出现因为关注后而出现否定性的意见,但是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性的文字,都说明戏曲序跋作者在戏曲的发展流变史上所曾经留下的痕迹、所发出的声音。
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是由他们独特的心理结构所影响的。
中国传统文人内心的梦想就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不能立德,则退而求其次立功,不能立功,再退而以求立言。作为读书人,有思想的读书人,他们既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又是具有独立思想的阶层,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正如李春青先生在《诗与意思形态》中深情赞美的“惟有儒家学说贯穿了一种极为自觉、极为清醒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意思。他们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士人,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念系统,我们既不属于君权范畴,又不属于庶民范畴,我们是承担着巨大社会责任的独立的一群。”[2]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是中国士人的灵魂深处的一根弦,是浸润进其灵魂深处,已经内化为其性格特征的一种责任,并且这种责任具有延续性、甚或是遗传性。也就是说中国的读书人,在接受中国的“四书五经”的过程中,逐渐的不自觉的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没有人强迫、自己也不刻意为之,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已经在潜滋暗长,并最终成为充盈读书人内心的一股强大的风暴: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立功、立言具体到作家、理论家就是要标立文学的“再使风俗淳”的社会功能,重视文学的劝善惩恶的效果、强调作品的道德内容,通过作品的社会功能来再现其实用价值。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重视戏曲文学作品的道德内容、强调其社会功用一直是戏曲序跋体批评者固有的精神,它已经内化为一种心理结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存在着,在支配着你的思想、支配着你手中的笔,通过笔进而不自不觉的抒写所需要的文字。
二、戏曲序跋批评者的心理结构对戏曲序跋的影响
卡尔·曼海姆指出:“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社会群体,其任务在于为社会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我们称它们为‘知识界’。一个社会愈是处于静态,这个阶层将愈可能在社会中获得明确的身份或社会等级地位,因此,巫术师、婆罗门、中世纪的教士都被看做知识阶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在其社会中享有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的垄断性控制权,而且享有对于重建其他阶层朴素形式的世界观或调节其差异的控制权。”[3]这个论断是很有见地的,标明了知识阶层的特点:独立的思想与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控制欲望。戏曲序跋体批评的作者毫无疑问是知识阶层,他具有知识阶层的属性、承担着知识阶层的责任。他的心理结构中重视文学作品的道德内容、强调其社会功用在戏曲序跋中的表现就是通过强调戏曲是和传统诗文一脉相传的论断从而提高其社会地位;通过论述其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来彰显对民众的控制。
不管打开吴毓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还是蔡毅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序跋汇编》,在戏曲序跋中强调戏曲源自传统诗文、是传统诗文在新阶段的代表和戏曲具有教化功能的文字可以说是触目皆是。这两类文字表述构成了中国古代戏曲序跋的主轴。
(一)通过强调戏曲源自传统诗文来为戏曲正名,以“名正则言顺”来提高戏曲的地位。中国重视渊源传承,强调正统观念。诗文在传统社会中一直是正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戏曲要获得发展,就要时刻强调戏曲源自传统诗文,是传统诗文在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阶段、是诗文体在新时期的变异。虽然文体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戏曲贯穿的还是传统诗文的内核,传承的还是传统诗文的精神。
如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中言:
“世之共称唐诗、词、大元乐府,诚哉”[4]!此处罗宗信将戏曲和唐诗、宋词列于同一位置之上,并且将之作为元代的代表性文学样式而大加称赞。元·杨维桢在《<渔樵谱>序》中云:
“诗三百后,一变而为骚,再变而为曲引、为歌谣,极变为倚声制辞,而长短句、平仄调出焉”[5]。杨维桢从声韵的角度表明戏曲是和传统诗文一脉相承的,强调其在文学发展历程中新变与继承。
不管是罗宗信还是杨维桢,都在强调戏曲和传统诗文是一脉相承的,戏曲和传统诗文是可以等量奇观的,是处于一个水平线上的文体形式。元代如此,明清时期,认为戏曲同诗词同源,为戏曲正名的戏曲序跋仍然层出不穷。如明代的王骥德在《<古杂剧>序》言:
“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后律而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亦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极矣”[6]。明代的臧晋叔在《<元曲选>后集序》云:
“所论诗变而词,词变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变益下,工益难”[7]。邹彦吉在《<词林逸响>序》云:
“故雅降为风,风降为骚,骚变而汉魏有诗,诗变为李唐工律。词盛于宋,萟林之雅韵堪夸;曲肇于元,手腕之巧思欲绝。至我明,而名公逸士嗽芳撷润之余,杂剧传奇种种,青出古人之蓝,而称创获”[8]。邹式金在《杂剧三集小引》曰:
“《诗》亡而后有《骚》,《骚》亡而后有乐府,乐府亡而后有词,词亡而后有曲,其体虽变,其音则一也。声音之道,本诸性情,所以协幽明,和上下,在治忽,格鸟兽”[9]。吴伟业则在《杂剧三集序》言:
“汉、魏以降,四言变为五七言,其长者乃至百韵。五七言又变为诗余,其长者乃至三四阙。其言益长,其旨益畅。唐诗、宋词,可谓美且备矣,而文人犹未已也,诗余又变而为曲。盖金、元之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接,一时才子如关、郑、马、白辈,更创为新声以媚之。传奇、杂剧,体虽不同,要于纵发欲言而止。一事之传,文成数万,而笔墨之巧,乃不可胜穷也。元词无论已。明兴,文章家颇尚杂剧,一集不足,继以二集”[10]。
易道人在《洛神庙序》云:
“原夫风雅一变而《离骚》,再变而赋,三变而乐府、古诗,四变而近体,武五变而诗余,六变而传奇”[11]。李黼平在《<藤花亭曲话>序》中言:
“《扶犁》、《击壤》后有三百篇,自是而《骚》,而汉、魏、六朝乐府,而唐绝,而宋词、元曲,为体屡迁,而其感人心移风俗一尔。”[12]张坚在《怀纱记自序》云:
“《三百篇》后有《离骚》。骚一变为词,再变为曲。骚顾风雅之变体,而词曲之始基也。唐时,梨园弟子,惟清歌妙舞而已。自元人传奇作,则宾白具”[13]。尤侗在《<倚声词话>序》中云:
“盖声音之运以时而迁。汉有铙歌横吹,而三百篇废矣。六朝有吴声楚调,而汉乐府废矣。唐有梨园教坊,而齐梁杂曲废矣。诗变为词,词变为曲。北曲之又变为南也。辟服夏葛者已忘其冬裘,操吴舟者难强以越车也,时则然矣”[14]。
从以上列举的明清的一些戏曲序跋可知,认为诗词曲、戏剧同源的观念一直贯穿着戏曲的发展史。虽然强调的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如王骥德的“代擅其至”、臧晋叔的“其源本一”、皱式金的“声音之道,本诸性情,所以协幽明,和上下,在治忽,格鸟兽。”但不可否认的的是,强调戏曲的功用,强调其本源同一一直是其核心。戏曲序跋作者如此强调此观点其目的就是要为戏曲正名,要抬高戏曲的社会地位。在俗人的眼中,戏曲的地位是卑下的,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而诗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处于正统高雅的地位。把诗词曲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是同源相生、顺延而变,就能改变戏曲在世俗中“被卑下”的文体观念,从而拔高戏曲地位,为戏曲正名。
如果说戏曲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形式在元代兴起乃至大盛,还不被世人看好、认为其地位卑下,所以元代戏曲序跋作者在通过戏曲序跋对戏曲作者、作品进行评价、推介是为了抬高戏曲作家、作品的社会地位,为戏曲作家、作品正名。通过元代戏曲序跋的推进,明清时期戏曲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戏曲在统治者那里已经得到部分的认同,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认为豪富之家必须要藏有《琵琶记》这样的戏曲剧本以此来匡正人心,就是很好的例证。清代的宫廷戏曲也很热闹,宫廷养有专门的戏班,也是认识到戏曲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对于匡正社会风气、净化社会流俗等具有的作用。那么明清时期的戏曲序跋再一再的强调戏曲和诗词乃是一脉相承、源自诗词曲,是诗词曲在新的朝代的变体就在于对戏曲序跋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强调戏曲作为一门综合性舞台艺术在诗词的基础上的更加复杂性,就如吴伟业认识到的“要于纵发欲言而止。一事之传,文成数万,而笔墨之巧,乃不可胜穷也。”而他们的这种认识反过来又推动了戏曲的发展,强化了戏曲的社会地位。
戏曲序跋作者在为戏曲正名的时候,除了强调戏曲与诗文同源之外,还对戏曲作家予以高扬。以肯定戏曲作家或戏曲论著作家来肯定其作,从而达到为戏曲正名的作用。如虞集在《叶宋英自度曲谱序》云:
“临川叶宋英,予少年时识之,观其所自度曲,皆有侍授,音节谐婉,而其词华则有周邦彦、姜夔
之流风余韵”[15]。
虞集高度肯定叶宋英在度词谱曲方面的才能,将其与谱曲的名家周邦彦、姜夔相提并论。周邦彦和姜夔都是词学史上的名家,周邦彦被后人称为“词学之冠”,姜夔是南宋江湖词派的代表性作家,这里将叶宋英和周邦彦、姜夔这样的词学大家相比,认为他的曲有周邦彦和姜夔词的“流风余韵”以肯定戏曲作家的才能来肯定戏曲创作。
张择在《<青楼集>序》中赞扬夏庭芝:
“夏君百和,文献故家,启宋历元,几二百余年,素富贵而苴富贵。方妙岁时,客有挟明雌亭侯之术,而谓之曰:君神清气峻,飘飘然丹霄之鹤。厥一纪,东南兵扰,君值其厄,资产荡然,豫损之又损,其庶几乎?伯和揽镜,自叹形色。凡寓公贫士,邻里细民,辄周急赡乏。遍交士大夫之贤者,慕孔北海,座客常满,尊酒不空,终日高会开宴,诸伶毕至,以故闻见博有,声誉益彰”[16]。
此序对《青楼集》的作者夏庭芝从家世出身“夏君百和,文献故家,启宋历元,几二百余年,素富贵而苴富贵”、身形气质“君神清气峻,飘飘然丹霄之鹤”、与人交往“凡寓公贫士,邻里细民,辄周急赡乏。遍交士大夫之贤者,慕孔北海,座客常满,尊酒不空”以及所掌握的伶人资料“终日高会开宴,诸伶毕至,以故闻见博有,声誉益彰”等情况进行介绍与述评,高度评价其为人,赞颂其周济乡邻的善行,从而肯定《青楼集》这一优伶著录集。朱凯在《<录鬼簿>后序》中赞美钟嗣成云:
“君之德业辉光,文行浥润,后辈之士,奚能及焉。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日居月诸,可不勉旃”[17]。
此序也是从文德两个方面对《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进行了赞扬,应该说是非常高调,赞颂其德用的词语是“辉光”,称赞其文用的是“浥润”,并且说后来的人都赶不上他,即“后辈之士,奚能及焉”。当然赞扬的目的还是为了推介《录鬼簿》,从而肯定其在文坛上的地位以便为戏曲正名。
在明清时期的戏曲序跋中,对作者的肯定、赞扬、推介更是不可其数。因为在戏曲序跋中,存在着自序和他序两种情况。自序不必说,是自己为自己的戏曲剧本、戏曲选本、戏曲论著等作的序言、一般会比较谦虚。而他做的戏曲序跋则序跋作者和戏曲文献作者一般是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如为父子像丁慎行为丁耀亢传奇《西湖扇》所做的《重刻西湖扇传奇始末》;翁婿如冯肇曾为黄燮清杂剧《居官鉴》所做的《居官鉴跋》;师生如吴作梅为洪昇的《长生殿》所做的《长生殿跋》、吴秉钧为万树的《风流棒》传奇所做的《风流棒序》等。不管是父子、翁婿还是师生,一般都是后辈为长辈作序,所以本着为尊者讳的心理也会对戏曲文献的作者进行赞扬。
还有戏曲序跋的他序作者一般和戏曲文献的作者如果是同时代的就是友人关系,既使不是同时代的也是因为欣赏戏曲文献而作序跋,既然欣赏戏曲文献,就没有不欣赏戏曲文献的作者,所以在作戏曲序跋的时候难免会对戏曲文献的作者进行赞扬似的推介。
(二)强调戏曲的教化功能,肯定戏曲在惩戒人心、和谐社会的功能是戏曲序跋者为社会立言的又一例证。
“文学批评并不只对文学文本做出阐释,它还将触角伸向广阔的社会领域,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向社会发言,通过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导向,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提高读者理解现实生活、辨别美丑善恶的能力,从而维护或批判某种意识形态,推动社会的进步。”[18]
自从有了戏曲文献,戏曲的教化功能就一直被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所紧紧抓住不放。《诗大序》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强调教化作用,因此在表达戏曲的教化功能的时候,戏曲序跋也是戏曲批评家最好的文体表现形式。
在戏曲序跋的发展中,从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序》开其端一直到清代末年,关于戏曲的教化功能就一直不绝于耳,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戏曲序跋会抛弃戏曲的教化功能。如南戏著名作家高明提出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邱濬在《五伦全备记》“副末开场”中云:“这本《五伦全备记》,分明假托扬传,一本戏里五伦全。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在第29出《会合团圆》中又云:“这戏文一似庄子的寓言,流传在世人搬演。”王守仁云:“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决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诚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19]这都是强调戏曲具有教化人心、善风俗等功能的典型言论。
在戏曲序跋中宣扬“以理节情”,重视道德教化、强调戏曲作品的惩恶扬善的功能也是戏曲批评家们乐此不疲的事情。请看明代叶桠沙在《<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篇末评语》言:
“先儒谓文字无关世教,虽工何益?是编假一目连,生出千枝万叶;有开阖,有顿挫,有抑扬,有劝惩;其词既工,而关于世教者不小也,岂特为梨园之绝响而已乎”[20]。再如清代的采荷老人在《<三星园>乩序》云:
“夫传奇者,乃稗史之余,效《关雎》之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忠良者获其福报,奸邪者,蒙其显诸,赏善罚恶,丝毫不爽,乃天意之巧,不能为蛊惑,起人向往之心,发人忠诚之感,欲其踊跃慕义者也”[21]。
以上都把道德教化作为戏曲作品的主要内容,认为戏曲作品“有抑扬,有劝惩;其词既工,而关于世教者不小也”、“忠良者获其福报,奸邪者,蒙其显诸,赏善罚恶,丝毫不爽,乃天意之巧,不能为蛊惑,起人向往之心,发人忠诚之感,欲其踊跃慕义者也”的功用。把“以理节情”看成是戏曲创作的基本准则,目的就是要戏曲在社会上起到劝善惩恶、荡涤社会风气之作用,从而起到教化人心,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
戏曲具有的以表演世俗中“喜怒悲欢”之事,可以举“贤奸忠侯、理乱兴亡”,可以达到“能使草野间巷之民,亦知慕君子而恶小人”的作用。充分肯定戏曲艺术的“劝善惩恶”、“激动人心”的效果;充分肯定戏曲不仅能影响士大夫阶层,而且在人民群众中更能起到“风教”的作用。
为社会立言,为社会树立起规范和标准,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正如李春青先生所言:“儒家从甫一诞生,就是以整个社会各个阶级共同的教育者和导师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认为为全民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是他们的天职。……在他们那里,劝说人民接受统治者的教育、承认既定的社会等级,认同自己被统治者的身份的言说也随处可见。”[22]这的确是符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士人的一种天职或是实实在在的道出了中国古代士人心声的言论。
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心声,所以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份子,戏曲序跋体批评的作者也就毫无例外的通过强调戏曲源自传统诗文来为戏曲正名,从而提高戏曲的地位;通过强调戏曲的教化功能,肯定戏曲在惩戒人心、和谐社会的功能从而将戏曲融入主流社会,被上层统治者接受,从而为戏曲的扮演与传播打开方便之门。
[1]唐明生.建国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研究述评[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2(2):81-85.
[2]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9.
[3]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11.
[4]罗宗信.《中原音韵》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12.
[5]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1[M]//四部丛刊影抄本.
[6]王骥德.《古杂剧》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137.
[7]臧晋叔.《元曲选》后集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149.
[8]邹彦吉.《词林逸响》序[M]//王秋桂.善本戏曲丛刊:词林逸响.台湾:学生书局,1984:9.
[9]邹式金.《杂剧三集》小引[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459.
[10]吴伟业.《杂剧三集》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321.
[11]易道人.《洛神庙》序[M]//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1672.
[12]李黼平.《藤花亭曲话》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584.
[13]张坚.《怀纱记》自序[M]//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1706.
[14]尤侗.《倚声词话》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347.
[15]虞集.《叶宋英自度曲谱》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8.
[16]张择.《青楼集>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14.
[17]朱凯.《录鬼簿》后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18.
[18]胡亚敏.论当今文学批评的功能[J].社会科学辑刊,2005(6):172-177.
[1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3.
[20]叶桠沙.《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篇末评语[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80.
[21]采荷老人.《三星园》乩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549.
[22]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7.
On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Xu-Ba Formation Critique of Ancient Chinese Drama
TANG Mingsh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Xiangyang 441053,China)
Xu-Ba Formation critiques on ancient Chinese dramamainly reveal the reasons for its creation,sources of its theme and content,its distribution and dissemination,its development history,etc.These critiques attatch much importance to themorality of drama literature,which is related to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ir social function closely.
Ancient Chinese drama;Xu-Ba Formation Critics;Psychological structure
I207.37
:A
:2095-4476(2015)03-0042-05
(责任编辑:倪向阳)
2015-01-29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9CZW001)
唐明生(1976—),男,湖北谷城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戏曲理论。
——《贾平凹长篇小说序跋注译》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