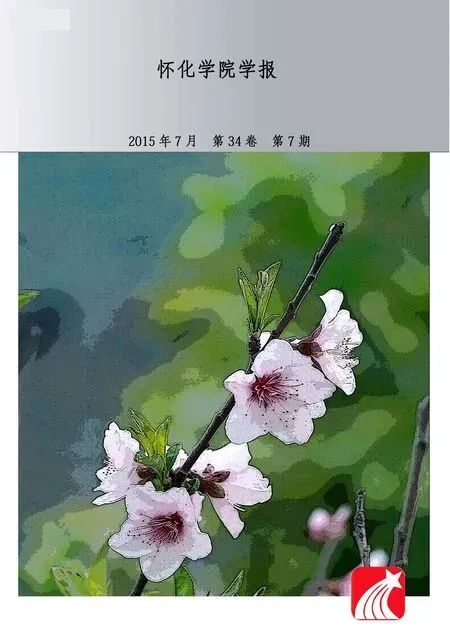论徐家干《苗疆闻见录》及其文化价值
(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550025)
“苗疆”,从古至今向来指的是中国西南部的疆域,包括云南、四川、贵州、湖南、重庆、广西等各省市的部分地区。《苗疆闻见录》中所记载的是雷山、台江、剑河、黎平、榕江、从江等地区。其中雷山素有“苗疆圣地”之称,被誉为苗族文化中心;台江县更堪称“天下苗族第一县”,这些地区史称“苗疆腹地”。古苗疆之地与世隔绝,素来很少为外界所了解。直到清朝雍正年间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积弊,当时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取消土司世袭制度,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即“改土归流”。之后,清政府在此设置府、州、厅、县等行政单位,史称“新疆”。
一、徐家干其人与《苗疆闻见录》其书
徐家干,字稚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举人出身。同治十年(1871年),徐家干赴京参加会试落选,后经同乡陈宝箴介绍,担任湘军苏元春部书记,因缘得以参加咸同苗民起义,这是《苗疆闻见录》著成的契机。徐家干随苏元春到达贵州的第二年,苗民起义遭到镇压而失败,徐家干即随苏元春部留驻今台江县施洞口,其间“师行出入,靡役不从”?[1],而后徐家干在书中的序中说到“军旅余间,略加询考,今昔情形,无甚异同,兹就耳听目睹随笔记之,曰《苗疆闻见录》”[2],这就是本书的来源。据记载,此书终于光绪四年(1878)著成。光绪五年(1879)徐家干随湘军撤回湖南;九年冬,他又调往湖北筹办江防,并任荆州太守。
《苗疆闻见录》是一本记载清朝咸同年间苗疆贵州的大小事件,书中描写了苗疆的社会历史、山川地理、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内容。此书在光绪四年成书后,深受史学家重视,曾收录于(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卷10中。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前两卷记录了咸同苗民起义的60余个重要发生地,并以这些地名为标题,记述了咸同苗民起义的大小事件;最后一卷,类似于杂记,共65 篇,后世整理出版的校注版中的标题多为校注者加上的,这65 篇内容繁杂,囊括了清代“苗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风俗、习惯、民间技艺等多方面内容。
二、《苗疆闻见录》与咸同苗民起义
前面曾说到,《苗疆闻见录》是作者随军西下苗疆平叛苗民之乱时根据所见所感而记录,而这咸同苗民起义其起因追根究底是清朝实行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自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也使得“苗疆”地区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遭到破坏。
据记载,改土归流之后,随着“苗疆”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清代雍乾、乾嘉、咸同时期,贵州苗族地区先后爆发了三次苗民大起义,其中以咸同苗民起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因此,《苗疆闻见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视作咸同苗民起义的产物。
咸同苗民起义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由苗民领袖张秀眉所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反清农民起义。咸丰五年(1855年),张秀眉领导苗民在掌麻你歃血起义,后直攻台拱厅城。他揭竿而起之后,“数万可以立至”[2]。张秀眉率起义军先后攻下清江、台拱、黄平、朗洞、丹江、凯里、八寨等地,战争波及四川、湖南、广西,清政府随后立即调集军队前往镇压。同治十一年(1872年),张秀眉在今雷山县陶窑乡乌东坡战败被俘,于1872年5月22日在湖南长沙英勇就义,他所领导的起义长达18年。
此外,历史上,贵州很早就已形成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长期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就在这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繁衍生息。然而,自古以来,这些小民族的族民就共同遭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歧视。因此当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席卷大江南北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怒火也燃烧了起来,突破了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走上了联合反抗剥削压迫的起义道路。
咸同苗民起义的主力军是这片土地上的苗族同胞,其他民族的起义军却也同样参与其中。苗族起义军与侗族、水族、布依族起义军,以及号军等各民族的起义军联合作战,谱写了一曲曲血肉凝成的民族团结的壮歌。统治者当时哀叹:“黎古军务难平,皆由土贼(侗军)与外贼(苗军)相接,大兵入境,则咸归各寨。大兵一撤,仍出没无常”[3]。
《苗疆闻见录》中对此次起义的描写是这样的:“计自有明以来,苗之‘叛’者屡矣,其出扰之残,相持之久,要以咸同间最为甚云。”[2]书中作者对此次苗民之乱的描写中,可见其规模之甚、影响之广、历时之久。
这场持久的战役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飘之战”。本书中用一个较大的篇幅描述了战争的来龙去脉,这是在咸同苗民起义中起义军打的最漂亮的一场歼灭战。这场战争发生在黄平县城东南三十里的黄飘,此地“四山环屹,异常陡峭”[2],是天然的防御之所,书中还因此举了一个例子:“苗酋雷金挡聚众作乱,恒恃此为负隅之固十数年,称深巢天险也。”[2]刚开始,湘军一路深入黔地,先后攻克寨头、镇江、清江等地,黄飘之前,军中幕僚曾根据苗疆情况认真分析了此战的利弊,认为“此地尚未可取”[2]。然而军中将领却不屑的认为:“区区黄飘,譬之破竹有余刃矣”[2]。后来,此战起义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从一方面来说是清军轻敌所致。
战争开始,清军至,“苗以数百人迎战,佯败诱之。”[2]这招诱敌之计奏效,果然清军将领“维善得意,甚一鼓深入”[2]。二万余敌人就这样一字长蛇似地全被诱入罗网。接近中午时分,黄飘四面环山的谷中山顶一声炮响,起义军伏兵四起,犹如猛虎般冲向敌人,四面擂木、滚石、飞炮如雨,“炮石交至,维善军乱不能支,败溃。”[2]后记此次战役“死亡将士约三千数百”[2],据《湘军志·援贵州篇》,黄润昌、邓子垣所领有万人,荣维善所部六千人,另合李元度旧部2 500人,合计1.85万人[4]。
回顾历史,黄飘战役在整个咸同起义过程中作用不小,虽然未能挽救1873年苗族起义军的最后失败,但其影响仍旧不可低估。在黄飘大捷后,打破了清军在这一年对起义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而使起义形势出现的危局,起义军乘胜收复了许多失地。
历史上,每一次的农民武装起义总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此次咸同苗民起义也不例外。
首先,改土归流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后,部分世袭土司不甘权力被夺取,私底下时刻图谋着反叛夺权。此书中第三卷就专门有一篇描写了苗疆土司对苗民之乱的作用,书中说到:“历来苗乱,半由土司激愤而成。”[2]其次,清朝军队接管这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部分清军却依仗职权大肆掠夺当地民众,大失民心。清政府所派流官骤然增加赋税,兴派徭役,自身又贪赃勒索等。这一点在《苗疆闻见录》可以找到佐证:“六厅之地,本无钱粮。而衙门公私等用则皆以差徭采办为例,常有产业已入汉奸,而陋俗仍出于苗户,秋冬催比,家无所出,至有掘祖坟银饰以应之者。”[2]最后,清朝政府虽派遣流官治理,但流官一来不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二来少数民族对异族的排斥,导致管理不当。
总之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官府的压榨,高利贷者的盘剥,使广大人民更加贫困,军民矛盾激化,从而点燃了起义烈火,苗民揭竿而起,地方土司也乘机反叛。
三、《苗疆闻见录》与文明的传播
“文明”是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频率非常高但又一时难以说清道明白的一个概念。有学者认为文明指的是“文化的较高发展阶段,是先进的文化所达到的一个程度,在这样的文化里,文化机体的各方面都有良好的发展。”[5]
文明的扩散与传播是人类社会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文化或文明形式从一个人类群体扩散或转移到另一个人类群体,引起他文化或他文明群体的互动,从而产生文化或文明间的接触、碰撞、适应、吸纳、拒斥、抗争、整合等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汉文明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规模传播,最早始于汉唐时期,汉武帝遣唐蒙入夜郎古国,招抚夜郎王多同,并于元光四至五年(前131~前130)在其地置数县,属犍为南部都尉。
文明的扩散与传播既表现于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表现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内部不同民族、不同族群之间,还表现于同一民族或同一族群的不同支系之间。《苗疆闻见录》一书中通过大量对苗民之乱的记述,从一个角度来说展现了以清政府为首的主流文明向西南苗民部落的传播与扩散。
首先,这种文明的传播表现为国家政治力的强力传播。清政府通过政治的方式强制推行改土归流,取消了世袭土司对地方的割据,权力收归中央。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西南苗地设台拱、清江、八寨、丹江、都江、古州“苗疆六厅”,封建王朝的势力渗透进去,也带去了别样的文明。《苗疆闻见录》中所记载之事件,皆因此而起。对苗民起义所采取的武力镇压,也可看做是以军事手段为依托的一次文明推进的过程。
其次,文明的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文明的传播还表现为接触过程中互相的融合。《苗疆闻见录》下卷,“汉民变苗”这一篇就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很好的事实证明。江楚之人“懋迁熟习,渐结亲串,日久相沿,侵成异俗”[2],传播的范围很广,“清江南北岸皆有之”[2]。
此外,文明的传播,依靠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强制力。自古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除了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威慑之外,治理化外之民最好的方法还在于“教化”,本书载有“设立义学”一文:“新府之设旧郡不同,外彝之治与内地殊异,非徒赖尔抚安,而实资尔控制”[2],“诚得治苗之要”[2],可见当权者早已深谙此理。于是“于抚安控制之中加以教化”[2]、“因地置馆,延师设教,以诗书,导以礼仪”[2],以达“日染月化,数十百年后习俗混同,斯乱机遮已矣”[2]。
总的来说,无论是本书中主要反映的史实“咸同苗民之乱”,还是以地名为纲而记录的苗疆各地的地理方位、行政归属以及经济状况等,都不仅是反映反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而是表现了清王朝通过“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强力传播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当这些文明与苗民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差异,苗民在这种文明的碰撞过程中产生的不适,都是文明传播交流的表现。
四、《苗疆闻见录》的价值分析
(一)《苗疆闻见录》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本书以纪实的方式,相当完整的记录和保留了历史事实,完整记录了咸同苗民起义这个事件,也保存了咸丰以后西南一带的不少地方史实,这对于我们了解改土归流后百余年间“苗疆”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它与王闽运的《湘军志·援贵州篇》、凌惕安的《咸同贵州军事史》、罗文彬的《平黔纪略》等相互补充,或补他书之所无,或详他书之所略,为后世还原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古苗疆苗民社会生活画卷,也保留了黔东南苗、侗等少数民族的许多民族关系史资料。
综上所述,《苗疆闻见录》不仅在苗学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同时也印证和补充了清代苗疆文正史。
(二)《苗疆闻见录》保留了西南少数民族许多重要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
《苗疆闻见录》下卷中,有多篇文字记述了古苗族人民的服饰、婚姻、饮食、技艺等内容,使后人对古苗疆的民风民俗有所了解。如清水江流域的台江、锦屏一带,划龙舟习俗古已有之。书中记载台江等地苗族“好斗龙舟,岁以五月二十日为端午。竞渡于清江宽深之处”[2]。关于龙舟形制,“其舟以大整木刳成,长五六丈,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中能容二三十人,短桡激水,行走如飞”[2]。侗族地区由以地域为纽带的村与村、寨与寨组成,并以军事防御和武装保卫共同利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曰“款”,又曰“门款”。本书载:“曰水口,曰南江,曰古邦,曰高岩,号称四脚首寨,余各随所近者附之……凡地方有事,须合众会议者,则屠牛分四脚传之以为之约,因即以四脚牛名。”[2]这种古老的社会组织对于维持村落治安秩序,整合民族精神文化,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清代,随着贵州清水江流域的开发,带来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互动和交流,甚至婚姻往来。本书记载:“其他有汉民变苗者,大多江楚之人。懋迁熟习,渐结亲串,日久相沿,浸成异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所称‘熟苗’,半多此类。”[2]历来文献多记载少数民族文化被“汉化”,而这里却记载了汉族同样学习少数民族文化。这些资料在民族学研究中具有十分珍贵的参考价值。
(三)《苗疆闻见录》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书中有许多对苗疆山川地理的描写、对苗民依据天险对抗官兵的描写,这是由于要掌握苗民起义军的作战部署需要结合苗疆山川地势的情况,徐家干除了要亲下苗疆,还要特别注重对地理情况的考察。书中记述地名并通过这些重要地名来反映这次起义经过的内容约占了本书篇幅的三分之二,如描写台拱厅,“迤西而北而东,山峰屹立。厅南乌尧坡高数百仞,山峻溪深,寸步百险。西南平衍,灯火万家”[2]。书中对于山川之势的生动描述,虽不是为达文学高远之境,而是详实描述了苗疆山川之险以为清军提供一个行军参考。但其细腻的笔触,将苗疆山川之险描绘得淋漓尽致,文字简练、形象生动,有其独特的风格,可使人们从他的描绘中,有身临其境之感,确实有值得人们去学习与借鉴之处。其次,书中对战争场景的描述更是有声有色,战争情节生动,风格粗犷,通俗易懂;而对人物的描写又是细腻的,能够抓住人物最具特色的一面,以上所述,都表现了《苗疆闻见录》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
五、结语
该书就像一部清代贵州苗疆地区的简明通史,篇幅不长,却能让人对清朝咸同后期的苗疆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方面都有所了解与认识。苗疆在人们的印象中,总带有些神秘,古苗民更是一群神话般的存在,但这本书从生产生活、社会生活等等角度描写了苗民或淳朴、或剽悍的形象,反映了苗族社会生活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特点。
虽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中内容或许不尽真实,作为一位封建文人的著述,由于受到阶级、民族及时代的局限,书中不免会记录一些消极、错误的东西,但书中也体现了一些积极思想,通过这本书使人们了解到许多从前不曾了解的苗疆人和事,也算是一种难得的收获。总之,人们只要端正自己的立场,带着鉴别的眼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实自己。
《苗疆闻见录》历经百年,虽然时代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变异,但它却能一直保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传承性,直至今日。《苗疆闻见录》在1997年出版了校注版,这个版本更是为学者们深入研究苗疆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便利。
[1]陈延安.《苗疆闻见录》价值略说[J].学理论,2010 (22).
[2]徐家干.苗疆闻见录[M].吴一文,校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3]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M].贵州:慈惠图书馆,民国21年(1932).
[4]王 运.湘军志·援贵州篇[M].长沙:岳麓书社,1983.
[5]彭宏.社会科学大词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