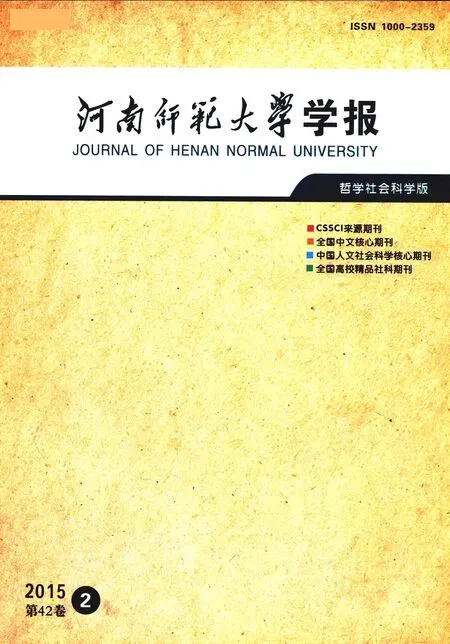论唐代科场符瑞类试赋的现实观照
王士祥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唐代科场试赋内容丰富,就《文苑英华》所收录之40类主题而言,与现存科场试赋直接相关者达17类。这些主题大都围绕帝王展开,是对前朝或当时帝王政治、文化生活的反映,体现出了试赋的时代特征。在唐代科场试赋中,符瑞类主题在实现朝廷选官的政治目的时,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观照,足见命题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现实需要。
要对符瑞类试赋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白何为符瑞和明确此类赋在唐代科场上的留存状况。所谓符瑞即吉祥的征兆,是古人心目中天人感应的某种呈现。如汉朝的谷永在其《灾异对》中指出:“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藉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百姓寿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1]376符瑞出现与否与王者能否推行仁政紧密相关,这就是刘辅在《上书谏立赵后》中所云“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1]394。关于这个问题,班固在《白虎通义》卷五中亦云: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允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荚生,秬鬯出,太平感。[2]
这段话不仅明言符瑞是在“天下太平”之时且“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允塞”的情况下应“王者”之德而出现的,而且指出,因为“德至天”或“德至地”的不同,符瑞还会表现出物象与天象的区分。
无论是物象还是天象,均表现为瑞象。这是对一个时代气象或王者政风的颂美,甚至是帝王受命的征兆,因此受到有心者的青睐。在传统历史文献中关于符瑞的记载可谓多矣,甚至沈约在《宋书》中专列《符瑞志》三卷,详尽列出了自太昊至宋孝武帝期间的符瑞现象。这些现象多印证了“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的理论,因此沈约强调“符瑞之义大矣”[3]759。既然如此,历代莫不对充满神秘感的符瑞表现出重视,唐朝以之为题进行官人选拔考试便是重视的具体体现之一。
据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统计,在《文苑英华》“符瑞”类中直接收录的试赋有开元四年(716)进士科所试《丹甑赋》、开元二十七年(739)进士科所试《蓂荚赋》、建中元年(780)文词清丽科所试《指佞草赋》、贞元十三年(797)进士科所试《西掖瑞柳赋》。四题显系“德至地”而产生的符瑞。《文苑英华》中所收录的宝应二年(763)进士科所试《日中有王字赋》、大历四年(769)博学宏词科所试《五星同色赋》以及贞元十二年(796)进士科所试《日五色赋》虽列于“天象”类下,但据上引班固《白虎通义》语判断则当属“德至天”而产生的符瑞。据《文苑英华》统计,两类试赋共存录16篇。只是这16篇符瑞类试赋均为省试赋,在解试赋中尚未发现此类主题。
综观唐代科场符瑞类试赋可以发现,此类试赋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换言之,作为严肃的政治活动,此类试题并非随意设置的,而是与当时的具体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关。就现存符瑞类试赋来看,开元四年进士科所试《丹甑赋》、开元二十七年进士科所试《蓂荚赋》属玄宗时代,宝应二年进士科所试《日中有王字赋》、大历四年博学宏词科所试《五星同色赋》属代宗时代,建中元年文词清丽科所试《指佞草赋》、贞元十二年进士科所试《日五色赋》、贞元十三年进士科所试《西掖瑞柳赋》属德宗时代。通过文史互证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命题折射出了不同的时代需要。
开元年间,玄宗励精图治,创造了李唐王朝的“全盛日”。诗人杜甫在《忆昔二首》其二中感慨当时“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4]。虽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所引柳芳《唐历》可知杜诗所回忆者当属开元后期,但玄宗初期亦采取有积极的劝农措施,如《新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元年正月辛巳,皇后亲蚕。”[5]122“皇后亲蚕”看似象征性的活动,实则表达了朝廷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态度。在这种背景下以《丹甑赋》为题选官,无疑表现了朝野对丰年的渴望。沈约《宋书·符瑞志下》云:“丹甑五谷丰熟则出。”[3]852唐人崔融在《代皇太子贺石龟负图表》中亦云:“百宝用而银瓮满,五谷丰而丹甑出。”[6]也就是说,丹甑的出现往往象征着五谷丰收,所以史翙在赋中说:“应皇运而无疆,报时丰于有国。”[7]391在农业社会,希望丰收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不过从史翙赋中“天应灵贶,人期至丰”句来看,《丹甑赋》所限韵脚“国有丰年”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美好的心愿,或者说当时相较以前已经表现出丰年的势头。
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玄宗开元后期终得复振“贞观之风”,“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抱怨”[8]236,这种太平景象通过开元二十七年的《蓂荚赋》进行了歌颂。文献记载,尧为天子,蓂荚生于阶下;后来,周公作乐而天下治,蓂荚再现。李善注《文选》张衡《东京赋》“盖蓂荚为难莳也”句云:“蓂荚,瑞应之草,王者贤圣,太平和气之所生,生于阶下。”[9]此时以《蓂荚赋》为题,并非单纯追模尧帝盛世,而是意在突出当下承平,其实程谏赋中所云“盖历代而难值,至我后而斯呈”[7]399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吕諲在赋中亦指出“惟我后之钦若,亦合符而受赐”,突出了蓂荚的现实意义,即玄宗朝大道已行,主圣臣忠,所以才会通过蓂荚“表皇王之瑞”。
安史之乱中,肃宗长子李豫“常从于兵间”,并于乾元元年(758)四月被“立为皇太子”。肃宗崩于宝应元年(762)四月丁卯日,皇太子李豫于己巳日“即皇帝位于柩前”[5]167,是为代宗。其时不仅“余孽犹在”,而且多处叛乱,可谓内外交困。对于刚刚即位的代宗,树立自己的权威成了当务之急。宝应二年进士科所试《日中有王字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仅凭题目中“日中有王字”已经不难窥见朝廷借日颂君维护代宗权威的意图了。乔琮赋云:“至尊者王,至明者日。处其位兮无二,配其德兮惟一。”[7]16太阳与帝王都是独一无二的,将帝王与太阳对等,巧妙地将颂日和颂君融为一体。日中王字的出现必在王者“布德而上通”之时,其意义在于“昭宸聪,彰国风,焕乎黄道,赫矣苍穹,表皇纲之不紊,延圣祚于无穷”[7]17。郑锡赋中也认为,日中之王字“乃圣人合契,至化玄通”,“因嘉瑞以增德,合元符而降祚”,而大明“吐象成字”时正呈现出“河清海晏,时和岁丰,车书混合,华夷会同”[7]16的社会特征。这无疑是对代宗权威的宣示!
安史之乱平定后,代宗朝并未迎来全面和平。据《新唐书·代宗本纪》记载,自宝应二年七月始,吐蕃数次作乱,先后陷陇右诸州、邠州,“寇奉天、武功”,至十月甚至“陷京师,立广武郡王承宏为皇帝”[5]168。此外,尚有诸多内忧外患,仅以永泰元年(765)而言,正月“歙州人杀其刺史庞浚”;“二月戊寅,党项羌寇富平”;“七月辛卯,平卢、淄青兵马使李怀玉逐其节度使侯希逸”;“八月庚辰……仆固怀恩及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寇边”;九月“甲辰、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项羌寇同州,浑、奴剌寇盩厔,京师戒严”;十月“己未,吐蕃至邠州,与回纥寇边。辛酉,寇奉天。癸亥,寇同州。乙丑,寇兴平”;闰月“辛亥,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旴反,寇成都”[5]171-172。内忧外患使和平成了人们最殷切的期待。大历四年博学宏词科所试《五星同色赋》便是朝廷和平愿望在科场上的文学书写。《史记·天官书》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10]五星同色是天下和平的象征。现存崔淙赋认为,五星之所以会出现同色瑞象是因为“我后运乾之符,握坤之纽,表正万方,肇康九有。启土继圣,乃人和而岁阜;顺时立政,故天长而地久”[7]42和“我后修五礼,偃五兵,君臣一德,歌舞以行。斯仓斯廪,如坻如京。玉衡正,太阶平”,只有帝王多行王道,惠化万民才能引起上天的感应,“遂使金也、水也,不能知白而守黑;木也、火也,不能全曜而自贞。乃并用而丕变,与黄中而同明”。在崔淙看来,五星同色不仅是“助我后夙兴之勤思”,也是“表圣皇夜寐之勤政”。需要指出的是,两《唐书》中并未记载大历四年或此前出现过“五星同色”的瑞象,因此以“五星同色”为题应属更多地反映了和平的愿望。
“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皇太子于癸亥日“即皇帝位于太极殿”[5]184,是为德宗。德宗初即位便“贬常衮为河南少尹,以河南少尹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5]184。据《新唐书·崔祐甫传》知,祐甫“性刚直,遇事不回”[5]4667,特别与常衮积怨已久,因此一旦任相即革惩前弊。崔祐甫当国之前,“官赏缪紊”。具体来说,“元载用事,非贿谢不与官,刬塞公路,纲纪大坏”,常衮登相位后,虽然“惩其弊,凡奏请一杜绝之”,但“惟文辞入第乃得进”,结果造成了“无所甄异,贤愚同滞”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崔祐甫“荐举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莫不谐允”[5]4667,崔祐甫的举措相对此前自然是新气象,因此赢得了德宗的赞许。建中元年(780)文词清丽科所试《指佞草赋》也是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进行的。指佞草原名屈轶草,因佞人入朝则屈而指之,故又名指佞草。这种草代表直道的品质,故梁简文帝《大法颂》云:“草名指佞,便辟去朝;兽称触罪,奸回放黜。”[1]3022在朝廷中,佞与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品格,梁肃赋称:“佞者,小人之道;直者,为国之宝。”[7]399在当时人看来,以元载为首的官场充满了佞邪之气,虽有常衮“惩其弊”,但又因其个人好恶造成了新的弊病。崔祐甫颇似指佞草,登位宰相后使“便辟去朝”“奸回放黜”,官风为之一振。指佞草同其他符瑞一样,逢时效灵,其出现意味着“圣泽濡煦”的时代特征,昭示了德宗亲贤臣的意愿。即沈封赋中所称的“所以彰吾君之睿圣,所以表吾君之徳馨”[7]400,只有“勤施五至,克奉三无,多忠良之士,绝谗佞之夫”,才能营造出郑辕赋中所写的“野退宵人,朝多髦士,同鱼水之合契,绝螮蝀之莫指”[7]400政治氛围。所以,《指佞草赋》的意义一在歌颂德宗所用得人,二在礼赞崔祐甫举措得力。当然,应试者没有忘记化身灵草,像沈封赋中所说的那样“君子在位,我则恭默以倾心;佞人入朝,我则无私以直指”,去辅佐帝王实现大化的盛世。
德宗继位之初雷厉风行,大有图强复兴之志,但是后来随着改革屡屡受挫,施政风格大变,由最初信任宰相演变为猜忌大臣,甚至形成了拒谏饰非、刚愎自用的性格。《新唐书·德宗本纪》称:
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5]219
前后变化令人瞠目!尤其是贞元十年(794)以后,裴度、李逢吉、王涯、崔群、李夷简、令狐楚相继为相,人事变动之勤已经充分暴露德宗“猜忌刻薄”的品性和直道难行于世的事实。贞元后期,德宗已经习惯了谀颂之声,有心之人自然会投其所好。贞元十二年进士科所试《日五色赋》便迎合了德宗的心理需要。此赋题出《礼斗威仪》:
政太平则日五色,政颂平则日黄中而赤晕,政和平则日黄中而黑晕,政象平则日黄中而白晕,政升平则日黄中而青晕。[11]
从题目出处不难知道此题意在歌功颂德。李程以《日五色赋》被擢状元第,他不仅破题以“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八字将颂日与颂君不动声色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且接下来“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验瑞典之所应,知淳风之不遐。禀以阳精,体乾爻于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气于皇家”[7]28几句也是时刻将太阳与君主对举,或以太阳比喻君主,或用太阳彰显君德,塑造着皇家的太平气象。另外,赋中还有诸如“舒明耀,符君道之克明;丽九华,当帝业之嗣九”,“浩浩天枢,洋洋圣谟,德之交感,瑞必相符”,“天有命,日跻圣,天阶平,王道正”,“设象以启圣,宣精以昭德”等句,同样是在不遗余力地借颂日宣扬皇家的恩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日五色赋》考试当年还是之前,德宗时代均未出现承平景象,反而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5]219。所以,此题与大历四年博学宏词科所试《五星同色赋》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用浪漫主义笔法表达了时人对承平的呼唤。
相对于贞元十二年的《日五色赋》而言,次年的《西掖瑞柳赋》则具有强烈的写实性。两《唐书》均记载有吕渭以瑞柳为题试进士事,《旧唐书·吕渭传》载:“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死,兴元元年车驾还京后,其树再荣,人谓之瑞柳。渭试进士,取瑞柳为赋题。”[8]3768此题限以“应时呈祥,圣德昭感”为韵,八字与题中“瑞柳”二字共同体现了主考官的命题旨趣。考生只能顺着颂圣的思路构思行文,这应该是每一个考生都能意识到的问题。故陈诩赋开篇即云“柳变西掖,瑞彰圣时”[7]396,将柳的枯而复荣与圣时紧密结合了起来。德宗圣驾巡游未转时,这棵柳树“独孤凋而枯瘁,似永隔于风光,无絮花之似雪,意膏露之疑霜”,完全处于枯瘁的状态;可是当“千官捧日以输忠,万姓从龙而翊圣”之际,这棵枯柳却在“彼众芳之已歇”时独“得秋而始盛”,表现出“异于常材”的生机。这就是郭炯在赋中所说的“当圣泽未沾,故兀然枯瘁;及天光回照,遂蔼尔敷荣”[7]396。
可是主考官吕渭用心良苦的溜须拍马并未能赢来德宗的赞许,《新唐书·吕渭传》称:“帝闻,不以为善。”[5]4966因为这个题目让他再次记起了当年奔逃的耻辱,兴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丁卯,如梁州”[5]190,至七月德宗始返京师。这就是陈诩赋中所言之“望车尘之行幸,慰都人之怨思”和史书中所谓之“兴元元年车驾还京”。作为帝王,因避乱远离京师本就不是光彩之事,又在十余年后被再次提起,所以与其说是借瑞柳歌颂皇恩,不如说是因瑞柳揭露了伤疤。也是在兴元元年,德宗在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问题上颁诏罪己:“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12]公开声明自己失道、不君,并从此调整了对方镇的政策,作为皇帝的德宗已然颜面无存,又何来至德动天使“枯朽效祥而发生”呢?所以,如果贞元十二年的《日五色赋》重在务虚的话,贞元十三年的《西掖瑞柳赋》则必然会勾起德宗真实且不堪回首的记忆,那么“不以为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不管如何,我们不能否认《西掖瑞柳赋》与当时现实的联系。
通过以上考述,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分布于玄宗、代宗、德宗三朝的符瑞类科场试赋与命题时的政治背景或文化背景有紧密的关系,是当时时代氛围在科举考场上的文学呈现。主考官结合时代大背景设置试题,无论是歌颂真实的盛世还是寄寓美好的愿望,无不体现出了对现实观照的意义。总之,看似简单的科场文学创作,实则是服务于时代需要的政治书写。
[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班固,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283.
[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874.
[4]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759.
[5]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2201.
[7]李昉,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8]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萧统,李善,等.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65.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322.
[11]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15.
[1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7391.
——以清代江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