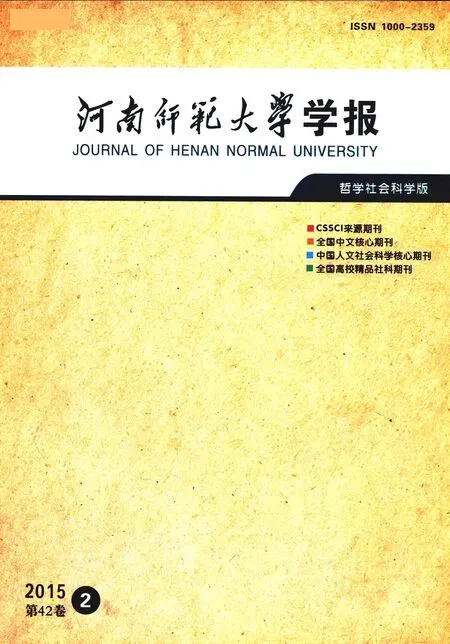魏晋自然观与“秀骨清像”
张 俊 沛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魏晋自然观与“秀骨清像”
张 俊 沛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魏晋六朝时期美学的重大突破之一,便是实现了自然的人格与自然的审美态度相统一。对自然的人格的追求与熔塑,促成了士人对“秀骨清像”的追捧,对自然美的热衷形成了魏晋所特有的新自然观。这既促进了山水美学的繁荣,又带来了文学、书画艺术清新脱俗的新面貌,并且对整个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走向及审美标准的确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秀骨清像;自然观;虚无;虚静
以“秀骨清像”为代表的魏晋风度试图通过言行、诗文、艺术来展现士人的精神气韵,用自然朴素的艺术风格来体现自然的人格,是魏晋士人的自然主义美学观的表现形式之一。对“秀骨清像”审美标准的追捧,同时也引发了对自然美的热衷,形成了魏晋所特有的新自然观。
魏晋六朝的文学家和美学家所以能够把自然的人格与自然的审美感悟交融成一体,把人品与文品至于统一的高度,除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变迁因素,从思想根源来说,是这些文人自然意识的觉醒。自然真率的情感抒发,才能实现人格的独立,创作的作品才能真实感人[1]。本文旨在分析“秀骨清像”与魏晋自然观所共通的思想根源,开掘其对山水美学及文学、书画艺术的深层影响。
一、“秀骨清像”中的自然观
“秀骨清像”源自唐代张怀瓘在其《画断》中对陆探微绘画的评语:“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矣。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虽妙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像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2]陆探微的”秀骨清像”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人物清秀瘦削的体貌和清圆有力的绘画用笔;第二,精神层面的理想人格,也即人物内在的清刚、峭拔、智慧超脱的精神品质。所以当人们面对画面时会产生“令人懔懔若对神明”的感觉。其实“秀骨清像”的意义远不止于绘画,它具有浓厚的魏晋时代色彩,是对文雅俊逸、超凡绝尘的气质以及不可言说的智慧与精神的解读,也是具有超然自得、高不可攀的魏晋名士形象的代名词。分而述之,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有其明确的指代性,例如“清”“秀”及“骨”皆为魏晋人物品藻词汇中最常用的词,在专门记载当时士大夫言谈轶事的《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例如,王羲之“风骨清举”,温娇“标俊清彻”,嵇康“风姿特秀”,王衍“岩岩秀峙”等。
凡“秀”,皆清、明、朗,而非含糊、暖昧。所以多组词为清秀、明秀、秀朗。人的形象不俗,必有骨秀,骨粗俗,人必粗俗,诗文书画皆然。秀才者,腹中必有诗书学问的内涵,即内有秀骨的表现。诗文书画皆如此,结构含糊不清、层次不明,都不能被称为佳作。《文心雕龙·隐秀》有云:“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玉和珠潜在水底,而水上之波纹则方圆有异。由此可见,“秀”虽隐于内,但其外在气质必然不俗。它常与“清”字合用,如“山清水秀”“眉清目秀”等。而“眉清目秀”作为一种美的类型,显然不同于“浓眉大眼”的那种阳刚之美,更非赘肉满身者。凡秀者,必有清瘦的感觉,这也一语道出了魏晋所崇尚的美之特征[3]。
骨的本义是骨骼,后来与相术结合,汉人以骨法相人,所谓“人之贵贱在于骨法”。东汉王充的《骨相篇》有“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4]。在魏晋时期,“骨”进入人物品藻之范畴,用来评价人的个性、气质、精神和品格。《世说新语·品藻》论:“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5]这里的“骨气”正是指人的一种气宇轩昂的精神风度,即“神”。与此同时,“骨”也进入了书画的品评。顾恺之的《论画》一篇,几乎每一画皆注意到“骨法”。评《周本纪》“重叠弥纶有骨法”,《伏羲·神农》“有奇骨而兼美好”,《汉本纪》“有天骨而少细美”,《孙武》“骨趣甚奇”,《列士》“多有骨俱”,《三马》“隽骨天奇”等,皆以“骨”来品评绘画艺术。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也多次论及“骨”,如“曹不兴……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张墨,荀勖……但取精灵,遗其骨法”,“江僧宝……用笔骨梗,甚有师法”,等等[6]。
“骨”的概念,从生理骨骼到相术中的贵贱之体;到人物品藻中的精神气质和品格美;再到书画艺术品评中骨法用笔的线条美,及构成画面总体“气韵”的关键因素,“骨”已转化为一个彻底的美学概念。
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象征意义。当“清”这个概念被崇尚水德的道家崇高化后,它便与静、明、虚、淡结合,成为中国人提升道德修养,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必由之路,最终达到一种清静自然的最高境界。魏晋人有着浓厚的尚“清”情结。钟嵘评诗,尚用“清雅”“清拔”。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讲,具有“清气”的画,其品格自然不俗。由此,“清”成为魏晋时期最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清像”一词也包含内外两层涵义,其一是外显的超凡脱俗、质朴天真的气质风范;其二是内在的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的品德情操、志向报负。
研读以“秀骨清像”为特征之魏晋士人的内在修为,自会引出两个关键词。其一是“虚无”。虚无是自然的核心,是对有的超越,所以它代表了一种超尘拔俗的境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是一种恬淡宁静的心境,表现着精神领域最深处的智慧和情操。在文人的视域中,只有圣明之人以其独有的神明才可体悟并拥有,所以这种超越的精神境界成为魏晋士人的毕生追求;但魏晋时代背景下的“虚无”,也有其负面的形态,如果把它从理性思辨的立场转换到人的情感、情绪领域,就变成了晦涩、抑郁、荒凉、苦闷与分裂。第二个词是“虚静”。“虚静”是心境自然的呈现。《庄子·天道》有云:“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圣。”又云:“水静犹明,而况精神。”“休则虚,虚则实,实则备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7]85虚静则空灵明澈,面对惊涛骇浪,内心保持虚静空明的状态。“涤除玄览,能无疵乎”[7]125,排除私欲成见的干扰,作深远的观照,以察知事物变化的真相。“虚静”更深的意义是暗指一种沉稳、安定的人格形态,庄子把这层意思透辟地发挥了。《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应帝王》中讲了:“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8]70即通过对道的领悟和把握,保持虚静的心态,塑造稳定的人格修养,培养超越的人生境界。
抛开时代精神中的负面内容暂且不论。魏晋六朝士人的理想即是,拥有虚静的心态、沉稳的人格,到达超越凡俗的“虚无”境界,既能飘然于四海之外独来独往,又能沉潜于世俗畅游无阻,随遇而安。这既是举手投足间自有的一种飘逸雅致的“清像”,更是平淡、从容、镇定的“秀骨”所展现出的魅力。由此也可以总结,“秀骨清像”更倾向于对人内在素养的注重。按《晋书》本传,王导之子王恬,字敬豫,“王敬豫有美形,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王恬少时好武,因此不为公所看重,王导看见他就忍不住发脾气,对他表示不满,感叹其才与貌不相称。此例道出了在魏晋士人眼中,仅有美的形貌是不够的,人物之形,要与人物内在的文化素养、才情风度相一致。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论,“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9]。
二、山水美学中的自然观与士人人格美
清玄世风所及,魏晋六朝刮起了一股乐山乐水的热潮,山水在士人眼中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山水神秘无限,给人自由、洒脱的遐想;林木葱郁,给人出世的清新之感;清风朗月,给人纯净澹然的审美感受。且山水林泉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非常符合老、庄清静自然的哲理,崇尚老、庄,或归于山林,或“登山临水,竟日忘归”[10]67,成为魏晋士人的追求。而山水美学中更是包含了很多和“秀骨清像”的人格之美相通之处,且人格美与自然美密切相关,自然山水成为人借以达道的媒介。
其一,由于对山水自然美的向往,魏晋的清谈家们常常借山水之美来评价人物的风姿、气度、性格之美。叶朗曾指出:“当时就出现了一种社会风气,就是以自然美来形容人的风姿、风采。”[11]如:王戎赞清谈领袖王衍:“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王衍赞郭象的言谈:“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王导赞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5]这既说明山水之美为魏晋士人所认识,同时也说明人的风神气骨与山水之美具有了相通之处。人可以从对自身的审美感受生发出对自然山川之美的感悟;又可以从对山水自然的体会中引申出对士人容仪、气质的品评。
其二,隐士文化在魏晋六朝的流行。“自由”是魏晋自然观的目标和理想。很多追求自由的士人,或主动放弃为官,或为了避祸,转而归隐山林,隐逸成为了他们实现自由追求的最佳途径。庄子把仕宦生活称为“羁”:“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12]晋隐士郭瑀面对征召之使时以鸿翔明志:“此鸟也,安可笼哉!”[10]50
同时,坚守人格自由也是魏晋风度的理想,是魏晋士人共同的追求目标。陈传席先生认为,魏晋士人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既是为了观道,也是为了怡情,作为士之一分子的魏晋隐士与一般文人士大夫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魏晋隐士对自然审美的主观需求更为强烈[13]。就当时的权贵而言,对这些性格另类的隐士的容忍也是其彰显风度的表现,《世说新语·雅量》中就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时的社会舆论给予这样的文人隐士极大的认同甚至于是仰慕,如阮籍的儿子阮浑就“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由此可见,推崇“秀骨清像”为审美标准的社会,无意中为隐士归于山林,追求自由,且性格桀骜不驯创造了一个宽容的大环境。
三、魏晋文学、书画的自然之风与秀骨清像
“秀骨清像”之风笼罩着六朝士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其影响之广,不仅外显于人人以清言玄理为尚;也不仅表现在容貌和精神气质上的清秀、飘逸、自在、洒脱;同时还幻化为一种审美旨趣而体现在魏晋六朝的诗文书画当中。
首先,魏晋六朝对于自然的推崇,使得主流美学家和文学家把艺术作品风格的清真自然、素朴无华作为品评的最高标准。刘勰说:“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14]《南史·颜延之传》载:“(颜)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日:‘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之终身病之。”[15]此例可见,在崇尚自然的审美风尚之下,延之铺锦列绣的美是无法与谢灵运出水芙蓉的美相比拟的,就连颜延之听到别人的评价后也“终身病之”。翻开魏晋南北朝遗存的大量文艺作品,颇多使用到“清”“秀”的审美概念,这一现象说明天真清丽的美,是魏晋六朝评价艺品与文品的重要尺度。
其次,文学作品是作者内心情感的真实体现,真率的情感是构成艺术的前提。如作者能直抒胸臆,不加藻饰,作品的言辞风格也自然较为素朴天然。《庄子·渔父》有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8]51但在魏晋以前,因统治者本能地惧怕人们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尽情宣发,这一简明、深刻的哲理被“成教化,助人伦”“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儒家思想所左右。总结来说,魏晋文学摆脱了道德教化的附庸,具有了非功利性、个体性的特征,成为士人表达内心情感、抒发胸中意气的重要介质,更成为士人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衡量以“秀骨清像”为代表的士人文化修养的尺度之一。
其三,魏晋六朝文学、艺术所崇尚的至真至美渗透在艺术生命体内,成就了清雅高洁的艺术品格,呈现出尚美崇真的名士气象。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书法,嵇康“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充满空灵的诗歌,顾长康“传神写照”而富有神采气韵的人物画,既是艺术中的极致与精品,又是魏晋风度的典范与写照。阮籍与陶渊明的诗文产生于对悠闲自得田园生活的向往,他们以人生的视角去体悟自然,并以自然的本真来提升自我的价值,努力让自己的生活之趣和精神之境都回归于自然。其诗文深刻而精辟的独白与感悟,丰富了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深化了魏晋风度的内涵,使得这些尚真、尚意的作品与“秀骨清像”的神姿一样成为魏晋风度的外在表征。
魏晋六朝的时代背景便是儒家思想已不能再垄断当时的精神领域,带有“自然”“清静”“虚淡”的道家思想适应了当时的需要,登上了历史舞台。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7];庄子反复强调的虚静之心,都与士人的精神追求相吻合。魏晋士人时刻都在追求从体貌到心神,从立身到处事,从人生态度到人格的完美。我们之所以把研究魏晋精神的关键词定格在秀骨清像上,是因为这种优雅的审美意识,表征了魏晋六朝特有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精神,它与玄风荡拂的六朝自然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且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并对后世艺术审美标准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袁济喜.自然的人格与自然的美学——魏晋南北朝美学札记[J].福建论坛,1986(2).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150.
[3]陈传席.论骨秀[J].美术,1996(9).
[4]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56.
[6]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81.
[7]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9]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96.
[10]房玄龄.晋书:阮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18.
[14]刘勰.文心雕龙[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69.
[1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0.
Natural view in Wei Jin Dynasties and “elegant skeleton and delicate feature”
ZHANG Jun-pei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One of the major breakthroughs in aesthetics in Six Dynasties period is to achieve a unity of natural personality and aesthetic attitude. Pursuit and melt of natural personality contributed to Scholars’ elegant skeleton and delicate feature. The pursuit of natural beauty formed unique and new natural view in Wei Jin Dynasties. On the one hand, it didn’t only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also bring a literary, artistic painting delightful new look. On the other hand, i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hole aesthetic standards.
elegant skeleton and delicate feature; natural view; nihility; emptiness
2014-07-25
B835
A
1000-2359(2015)02-0147-04
张俊沛(1979—),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美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