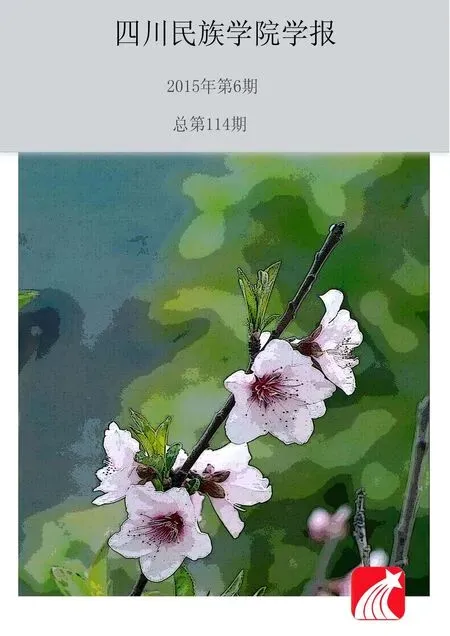浅析华锐藏族白牦牛文化的生成及延续
徐 燕
★历史·文化★
浅析华锐藏族白牦牛文化的生成及延续
徐 燕
1973年,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出土了一件硕大的牦牛青铜器,本文以该牦牛青铜器为切入点,尝试探讨作为自然之物的白牦牛为何会衍变为文化之物、它又是如何由物化形象变成文化符号的、这种文化符号何以被固定下来并得以传承和发展等问题。
天祝;华锐藏族;白牦牛文化
一、前言——由一件牦牛青铜器引发的思考
某日,百无聊赖,随意翻阅着一本名叫《天祝博物馆文物荟萃》的刊物,突然被一件硕大牦牛青铜器的图片所吸引。仔细看插图旁的文字简介,原来这件牦牛青铜器于1973年出土于我国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身长118厘米,背高51厘米,前脊高61厘米,臀高52厘米,腹径30厘米,角长40厘米,尾长30厘米,重75公斤,是目前我国出土的唯一以牦牛为造型的青铜器。
该青铜器以天祝白牦牛为原型,选择牦牛伫立的姿态,从它那粗壮有力的四肢和灵巧结实的蹄腕及其他部位特点,可以判断出它具有雄性生理特征;其结实的脖颈、宽阔的前额,又使它平添了一种令人生畏的雄威,给人以力量与雄健的美感享受。牛首微微伸向前方,双目圆睁,沉寂而暗涌着力量。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铸造者对于犄角和牛尾的设计:弯度优美、充满锋芒的双角向上托起,却在末端微微后抑,显得锋芒顿收,给人以强大却和善的印象;牛尾向下低垂,与一对锐利的犄角前后呼应,使整个作品显得匀称、协调。整件牦牛青铜器硕大而敦实,形体结构严谨、质朴、气质雄浑,其铸造和冶炼技术均堪称一绝。
这件牦牛青铜器激发了我浓厚的兴趣,仔细端详着图片上的器物造型,细细揣摩着图片旁的文字说明,然后不经意间冒出这样一个疑惑:华锐藏族先民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铸造了如此硕大的牦牛青铜器?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面具之道》中探讨各式各样的面具造型究竟为何制造、有何用途时所认为的——答案一定要在面具所属文化体系中寻求——一样,[1]要探讨牦牛青铜器的铸造原因,也不能就事论事,或者单从作为独立事物的牦牛青铜器本身寻求解释,而要将其放入所属的文化系统当中去探索。可以确定,在华锐藏族先民的心中,白牦牛一定有着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性甚至超越了白牦牛作为自然之物的形象本身,上升到一种文化象征符号的高度,因而才出现了以其形象为原型的艺术作品。那么,作为自然之物的白牦牛为何会衍变为文化之物?它又是如何由物化形象变成文化符号的?这种文化符号何以被固定下来,并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将致力于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华锐藏族与白牦牛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为建立一个人与物之间和合共生的社会文化生态体系提供启示和思考。
二、白牦牛文化的生成及延续
在笔者看来,文化是一种广义的赋意活动,是人们运用符号为生命、为事物赋予意义的过程。如上文所述,在华锐藏族先民的心中,白牦牛有着特殊的地位,出于这一特殊性,华锐藏族为白牦牛赋予了一定的文化符号意义,从而形成了白牦牛文化,作为华锐藏族文化体系的一个扇面、一个子集。以下,本文将具体探讨华锐藏族为何赋予白牦牛一定的文化意义,即白牦牛文化为何生成、其生成途径如何这两大问题。
(一)白牦牛文化生成的原因
任何事物被赋予一定的文化意义,其根源都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有关,白牦牛文化也是如此。华锐藏族先民在最初的生存活动中,对白牦牛实用功能的认识与利用是白牦牛文化生成的根源。从商周时期羌戎驻牧,到明清时期不植五谷、唯事畜牧,可以说白牦牛始终与华锐藏族唇齿相依、休戚相关,影响到华锐藏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交通运输工具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白牦牛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形态和生理特征:全身毛色结白如雪,轻软纤细,浓密厚实,享有“草原白珍珠”、“祁连雪牡丹”之美誉;四肢健壮有力,善爬山越岭,负载量大;嘴唇圆薄,齿质坚硬,擅采食高山草场的低矮型牧草,能耐寒耐饥;鼻孔大,气管粗短,肺叶十分发达,能够在空气稀薄的高山峻岭中长久负重而行;心脏和胸部发育良好。因此,白牦牛独特的生理结构特征,使其可在海拔3000多米、最高至6000多米处憩息,可在天寒地坼、雪虐风饕的天气里,依然泰然自若地驮物前行。因此,在只能选择动物为交通工具的年代,人们乘骑、驮物都依赖于白牦牛。尽管在华锐藏区也有一定数量的骡、马等可用于乘骑、驮物的动物,但由于其生理特征不如白牦牛适应当地环境,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由此,白牦牛便成为当时华锐藏族地区最常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华锐藏族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财富的象征
白牦牛的饲养历史源远流长,《凉州府志备考》中就有有“白牛食雪山肥草,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可合旃檀”之表述。[2]可以说天祝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是白牦牛繁育成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中,天祝的藏族牧民也积累了丰富的饲养管理经验。因此,天祝成为世界珍稀动物白牦牛的唯一产地,有着“天下白牦牛,唯独天祝有”的美誉。[3]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天祝很多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而白牦牛生产则是畜牧业经济的基础,它的产业收入是黑牦牛的4倍,是其他普通牛的5倍。因而白牦牛成为华锐藏族的重要财富之一,华锐藏族民谚称:“千金难买牦牛肉,稀贵更属白牦牛。”*华锐藏族民谚,田野调查过程中从牧民哪里搜集而来。人们相互之间争强比富常以白牦牛的多少为主要依据,可以说,拥有白牦牛数量的多少成为华锐藏族占有财富量多寡的重要标志。
3.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白牦牛不仅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和财富的象征,也是华锐藏族维系日常生活所需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饮食
藏族的特色饮食主要由糌粑、肉类、奶制品、酥油茶等构成,其中绝大多数食品或直接取自白牦牛,或用白牦牛产品加工而成。比如,牛奶是华锐藏族最常见的日常饮品,除了可直接食用外,还可以用来制作酥油、酸奶、奶渣、奶糕等奶制品,或熬制奶茶,这些都是华锐藏族极其重要的饮食;再比如,糌粑是华锐藏族最常见的食物之一,分为两种,一种是将青稞、燕麦等炒熟磨制而成,称为粮食糌粑;另一种是将白牦牛肉风干后制成,称牛肉糌粑。牛肉糌粑本身所需的原料就源自白牦牛,而且糌粑的食用方式也与白牦牛有关——是用酥油奶茶将其调成糊状后捏成团来食用的。此外,华锐藏族食用的肉类,主要有牛、羊、猪肉三种,尤以白牦牛肉为主。食用方式一种是制成牛肉糌粑食用,一种是佐以胡椒、盐巴等调料,煮制成“开锅肉”食用,还有一种是制成牛肉干食用,一般在夏秋季制作,冬季食用。其制作方法是把牛肉切成条状,洒上盐水,晒干或阴干。在藏族饮食中,不仅主要食品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白牦牛,就连熬茶煮饭所需的燃料——牛粪,也源自白牦牛。
(2)服饰
除饮食外,华锐藏族的服饰原料大多也来自白牦牛。白牦牛的绒、毛轻柔典雅,保暖性强,以其为原料制作而成的衣服,美观大方,别具一格。《北史·附国传》 中就有“以皮为帽……衣多皮裘,全剥牛脚为靴。”的记载。[4]如今,白牦牛的绒、毛产品仍然是华锐藏族服饰的主要原料。
(3)其他
早在古代,华锐藏族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白牦牛绒毛易上色的特性,将其染制成各种缨穗,用于兵器、旌旗和帽子上,作为力量的象征。此外,用白牦牛毛制成的拂尘、长髯等也作为戏剧表演中的重要道具而被广泛运用。除上述用途外,白牦牛的角、骨、蹄、牛尾,甚至内脏等也都在华锐藏族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用途,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总之,就是因为白牦牛与华锐藏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因而,华锐藏族与白牦牛之间形成了一种纠缠。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5]当华锐藏族将这种人——物之间的关系编织到意义的图景中时,就构建出了以白牦牛为象征符号的文化体系,从而使作为自然之物的白牦牛被赋予文化的意义,衍化为文化之物。
(二)白牦牛文化的生成与延续
1.作为图腾的白牦牛文化意义
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神。”[6]这便是白牦牛之所以成为华锐藏族先民部落图腾的重要原因。在华锐藏族社会中,流传着诸多由白牦牛图腾观念衍生出来的图腾神话。这些神话,有的将白牦牛视为祖先或保护神,有的视其为化生万物的创造者,以口承或笔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如《王统世系明鉴》记载:“大臣洛昂篡夺王位,役使王妃为马牧。一日,妃於牧马处,假寐得梦,见耶拉香波山神化一白人,与之缱绻,既醒,则枕藉处有一白牦牛,倏起而逝。迨满八月,产一血团,有如拳大,微能动摇。念若抛舍,肉自己出,未免不忍。养之,又口眼均无,遂以衣缠裹之,置於热犛牛角中。数日往视,出一幼婴,遂名为降格布·茹列吉。”[7]这则神话表明了华锐藏族祖先的传承系谱,即白牦牛与华锐藏族的祖先耦合,繁衍出氏族精英,从而部分解释了华锐藏族的起源问题,是典型的白牦牛图腾神话。又如,在华锐藏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则神话故事:“华锐藏族的祖先华秀曾居住在巴颜喀拉大雪山下,拥有众多的牛羊,但草场却日渐不足。于是,华秀告别弟弟阿秀,带着一部分人马去寻找新的草场。他祈祷山神指明前行的方向,这时,一个骑着白色骏马的神灵出现在天空中。于是,华秀一行人向着神灵前行的方向出发。当他们快要走出一个石峡的时候,黑牦牛群里却突然发出悲怆的哞叫声。这时,从身后的雪山深处,出现了一头白牦牛,它哞叫着,向石峡方向奔去。说来也怪,白牦牛出现后,黑牦牛就都停止了哀哞,跟着白牦牛一起向石峡奔去。当华秀一行人紧跟牛群跑出峡口时,看到所有的黑牦牛都死了,只留下那头白牦牛正和一个黑色的巨怪角斗。最终,白牦牛战胜了巨怪。这时,之前骑着白马的神灵又出现在天空中,于是华秀及部落牧民们赶着那头唯一活下来的白牦牛,跟随神灵继续前进。最后,那神灵在马牙雪山脚下停住,这里溪水潺潺,碧草如茵,是一块驻牧的好地方。于是,华秀一行人便世代定居在这里。那头唯一活下来的白牦牛喝了马牙雪山的圣水,繁衍了一群又一群,从此华秀和他的部落牧民们便很幸福地生活在这里。”[3]这则神话故事讲述了华锐藏族与白牦牛的发生与繁衍历史,为华锐藏族的族群来源及白牦牛的存在繁衍进行了历史追溯与合理解释,从而为华锐藏族的白牦牛崇拜提供了意识共鸣与情感支持。此外,古代一些有名的山神,如雅拉香波山神、岗底斯山神等,在一些神话故事中也都化为了白牦牛。如《莲花生本生传》中记载:“莲花生大师来到先(年)保沟,先(年)保山神变成山大的白牦牛……”。[8]总之,华锐藏族先民最初因“浑身是宝”的白牦牛对其生存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作用而产生白牦牛崇拜,使得白牦牛从客观生理存在走进人们的精神信仰中,人们将其视为图腾崇拜物,赋予一定的文化意义,并通过诸多的神话传说为其增添了奇幻色彩。人们看见白牦牛总会不自觉地记起相关的图腾神话,白牦牛的文化意义便在这一次次记忆中被重新演绎。可以说,图腾神话为白牦牛文化意义的生成提供了沃土。
2.宗教信仰中的白牦牛文化符号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环境,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9]随着白牦牛图腾崇拜的日益倡兴,白牦牛不仅扮演着氏族祖先或万物创造者的角色,还被斌予神性,逐步纳入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庞大的神灵体系之内,占据着较高的地位。譬如苯教的跳神或祭祀活动中,都会用白色牦牛作为吉祥、平安、善良、美好的标志;苯教将白牦牛视为保护神,在其神舞表演中,常戴白牦牛牛头面具,用以驱邪降魔;一些苯教寺院,对刻有符咒的白牦牛头骨顶礼膜拜,以企盼世间五谷丰登,吉祥如意;另外,苯教的法事活动中,还用白牦牛牛角作为抵挡敌人的法器。在华锐藏区曾流传这样一则传说:早在1600年前,今天祝的哈溪、毛藏、祁连一带水草丰美,居住着很多的吐谷浑牧民。当时吐谷浑人信奉苯教,遇到大事小事,总要请苯布子苯布子卜算禳解。因此,当时苯布子在吐谷浑人中有着很高的权力和威望。有一年,吐谷浑人的牛羊成群地死,牧民们没有办法,只好请最德高望众的老苯布子卜算。老苯布子推算出牛羊成群死亡的原因在于上天要求吐谷浑人为自己供奉一头神牛坐骑。于是,牧民们请求老苯布子寻找神牛。老苯布子骑着自己的驮牛,一个帐圈一个帐圈地挑选。最终,他在毛藏的一个帐圈里,发现了一头与众不同的白牦牛。这头公牛高大威猛,双眼炯炯有神,四肢坚如铜柱,哞声洪亮,群山回响。老苯布子认定这头牛就是天神要的神牛坐骑。于是在征得牛主人同意后,老苯布子将它供奉给了天神。很快,畜群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从此以后,这头神牛就不时地在吐谷浑人的各个畜群中出现,它到了哪个畜群,哪个畜群就兴盛。这之后又过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神牛不再出现了,人们知道,随着神牛的消失,灾难又会降临。于是,人们去请教那位老苯布子,老苯布子用尽平生最后一点力气卜算出,吐谷浑人若想保住畜群就必须为天神造一头永不消失的神牛。但是老苯布子仙逝得太早,并未说清楚如何才能造一头永不消失的神牛。人们没有办法,只好去请教仅次于老苯布子的霍尔阿爸,霍尔阿爸指出,只要铸一头铜牦牛,就能保证永远留存下去。于是人们在毛藏乡一个叫铜匠沟的地方找到了很好的铜矿,开山取矿,砌炉炼铜,铸造铜牛。后来,人们将铜铸的神牛供奉在寺院中,让它护佑着这方生灵。就这样过了一百多年,吐谷浑国遭遇到了战争,为了避免铜铸的神牛被毁,霍尔阿爸和他的两个徒弟带着铜牛南逃。最后,霍尔阿爸因不堪艰苦跋涉而倒下,他的两个徒弟怕带着沉重的铜牛连自身都难保,于是两人将铜牛掩埋在了一块向阳地,想等到战乱后再取出,没想到二人一去不回。就这样过了一千多年,直到1972年,天祝县哈溪公社的峡门台在平整宅基地时发现了铜牦牛,才使得它得以重新造福这方生灵。[10]从这则神话故事中可以窥探到华锐藏族的白牦牛崇拜与苯教信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传,苯教的保护神是一位持长矛穿白衣的白神,因而苯教崇尚白色,在其统治时期,尊奉白牦牛为“神牛”。无论传说的真实与否,该传说及白牦牛被赋予的文化意义都在华锐藏区世代流传。在一次次的传承中,白牦牛被赋予的文化意义被一次次操演,同时,又被添加上新的内容。因此,白牦牛的文化意义并不先天存在,也不仅仅凝滞于白牦牛自身,而是人为的、变动不居的、不断积累应运而生的。
3.日常生活中的白牦牛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渗透到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日常展演。白牦牛不仅被视为华锐藏族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中的象征符号,而且其文化意义被更多地演绎为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种演绎,反过来又巩固和延续了白牦牛文化。
(1)用白牦牛头骨降魔祛邪
在华锐藏区,很多人家或寺院里,都会在白牦牛头骨上镌刻六字真言,挂在墙上或者门口,用以降魔祛邪。白牦牛头骨祛邪的文化意义或许与上文当中所提到的,苯教常对刻有符咒的白牦牛头骨顶礼膜拜,以企盼太平盛世有关;又或许只是出于普通百姓趋吉避凶的心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何能让生活幸福美满才是最实际的事情。因此,较强的吉凶意识使得华锐藏族在为白牦牛赋予文化意义时,表现出了朴素的趋吉避凶的价值观。无论华锐藏族是出自什么原因用白牦牛头骨消灾辟邪,总之这种降魔祛邪、趋吉避凶的心理丰富了白牦牛的文化意义,使其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发展。由此可见,消灾辟邪意识是白牦牛的文化意义生成及延续的重要推力。
(2)白牦牛舞
在华锐藏区,有着很多以白牦牛为题材的舞蹈,有的反映华锐藏族对白牦牛的驯化过程,有的表达了白牦牛与牧人之间水乳交融的深厚情感,还有的歌颂白牦牛给华锐藏族人民带来的恩惠……那些抑扬顿挫的旋律,曼妙轻盈的舞姿,给人醍醐灌顶般的大彻大悟与精神气度。据藏文文献记载,早在8世纪,吐蕃百姓就曾跳牦牛舞以庆祝桑耶寺的落成。由此可见,牦牛舞历史之悠久。一般而言,白牦牛舞多为十三人左右,有时则多达上百人。传统的十三人表演多反映华锐藏族对白牦牛的驯化过程,除一人(一般为年轻女子)扮演放牧人外,另外十二人分两组分别扮演公、母牦牛。每两人扮演一头牦牛,一前一后,二者同披一张用白色毯子仿制的白牦牛皮。前者立身,头戴仿制的白牦牛头,身披“白牦牛皮”前半段,用以表现白牦牛的头、颈,穿白色长裤用以表现白牦牛的前蹄;后者躬身,披“白牦牛皮”后半段,用以表现白牦牛的躯干及尾部,同样穿白色长裤,用以表现白牦牛的后蹄。为了使舞台效果更佳,白牦牛舞中所使用的道具在逐年改进,从用材质地到外显效果均有提升,比如用来表现白牦牛头的道具就由简单的白色面具演变为由白色毛毯和铁丝支架仿制的白牦牛头。该舞蹈中,先是一头雄性白牦牛出场,银光熠熠,竖角悬蹄,似从雪域高原走来的精灵。接着,牧人手拿皮鞭,吟着牧歌出场。随后,其余白牦牛相继出场,时而奔跑,时而嘶鸣,时而互相抵角嬉戏,嫣然一副野性十足的样子。这时,牧人用皮鞭和驯导之词将白牦牛逐个驯服,白牦牛便一一卧下,表现得温顺随和。于是牧人便放下皮鞭,拿着挤奶桶去母牛那里挤奶。最后,牧人手捧洁白的哈达一一搭在被驯化的白牦牛犄角上,以表达对白牦牛所给予诸多恩惠的虔诚感激之情。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背景音乐时而汹涌澎湃,时而婉转悠扬,在音乐的烘托渲染下,整个舞蹈起伏跌宕、曼妙蹁跹 ,不得不令观者颇涉遐想。
舞蹈是一种以经过提炼和艺术加工的人体动作表达人们内心情感、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因素,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标志反映于舞蹈中,从而折射出该民族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白牦牛文化意义的延续与发展,也与白牦牛舞的盛行密切相关。这不仅在于白牦牛舞本身就是集华锐藏族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等于一身的文化现象,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从而积淀并发展着白牦牛文化。同时还在于人们在观看白牦牛舞表演时,能够感受到华锐藏族的文化特征,并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本民族文化的浸润,从而传承并延续着自身文化。
(3)文人墨客笔下的白牦牛
白牦牛文化意义的流行与延续,与文人墨客的倡导附和密切相关——从最初的实际功用,到文人墨客们审美关照下的赋意,其文化意义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这些名人雅士赋予了白牦牛鲜明的人格色彩,通过理想人格的赋意,使白牦牛逐渐成为人格化的物,具有了新的文化意义。近年来,以白牦牛为体裁的文学作品、书画作品、音乐作品灿若繁星,熠熠生辉,为白牦牛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积蓄了能量,提供了动力。可以说,文人墨客们对白牦牛的推崇与喜爱,为推介和发展白牦牛文化提供了助益。
(4)白牦牛工艺品
白牦牛工艺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凝结于其上的各种纹样、审美意识、艺术创造,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源于华锐藏族对白牦牛神态的捕捉,在亲身体会、亲眼目睹中,白牦牛的千姿百态被浓缩成了艺术创造,提炼成了审美意识。因此,可以说白牦牛工艺品是由浓厚的白牦牛文化打造出来的,是华锐藏族的生活艺术,体现着他们的情感、智慧和创造精神。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民族特色、本土文化气息的产品更受游客的青睐。而白牦牛工艺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资源,在旅游休闲文化的背景下找到了市场,从而由民族工艺品发展为旅游工艺精品,历经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一过程远不是对民族工艺品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旅游休闲文化背景下对民族工艺品的创新,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观念的改变。作为一种现代生活,休闲旅游既有与传统文化交叉重叠的内容,也有超越传统的新的拓展。因而,在打造旅游工艺精品的过程中需要关注旅游生活的时尚、审美等方面;二是新技术的介入。当民族工艺品作为旅游产品被开发时,由于生产规模被不断扩大,因而,在其生产加工的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采用新技术和现代机器;三是工艺品性质的改变。如白牦牛头骨和面具等,过去主要是用以驱邪降魔,现在其神圣性渐渐淡化,甚至仅仅用于陈设和观赏;四是在审美关照方面,开始将游客的需求纳入考虑的范畴,从而糅合了传统与现代,既不失本土文化的特色,又增添了外来文化的风格;五是原材料的替代。这种替代,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可取的方面。其合理性在于,用可再生材料替代某些不可再生的原材料,可以有效保护资源。但有的原材料替代则不可取,如牛角梳的现代制作中,往往会掺杂一些化学制品,不仅降低了该工艺品的品质,而且对于生态环境、人体健康也产生了不可轻视的负面影响。总之,传统民族工艺品在旅游休闲文化背景下发展为旅游工艺精品,这一过程一方面对于促进华锐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丰富华锐藏族白牦牛文化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对华锐藏族白牦牛文化所产生的涵化作用也值得关注和反思。
结 语
总之,任何一种文化,其生成、延续和发展都与“人”的推介紧密相关。白牦牛的赋意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其文化意义并不先天存在,也不凝滞于白牦牛自身,而是人为的、应运而生的、不断积累的。从本文的论述可知,尽管白牦牛相对于人而言,是自然界的独立存在物,但由于华锐藏族生存发展的需要,与之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性。因而,华锐藏族先民逐渐对白牦牛产生特殊的情感,不仅将白牦牛视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资源,还将其融入到精神寄托的层次,通过将其幻化为图腾动物和宗教信仰的象征物,赋予其一定的文化意义。这一文化意义又通过日常生活展演和艺术作品等方式被不断地呈现和操演,从而趋于定型,形成较为固定的文化意义。并最终在文人雅士的赋意和旅游文化的推动下,得以丰富和发展。由此,可以窥探到华锐藏族与白牦牛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为建立一个人与物之间和合共生的社会文化生态体系提供启示和思考。
[1]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张祖建译.面具之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p14-16
[2](清)张澍.凉府志备考·物产[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p73
[3] 钱德云、靳万龙.天祝风情[M].天祝:天祝藏族自治县旅游局,1999年,p139、p139-140
[4](唐)李延寿.北史·附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p3193
[5]梅晓云.文化无根:以V.S.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p148
[6][德]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著,王太庆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p438-439
[7]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吐蕃王朝世系明鉴)[M].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p34
[8] 洛珠加措、俄东瓦拉译.莲花生大师本生传[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p399
[9] 马克斯恩格斯全集·卷二十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p63
[10]李占忠.天祝铜牦牛的故事[J].中国土族,2008年第6期
[责任编辑:林俊华]
On the Birth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White-yak Culture in Huarui Tibetans
Xu Yan
In the light of the yak bronze unearthed in the Haxi Town of Tianzhu Tibetan Autonomous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in 1973,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y did the natural white yak change into a cultural white yak, how did it materialize into a cultural symbol, and how was thi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mbol fixed?
Tianzhu Autonomy County; Huarui Tibetans; white-yak culture
徐 燕,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14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海淀,邮编:100081)
G127
A
1674-8824(2015)06-004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