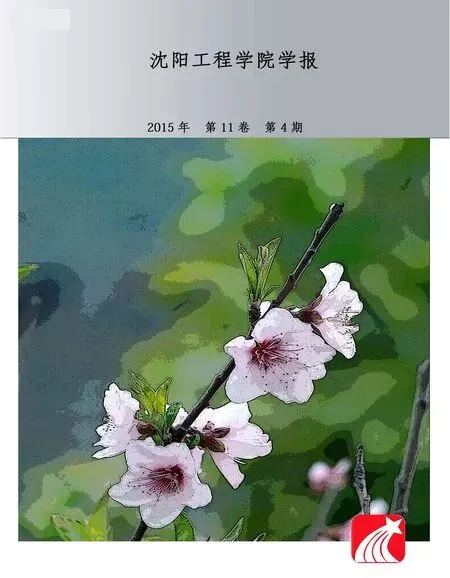时代的记忆 永恒的丰碑
——抗战诗歌刍论
曹 帅
(营口理工学院基础部,辽宁营口 115000)
时代的记忆 永恒的丰碑
——抗战诗歌刍论
曹 帅
(营口理工学院基础部,辽宁营口 115000)
抗战文学作为历史的化石记载了中华民族在灾难岁月中的创痛与希望,抗战诗歌,以其灵活性、丰富性和战斗性的优势成为抗战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分别从历时性角度纵向梳理抗战诗歌的发展脉络,从共时性角度横向铺排抗战诗歌的地域性风格差异,同时着重介绍了较为突出的抗战诗人和诗人团体,从审美价值追求、大众化倾向和多种艺术形式的探索、新诗的丰碑和时代记忆的角度探讨抗战诗歌的艺术价值。
抗战诗歌;发展历程;风格差异;诗人群体;艺术价值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解放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艺术作为时代的记忆、历史的化石,在彼时壮烈的阶段汇入历史的洪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记载了民族的创痛与希望,流血与战斗。
诗歌,以其灵活性、丰富性和战斗性的优势成为当时抗战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作为文学史概念的抗战诗歌,主要指自1931~1945年间,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诗歌创作。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了对华侵略的步伐,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借卢沟桥事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日寇的炮火震醒了中华儿女,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开始奋起抵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保家卫国的壮歌。抗日的烽火不仅点燃了全国军民的爱国情怀,更点燃了知识分子的创作激情。“家国不幸诗家幸”,诗人们一改往日雍容优雅、温柔敦厚的诗歌风格,以雄浑慷慨的壮志豪情展现了受难民族灵魂的裂变,以暮鼓晨钟的岿然呈现了一幅幅壮阔的历史画卷。
一、抗战诗歌的民族救亡动员作用
抗战诗歌不仅只是主题突出,风格倾向一致,因其地域区分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而同时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从历时性角度纵向梳理抗战诗歌,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地区沦陷,此时的诗歌创作主要是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怒斥,对不争的国民的呐喊,对奋起抗争的呼唤。“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如正义的指挥刀之能组织人民的步伐,诗人的笔必须为人民精神的坚固与一致而努力[1]261”。如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1935年8月写于汉口),“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诗人以追忆的方式悼念为国捐躯的战士,与战士顽强杀敌相对比的是国民政府卖国求全的可耻行径,“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亲善’!‘睦邻’!啊!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最后诗人以“不幸的一群”自居号召被压迫者反抗无情的奴役。另如雷石榆的《坟墓和活路》对卖日货的奸商的斥责,“难道半国失地还太少?千万同胞被杀还不多?奸商!只顾个人的腰包,不管民族的大祸!”诗尾更对其提出了严厉的警告“清醒脑袋想想吧!眼前摆着坟墓和活路!”再如胡适的《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铭》,“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诗人以抗日号召作为对烈士最好的缅怀。
(2)伴随着日军全面侵华的炮火,诗人们迅速感应时代的脉搏,吹响了抗战的号角。抗战初期,勇士们渴望驱除鞑虏,知识分子渴望奔赴战场,全国人民沉浸在同仇敌忾的激越情绪之中,诗歌适时地成了时代情绪的传声筒。胡风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中提到“民族革命战争的炮声把文艺放到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里面。这以前,作家底世界是书斋,是客厅,是教室……但炮声一响,这些全都受到了震动”“他们兴奋地,或者想镇静而不得地跑了出来,想愿意去的或能够去的各种各样的领域分散。跑向热情洋溢的民众团体,跑向炮火纷飞的战场……[2]71”此时的诗人们是兴奋的、是热烈而激进的,此时的诗歌也大多是直抒胸臆的,如郭沫若的《雷电颂》:“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另如张季纯的《给我一枝枪》:“给我一枝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那个能够再忍让!”控诉侵略者罪行同时迫切赶赴战场的呐喊传达了诗人报仇雪恨的急切愿望。再如臧克家的《兵车向前方开》:“炮口在笑,壮士在高歌,风萧萧,鬃鬃在风里飘。”从这些抗战初期的激情之作,可以想见当时全国人民共同抗日、一致赴敌的乐观氛围。初期的抗战诗歌已不同于以往“诗以言志”风流韵致的精英认知,而呈现出明显的现实性审美价值追求,即追求强烈的现实功利价值,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和宣传工具——唤醒民族情绪的利器,鞭挞反华势力的匕首。另外,此时的抗战诗歌倾向于摒弃“五四”新诗的自由体式的向往,转向了中国传统诗歌音律化追求,注重诗歌朗朗上口的音韵性和节奏感,如郭沫若的《中国妇女抗战歌》:“上前线,上前线,带着我们的针,带着我们的线。”《归国杂吟》:“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3)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人们逐渐从初期的高亢战声中清醒过来,认识到胜利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残酷,由此,抗战诗歌的题材得以丰富和扩展。既有延续初期的歌颂战斗和勇士的激昂战歌,如田间的《义勇军》,以一个义勇军为形象主体叙写杀敌得胜的昂扬。曹葆华的《西北哨兵》,以凝练的诗句刻画了一位坚守哨岗“控制着群山万壑”的士兵的英姿。又有描写受难的人群,失却了家园的灾难世界,如许幸之的《铁蹄下的歌女》,如泣如诉呈现了“被鞭挞的遍体鳞伤”的歌女的悲惨命运。管火陵的《家》,诗人只能在记忆中找寻那美丽而朴素的家乡。有对抗日烈士的深沉悼念,如郑振铎的《我们的伤痕永不在背上》,写出无论耳边响荡着怎样的狂雷般的炸裂声,追忆勇士们永远向前的战斗精神是我们对英雄最好的祭奠。还有对光明的期盼和对胜利的呼唤,如丹茵的《重庆的雾》:“阴沉的雾就要散了!在它的后面会出现一轮红辉的太阳!”
与创作题材的扩展相应的是抗战诗歌的审美形式也得到了提高。随着新月派、现代派诗人群体的融合,对抗战诗歌的审美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前一直被忽视的诗歌的艺术审美特性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抗战诗人们开始探讨如何丰富和提高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艾青在《诗论》中提出“好的诗篇,常是产生于我们被新鲜的意象和新鲜的语言如此适合地溶化在自己的思想里,这一机会里,猛烈地袭击我们却被我们获得的时候”,“诗人主要的是要为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感情,寻求形象[1]262”“朴素是对于辞藻的奢侈的摒弃,是脱去了华服的健康的袒露;是挣脱了形式的束缚的无羁的步伐;是掷给空虚的技巧的宽阔的笑。”艾青强调的是一种更为纯粹,更为自然的朴素的诗美,这也是这一时代的诗风。在艾青诗歌理论的影响下,诗人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情感的外化,如钟辛的《蒲公英》,像灯盏一样的蒲公英,“没有妖艳的颜色,没有袭人的香气”却能让种子“和着理想”随风飘去。这生长在烈士坟茔的蒲公英寄托着诗人的哀思,也寄予了无限的革命星火的遐想。
(4)抗战中后期的诗歌,仍然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审美追求,随着诗人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此时的抗战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表现更为真切、细腻和丰富。“生活就是一篇伟大的诗[3]。”臧克家的《社戏》描写了观看社戏,满足归来的平实生活。1931~1945年,这旷日持久的战争终见光明之时,诗人们难以抑制对胜利的狂欢,爱国诗人绿原的史诗性长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呼喊:“胜利来了:啊,火种”“胜利是你的,中国!”“我们庆祝胜利,不用鞭炮不用狂吹的号角。”全诗情绪饱满,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诗中跳跃的字眼“胜利”“庆祝”气势雄浑,节奏鲜明,造成一种强大的冲击力。此时的政治讽刺诗也是突出的创作潮流,如臧克家的《人民是什么》《生命的零度》等。
值得一提的是戈茅的《人类审判宣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年代,整个世界陷入了残酷的战争。”诗人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宏大视角,以世界的高度,以全人类的立场对一切残酷的战争的始作俑者进行审判和声讨,充满现实的感召力。
二、抗战诗风的地域差异
抗日战争这场关系整个民族的战役致使华夏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抗战的文学、抗战的诗歌在动荡中共同表现着时代的主题,但根据地理区域的差异,抗战诗歌的发展和风格又有所不同,进而形成了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三种不同的创作风貌。
(1)解放区作为抗战的圣地天然地具有滋养革命情感、培养革命文学的土壤,解放区文艺自觉地把大众的审美趣味作为诗歌创作的标准,书写解放区的生活与斗争。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发展要求,一时间文艺贴近工农兵生活成为创作的主流意识,诗人们把诗歌与传统民间艺术相结合进行了“新诗歌谣化”的尝试。中国诗歌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诗歌形式的多向探索,包括新诗朗诵运动、歌谣化、大众合唱诗等广泛的试验。到了40年代的解放区在毛泽东文艺观的引导下,“新歌谣”的创作成为解放区文艺中最为突出的形式。所谓“新歌谣”指的是“在民间传统歌谣形式中注入革命的内容,以达到宣传、教育、普及革命思想的目的。歌颂革命、革命政党、政权、领袖与军队,就成为新歌谣的基本主题[4]591”。在表现内容上,解放区的抗战歌谣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如公木的《军队进行曲》;其次是歌咏军民鱼水情,如《我们的八路军》;还有写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的,如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等。解放区抗战歌谣是广大军民在长期的战斗中创造的艺术,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瑰宝,也是民族精神的财富。
另外,长篇叙事诗的勃兴也是解放区诗歌创作的重要表现。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全诗共三部,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和手法成功塑造了王贵和李香香两个觉醒了的青年农民,“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结不了婚”,将人物的爱情命运同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揭示革命对个人幸福的决定作用。此后,解放区便掀起了叙事诗的热潮,如田间的《赶车传》、艾青的《雪里钻》等。在解放区抗战诗歌的创作中除了宏大叙事外,也有一些诗人坚持自由的抒情诗的创作,如魏巍的《蝈蝈,你喊起他们吧》:“你可曾看见,在他们的梦里:手榴弹开花是多么美丽,战马奔回失去的故乡时怎样欢腾,烧焦的土地上有多少蝴蝶又飞上花丛!”诗人同昆虫对话,赞美战士们收复失地、英勇杀敌的风姿。
(2)国统区抗战文学格局的建立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标志的。《七月》是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刊物,它的编者胡风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底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思想路线[2]8。”这表明尽管处于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高压下,尽管身处黑暗的恐怖环境里,国统区的诗人们仍然渴望以诗歌作为武器,将爱国主义情怀融入时代的强音,参与到民族解放的伟大革命中来。如最初发表在《七月》上的胡风的《血誓》:“卢沟桥的火花燃起了中华儿女们的仇火,在枪声炮声炸弹声中间,扑向仇敌的怒吼,冲荡着震撼着祖国中华的大地。”另如艾青的长诗《向太阳》,全诗共分九节,抒情主人公由沉睡中醒来,经过黑暗、绝望、彷徨的昨天,最终在太阳的光照中感到宽怀和热爱。经过抗战初期的昂扬激愤的英雄主义基调之后,国统区的诗歌创作进入冷静的反思阶段,诗人们的沉潜及文学创作的阶段性调整给国统区诗歌创作带来新的活力。诗人把对黑暗的诅咒、对光明的呼喊作为创作的心理,反映在文学上使得政治讽喻诗成为国统区抗战诗歌的一抹亮色,如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人民是什么》。
(3)沦陷区文学的范围除了上海沦陷区文学之外还包括“1931年‘九一八’之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华北沦陷区文学,再加上台湾地区文学、后来沦陷的南京、武汉、桂林、香港等地的文学[5]”对于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比较匮乏的,对沦陷区的抗战诗歌的研究更是如此。
沦陷区的作家们一直处于严苛压制的言说环境中,“从政治气氛上说,日本侵略者的高压统治和严密的文网制度使得沦陷区诗人们无法直面现实,所缺乏的是培植大众化通俗化诗作的土壤;从生活环境上说,求生存已经成为几乎每个诗人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6]”。在侵略者文化管制的特殊环境里,沦陷区的文学家不得不向内看,多侧重自我的抒发,写“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但沦陷区诗歌创作并不是一片虚空,作为战争废墟上的精神存在,同样给予了后世无数的惊喜。丁景唐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沦陷后曾编辑文学刊物,出版诗集《星底梦》,其中《五月的雨》:“人像生活在狭隘的樊笼间,冀望天边的黑云早日消敛。莫道烦厌的日子,挨过一天又是一天;忍看大好光阴在眼前等闲逝去。五月的雨,到头来终有停止的一天。”诗人用五月大雨滂沱暗指当时沦陷区窒闷的氛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深处沦陷区的诗人的苦闷和冲破桎梏的渴望。另如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序诗中以“将来,将来,……待到了血和爱的时候,”在“血,热和爱”的时候呼唤一个新的时代。沦陷区的流亡之歌是最为哀婉动人的,石雨的《沉忧》:“我相识的人,你为什么在边道上徘徊呢?……但这个地方,这灯光找不到的地方。”表达了诗人在黑暗政治环境中的困惑和彷徨。在“意识形态真空”“文化断裂”的沦陷区,诗人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含蓄地表达抵抗的声音,传达着对民族解放的希冀。
三、救亡历史推动了抗战诗歌的繁荣
前方战场硝烟弥漫,在文学这没有硝烟的阵地上,抗战诗歌大量涌现,诗歌流派不断崛起,诗歌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诗歌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诗歌,已经成为大时代乐章中最为强劲的洪钟大吕。
左联领导下的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成立于1932年9月,除在上海建立总会外,还先后在北平、广州及日本东京等地建立分会,发起人包括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等,坚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直接、自觉的血肉联系”的中国诗歌会提出“国防诗歌”的口号,创作了大量鼓动抗日爱国情绪的诗歌作品。
“现阶段的中国诗人任务与使命是中华民族自由解放[7]。”“在抗战声中,全人类为和平,为自由、幸福而战斗的炮火进行里,我诚然敢毅然不顾惜自己的业已存在的生命了[8]。”蒲风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笔耕不辍地为抗战而努力,创作了大量抗战主题的诗集,如《六月流火》《抗战三部曲》《钢铁的合唱》《摇篮歌》等,其中《我的思念在大海东》:“我是真理之子,真理长在我心中。那怕瘴氛横阻大海东;我要用大炮轰去一切氛和雾,我要用热情、教养去扫荡那蛮风!”在民族危难的时刻,蒲风想到了台湾,传达了民族统一的愿望,而《我迎着狂风和暴雨》通过“我不问被残杀了多少东北同胞,我要问热血的中国男儿还有多少。”发出了抗日救国的怒吼。
另一位中国诗歌会发起人是诗人穆木天,歌颂人民群众的英勇顽强,痛斥侵略者的血腥残暴是他诗歌创作的突出主题,如《扫射》《七月的风吹着》《守堤者》等,穆木天的诗歌创作澎湃奔放,多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将诗情喷薄而出,他的诗作《我们要作真实的诗歌记录者》,“在黄河北岸,震响着杀敌的号角!在珠江口,吹动了抗战的军号!……中华民族伟大的诗人,巨人般地,站起来了。”全诗气势宏大、铿锵有力,展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画卷。
抗战时期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还有七月诗派,是以《七月》以及后来的《希望》《诗垦地》《诗创作》为基本阵地。七月诗派是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主要理论领导人胡风在《七月》发刊词中一再表明,文学与反侵略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革命文学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同产生,一同受难,一同成长。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转过来养育了这个斗争[9]198。”七月诗人是要以文学作为武器服务于抗日救亡运动,又在抗战中激发文学的生机。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七月诗派的灵魂人物艾青认识到了新的时代语境下诗人的使命,“对于这民族解放的战争,诗人是应该叫付出最真挚的爱和最大的创作雄心的。为了这样,我们应该羞愧于浮泛的叫喊,无力的叫喊[1]281”。他怀着极大的悲悯关注祖国与人民的命运,将受压迫受蹂躏的一群的触目惊心的苦难呈现在读者面前,如《乞丐》《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补衣妇》,诗中进行苦难的呼喊的同时,艾青又是十分执着地追求着真善美,“真、善、美,是统一在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1]259”。通过诗歌诗人传达了自己对于光明的渴求,如《向太阳》《火把》。
此外,七月诗人还有被称作“时代的鼓手”的田间,他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全诗节奏明快,犹如进军的鼓点,召唤读者奔赴战场,另如鲁藜的代表作《夜葬》《延安散歌》,绿原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曾卓的《狱》等展现了七月诗人关注现实、关注大众的敏感及七月诗歌丰富深刻的审美风格。
抗战诗歌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诗歌并非直关抗战,但同样关注现实,颇具艺术水平的诗人诗作,臧克家即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臧克家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他从小生活在农村,耳闻目睹了农民的悲惨处境。1933年还是大三年级学生的臧克家,在闻一多、王统照等人的帮助下出版了诗集《烙印》,用诗歌“唱着生命的不幸”,如《老马》:“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的垂下!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以老马为象征,概括了旧中国农民身负重荷的苦难以及诗人对造成这苦难的愤怒和诅咒。诗集出版后即获得了诗坛的认可和赞誉。在臧克家的诗歌创作历程中,他始终力图让自己的诗情围绕着大时代,“以诗情为大时代摄影[9]192”。七七事变之后,诗人辗转到了抗战前线,先后出版了《从军行》《泥淖集》《淮上吟》等诗集,《从军行——送珙弟入游击队》:“明天,灰色的戎装,会把你打扮得更英爽,你的铁肩头,将压上一支钢枪。今后,不用愁用武无地,敌人到处便是你的战场。”臧克家这一阶段的诗歌充满着强烈的爱国激情。1942年诗人到重庆后以凝练、质朴的诗句书写了对泥土的眷恋,以及黎明前的黑暗的痛苦挣扎,真正写就了关注现实生活、体现大时代精神的“泥土的歌”,发表了诗集《泥土的歌》《古树的花朵》。如《春鸟》诗作开篇虽然格调明丽,而诗末诗人告诉人们“我的喉头上锁着链子,我的嗓子在痛苦地发痒。”
臧克家既注重诗歌的内蕴,也注重诗的艺术,他强调“还有一些人在做口号诗,我是反对的。在作者或者想用它作为一种宣传思想的工具,不过,口号没有力量,满篇的鲜血和炸弹是不能叫人感动的,何况在诗的本身已失掉了诗的条件呢[10]”。臧克家的抗战诗歌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围绕大时代的主题,二是不以消解诗歌的艺术价值为代价去追赶时代精神。他以独特的创作姿态、诗人敏锐的时代感悟在抗战诗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此外,现代主义诗人卞之琳和何其芳也是极力追求诗歌精神和艺术的平衡。抗战爆发后,卞之琳受时代感召用半格律体或格律体创作关注邦国大事的诗歌,他的诗集《慰劳信集》是对抗战生活、人物和事件的诗意记录,不仅有历史价值更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何其芳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诗风朴素、明朗,也是关注风云激荡的社会现实的应时之作。
四、抗战诗歌的审美时代特点
抗战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国难,人民在灾难中觉醒,诗人们用如椽之笔作为捍卫民族尊严的武器。抗战诗歌就是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非常时段里的诗美特征。
1.审美价值追求:时代与政治的合谋
在国破家亡的苦难年代,唤起同胞的觉醒与抗争,歌颂抗日将士的英勇顽强,揭露侵略者的残暴,哭诉战争带来的伤痛成为这个时代突出的主题,“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诗的繁荣基础在民主政治的巩固上,民主政治的溃败就是诗的无望与衰退[1]261”。1942年5月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抗战文艺的发展方向,并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强化了诗歌的政治意识,也使得抗战诗歌的政治功利色彩凸显得淋漓尽致。
身处狂风暴雨的时代,诗人们都自觉地接受了时代的感召,放弃表达个人情绪的悲喜,摒除风花雪月的恋歌,认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能写诗已经是可耻了,而再闭上眼睛,囿于自己眼前苟安的小范围大言不惭地唱恋歌,歌颂自然,诗做得上了天,我也是反对,那简直是罪恶![11]”“雨巷诗人”戴望舒在民族危难面前,同胞水深火热的挣扎面前,不再沉湎于个人的哀愁转而创作了《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等诗作。诗风唯美的何其芳以抗战为界开始从诗歌中寻找革命,如《秋天》。胡风写于1937年的《为祖国而歌》:
为了抖掉苦痛和侮辱的重载
为了胜利
为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
为了你啊,生我的养我的
教给我什么是爱 什么是恨的
使我在爱里恨里苦痛的,
辗转于苦痛里
依然能够给我希望给我力量的
我的受难的祖国!
诗人向受难的祖国呈现了自己炽热的心,一个诗人对于祖国的无限忠诚。1942年,诗人陈辉创作了同名长诗《为祖国而歌》:“祖国呵,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我高笑,因为呵,我—你的大手大脚的儿子,你的守卫者,他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诗’。”同样是向祖国传递了最为缱绻的依恋和坚定。由此可见,抗战诗歌中,诗歌与战争结合,为抗战救亡的政治服务是诗歌的前途,也是时代的需要。
2.大众化的追求与艺术形式多样化表现
早在“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中,隐约可见文艺“大众化”的倾向,30年代左联在上海兴起了大众化运动,直到中国诗歌会的成立,蒲风等人正式提出了中国诗歌会创作“大众歌调”的主张,认为诗歌应做到“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9]156”。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提到“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什么是大众化呢?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2]”。
抗战诗人为将抗日救亡的主题诉诸大众,为了宣传调动人民的战斗热情,为了诗歌与大众的真正意义的接近,创作大众能理解和接受的作品,诗人们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诗歌语言的散文化,艺术形式的民间化。
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白话口语皆可入诗,格式自由不拘,多采用重复的方法造成一种语意的强调和音节的和谐押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五四”自由体新诗的又一种发展。如艾青的《乞丐》:“在北方,乞丐徘徊在黄河的两岸,徘徊在铁道的两旁。在北方,乞丐用最使人厌烦的声音,呐喊着痛苦……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另如《马凡陀山歌》:“忽听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拎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采用怪诞通俗的白话语言让“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理解诗意。
为了“要使得诗重新成为‘听觉艺术’,至少是可以不全靠眼睛的艺术,而出现在群众之前,才能使诗更普遍地,更有效地发挥其武器性,而服务于抗战[4]569”,抗战诗人的另一个尝试是民间化、平民化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探索。“本来,诗底本质,在文学上对读者所要求的较高,读者必须有响荡的文化水平才行。但现在对诗的要求是愈广泛地动员民众愈好,所以诗也要求和民众愈接近愈好。诗人也要求能直接地教育并提高民众底意识。以前,诗底发表方法是在大报章杂志上面或印单行本。而现在,诗人自己也感到不够,为了要更广泛地接近民众,诗人得找出各种方法:一是诗朗诵,一是街头诗,一是诗画展览,一是旧形式底利用,一是多做歌。开辟了许多的道路[2]55。”其中朗诵诗被称为“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如高兰的《是时候了,我的同胞》:“人在怒吼,马在嘶叫,苍天在旋转,大地在狂啸,子弹在枪膛跳跃,大刀在手中咆哮。”以适合朗诵的口语向人民发出时代和历史的呼喊,充满战斗性和感染力,引导人民奔向救国的战场。
歌谣体诗歌,即将民间歌谣与诗相结合,通过反复咏唱,增强节奏感和抒情氛围。如以陕北民歌“信天游”为基础而创作的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至今广为传唱的《黄河大合唱》和《游击队歌》。另外,比较突出的表现形式还包括街头诗、传单诗、手榴弹诗等。
3.新诗的丰碑与永恒的记忆
抗日战争作为近现代历史最为沉重、最为壮丽的一页,已经深深地镌刻进历史的年轮,化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抗战文学使这记忆变成永恒,而诗歌因其灵活性和战斗性成为抗战文学中激进的先锋,它现实主义的写作笔法使得直至今日我们再诵读那些抗战诗篇仍能感受时代的战声、触摸诗人澎湃的热情。
“诗歌之发达,是由于在这个神圣伟大的战争的时代,对着层出不穷的可歌可泣的事实,作家容易得到感动以致情绪的跳跃。而他要求表现时所采取的形式,就是诗[2]52。”历史不会忘记,先驱们用诗句记载民族的苦难、流亡者的悲歌,如刘心皇的《人造地狱》、穆木天的《我们的诗》《歌唱呀,我们那里有血淋淋的现实》。历史不会忘记,中华儿女对受难祖国的炽热忠诚与民族危亡的抵抗,如田间的《义勇军》、启海的《到敌人后方去》;历史更不会忘记我们一次又一次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如祝实明的《前线——纪念四月七日台儿庄的大胜利》。
诗歌在记录时代风云提醒后世勿忘国耻的同时,留给我们的深刻反思也是发人深省的。“侵略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侵华战争,除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穷凶极恶、猖狂无似外,近百年的积贫积弱,政治的腐败,外交的无能,保守、封闭、一盘散沙等旧时代民族性的某些弱点,也是中华民族饱受欺凌的深刻原因[13]。”国富则民强,祖国强大才是人民幸福和尊严的保障,这在时代发展的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另外,在新诗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抗战诗歌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页纵使蒙受了诸多非议,称其“艺术的贫弱”,“公式化倾向”,但历史地看,抗战诗歌确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完成了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也通过艺术上的多样化选择和尝试展示了中国新诗的风流华彩,抗战诗歌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不失为一座耀眼的丰碑。
称抗战诗歌为丰碑,不仅是因为它很好地继承了五四以来新诗的革命传统,配合了抗战的主题,完成了宣传和推动战斗的使命,更是源于它对诗歌艺术的多方面的探索,主要体现在诗体、诗歌精神、诗歌传播方式这几个方面。为了实现诗歌的大众化路线,实现诗歌和人民的真正意义的接近,诗人进行了包括歌谣体、政治抒情诗、政治讽刺诗等多种诗歌形式的探索;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抗战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代的主题赋予了诗歌独特的精神风貌——热烈、激昂,这是诗的品格,也是时代的风貌。由于社会对诗歌审美价值取向的改变,诗歌的传播也有较大的突破,包括朗诵的形式、街头诗、配乐说唱、诗画展、与民间文艺相结合等形式,演绎了诗歌传播的丰富而新鲜的图景。
“一个时代艺术真正繁荣的标志是,总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与天才代表[9]527。”按照这样的标准,抗战时期无疑是诗歌艺术繁荣的时代,经过了五四新诗的积淀,抗战诗歌本已积累了大量的艺术经验,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下,携着其崇高的革命主题、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伟大的民族精神、强烈的民族正气及波澜壮阔的史诗格调,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这些在血与火中产生的诗篇,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成为时代的记忆,诗歌史上的丰碑。
[1]刘 屏.艾青[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胡 风.胡风评论集: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臧克家中国现代文学馆.臧克家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78.
[4]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吴景明,韩晓芹.中国现代文学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84.
[6]吴晓东.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导言[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8.
[7]周晓风.新诗的历程:现代新诗文体流变1919-1949[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285.
[8]蒲 风.蒲风选集: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594.
[9]蒋登科.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M].成都:巴蜀书社,2010.
[10]臧克家.臧克家文集:第九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4.
[11]臧克家.论新诗[M]//中国现代文学馆.臧克家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218.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8.
[13]李良志.抗战诗歌·序言[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2.
The M emory of Era and the Eternal M onumentalW ork——On Anti-Japanese W ar Poetry
CAO Shuai
(Department of Basic Teaching,Yingk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ingkou 115000,China)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s fossil records the trauma and hope of the Chinese in the disaster years.Poet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 ith its advantages of flexibility,richness and m ilitancy has become themost active par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This article respectively combs the development of Anti-Japanese War poetry,arrangement poetry styl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at the same time,introduces the outstanding poet and the poet groups.in the en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etry art value from the follow ing aspects such as the pursuit of aesthetic value,popular tendency and a variety of art forms to explore,and the new poem monument and eramemory.
Anti-Japanese War poetry;development;style differences;The poet community;art value
I206.6
A
1672-9617(2015)04-0454-08
(责任编辑伯灵校对伊人凤)
10.13888/j.cnki.jsie(ss).2015.04.004
2015-08-22
曹 帅(1984-),女,辽宁鞍山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