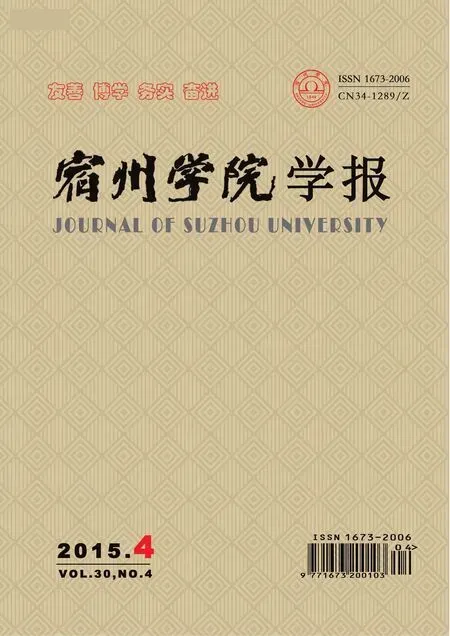社会资本在中国农村民间组织运作中的作用
李正中,王富春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社会资本在中国农村民间组织运作中的作用
李正中,王富春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在分析目前学者对农村民间组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资本在农村民间组织运作中的作用。社会资本理论注重分析文化因素对个体活动及个体间关系的影响。在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运作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促使人们向组织提供资源,以换取所需,规范机制则降低组织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对组织的信任,而基于闭合社会的关系网络机制和“亲亲”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关系则充当动员网络资源,限制“搭便车”行为以及扩大社会资本获取渠道的作用。当前,社会资本在中国农村民间组织运作工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熟人社会情境下容易产生制度规范困境的难题,需要政府与民间组织互派代表,定期协商,互相吸纳与合作。
农村民间组织;社会资本;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网络
1 农村民间组织研究概述
时下对中国农村民间组织开展研究的学者众多,代表人物有俞可平、熊培云、李熠煜等。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数量约为300万个,而其中大约200万左右根植于农村地区[1]。之所以产生数量如此巨大的民间组织,主要缘于改革开放后,国家取消将所有农民纳入“体制内”的人民公社,代之以农民自主生产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政府权力机构对农村的控制相对放松,使得农村地区拥有了一定的自主空间,能够发展出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2]。此外,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不足,国家优先发展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的政策,使得农村处于资源长期紧缺的状态,迫使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如敬老会、筑路会、各种基金会等[2]。本文所述湖南邵东乡村的一个教育基金会也是此种类型。
还有学者指出,农村精英分子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中国古代皇权的统治范围至多只能延伸至县,县以下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则依靠作为农村精英代表的不吃皇粮的乡绅阶层。近代以来,依靠乡绅衔接权力中心与偏远地区的双轨制被摧毁,原先作为乡绅的农村精英不再作为中间阶层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机构对农村控制的相对放松,部分农村精英人士得以解放出来,这些活跃在农村的精英阶层,办事能力强,拥有广大农民认可的权威,拥有良好的号召力。他们对农村众多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
学术界对民间组织的研究理论,较经典的有公民社会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前者以周珍等人为代表,其理论可以概括为:随着人们公民意识的觉醒,各种社会组织和群体自发组成自治空间,减少政府机构对社会的干预和过度市场化,解决政府和市场所不能解决的种种问题,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对社会的损害[3]。然而公民社会理论最初是西方学者用来研究欧美地区非营利组织所采用的理论工具,而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产生、发展模式和运作机制都烙有鲜明的本土印记,把当下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简单归附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仍然值得商榷。社会资本理论则着重分析种种文化因素对个社会组织运作的影响,比较典型的研究案例为董翔薇女士对当代宗族组织的研究。她认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包括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信任网络,而传统社会关系本位的特征决定了宗族的组织特征与功能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因子[4]。考虑到中国农村留下的传统文化因素的烙印较深,尤其是“关系”对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本文即采用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的理论工具。
2 社会资本与关系网络
在日常生活中,人情、关系、面子构成了中国人社会交往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正式关系失去效用的时候,上述要素往往能够另辟蹊径,促使问题的解决。这些不那么光明正大,却作用非凡的潜规则,则构成了人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多少是制度化的。”[5]布尔迪厄将社会资本细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并且遵循某种规范,因而是有迹可循的。
理性行动论代表人物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包含了他人对行动者的信任,行动者之间的信任使得组织与群体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6]。格兰诺维特则提出了“弱连带优势”理论,认为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由于行动者互动频率、情感力量、亲密程度等因素分为强弱不同的程度。人们通过家人、亲属、挚友等强关系虽然更容易获取社会资本,但强关系数量毕竟有限,所获取的资本也因强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在地域、职业等因素上的高度相关性而在资本总量和多样性方面受限。而弱关系,如同学、同事等相熟关系数量较大、分布范围较广,因而,通过弱关系可以拓展社会资本获取的渠道,使得组织或个人在交换活动中得到总量上更多的社会资本[7]。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的概念包含以下内容:
(1)社会资本不完全是物质性资本,可以在社会网络中通过互动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本,因此,社会资本是一种影响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关系的资源。
(2)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也是获取其他形式社会资本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弱连带优势则增强了人们从关系网中获取资本的能力。
(3)信任机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机制,它出于人们获取自身利益的需要,并使得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4)社会资本的规范机制降低了集体行动的不可预见性,增进了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感。
本文试图在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以湖南邵东县文珍教育基金会为例,阐释社会资本在农村民间组织运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3 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作用——以文珍教育基金会为例
通过网络了解到位于湖南邵东县坝上村的文珍教育基金会,这是一个较典型的自发的农村民间组织。该基金会的发起方张氏宗族,在当地是一个有名望的大家族,自1996年始,几位领头人物开始商议建立基金会,以帮助贫困家庭学生读书。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本地村民和家族成员中筹得足够的资金,开始资助当地家境困难的学生[8]。在这一例子中,可以考察到社会资本的四种重要机制。
首先是基于闭合社会的关系网机制。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网,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差序格局”是一种代表性的理论:“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9]传统社会的关系网是以核心小家庭为基础,血缘纽带为支撑的。追溯其思想来源,则是传统的儒家“亲亲”思想。所谓亲亲,就是“亲其所当亲”,以血缘的亲疏为标准规定人们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中国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中,缺乏多元化的资源与信息交流渠道,人们的交往更加依赖这些有限的关系网。基金会所在的坝上村,大部分村民都姓张,都是张家后代,彼此之间关系密切。这种闭合的关系网可以充分动员身处网中的人们所拥有的资源,并且能够有效限制关系外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从而有效地保证了集体成员的合作行动的效率。基金会之所以打着张氏家族的名义,就是为了以宗族的名义,发动大家积极捐款。如果没有这一关系网,筹款活动就可能无从下手。
其次是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科尔曼认为,信任关系的建立源于行动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趋向。一个基本的信任关系的双方分别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委托人之所以将自己掌握的部分资源转交给受托人,是相信通过建立委托关系,可以得到相比之下不建立委托关系时获得更大的利益[10]。当地村民之所以愿意投资基金会,是因为基金会承诺为当地家庭困难的孩子提供资助,以完成学业。这对村里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受到集体资助的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会回报当初的资助者。在权衡得失之后,大家选择相信基金会,一个简单的信任关系就形成了。如果基金会的承诺不够美好,或者村民们认为捐助所换来的回报价值低于期望,则不会形成信任关系,也不会有人捐钱了。
再次,社会资本的规范机制也确保该基金会的持续发展。布尔迪厄认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能有效降低组织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并在交换行为中顺利地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本[11]。文珍基金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设立理事会,理事成员由基金会成员大会选举产生,采用无记名投票,不事先提名候选人;财务制度上,为确保财务透明,设出纳和会计,捐款存折由出纳保管,取钱印章由理事长保管,开出票据则由会计保管,俨然是微缩化的“三权分立”架构。严密规范的制度,增强了人们对基金会的信任,使组织得以持续运转下去。
最后,基于“亲亲”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关系”,在基金会的筹办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珍基金会刚开始筹建的时候,难以获得捐助,因为大家都处于疑虑而观望中,必须有人率先带头捐钱,才能给人们以表率。而最先捐款,同时也是捐钱最多的两人在社会和地理空间上离张家村相去甚远,他们虽然同为张氏后人,但早已远走他乡,两人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财富。以“差序格局”分析,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弱关系”。但基金会的发起者成功打动他们为基金会捐款,这是建立在同一宗族基础上的弱关系凸显出的独特力量:首先,通过这两位捐助者的人脉,能够联系到更多的潜在捐助者,拓宽了基金会吸收资金的渠道;其次,这两位的捐款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增强了人们对基金会“办实事”的信心,有效地带动了还在观望的村民。此后,村民踊跃捐款,很快筹得了基金会的启动资金。
4 社会资本在农村民间组织运作中的困境与对策
如前所述,在社会资本视角下,闭合社会关系网络机制、信任机制、规范机制和弱连带优势在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运作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因素也如同双刃剑一般,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阻碍,形成了发展困境。最典型的即为制度规范困境,具体表现为熟人社会下组织的正式制度与成员之间非正式关系相矛盾的困境。
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影响人们活动的重要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非正式社会关系既能促成组织的运作,也可能对其发展产生消极作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熟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能够绕过正式制度,造成俗话说的“走后门”现象。正式制度拒绝“走后门”,要求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按照程序进行,而非正式关系却将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作为能否成事的标准。当组织的活动同时遭遇这两种条件时,困境就产生了。笔者在考察文珍教育基金会时曾听说过这样一个事例:基金会一副理事长打算造新房,于是想向会里借钱,其人既是副理事,又给筑路会捐了2万元,彼此都是熟人,这使得组织的其他成员很难办:“这是大家的钱,今天你借1万,明天我借1万,没几天钱就没有了,这口子开不得。但是又不能这么讲,大家都是一家人。”在农村民间组织中,这一类制度规范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很多民间组织都因为内部熟人关系破坏了组织正式制度与原则,既降低了组织的办事效率,也影响到其他人对组织的信任,使得组织运转受到影响。
由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总倾向于追求自我利益,所以仅依靠组织成员的自律无法克服这一困境,笔者认为,民间组织与基层政府互相吸纳合作是一种相对可靠的解决办法。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是以法律形式确认的广泛认可的正式制度的执行代表。基层政府可以指导民间组织的制度建设,完善制度规范,并在保持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监督民间组织的活动。同时,在政府职能顾及不到的地方,民间组织又可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与政府机关实现职能互补。在具体的做法上,建议基层政府与民间组织互派代表,定期开展协商会,此举既能使政府及时了解民间组织的活动情况,听取民意,指导民间组织的自身建设,同时,也方便民间组织对政府开展民主监督,配合政府政策开展相应的活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5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农村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社会资本的诸机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已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民间组织和基层政府有着共同的治理空间,在组织上也可以彼此吸纳、互相合作。为了克服面临的熟人社会关系网下容易产生的制度规范的困境,需要加强政府的指导工作,将产生于民间的社会组织整合到合法的管理程序中来。同时帮助它们进行自身的组织建设,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民间组织的能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1]俞可平.中国民间组织与治理:以福建省漳浦县长桥镇东生村为例[EB/OL].(2006-8-24)[2014-11-30].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6/08/1181.htm
[2]李熠煜.当代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研究[J].人文杂志,2004(1):167-168
[3]周珍.我国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研究[J].华中人文论丛,2010(1):18-20
[4]董翔薇,崔术岭.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宗族: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J].学术交流,2009(3):160-163
[5]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
[6]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120
[7]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6):1360-1380
[8]刘逸中.坝上教育基金会,助推重教好学风尚[EB/OL].(2012-10-10)[2014-11-30].http://www.chinashaodo ng.com/Info.aspx?ModelId=1&Id=18705
[9]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3:26
[10]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
[11]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415
(责任编辑:周博)
10.3969/j.issn.1673-2006.2015.04.002
2014-12-11
李正中(1989-),安徽合肥人,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F320
A
1673-2006(2015)04-0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