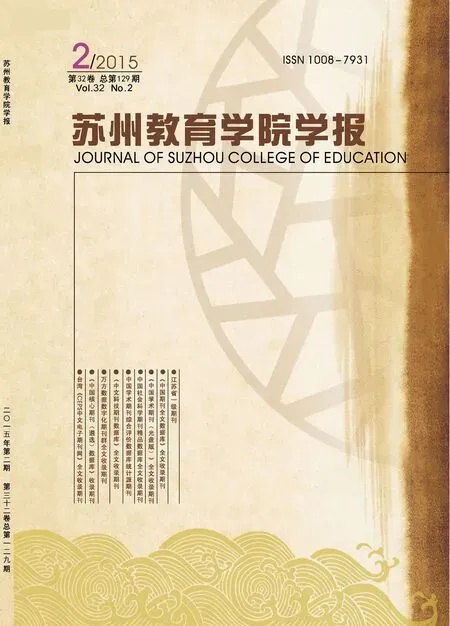从《孔乙己》看鲁迅的悲剧意识
摘 要: 发表于1919年的《孔乙己》,是鲁迅作品中最富于悲剧性的一篇小说,它通过对孔乙己一生悲剧命运的讲述,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冷漠凉薄的人情世界。“孔乙己”的悲剧既透射出一种民族与文化的悲剧性内容,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孤独与绝望,并蕴含着鲁迅先生反抗绝望、打破现状的期盼和决心。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2-0038-04
收稿日期: 2015-02-28
作者简介: 席志武(1985—),男,江西高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A Review of Lu Xun’s Tragic Consciousness via KongYiji
XI Zhi-wu
(College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KongYiji, published in 1919, is the most tragic story of Lu Xun. By narrating Kong Yiji’s tragic fate, it reveals an indifference and cold-blooded human world for readers. The tragedy of Kong Yiji refl ects the tragic contents of a nation and culture. The novel can also be said to refl ect the profound inner loneliness and despair of Lu Xun. Meanwhile, it embodies Lu Xun’s hope and resolution to revolt against despair and to reverse the current situation.
Key words:KongYiji;Lu Xun;tragic consciousness;revolt against despair
《孔乙己》 ①,据孙伏园讲,是鲁迅先生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小说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1]。小说发表于1919年,那时正值中国文化思想大解放与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作为立志“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选择了20多年前的“咸亨酒店”这一特殊的时空环境,通过塑造“孔乙己”这一落魄知识分子的形象,给读者营构出一个彻底绝望的叙述空间。
一、孔乙己的边缘身份
小说开篇就交待了咸亨酒店的顾客状况,大致分为两类:“短衣帮”和“穿长衫者”。这种分类完全因财富多寡而自然形成,实际也是一种社会等级的真实写照。“短衣帮”通常只能花四文钱买一碗酒,所以在柜台外站着喝;而“长衫主顾”则相对阔绰,可以花上十几文,所以傲慢地踱到包厢,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长衫者”的这种“傲慢”,显而易见是“傲慢”给“短衣帮”看的,“短衣帮”对于社会的不公现象自然也习以为常。两类人相安无事,毫无瓜葛。而所有这一切都被酒店里的小伙计“我”看在眼里,一切亦顺理成章,习惯成自然。
独一无二的“孔乙己”似乎正好处于这二者之间:他跟“短衣帮”一样站着喝酒,却又跟“长衫主顾”一样穿着长衫,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小说中那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读起来实在耐人寻味,这既是孔乙己一生的写照,同时又隐隐映照出封建时代所有落魄文人的处境和地位:在经济状况上明明是个穷人,可又穿着长衫;在精神生活上明明是读书人,偏偏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传统社会的中国文人,大抵都怀抱有“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跻身仕途。或许人们总是习惯于被“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理想所感动,却往往忽视了那些被科举埋葬了的卑微的生命。
边缘的文化身份不仅让孔乙己的外形显得独特,而且也让他在“短衣帮”和“长衫主顾”两个阶层中表现得格格不入。在酒店里,他最终沦为掌柜和“短衣帮”任意嘲笑挖苦的对象。这“笑”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一种得意者对失意者的居高临下。而12岁的“我”当然也是参与其中的一个。因为孔乙己读过书,满口“之乎者也”,这在“短衣帮”来说,实在是迂腐可笑。而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孔乙己还经常偷书,可是偷盗本领又并不怎么高明,每每被人抓住,便遭一顿毒打,以至于“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偷书而被打,这在“短衣帮”看来,原本也是一件值得观赏的好戏。明明被打了,可孔乙己偏偏又碍于面子矢口否认,以狡辩的方式来捍卫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小说通篇充满着肆无忌惮的笑声,似乎孔乙己是全天下最好笑的笑料。然而,这种笑本身似乎又毫无意义,因为孔乙己的存在对于所有人来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小说写道:“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句话大约算是全篇最令人感到“凉薄”之气的了。事实上又何止孔乙己的生存状态如此?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孤独,它所深刻揭示的,正是鲁迅内心深处一种无所不在的悲哀感和绝望感,一如他在《野草》中藉“独语体”的方式所表露出的寂寞孤独一样。
孔乙己终因偷窃而在得势的丁举人的毒打下成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对象。“短衣帮”的嘲笑似乎并没有在身体和精神上摧毁他,而彻底毁灭他的是原本与他有着一样身份而又最终得势的丁举人。落魄的文人被得势的文人暴打,“打折了腿”,最终只好用手走路;原本是“身材很高大”的人,最终只能盘腿坐在门槛上被人居高临下地俯视。掌柜及其他人仍只是取笑他,到这时候,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也全然被耗损殆尽了。
二、孔乙己的生活世界
由于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的半知型叙事方式,所以所呈现的孔乙己的生活多发生于咸亨酒店。对于孔乙己酒店之外的生活,则所知甚少。不过可以推断的是,孔乙己作为一个穷酸落魄的读书人,脸上长了皱纹,且有着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可见他已步入中老年。令人奇怪的是,他似乎一直没有家庭,没有亲人,没有兄弟,也没有人关心他的死活。酒店外的生活对他而言也完全是一个冷冰冰的凉薄世界。
而在咸亨酒店,孔乙己的交往对象主要为“短衣帮”,因为常常站着一起喝酒。喝酒似乎已成为他主要的一种存在方式。虽然小说通篇都可见孔乙己是供人嘲笑的对象,但从他与“短衣帮”的交往来看,实际仍可见出孔乙己身上所固守的文人傲气。比如有人说:“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孔乙己并不回答,他用一种看起来极为“傲慢”的方式对此进行回击,“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这一“排”字用得是极为精彩的。孔乙己此举,充分说明他在“短衣帮”面前固守着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感—“短衣帮”只能花四文钱买一碗酒,孔乙己偏偏买了两碗,而且还要了一碟茴香豆,回击得似乎铿锵有力。还有一次有人问他:“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同样表现出一种不屑置辩的神气,等于是用表情回答了这个问题。由此可见,孔乙己在“短衣帮”面前有着极为强烈的自尊。不过,这样的自尊实际上仍是软弱不堪,当有人指出他因偷书被吊着打,并问他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没捞着时,孔乙己的自尊立马消失不见,显露出一副落魄与颓唐的样子。
显而易见,孔乙己与“短衣帮”的交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这又是一种怎样落寞的心情呢?与孩子交往无疑是一种简单纯粹的人际关系,因为孩子单纯,没有如成人那样多的世俗偏见。可是,实际情形比想象中来得更糟,“我”作为一个只有十二岁的伙计,骨子里同样是瞧不起孔乙己,这一点与“短衣帮”并无任何区别。当孔乙己问“我”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时,“我”的内心竟充满了对他的鄙夷与厌恶:“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然而,与“我”的不耐烦及不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乙己却表现得无比耐心和真诚,没有偏见,极为动人:“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孔乙己这种真诚的赤子之心在与“邻居孩子”分吃茴香豆的时候也表现得同样明显,这种情形跟他与“短衣帮”的交往状态是全然不同的。虽然,极有可能这些“邻居孩子”都是“短衣帮”的孩子,且这些孩子长大后都极有可能成为“短衣帮”。孔乙己的真诚最终还是落了空,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回应,而孩子的冷漠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对孔乙己的损害。也就是说,孔乙己与“短衣帮”之间的隔阂,在孩子这里同样存在着。这一点T.赫斯特(Theodore Huters)揭示得十分清楚:“《孔乙己》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叙述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参与了对孔乙己的折磨。” [2]此正深刻地道出了鲁迅的悲剧性意识。
小说的令人绝望之处,也正恰恰体现在孔乙己的生活世界里。在孔乙己的生活世界中,何家、丁举人可以打他,“长衫主顾”们疏远他,“短衣帮”和掌柜耻笑他,孩子的心里也厌恶他……这样一种“凉薄”的生存困境,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自己曾经历过由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 [3]。由此,作者对于世态的凉薄有着深切的体会,这种感受,想必与孔乙己的感受是息息相通的。
三、孔乙己的悲剧象征
如果说小说《孔乙己》呈现的“咸亨酒店”是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社会缩影的话,那么我们从中很难看到它有任何变好的可能。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人的身上能体现出“正能量”,也没有一人能够担当得起让社会变好的使命。
何家和丁举人,隐隐表现出一种无所不在的淫威,他们是得势的文人,是现实社会秩序的当权者和捍卫者。鲁迅通过简单几笔,就将他们为富不仁、凶残狠毒的秉性勾勒得淋漓尽致。“短衣帮”,本身是社会的底层民众,封建时代的不幸者,可他们愚昧无知,对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还常以取笑他人为乐。掌柜,只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奸商,卖酒兑水,又有着一副凶恶脸孔,他唯一念念不忘的,是“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虽然“品行比别人都好”,且对孩子极有耐心,极诚恳,但有时又免不了做些偷窃之事,最后终于被打残,落得个悲剧下场。孩子们,兴许是未来的希望,可“我”的表现并不比“短衣帮”好多少,或许,长大后还能更坏……这样的社会模式显然不是鲁迅愿意看到的,也是绝对要打破的。
在传统“四民”社会中,孔乙己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形象,原本是乡民追随的楷模,原本肩负着兼济天下的神圣使命。可在他身上,传统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启蒙模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民众对他尽情的挖苦和冷嘲热讽。这个镜头后面,实际上又隐含着鲁迅本人的态度,即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深刻,以及对于思想启蒙所保持的冷静,同时又未尝不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孤独。从某种程度上说,愚陋怯弱的国民性,几乎成为当时社会前进的巨大阻碍。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中,鲁迅曾激烈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并借狂人之口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号,表达对孩子以及对未来的希望。而在《孔乙己》中,我们似乎根本看不到孩子身上的善良本性,也看不到任何拯救的可能性,也许这些孩子仍只是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将重复上演着“咸亨酒店”里所发生的一切。
从这一角度来看,鲁迅的悲观与绝望于此变得更加彻底,他通过小伙计“我”来讲述孔乙己的悲剧人生,既否定了这个由丁举人掌控的生活世界,也否定了孔乙己的落魄命运,还否定了拯救孩子的可能性。这与之前《狂人日记》里喊出“救救孩子”的期待不同,又与之后《药》里在夏瑜的坟上添个花环也不同,鲁迅于此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人情的“凉薄”,更是一种面对四壁黑暗的孤独和绝望,同时又是鲁迅反抗绝望最为鲜明的艺术表达。汪晖指出:“‘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并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探讨,而且同时体现为对普遍存在的人生状态的观察和思索。‘绝望’不只是对个体而言,而且包含着深刻的民族与文化的生活内容。” [4]鲁迅也正是通过对落魄文人孔乙己悲剧命运的揭示,呈现出他对于转型时期的近代社会的深刻认识和深沉思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5]由此而言,孔乙己的悲剧可以说是病态社会中不幸的知识分子的悲剧,这个悲剧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病态社会中丁举人的凶残险恶,照出了“短衣帮”的愚昧麻木,照出了孩子的淡漠冷酷。而持这面镜子的人,一个以“改造国民性”为志向的思想启蒙者,他冷冷地看着镜中所呈现的这个病态世界,内心充满了绝望的悲观情绪。在这种绝望当中,实际又透露出鲁迅对于绝望的反抗,这种反抗的姿态,恰恰又是基于鲁迅对于“不幸人们”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于社会人生的赤诚热爱。
现代作家司马长风将鲁迅比作是深隐在作品幕后的“满身铜盔铁甲的武士” [6]。事实上,透过这层帷幕,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鲁迅内心深处的悲哀,以及他所感受到的冷漠凉薄的人情世界。他将自己所见的悲哀与阴冷世界赤裸裸地袒露给我们看,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印证了李泽厚对他所作的评价:“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