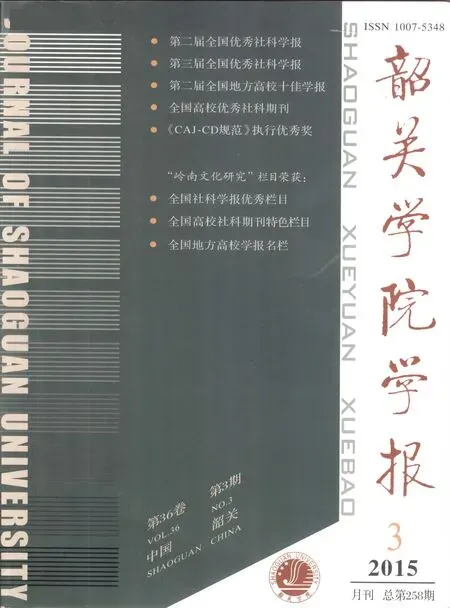韦应物山水诗中的“以我观物”探究
陈小珏
(韶关学院文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韦应物山水诗中的“以我观物”探究
陈小珏
(韶关学院文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中唐诗人韦应物的山水诗,以其淡雅的风格受到世人的推崇。但这种纵情山水之情又不同于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而多出几分幽深的情思。这是缘于韦应物好“以我观物”,而不是“以物观物”。在寄情山水中,时时流露作者自己的主观情感,充分体现了中唐时期大历诗风中落寞感伤的一面。
韦应物;山水诗;以我观物
在我国古典诗词史中,山水诗虽不乏少数,却多注入在羁旅、赠友和游览等诗歌中,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划分类型。按陶文鹏、书凤娟主编的《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中的说法:“山水诗,就是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和表现对象的诗歌。山水诗并不限于描山画水,它还描绘与山水密切相关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1]而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是山水诗的主要表现特征。韦应物的山水诗亦是如此。今所见四部丛刊本的《韦苏州集》分十四类,即赋、杂拟、燕集、寄赠、送别、酬答、逢遇、怀思、行旅、感叹、登眺、游览、杂兴、歌行[2]271。但是在这十四类的寄赠、送别、行旅、登眺、游览中,却多处可见诗人纵情山水、抒发人文情怀的踪迹。因而,这几类诗也最能代表韦应物山水诗的特色。
一、韦应物山水诗中“以我观物“的情感基调
对于韦应物山水诗的风格,唐人司空图曾评有“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与李生论诗书》),将他与王维相提并论,即是肯定韦诗淡雅的风格。今人对韦应物的山水诗研究也多将他与王维进行比较分析。但无论是前人还是今人,对二人语言上的淡雅风格总能达成共识。然而不同处在于,王维的山水诗里,往往充满了远离凡尘的恬静色彩;韦应物的山水诗中,则少了这份闲适的空灵,显得略为沉重。因为他的诗中,总是藏着一颗不安的灵魂。影响到诗歌创作中,便是处处表露自己的情感。山水景物在他的诗中,已不再是营造氛围和境界的主角,而只是感情的寄托。这也是他不同与其他山水诗人风格的最大之处。他将自身渴望超脱又因现实的顾盼而不彻底的一面,珍惜深厚友谊、亲情的一面,以及体恤民情的一面,一一通过山水诗表露出来。使我们在他的山水诗中,体会最深的不再是迤逦的自然风光和物我浑化的“优美之境”,而是诗人无处不在的情感表达和那份幽深的色彩。
韦应物山水诗中这种无处不在的情感表达,实质即是一种“以我观物”的意境表达。依据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对“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的解释为: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3]
韦应物的山水诗中,正是体现了“物皆我之色彩”的“以我观物”。从魏晋南北朝时山水诗开始趋向成熟和完善,唐代后,经历了由自然景观的外部世界审美到内心世界对自然景观的感悟过程。其中,无论是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谢灵运的“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还是盛唐诸多诗人的山水诗歌,多表现为“以物观物”的意境构造。往往在诗歌中呈现的是物我合一的浑然境界。他们在用笔墨构造山水景观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意趣融化其中,常于平静宁和中达到“得意忘言”的境界感受,即“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也就是无我之境。所谓无我之境,并不是指诗人不带任何的主观情感融于诗中,而是指作为审美主体的“我”,不受外物的牵绊,达到“吾心宁静之状态”,在沉浸于外物之中达到两忘的境界。如前所述,在盛唐诗人中,李白、孟浩然、尤其是王维的山水诗,都表现为“以物观物”的审美意境特点。
但到中唐韦应物的山水诗里,这种审美意趣被逐渐退化。和他们的诗作相比较,韦应物山水诗中的主观色彩更浓一些,即以“有我之境”的表达为主。所谓“有我之境”,也不是指感情强烈个性鲜明之境,而是指“我”的意志尚存,且与外物有着某种对立的关系,当“外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威胁着意志时观物而所得的一种境界[4]。这一特点,在韦应物的山水诗里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在表现隐逸情怀的《龙门远眺》《蓝岭精舍》《东郊》等诗中,外物的景和“我”之意志,便是分离的。他可以于造景的闲适恬静里,突转笔锋为忧虑和不安的情绪。甚是在表现友谊之情的《广陵遇孟九云卿》《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亡妻之念的《除日》《对芳树》等诗中,直接用冷色调的意象来造景,以衬托自己失意伤感的情怀。同时,如上所列诗篇的分析,这种“外物大不利于吾人”的威胁,在韦诗中时而表现为景与情的背离,时而又表现为因景催发意志的发生,真实反映了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
二、韦应物山水诗中“以我观物“的诗作表现
受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的影响,唐诗到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已消顿了盛唐豪侠任气的风貌,退之为幽雅清淡。因而在韦应物的山水诗中,少了几分盛唐诗中超然平和的意境,却多出几分幽深的情思。山水景物,已不仅是他的抒情对象,更是寄托情感的方式。笔者按这一思路,将韦应物的山水诗以情感的表达类型大致分为三类:隐逸之情、友情之意、哲学之思。
(一)隐逸之情
此类诗歌,是韦应物山水诗的主要构成部分。纵观诗人的人生经历,从少年任侠,入宫为玄宗的三卫近侍,到后来的折节读书,入仕做官,韦应物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及衰的过程,“携手思故日,山河留恨情。存者邈难见,去者已冥冥”,山河的破碎,人世的变迁,都催发了这种特定时代下的心理。同时,官场的黑暗和自身高洁的志向,也使得他转而退求其内,独善其身。和陶渊明“退而结网”的精神不谋而合,而表现为一种隐逸情怀。元人倪瓒在《清閟阁全集卷十谢仲野诗序》中就评有:“韦、柳冲淡萧散,皆得陶之旨趣。”[5]644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亦提:“左司性情闲淡,最近风雅,其恬淡之处不减陶靖节”[5]645。将韦应物的诗歌风格和陶渊明相提并论。如下诗作:
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
都门遥相望,佳气生朝夕。
素怀出尘意,适有携手客。
精舍绕层阿,千龛邻峭壁。
缘云路犹缅,憩涧钟已寂。
花树发烟华,淙流散石脉。
长啸招远风,临潭漱金碧。
日落望都城,人间何役役。(《龙门远眺》)
在感悟山水的惬意中,诗人怡然自乐。从远景到近景,视觉到听觉,都在抒发“素怀出尘意”的向往。全诗以写景为主,但这种景却并未让诗人忘情融入到山水的怀抱中。他只是在借游赏山水来忘却俗世的烦恼,想从隐逸中寻到归避。所以诗的末句,才会突然辗转情思感慨“日落望都城,人间何役役”。他的隐逸诗,虽效仿陶体旨趣相拟,却少了一份陶渊明诗中,甚是盛唐诗人诗中那种纵情山水田园的豁达和从容,多了一份凄清萧散之气,在被立为诗人山水诗的极大成就之作《滁州西涧》中,也是在一片怡然的春景里,哀思重重。向往“独怜幽草”般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却又对“野渡无人”象征的官场中不在其位,不被其用的孤独感和失落包围。
同时,诗人的隐逸情怀又是摇摆不定的。他出身官宦之家,深受儒家入世精神的洗礼。《元和姓纂》卷二载韦应物出于北周逍遥公韦夐之后,其高祖为韦冲,任隋为户部尚书,封义丰公[2]272。《新唐书》亦载韦氏逍遥公房,韦冲子世冲,隋户部尚书、义丰公。冲子挺,象州刺史。挺子待价,相武后。待价子令仪,宗正少卿。令仪有五子:鉴,銮,錡,镕,镒(监察御史)。銮子应物,苏州刺史[2]272。在这样的家庭文化熏陶下,入仕为官的道路被视为人生价值的标准。但自身性格的耿直与官场黑暗的碰撞又时常让诗人对自己的入仕之路表示困惑甚至抵触。所以韦应物的一生,都是在任官和辞官的轮回中度过的。据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所记载,公元763年,韦应物任命为洛阳丞,在公元765及后两年内因惩办不法军士而被讼,后弃官闲居洛阳同德寺。公元774年,又委任为京兆府功曹,摄高陵宰。公元778年,为鄠县令,公元779年,除栎阳令,以疾告官。后又任尚书比部员外郎,滁州刺史任,在公元785年冬罢滁州刺史,闲居于滁州西涧,几罢几任。虽常是以告疾为由,但纵览全诗集,除开其在晚年写的《寓居永定精舍》中提到“眼暗文字废”,约莫有眼疾的倾向,并未从字里行间读出韦应物具体得过什么严重的疾病,倒是诗人在《广德中洛阳作》中有“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的感慨,可见真正病的是心。因时局的动乱,他只得“缉遗守微官”。但社会的责任感让诗人常常自省,渴望远离世俗的隐逸情怀又时时牵绊着他的心灵,所以就表现为吏与隐的矛盾:
所嗟累已成,安得长偃仰。(《蓝岭精舍》)
明晨复趋府,幽赏当反思。(《慈恩精舍南池作》)
所以在《蓝岭精舍》中,才会有“安得长偃仰”的无奈的感慨;在《慈恩精舍南池作》中,才会忽然从游玩的闲适中转为反思自己贪乐不务正事的行为,日人近藤元粹对此诗末句的评价为“趋府频频入诗,使人索然”[6]121。他以旁观者清的角度,看清了韦应物隐逸情怀之不彻底性。而这也正反应了他的吏隐矛盾之心态。“隐逸虽然从观念上说很符合中国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免与他们现实的功利态度相悖。”[7]96比之陶渊明的隐逸情怀,韦应物的山水隐逸诗是不够彻底和洒脱的。他只是借此来抒发忧思,让心灵得到暂时的解脱。他在观念上崇尚淡泊名利的生活,内心又眷恋功名仕途,所以才会在官场中几任几辞,呈现出一种难以取舍的矛盾心理。
(二)友情之意
“韦诗的又一特色是喜好在山林隐逸的洒脱氛围中表现友情交往的真挚醇厚,特别耐人寻绎。”[8]在他124首寄赠诗和67首送别诗中,多表现为这种友谊感情。并且诗篇中涉及多次且感情深厚的就有李儋、冯著、李博士等人。这种友情在诗中表现得含蓄却情深,“寄至味于淡泊”:
明月满淮海,哀鸿逝长天。
所念京国远,我来君欲还。(《广陵遇孟九云卿》)
冥冥花正开,扬扬燕新乳。
昨别今已春,鬓丝生几缕。(《长安遇冯著》)
楚山明月满,淮甸夜钟微。
何处孤舟泊,遥遥心曲违。(《送元仓曹归广陵》)
诗人用情至深,却不留痕迹。有送别时依依不舍的“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感慨重逢却岁月渐老的“昨别今已春,鬓丝生几缕”;有相聚欢畅时的“瓮间聊共酌,莫使宦情阑”。虽然造语简单,但在表达对朋友的所感所念上却是真切和深厚的。在《送元仓曹归广陵》一诗中,刘辰翁于第三句批曰:“可悲。”[6]116沈德潜也于第三句批曰:“苦句。”[6]116皆为悲苦之景。同时,他以景衬情,在意象的选择上多采用“哀鸿”、“残钟”、“寒山”等冷色调的景物,来寄托自己对友人的感情。这种感情看似消弭于凄清冷淡之景中,实是以一种反衬的手法。读来让人回味悠远。景至淡,而情至深。钟惺就评价韦诗为:“韦苏州等诗,胸中腕中皆先有一段真至深永之趣,落笔自然清妙,非专以浅淡拟陶者。”[5]647明人高棅也指出:“至浓至淡,便是苏州笔意。”[8]这种情感还出现在诗人寄托亲人之念的山水诗中。如《寒食寄京师诸弟》《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特别是在他的悼亡诗中。据孙望先生的《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载,韦应物于大历十二年秋末京兆功曹摄高陵宰任丧偶后作有十七首悼亡组诗,一部分诗作就以山水诗的样式表达了诗人对亡妻深深的思念:
冰池始泮绿,梅楥还飘素。
淑景方转延,朝朝自难度。(《除日》)
迢迢芳园树,列映清池曲。
对此伤心人,还如故时绿。(《对芳树》)
巢燕翻泥湿,惠花依砌消。
端居念往事,倏忽苦惊飙。(《间斋对雨》)
看似充满生机的景色中,诗人的心情是沉重的。亡妻之痛使韦应物“朝朝难自度”。在描山画水中,言辞淡雅,而用情至深,沾染着世俗生活的温热气息。
(三)社会之思
在韦应物的山水世界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他内心吏与隐的挣扎矛盾,他对于朋友和亲人感情的真挚深切,同时还能触摸到作为一名封建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敏锐的观察和解读,即勤政忧民的责任感: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
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
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
此诗与陶渊明山水田园诗中描述劳作生息的意趣有几分神似,如《移居二首》其二的“农务各自归,闲暇琢相思”。但陶渊明诗中更多追求的是自身融入其中后“得意忘言”的怡然自乐。而韦应物则是从劳动耕作中观照自身。在百姓人家春季农忙的氛围里,诗人看到的已不仅是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春耕图,更是从中体会到的农耕劳作的辛苦。所以,作为一名“不耕者”,诗人感到的是“禄食出闾里”的惭愧。他体恤民情,对百姓身上背负的徭役压力表示深切同情,并反思自己“尸位素餐”的行为。任滁州刺史时,面对平息动乱之后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亦感慨“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同样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这类情感的山水诗虽然不多,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韦应物忧国忧民的形象。他将自己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的关注带入诗中,因而在寄情山水的淡雅风格的气骨里,还透着一股世俗之气。
三、韦应物山水诗中“以我观物”感的形成原因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或者诗人,都注定要被自己所处的时代而打上特有的烙印。唐代至安史之乱后,社会由繁盛走向萧条,韦诗中所描述的“时丰赋敛未告劳,海阔珍奇亦来献”[6]132(《骊山行》)的鼎盛气象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时节屡迁斥,山河长郁盘”[6]67(《广德中洛阳作》)的动乱萧条景象。因而映照在文人的心态中,便随之缺失了盛唐那种宏大的气度,也就不再有盛唐诗人任气随意的从容,以及表现浩渺的大千气象的气概。退为转向观照自身,观照自己有限的生活圈。韦应物的山水诗中,即多以围绕自己对隐逸情怀中退和进的矛盾,对朋友的款款深情,对亲人的无限思念来展开。韦应物这种创作取向的特点,即是属于个人,也是属于同时代大历诗人的共性。作为中唐时期的大历诗人,刘长卿、皇甫冉、戴叔伦等,也多表现为这种狭小生活圈的自我观照。在刘长卿的诗中,“他对自己生存境遇的关心远胜于关心身外一切的总和。在他的诗中,个人的情绪永远是表现中心,其他事物都处于从属地位”[7]32,即是这种风格的写照。
同时,“在主题取向上,由偏重于表现理想转向偏重于表现感受,由社会生活转向伦常情感、身边琐事,感遇咏怀之作减少而酬赠送别之作激增”[7]3。韦应物的寄赠送别诗就有191首,约占全集的十分之三。其他大历诗人亦多好友情的酬唱之作,视其为宦途游览的重要情感表达。这些都表明韦应物和其他大历诗人的共性,程千帆先生在《唐诗鉴赏辞典》中提到:“着眼用力于写日常生活,时序的迁流,节物的变化,人事的升沉离合等方面的描绘,贯穿于悯乱哀时的情绪之中,便形成大历诗歌的基调。”[9]国家在经历肃、代两朝的喘息复苏后,虽然走向安定,但战争给百姓和社会带来的灾难并未得到平息。继而德宗任位期间短暂的中兴之梦被叛变动乱打破,加上连年的饥荒苛税,使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们也因自身生活的落魄和心灵创伤,失去了盛唐诗人匡扶天下的豪气,转为对社会失望的情绪,而显得伤感和落寞。所以,韦诗才会在寄情山水的惬意闲适里突然悲从中来,情不能自已;和友人的赠答送别诗里,惯用意境的冷清来烘托友谊的丝丝暖意。内心感伤的一面往往充溢于诗中,故而形成“以我观物,物皆我之色彩”。而韦应物山水隐逸诗中对陶渊明诗歌恬淡风格的继承,又以承前启后之势,成为宋代江西诗派所追求和向往的一种诗风审美情趣。
[1]陶文鹏,韦凤娟.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
[2]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
[4]黄霖,周兴陆.人间词话:导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7.
[5]陶敏,王友勝.韦应物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5.
[8]孙映逵.论韦应物的人格转换及其典型诗风[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3):57-60.
[9]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5.
Exploration on Wei Yingwu’Self-image Reflections of Landscape Poetry
CHEN Xiao-jue
(College of Literature,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In the period of the Mid Tang Dynasty,Wei Yingwu’s landscape poems were more in Chun Eau natural style by the world respected.But the exhilarating scenery of love is different from Wang wei’s Chan Poems”,and more than a deep emotions and thoughts.Investigate its reason,Wei Yingwu likes“in my view”rather than“observing the physical world to”,in her landscape poetry,himself subjective feelings shows all the time,fully reflected the style of Dali in the Mid Tang Dynasty about loneliness and sadness.
Wei Yingwu;landscape poetry;self image reflections
I206.2
A
1007-5348(2015)03-0023-04
(责任编辑:薄言)
2014-12-21
陈小珏(1985-),女,湖北阳新人,韶关学院文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