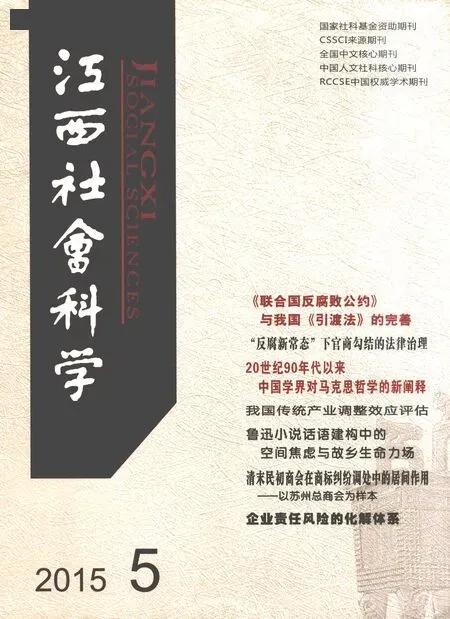直接适用的法之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王骞宇
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公布,该法第4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这是我国立法首次采纳“直接适用的法”制度。然而,《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得过于简单,仅明确指出强制性规定可以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颁布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一》)中,其第10条①对“直接适用的强制性规定”仅作出了指导性说明。上述两则法条皆未对直接适用的法之适用范围、方式及与其他制度间的适用关系等问题进行必要说明。为此,笔者利用北大法意中国裁判文书库搜寻相关案例后发现,自 《司法解释一》颁布三年多来,我国法院援引《法律适用法》第4条审理的涉外民事案件共17起,其中2012年10起,2013年7起。②在具体适用过程中,我国法官对“直接适用的法”之适用范围与方式存在理解上的差异,这不仅影响到“直接适用的法”制度的顺利运行,甚至会减损法律适用的明确性与可预见性。因此,通过司法实践检视我国“直接适用的法”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不足,并结合相关理论对实践中的困惑进行剖析,进而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这对于保障我国“直接适用的法”制度的有效运行,实现《法律适用法》所追求的在涉外民商事纠纷中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立法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直接适用的法的调整对象是案件全部争议还是特定争议
在17起案件中,有10起案件的法官主张直接适用的法调整案件的全部争议。具体表现为,法官在援引《法律适用法》第4条时往往采取以下或类似表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例如,上海一中院审理的“A公司与B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③的判决书中写道:“本案系涉外股权转让纠纷,转让标的系注册在中国的外商合资企业的股权。由于我国法律对注册在国内的外商合资企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强制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之规定,本案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从这段表述不难发现,法官在认定中国法律对涉外股权转让纠纷有强制性规定后,直接确定案件全部争议适用中国法。
然而,另有5个案件的法官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第4条中“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的表述只在强调特定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并未明示该强制性规定是制定国的法律适用。由于强制性规定通常会明确具体法律行为作为调整对象,因而,它的适用范围应被限定于具体的法律争议,而非所涉案件的全部法律争议,对那些与强制性规范不相关的争议,仍应通过其他法律适用方式确定准据法。也就是说,识别问题应当采用分割法。具体如浙江金华中院审理的“大新银行有限公司诉星光印刷(香港)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案”④的判决书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条: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本案当事人在《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该约定没有违反我国强制性规定,股处理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为准据法……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及弥偿书》虽约定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但)根据我国内地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此类担保应当依法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涉案担保合同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根据这段表述可以看出,法官首先对案件争议进行识别分类,对于涉及强制性规定的争议,通过援引第4条直接适用我国对外担保方面的强制性规范;对不涉及强制性规定的争议,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确定准据法。
上述分歧的症结在于对直接适用的法之调整范围的认定。从直接适用的法的特征来看,直接适用的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范围是具体特定的,这源于它具有自我空间限定的特征。所谓的“自我空间限定”特征是指规范本身包含连接因素,会对自身适用范围加以明确。这一特点被国际私法权威学者视为直接适用的法的必要部分。如法国教授Henri Batiffol与Paul Lagarde认为,公安法(Loisdepolice)往往自身内容中包含了连接点,类似于一个冲突规范。例如,法国1966年颁布一个法案第16条规定:有关海上运输的规定适用于 “以法国港口为起点或终点的运输”[1](P350)。Mayner教授认为, 直接适用的法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是自我空间定位规范,第二是实体性规范。[2]因此,直接适用的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强制性规范内容与目所特指的某一类法律关系,并不关心与强制性规范内容与目的不相关的法律关系。据此,法官通过援引《法律适用法》第4条处理案件中特定争议的做法更符合“直接适用的法”之内在特征。
此外,从直接适用的法的设立目的来看,《法律适用法》第4条用于调整案件部分争议将更符合“直接适用的法”制度的设计初衷。正如该制度创始人弗朗西斯卡基斯(Francescakis)教授所言:“直接适用的法源于法国法官为保护重大公共利益而对法律适用进行的变通。就目的而言,它与公共秩序保留是一致的,但相较于后者,它更具主动性。此外它因无需进行外国法查明而更加高效。”[3](P2)
可见,直接适用的法是一种积极高效的维护法院地国的重大公益的制度,其设计初衷并不在于解决所涉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若援引直接适用的法解决与重大公益无关的争议,无疑是对直接适用的法制度的滥用,甚至会导致法律公平和私人利益的损害。以金华中院审理的案件进行假设,本案《租赁合同》的有关争议当事人已约定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允许当事人对纯私人利益纠纷自主确定准据法的行为既符合《法律适用法》规定,又能兼顾私人间的利益。若此时仅因案件其他争议涉及强制性规定,而强制要求租赁合同纠纷亦适用中国内地法,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重大公共利益的保护,还会严重损害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的合理期待,造成不公正的适用结果。
二、直接适用的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有无必要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
从司法实践来看,指明与未指明强制性规范的判决书数量大致相当。⑤从指明行为的功能来看,明确指出涉外案件中直接适用的强制性规范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法官误认或滥用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提起申诉的权利。因此,认定指明行为是否必要的关键在于断定直接适用的法是否存在较高的滥用风险。
从直接适用的法的制度来看,《法律适用法》第4条存在较高的错用风险,而造成这种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强制性规范⑥的认定过于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客观且具有操作性的认定标准。“如何认定某些规范是国际性强制性规范是这个领域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它与纯国内强制性规范的区分往往取决于对该规范蕴含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与公共政策的认定,在德国国际私法中,若某一规范明确表明排除准据法而直接适用,抑或是该规范由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甚至刑法处罚保障实施,可被断定为国际性强制性规范……但不具备上述客观情形的规范也可认定为国际性强制性规范,这取决于该规范的性质与目的。”[4](P1230-1231)可见,即便是欧洲最权威的国际私法研究机构也未能制定出国际性强制性规范的客观认定标准。因此,对于“直接适用的法”中强制性规范的认定目前仍有赖于各国法院法官结合法院地的政策与公共利益,以个案分析(case by case)的方式进行。
在这种情形下,法官的指明行为无疑将有助于纠正法官在认定与适用强制性规范过程中的错误。山东省高院审理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等诉潍坊新立克(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案”⑦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在此案中,原审法院认为,案件中涉及借款合同关系、保证合同关系与抵押合同关系,并认为保证合同与抵押合同具有对外担保性质,因中国内地法律法规对对外担保问题有强制性规定,进而主张这两种合同关系应适用我国强制性规定。同时,原审法院在其判决书中明确指出相关强制性规定分别是 《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外债管理暂行办法》中的规定。终审法院在核实上述强制性规定后,发现这些强制性规定的对象均为境内机构,不适用于境外机构,而本案中抵押合同的抵押人是香港公司,属于境外机构,据此主张上诉强制性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的抵押合同关系。在其终审判决中,终审法院改变了原审法院的依据,主张“当事人意思自治”规则,而非“直接适用的法”确立抵押合同关系适用的准据法。不难发现,若原审法院未指明所适用的强制性规定,那么终审法院将无法核实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合理性,也无法做出改判,对适用法律错误的监督与救济也无从谈起。
因此,尽管法官并无义务在其撰写的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所涉的强制性规定,但鉴于对强制性规范的认定过分依赖于法院的自由裁量这一情形,法院应避免笼统地援引《法律适用法》第4条,应指明具体的强制性规定。
三、直接适用的法与单边冲突规范如何协调适用
前述上海一中院审理的“A公司与B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对“由于我国法律对注册在国内的外商合资企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存在歧义,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我国存在有关外商合资企业的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亦能理解为外商合资企业纠纷存在强制性适用中国内地法律的规定。依照后一种理解,该强制性规定更符合《2007年涉外合同司法解释》第8条,即有关“中外合资、合作、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等特殊合同的单边冲突规范。本案中,法官并未指明第4条所指的强制性规定,而是直接指出本案纠纷适用我国法,这种表述似乎更符合单边冲突规范的特征。由于单边冲突规范与直接适用的法都保护国家利益的制度,从效果上看,它们都导致法院地法的适用,但是两者影响的范围并不一致。如前所述,直接适用的法只调整涉及重大公益的特定争议,其他私法争议仍由冲突规则进行调整,而单边冲突规范用于全案的所有争议,若混淆两者的适用,会造成法律适用结果的改变。因此,对于法官而言,明确区分这两项制度并厘清两者的适用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从性质上看,直接适用的法是实体性规范,⑧它既确定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亦直接产生法律后果。Thomas教授称之为双重规范:法域选择规范(jurisdiction-selecting)兼结果选择规范(result-selecting)。⑨单边冲突规范是冲突规范,因其仅确定相关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体系,而法律后果则交由准据法决定。所以,单边冲突规范仅是法域选择规范。
从适用范围来看,直接适用的法仅调整特定的争议(issue),并未打算解决所涉案件全部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该制度可与多边冲突规范平行适用;相反,单边冲突规范调整所涉案件的全部争议,它与多边冲突规范是替代关系,无法平行适用。
直接适用的法与单边冲突规范也存在诸多相似点。具体而言,他们都明确法院地法律的适用范围,且都重视法院的期望(court wish)。他们都具有单边性,在实践中倾向于适用法院地法,而不考虑外国法的可适用性。由上可知,两个制度都具有维护法院地国家利益与社会重大利益的目的。同时,由于单边冲突规范的法域选择规范特征,它能将所涉案件的全部争议置于内国法律体系管辖,这无疑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内国法的适用。而直接适用的法因其自主空间限制性,往往基于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将自身适用范围确定在某一类具体法律关系或法律行为之上,其适用范围不及单边冲突规范。因此,在《法律适用法》第4条将直接适用的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明确限定为中国法的前提下,若某一案件亦可援引单边冲突规则时,应优先适用后者。
四、直接适用的法与法律规避制度如何协调适用
在东莞中院审理的两起涉外案件⑩中,在原审法院审理此案前,《法律适用法》尚未正式实施。法官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认定本案中所涉合同关系应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为准据法,而其中所涉《确认书》中的担保规定,因涉及我国外汇管理制度,且认定当事人有意回避该制度,进而参照《2007年涉外合同司法解释》第6条的“法律规避”而确定担保问题适用中国法。终审法院审理此案时,基于《法律适用法》已经正式实施,法官认为有关外汇管理的法规属于《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进而将适用外汇管理法规的适用依据由“法律规避”转变为“直接适用的法”。在《法律适用法》实施之后,似乎存在着一种“直接适用的法”取代“法律规避”的趋势。但是,广东省高院于2013年审理的“佛山东骏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佛山高明支行借款担保合同上诉案”11○给了我们相反的结果。具体而言,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债权转让合同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相关规定,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为准据法,而对于借款合同关系与担保合同关系,因原告无法向被告行使债权而不予确定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在上诉期间,原告以担保合同违反《法律适用法》第4条为由,请求终审法院认定被告担保行为无效,但是,终审法院最终却根据《2007年涉外合同司法解释》第6条的“法律规避”判定担保行为不发生效力。可见,法院在适用直接适用的法与法律规避这两种制度时存在分歧,
从性质上看,直接适用的法是针对冲突法体系的一项例外。[4](P1231)法律规避则是一项解决法律冲突的制度,在法律选择发生消极效果时,法院用于对抗、限制、排除外国法适用,而防卫法院地法之受侵扰。[5](P133)概言之,直接适用的法与法律规避都属于多边选法体系的例外制度,用于消除法律选择带来的不利后果,两者可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层面上替代适用。鉴于此,肖永平主张:“某些程度上《适用法》第4条的强制性规范就是法律规避的实践弊端促生的替代性制度。”[6]这是因为法律规避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即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意图难以查明。相较之下,直接适用的法无须探究当事人适用法律的意图,适用更为便利。但是,直接适用的法代替法律规避的情形是有限的,替代仅发生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这主要是因为直接适用的法的设立就是为了维护本国重大公益。所以,若涉外纠纷只涉及当事人为了纯私人利益而有意识地制造连接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对其不利的准据法时,仍只能通过法律规避进行处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直接适用的法是法律规避的完美替代方式。且在某一涉外纠纷涉及公共利益时,应优先考虑适用“直接适用的法”;若涉外纠纷仅涉及私人利益,且发现当事人存在规避法律的意图时,仍应依据法律规避加以处置。
注释:
①该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须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一)涉及劳动者保护的;(二)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三)涉及环境安全的;(四)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五)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的;(六)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
②截至2015年3月23日,笔者通过对北大法意中国裁判文书库的检索,共发现17起案件援引了这一条款。参见http://www.pkulaw.cn/CLink_form.aspx?Gid=139684&tiao=4&subkm=0&km=fnl.
③参见(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S1806号。
④参见(2013)浙金外商初字第38号。
⑤在笔者分析的17个案例中,有8个案例在判决书中明确指明所适用的强制性规范。而有9个案例没有明确提及所适用的具体强制性规范。
⑥《法律适用法》第4条中所述的强制性规定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国际性强制性规范,国际私法上将强制性规范分为纯国内强制性规范与国际性强制性规范两种。纯国内强制性规范是指不能通过合同加以减损的处理纯国内事项的规范。这一概念被《1980年罗马准据法》接受作为公约的第3条第3款。国际性强制性规范是指那些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时,忽视甚至排除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与冲突规范指引的法律,仅基于法规公法性质或一国公共政策而强制适用的国内法规。参见柯泽东著:《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6页。
⑦参见(2012)鲁民四终字第106号。
⑧这一观点已成为学界共识,Frank Vischer教授认为直接适用的法是指依其自身内容及目的而须适用的实体性规范,无须考量准据法的影响。参见Frank Vischer,General Cour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Recueil des Cours,Vol 1992 I,P162.Symeon C.Symeonides教授认为,直接适用的法是一个直接处理跨州纠纷的国内实体性规范。参见Symeon C.Symeonides,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Progress or Regres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P16.
⑨Thomas教授将为涉外争议确定应适用法律体系的规则称之为法域选择规则,而把为涉外争议直接确定法律后果的规则称之为结果选择规则。一般冲突规范仅是管辖权选择规则,而直接适用的法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管辖权选择规则,也是结果选择规则。
⑩东莞成益纸品有限公司与大新银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参见 (2011)东中法民四终字第75号与(2011)东中法民四终字第76号。
11○参见(2013)粤高民法四终字第53号。
[1](法)亨利·巴蒂福尔,保罗·拉加德.国际法总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9.
[2]吴光平.重新检视即刻适用法——源起、发展,以及从实体法到方法的转变历程[J].玄奘法律学报,2004,(2).
[3]Nicolas Soubeyrand&T.Struycken,Super-mandatory Rule:History,Concept,Prospect,Pallas Programe,2002.
[4]Jurgen Basedow Klaus J.Hopt,Reinhard Zimmermann with Andreas Stier,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5]柯泽东.国际私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6]肖永平,龙威狄.论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