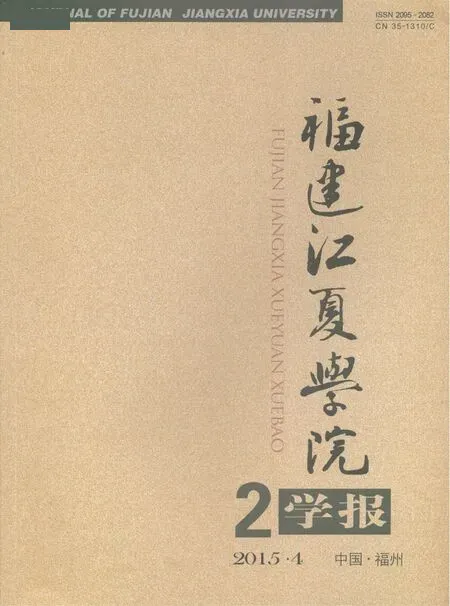论中国对条约中争端解决条款的保留及其完善对策
王 勇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201620)
“保留”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或一国发出继承条约的通知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如何,该国或该组织意图藉此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该国或该国际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力。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虽然正式确立了条约保留的“和谐一致原则”,但是在条约保留的具体规则方面却留下了很多空白之处,从而给各国的条约保留实践带来诸多不便。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致力于条约保留规则的完善,并且于2011年正式通过了关于条约保留的《实践指南》作为示范法。《实践指南》为条约保留设计了很多具体的规则,其中包括关于条约中争端解决条款的保留规则。中国迄今为止已经对26个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提具了保留。中国如何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参照《实践指南》的规定,完善我国关于条约中争端解决条款的保留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中国对解决争端条款保留的基本情况分析
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已经参加的,且对于解决争端条款作出保留的条约有26个,分别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世界气象组织公约》《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修订文本)》《〈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核材料实体保护公约》《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受国际保留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国际水道测量组织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关于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国尚未参加,但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解决争端条款保留的条约有3个,分别是:《关于国境自由的公约和规约》《关于国际性通航水道制度公约和规约》《〈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及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九年议定书》。
中国对解决争端条款保留所涉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中国对国际法院解决争端方式的保留,且中国所做的保留主要是针对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的保留。例如,1984年11月1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加入《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修订文本),同时对该公约的第28条第1款予以保留。①《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修订文本)第28条第1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本同盟成员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引用有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任一有关国家可根据国际法院规约向国际法院起诉,但有关国家同意通过其他办法解决时除外。向法院起诉的国家应通知国际局;国际局应将此事提请本同盟其他成员国注意。又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5年6月18日决定加入《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中国政府交存的加入书载明:对该公约第31条第2款持有保留。②《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第31条第2款规定:依照此种争端倘不能依照上开之方式解决争端两方中之任何一国作此请求时,应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此外, 中国也有对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提具保留的例子,但仅涉及3个公约:一个是《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该公约第32条第3款规定:如某一第26条(C)项所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为不能以本条第1款所规定方式解决之争端的当事方,该组织可通过联合国某一会员国请求理事会证求国际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提出咨询意见,此项咨询意见应视为裁决意见。第二个是《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该公约第8条第30节规定:除经当事各方商定援用另一解决方式外,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上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提交国际法院。如联合国与一个会员国间发生争议,应依照宪章第96条及法院规约第65条请法院就所牵涉的任何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当事各方应接受法院所发表的咨询意见为具有决定性效力。第三个是《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该公约第32节规定:除经当事各方商定援用另一解决方式外,本公约的解释和适用上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提交国际法院。如专门机构与一会员国间发生争议,应依照宪章第96条和法院规约第65条以及联合国与有关专门机构所订协定的有关规定,请法院就所牵涉的任何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当事各方应承认法院所发表的咨询意见具有决定性效力。第二种类型是中国仅对国际仲裁解决争端方式的保留,这种类型仅有两例:一个例子是中国对《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第29条的规定的保留,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对《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关于国际仲裁条款的保留。第三种类型是中国对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两种解决争端方式均提出保留。这两种方式在有些条约中是任意选择的关系,没有先后之分。例如,中国政府决定加入《核材料实体保护公约》的同时,声明不受该公约第17条第2款所规定的两种解决争端程序的约束。[1]此外,中国在加入《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和《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时也作出了类似的声明。这两种方式在有些条约中是有序选择的关系,有先后之分,即争端当事国先选择国际仲裁的方式,如果仲裁不成,则采取国际法院的方式。例如,中国政府于1980年9月10日交存《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时声明对该公约第12条第1款予以保留,该款规定:如两个或几个缔约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应用发生争端不能以谈判解决时,经其中一方的要求,应交付仲裁。如果在要求仲裁之日起六个月内,当事国对仲裁的组成不能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可按照国际法院规约,要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此外,中国对于《反对劫持人质公约》《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公约也作出了类似的保留。
中国对解决争端条款提具保留的主要原因是:(1)中国一贯主张和坚持以协商或谈判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2]利用协商和谈判的方法解决争端具有很多优点,主要优点有:一是直接性,即不借助于第三方,争端当事国自己掌握主动权、决定权;二是灵活性,争端各当事方可以互谅互让,有所妥协,以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三是有效性,即用协商与谈判方法达成的解决方案,易于得到履行,能够彻底解决争端。而且中国在实践中通过谈判与协商的方式解决了诸如边界争端、重大外交纠纷等很多棘手的问题。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一直很青睐协商与谈判的方式。(2)出于种种原因,中国对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中国迄今未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择强制管辖权,中国在实践中也没有提交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
中国对解决争端条款作出保留的主要决定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批准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批准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同时作出保留的决定,既体现了我国作出保留决定的较为慎重态度,又可以快速高效率地作出保留,还可以节约我国的行政资源。此外,中国政府对解决争端条款提具保留完全采取书面形式。
二、中国关于条约中争端解决条款保留的局限性
第一,中国关于条约中争端解决条款采取一概保留的做法过于武断。国际社会中各国的保留实践以及《实践指南》日益要求缔约国关于争端解决条款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争端解决条款本身即构成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便轻易地被缔约国保留或搁置;国际司法机构和国际仲裁机构也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并且重新获得多数国家的认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关于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采取一概保留的做法,确实是不适当的,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非议。
第二,我国关于条约保留的立法完全空白,且没有说明保留理由。我国关于条约保留的法律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一方面,我国实践中关于条约的保留行为很不规范;另一方面,我国提具保留时几乎从不说明作出保留的理由或原因,不易于其他国家理解和接受。上述情况也是我国关于条约中争端解决条款保留的局限性问题。
第三,没有回顾审查已经作出的保留。虽然我国已经对26个条约提具了关于条约中争端解决条款的保留,但是我国从来没有回顾和审查上述保留。上述保留是我国基于当时国家政治法律因素考虑而作出的。然而,时过境迁,其中某些保留可能已经完全过时了,从而根本没有必要维持了。通过回顾审查,我国可以及时撤回或修正这些保留。在这一点上,《实践指南》也是要求缔约国注意“被遗忘的保留”[3],以便及时予以撤回。
第四,我国尚没有全面深入地研究《实践指南》的规定。国际法委员会用了18年时间编纂成功的《实践指南》,内容丰富,评注详尽,且获得了各国的基本肯定,已经成为了条约保留的示范法规则。中国应该大力学习研究,吸收其精华部分,为我所用。
三、中国有必要调整与完善对解决争端条款的保留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条约中关于国际仲裁或国际法院的解决争端的条款几乎采取了一概保留的做法,鲜有的一个例外是中国没有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解决争端机制采取保留,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际上并不允许保留。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9条规定:除非本公约其他条款明示许可,对本公约不得作出保留或例外。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哪一条是明示许可保留的,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际上并不允许保留。笔者认为,中国很有必要调整并完善对条约国际解决争端机制条款的保留。理由如下:
第一,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法院与常设仲裁法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而日益获得各国的信任与好评。冷战以前,国际法院的西方国家籍法官占多数,受案范围也有限,而且受案数量也很少。冷战结束以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法官占了多数,法院的受案范围也由传统的领土争端扩大到侵犯主权、环境损害、投资争议、判决的执行、主权豁免、外交人员豁免等方面。相应地,国际法院的受案数量也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尽管冷战以前的常设仲裁法院处于与国际法院类似的境地,但是冷战以后的常设仲裁法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常设仲裁法院已经可以给国际法主体与国内法主体提供广泛的服务,这些服务不仅包括仲裁,还包括和解、调查、斡旋和调停。[4]此外,仲裁法院的规则也更加灵活和人性化。2007年,常设仲裁法院还在新加坡设立了“亚洲常设仲裁法院”,从而可以更加便利地为亚洲国家提供仲裁服务。
第二,我国政府对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与调整中。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对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采取完全拒绝与排斥的态度。1989年,中国政府宣布,今后对于涉及国际法院的条款,中国将采取不一概保留的态度,同年11月起,中国参加了五大国就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磋商。[5]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先后派出倪征燠、史久镛、薛捍勤担任过国际法院法官。其中,史久镛还在2003年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中国政府还指出:除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外,对于中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有关经济、贸易、科技、航空、交通运输、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公约一般可以不作保留。[6]613在中国与常设仲裁法院的关系上,冷战结束以后,在中国签署、批准或加入国际公约时,也开始对一些规定有仲裁解决争端的条款不再保留。[6]612从1993年11月开始,中国正式恢复在常设仲裁法院的活动,并且指派了中国籍的仲裁员。④1993年11月22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法院秘书长,通知中国恢复在该法院的活动,并指派李浩培(去逝)、邵天任、王铁崖(去逝)和端木正(去逝)为仲裁员。2009年5月4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致函法院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指派邵天任、许光建、薛捍勤和刘楠来为仲裁员。
第三,《实践指南》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93年将条约保留问题列入其议程,并且任命阿兰.佩莱先生为专题报告员。截止2011年底,报告员已经提交了17份关于条约保留的《实践指南》(以下简称《实践指南》),该报告基本完成并等待各国表决通过。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此专题上的不懈努力,不仅对条约保留问题本身,乃至对于整个条约法的发展来说意义十分深远。《实践指南》作为条约保留的示范法,获得大多数国家的肯定和支持。对于解决争端条款的保留作出了详细规定,填补了之前的空白,且对于中国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⑥2011年《实践指南》准则草案(3.1.5.7)规定:对关于解决争端或监测条约实施情况的条约规定的保留,就其本身而言,并非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除非:(一)保留旨在排除或更改条约的存在理由所必需的一项规定的法律效力;或(二)保留的效果是,使作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原先已经接受的一项条约规定方面,不受解决争端或条约实施情况监测机制的约束,而有关条约的根本作用正是为了实施这一机制。《实践指南》认为,虽然关于解决争端的保留本身并不被禁止,但是这种保留存在违反条约目的与宗旨,从而被判定无效的可能性。总之,《实践指南》要求缔约国在对于解决争端的条款采取保留时,必须十分小心谨慎。
四、完善中国应对解决争端条款保留的具体对策
第一,中国今后对于解决争端条款作出保留时应该全面考虑,再三斟酌之后再作出决定。我国过去对解决争端条款采取一概保留的做法,这种做法既简单粗放,又无形中大大增加了我国通过谈判方法解决争端的工作量,今后我国应该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权衡利弊以后,再作出保留决定。
第二,中国应该积极制定条约保留法律规则,为作出解决争端条款的保留提供法律依据。“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国在条约保留实践上的随意且粗放的做法亟待法律加以规范。在立法方面,可以考虑先制定一个暂行条例,等到时机成熟以后再制定一部条约保留法。该法一定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并积极参考借鉴条约保留《实践指南》的规定。
第三,我国对于解决争端条款作出保留应该尽可能说明理由。我国过去在作出保留时,一般都不说明理由。这种做法实际上很不利于其他缔约国理解中国作出的保留的初衷,并支持中国作出保留。中国说明保留的理由,还能够促成与其他缔约国就保留问题展开对话,成效显著。
第四,中国可以考虑撤回对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保留。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6条的规定,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大会临时委员会、要求复核行政法庭所作判决的申请委员会以及经大会授权的16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可以就执行其职务中的任何法律问题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国家不能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也不能阻止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包括任何个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也都无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6]591因此,即使中国对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提出保留,也无法阻止国际法院作出咨询意见。此外,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⑦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一方面,从法律上为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提供法律意见和依据,特别是帮助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履行对于提交它们的争端进行和平解决和报告的义务,甚至有时对争端的解决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或效果;另一方面,对国际法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且对于当事国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性质。因此,中国可以考虑撤回对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保留,即撤回《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3个公约对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保留。
第五,在我国对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和常设仲裁法院的保留方面,我国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对于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类条约的保留,我国一向执行的很好,一般不存在被诉的风险,所以应该积极撤回此类保留;对于经济、贸易、科技、航空、环境、交通运输、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公约,我国可以考虑逐步撤回此类保留。理由是上述条约主要是专业技术性的,如果发生争议以后,通过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的方式不仅可以便捷有效地解决争端,而且该解决争端机制对于条约有效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构成条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反之,如果一味通过谈判的方式不仅会大大增加我国的外交工作量,也不一定能便捷有效地解决争端;对于国防、外交类条约中的此类保留,由于涉及我国的重要国家利益,建议继续保留;对于人权类条约中的此类保留,应该区分情况,如果是不涉及我国重要国家利益的,应该撤回保留,如果涉及我国重要国家利益的,不要撤回保留。当然,撤回对上述保留应该逐步稳妥地进行,从而不断积累经验,创立更好地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
第六,我国要大力加强对《实践指南》的学习和研究,培养精通现代条约保留制度的外交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促使我国在条约保留方面走向法制化与现代化,增强与其他缔约国的交流协商,从而更有效地处理条约保留问题。
[1]国务院关于加入核材料实体保护公约的决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9:23.
[2]赵建文.国际法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93.
[3]ILC.ILC Reports[R].A/66/10/Add.1,United Nations,2011:195.
[4]谢晓庆.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常设仲裁法院[N],人民法院报,2004-12-08.
[5]管建军.国际法院的“复兴”和我国的对策[J],法学,1996:4.
[6]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