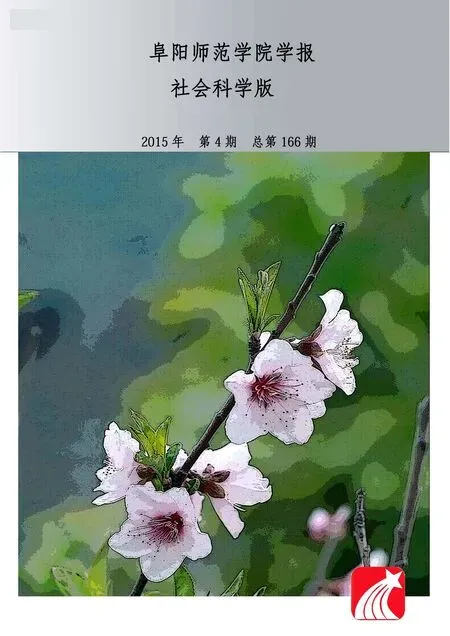庄子自由观与佛教自由观的比较研究
李金萍
庄子自由观与佛教自由观的比较研究
李金萍*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89)
庄子将“道”回落到现实与人生层面时,提出了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与追求。由于庄子的自由观是以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无奈为基础,以此抛弃世俗去追求“精神故乡”,这种类似“出世”的情怀与佛教的自由观有可比较之处。以《庄子》内篇为依据,通过对庄子自由思想和佛教自由思想的起源、实质、实现前提和方式的比较,来阐释二者的异同,并对庄子之自由的局限做适当的评析。
庄子; 佛教; 自由
庄子作为道家的代表人和集大成者,对“道”有着独特的理解。一方面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是万物本源、无为无形、以“自然”为法的思想,另一方面庄子之道对老子之道也进行了新的阐释。老子将“道”的法则运用于治国,造就了独特的无为政治的思想体系。而庄子则将“道”之中包涵的自然无为着重运用于塑造理想人格与提升人生境界。如果说老子为了追求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的“无为”是“为无为”,那么庄子抛弃人间事而追求逍遥的“无为”则是绝对的无为。庄子在将“道”落回到人生与社会现实层面上时,感受到了现实世界的困苦与精神世界的欢愉,于是在追求“神游”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自由思想。而这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的“精神自由”也一直为后人所推崇抑或质疑。
一、论世人不自由的起源
不论是庄子还是佛学,“自由”都涉及处理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二者的自由理论也都建立在困与苦的现实之上。二者不同的表现在庄子是直接以现实困境为基础,认为人在真实世界得不到完全的自由,于是企图以“精神自由”超越现实困境。佛教是认为世俗虽苦,但人感受到的苦是外部事物对被蒙蔽的人性起作用而产生的,从而导致人的不自由。
(一)庄子:物质与精神,天道与人道的对立
老子和庄子都追求与“道”合一的境界。但庄子的道与老子保全生命为目的不同,庄子将老子普遍的、客观的“道”与个体存在结合,将一般性的“道”内化于个体的精神世界,更高地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和超拔[1]。在人民苦不堪言的混战年代,庄子试图抛开个人价值在社会现实中的界定,不用仁义、道德、功用作为评价个人的尺度,而是将人本身从残酷暴虐、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中抽离出来,将人的评价体系、目标与追求上升到精神世界。从现象来看,人的不自由是由于战争纷扰的现实世界给人带来了无限的困苦与限制。“大知闲闲,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喜怒哀乐,虑叹变蟄,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庄子·齐物论》)可见,庄子认为整天为谋求名利,处理周围事物,精神损耗、身心俱疲,若能抛弃周身所担、神游于无穷,既能避免成为一无所知、一无所获的凡夫俗子,又能获得真正的通达与欢愉。从本质来看,现实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立,其实是“人道”与“天道”的对立。人的焦躁困苦、惦念混杂,以至于陷落于不自由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归根结底是“人道”违背了“天道”,不顺应自然,而多加人为干预。不论是人们对自身物质生活的盲目追求,还是孔孟强调道德的内心自觉和人格的自我实现,以“礼”规定着人们的视听言动,都是“人道”而非“天道”,这使人们陷入困苦之中,永远不能到达“自由”之境。“人道”规定的社会秩序、人生取向和功名价值,时刻约束和抑制着人们的自由。因此,庄子认为面对残酷的现实,要将人性本身重新皈依于自然,顺应天道精神。将异化的个性在自然中重新寻回,从而超越困境,达到无穷的“精神自由”。
(二)佛教:不自由源自“无明”
佛教也将“苦”看做人世间的本质属性,但重点不在于现实世界的纷杂混乱、变化无常,而在于各种事务和情境作用于人的心理,人因无法驾驭而在心中体味到的苦与恼。《心经》言:“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里的无明即是烦恼,为十二因缘之首,一切苦之根源[2]92。对于佛教来说,现实的生命同样是不自由的,是被束缚的。而不自由的起源在于人间事作用于生命结构的深处潜藏着的无明,人们的愚痴无法处理自身遭受的境遇,无法看透自性、无法觉悟。面对世俗世界,做不到通达真理、看透事物本质而一直维持愚昧的精神状态。可见无明又以其强大的力量控制着一切生命的一切活动,每时每刻的生存实践中都有无明的作用。无明不是由外在世界决定的,改变外在世界并不能消除无明。无明虽然没有实体,但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无明,生命会迷失真性,会陷入虚无,会被莫名的黑暗的力量所左右。所以佛教认为正是因为无明,人生才有各种苦难,如生、老、病、死、忧、悲、哀伤。而《心经》认为无明无尽,以死为末,无明为消,生生世世总有无明使人困苦,陷入轮回。因此,导致人不自由的始作俑者,就是人的“无明”。
二、自由的实质之比较
庄子之自由与佛教之自由除了在不自由的起源上不尽相同,对于自由内容与实质的规定亦有所差别。庄子的自由主要是指精神与心灵从世俗中抽离,通过修行达到无所羁绊,神游于无穷的状态。而佛教的自由指的是见其自性,涅槃之自由。
(一)庄子:“逍遥”与“游”
《庄子》以《逍遥游》为开篇,以“不知其几千里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为开端,以宏伟、辽阔的宏论惊于世人。将“精神自由”化作鲲鹏飞向天外之天、山外之山。庄子认为物质世界的行为自由都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有精神世界里的心灵自由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3]。结合庄子的处境及思想历程来看,“逍遥游”应指的是个体摆脱人世之累后精神的无牵无挂、怡然自得、来往无羁的自由状态。这表明,首先,庄子追求的“逍遥”与“游”并非“游”身,而是“游”心,也只有心灵才能无拘无束、无边无岸的逍遥,从而达到高度的绝对的自由。即心灵的“游”与逍遥、生命的自由才是“游”的精神实质。其次,自由是有层次的,应该是无条件、绝对的自由。“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庄子·逍遥游》),这种为外人称颂,官做得好、符合百姓和君主心意的人,在庄子那里只是小虫、小鸟的级别。对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宋荣子的境界,足以嘲笑前者小官小吏的狭隘,但“犹有未树也”,而对于可以御风而行的列子,庄子认为他仍“犹有所待者也”。因为列子虽然已近于神仙,但还需借助风力,进一步提高自身境界,还未至“逍遥游”。庄子所希望的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即没有时空限制的绝对的自由,不为外物所驱使和奴役,真正的主宰自身。“如果对尘世有所待,则必为外物所累,自然达不到逍遥游的境界。”[4]总之,庄子所指的逍遥是“无待”“无己”“无功”“无名”,而“无为”的逍遥。如“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迈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能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这种丝毫不为外物所累所伤的逍遥。庄子的自由是精神的自我超越,“逍遥”与“游”是庄子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
(二)佛教:明心见性即自由
佛教的自由,简而言之,即为见到自身的佛性。既指佛陀之本性,也指众生与自我成佛的可能性。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只是自己不自知。而阻碍我们自由的,也是因佛性被遮蔽而形成的诸烦恼。佛教认为最终形成无上的正等正觉,获得广阔无边的自由,最关键的就是向内认识自己心的本性。本性对于自我而言是生来即拥有的纯净。佛教认为,一切有情众生的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本就清净从未染污,如果众生能透彻地看清、明晰自身、自心的本质,心无外物,摒弃尘嚣对心的污染,当下就可以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而成证佛果。然而,有情众生的本性因受到无明幻相所蒙蔽,被轮回业报所控制,不能了知心的本性,所以永远在痛苦中而不能得以解脱。但并不是说自由无门,因为心的本性始终清净,无明是偶然和暂时的。只要众生看到自己的佛性,证悟解脱,则回归到心的本然明净进入自由。总之,庄子所提倡的自由与佛教所提倡的自由都是一种摒除我与人、物、现实时空的联系,打破现实枷锁、远离一切染污、回归于精神世界。然而庄子是以自然为法,追求心灵的“逍遥”与“游”于无穷,佛教是以见性为本,追求“自性”的完全呈现和作用。
三、自由实现方式的比较
不论是庄子的神游之境还是佛教的终极自由都有其实现方式,而庄子由于对现实的理解,其思想处于“出世”又“入世”的模糊地带,导致其“逍遥游”只能是遥远的目标和宏伟的幻想。
(一)实现途径的异曲同工:“忘”与超越
庄子认为既然不自由来源于“人道”对“天道”的违背,那么进入自由之境就必须放弃有为的人道,顺应无为的天道,即返璞归真。“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庄子·应帝王》)只有对各种事情都没有偏爱,丢弃雕饰,不染尘世,才能把握“天道”以实现人生自由[5]。而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心斋”,二是“坐忘”。乱世中的庄子深知人生苦的始作俑者就是追逐名利,欲望膨胀,最终伤及自我,世乱纷扰。因此,要在这乱世中安定下来,为精神的“神游”做铺垫,必须提高自身的认识,达到心灵的寂静。“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之以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摒弃包括权利、知识、名利、人伦关系、生死喜恶等一切杂念,用心与外界融合,用气接纳万物。倘若不排除扰乱心灵的外物和活动,是无法观于自身,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也就无望逍遥了。对于 “坐忘”,庄子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似乎与佛教中的“打坐”类似,是通过“坐”,脱离形躯、抛开认知与感受,从而与“道”融会贯通。佛教也讲究精神于形体中抽离,将形体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意”感受到的“色声香味触法”通通遗忘、摒弃。而庄子“忘”的关键,也在于“忘我”,从而心无挂碍,与道相通,以心灵超越时空,游于无穷,以获得真正的自由。
佛教也讲究一个“忘”字。我们把所看见、听见、感觉到或想到的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当成是实有的东西来执取,从而导致了贪、嗔、痴等一切烦恼的滋生。佛教所关心的,是如何去除无明,显露本性,得以解脱。《金刚经》言:“不应主色省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即是说不应该执着于世间的“色”,应当生起无所执着的清净心[2]50。“明心见性”既是自由的途径也是佛教的终极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大乘和小乘佛教均提倡“戒”“定”“慧”的修行方法。简而言之,世间纷繁以致心散乱,所以要戒、渐而达到定,而后就可以看清苦、空的佛理,达到智慧。当慧修得足够成熟时,就能彻底地破除无明、断除烦恼,进入自由之境。所以,在实现途径上,庄子与佛学的趋同点在于都是用修行达到清净本心,从而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
(二)无法实现的庄子的自由
庄子的“逍遥”是一种欲跳出现实世界,不受任何事物、责任、权利、烦恼的自由。尊卑上下、亲疏远近远不在考虑之中,有的只是无所羁绊,怡然自得。但人的躯体、情感、欲望是很难完全消失而达到庄子所提到的“神游”境界的。
庄子自由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庄子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佛法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因缘而生。“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都是依据一定的条件才能产生的[6]。所有事物都是依赖它物而生、而灭,全凭因缘。由于因缘不定,那么万物无常,不会独立存在,因此,佛教理解的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根本,是“空”。作为客观物体来说,“有”是现象,“空”是本质。而人之苦,就在于把“空”当成“有”,极端在意、苦苦追寻,执着于有、执着于我,然后产生贪、嗔、痴等等烦恼,因而受苦。正因为佛教把万物归为“空”性,那么达到自由即需脱离这个“空”的世间,断绝杂念,横空出世。而庄子是以“道”为本理解万物的。道为万物本源,万物具有独立的性质。面对“实有”的客观世界,以顺其自然,符合“天道”为本,想超脱谈何容易。顺应外界事物的变化,即有所牵绊。过于超脱,灾祸难免,过于顺应现实,则与返璞归真相背。此外,摒弃形体,思维与认知,更谈不上对逍遥的认识与追求,因此,庄子的“自由只在不受拘系,无所追求一面表现,而不能在建构方面表现。认知活动既视为‘累’,德性实践复视为‘障’,则更无可作‘实现’之境域”[7]。庄子提倡的自由不是天国或彼岸世界,精神的自由和超凡的人格恰恰还需要在世俗中得以实现。物质与精神、现实与心灵的矛盾使得摆脱世俗、逍遥神游只能是一种幻想。
总之,一方面,庄子的自由与佛教的自由都蕴含一种顺遂自然、安之若命的生存态度,并以返璞归真,摒弃世俗污染,追求本心与精神自由为相通之处。但这两种自由仍有本质差别。此外,庄子赋予万物独立性,而非佛家的“空”性,从而欲求在“实”中求“虚”,摆脱一切社会关系,绝非易事。“入世”无意,“出世”无望,不知如何“逍遥”。至人、神人、圣人最终也只能化作一场可敬、可叹的想象。
参考文献:
[1]付粉鸽.自然与自由——老庄生命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91.
[2]金刚经·心经·坛经[M]. 陈秋平,尚荣,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3]王富仁.论庄子的自由观——庄子《逍遥游》的哲学阐释[J].河北学刊,2009,29(6).
[4]周勤.论庄子的自由观与人生哲学——“逍遥游”三境界辨析[J].中国社会科学,1985,(1).
[5]安继民,高秀昌.庄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109.
[6]李勇.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28.
[7]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1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Freedom of Chuang-Tzu and Buddhism
LI Jin-pi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uang-Tzu proposed the pursuit of "spiritual freedom" when he talked about "Tao" in the real life. Chuang-Tzu's concept of freedom is based on the unsatisfied and helplessness of social reality and to abandon the secular to pursue "spiritual homeland". The detached thought is similar to the freedom theory of Buddhism. Taking the inner chapters of the Chuang-Tzu as the basis, this paper study on the Chuang-Tzu idea of freedom and the Buddhist liberal thought’s origin, essence, approach to 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some comments on the limitations of Chuang-Tzu freedom thoughts have been proposed.
Chuang-Tzu; Buddhism; Freedom
B0
A
1004-4310(2015)04-0035-04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4.008
2015-05-12
李金萍(1989-),女,满族,北京人,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