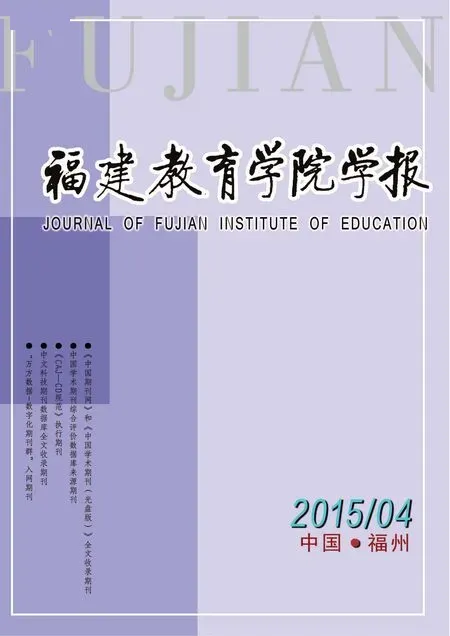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女性小说创作嬗递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女性小说创作嬗递
林珊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福建福州350003)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女性小说创作经历了复苏、发展、转向、拓展四个阶段,它们又分别表现为充满“人道”情怀的启蒙叙事、充满女性意识的性别叙事、充满“私语”特征的身体叙事、充满女性气息的底层叙事与历史叙事。
关键词:启蒙叙事;性别叙事;身体叙事;底层叙事;历史叙事
收稿日期:2015-03-10
作者简介:林珊(1964-),女,福建连江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副教授,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7.24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变革及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动,“女性文学”再一次浮出历史地表并得以发展。张洁、王安忆、铁凝、谌容、戴厚英、张抗抗、毕淑敏、池莉、方方、残雪、林白、陈染……这一继“五四”之后的又一个女作家群体,以独特的视角、独有的感悟、独卓的文姿、将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心路历程等落墨于文本之中,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绩。有批评家指出:“20世纪中国文坛出现了女作家创作的两次‘高潮’:一次是“五四”时期,另一次就是80年代。”[1]304其实,从女性小说创作来看,第二次高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开始,经由80、90年代并延伸至21世纪的今天。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创作经历了复苏、发展、转向、拓展四个阶段,它们又分别表现为充满“人道”情怀的启蒙叙事、充满女性意识的性别叙事、充满“私语”特征的身体叙事、充满女性气息的底层叙事与历史叙事。
一、充满“人道”情怀的启蒙叙事
启蒙,是作家力图将以往被认同并神圣化的某种思想价值体系摧毁,而后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价值体系的行动。这种行动经由人的理性反思,走出传统的束缚,具有“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性”。[2]434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的政治运动及人道主义思潮的涌起,新一轮启蒙运动也随即出现。人性问题重新进入文学视域。“人”的发现必然会伴随着“女人”的发现,于是女性意识便在充满“人道”情怀的启蒙叙事中闪现出来。
所谓女性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女人的价值的体验与认同。其表现为否定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关注女性自身的生存状态、生命体验与心理情感,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与地位。
张洁无疑是这一时期最具女性意识的作家之一。她以女性的视角审视人的精神领域,满含忧患意识,率领女性小说走出无性或中性的发展藩篱。她发表于1979年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承接了“五四”女性文学以“爱”来展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张扬的创作模式,不仅体现了“人”的解放的启蒙主题,而且以“爱”的千回百转展现女性心灵世界的丰富与湿润。小说通过女知识分子钟雨与老干部之间纯洁的精神之恋的描写,大胆否定了无爱的婚姻,肯定了女性获取“爱”的权利。但是像钟雨与老干部之间的那种过滤了一切欲望的“纯洁”爱情,不能不说带有巨大的缺陷性。作品对这种爱情的讴歌正好彰显了禁欲时代的社会压力及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不成熟性。在稍后发表的《方舟》中,张洁的女性视角有了延伸与拓展。她在小说的题记中写道:“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作者的女性意识明显地增强。作品通过对三位主人公曹莉华、柳泉、梁倩千疮百孔的爱情生活和在所谓“男女平等”的社会中的种种挣扎的描绘,直接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男权文化中心的社会现实。这在女性意识刚复苏的80年代初期,无疑具有先锋的意义。然而,作品对曹莉华们“雄化”的描写及她们在痛苦中渴望男人的庇护时发出“这世上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的喟叹,又显出作家对女性主体身份认同的不自信。
戴厚英的《人啊,人!》是80年代初期文坛上的一部厚重之作,作者紧扣时代脉搏,在传达极左时代“人性遭受摧残、人的尊严丧失得令人震撼的整体气氛”[3]109中闪现着女性意识。作品描绘了主人公孙悦对何荆天爱慕又难以成聚的痛苦,探究了造成人性异化的原因:“把精神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由于我们不自觉、自尊和自信。”“如果我们收回发出去的一切权力呢?那我们就能主宰命运。”[4]105,270然而,文本大而化之的“反思”主题与伤痕的倾诉,使作品的锋芒在女性意识的层面上只是浮光掠影地闪过。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洁、张抗抗、铁凝、张辛欣等大批的女性作家带着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朦胧追求,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爱的权利》《北极光》中的舒贝、岑岑,《没有纽扣的红衬衣》中的安然,《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里错过了你》中的“她”和售票员“我”等等。这些女性形象具有女性意识的萌芽,触及了女性在生活、事业、爱情中的处境及女性解放的命题,为读者提供了女性主体性重建的朦胧想象。但作者并未在这些问题上深入探寻。
可见,新时期之初的女性小说较之建国后“十七年”的“无性”文学来说,女性意识已有突破性的进展。但这种女性意识的显现亦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呼唤,基于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追求,即便女作家的文笔触及女性内心痛苦与困惑,但这种痛苦与困惑更多地来源于对“人”的价值的体认与女性社会角色上的不平等的感触,而对女性心灵深处的挖掘和文化层面的揭示、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还不是女作家们关注的重点,只是在反思人性回归的启蒙叙事中顺应着宏大的主流意识下进行有限的书写。
二、充满生命意识的性别叙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被视为西方女性主义经典的《第二性》《一间自己的屋子》《美杜莎的笑声》等论著在中国大量译介与广泛传播,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开始涌动,它们对“开启与培养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产生了重要作用”。[5]303女作家们开始以女性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话语基础,在文本中努力探索女性生命的本体价值。与前一阶段“人的意识”启蒙与追求“男女平等”的努力不同,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着力弥补张洁等女作家取消欲望的局限,张扬着女性生命中一向被遮蔽了的欲望体验,并把目光转向积郁在女性内心深处的生命之痛。女性小说的创作从“人的自觉”向“女人的自觉”迈进。
这一时期,王安忆和铁凝首先将小说的触角伸入女性的精神世界和情欲世界,以女性特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对传统的女性叙事进行质疑。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及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玫瑰门》等均以在爱的冲突中受难、思索与成长的女性为主角,对传统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颠覆。
《小城之恋》通过“她”与“他”在练功房一起练功过程所产生的强烈的性欲冲动及“她”与“他”在相互折磨与爱恋中所蕴藏的强烈的生命热望,淋漓尽致地描写女性经验中一向被遮蔽的欲望体验。《荒山之恋》描写金谷巷女孩与大提琴手欲爱不能的困境,以无比的勇气表现女性对情欲的主动操纵。《锦绣谷之恋》以婚外恋的形式叙写女编辑与男作家的邂逅使女性“重新发现了男人,也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的过程。《岗上的世纪》中的李小琴虽最终无法逃脱男性主宰的命运,但在干沟“野合”之中以女性的魅力与勇敢完成了自己对男性的再造。“三恋一世纪”将女性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生命需求的“这一个”凸现在文本之中,她们打碎了男性社会对女性贤淑、温婉形象的塑造,也超越了张洁《爱,是不能忘记》所表达的“精神恋爱”层面及《祖母绿》中为爱牺牲的道德层面,为女性寻求作为女人的那一部分权利而获得了性别意义。
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玫瑰门》对女性的生存形态与生命形态进行了深度的审视,它们与王安忆的“三恋一世纪”构成了深刻的互文性,共同标志着女性小说的成熟。
《麦秸垛》通过尚未得到文明开启的农妇大芝娘和知青沈小凤这两代人命运的轮回,阐释了在男权文化规约中女性被欺负被玩弄的命运。大芝娘与沈小凤被男性抛弃时所表现出的唯一的“反抗”竟惊人地相似——要求男人与她生一个孩子,别无他求。可见男权文化对女性深度内化的程度令人震惊。《棉花垛》中乔、小臭子被男性奸杀,米子用肉体换得生存,老效甚至想用媳妇的肉体换一双布鞋!这些情节的书写与暴露,揭穿了世俗权力意义上的女性生存悲剧。《玫瑰门》通过竹西的三次婚姻表现了女性生命原欲的不可遏制和蓬勃生命力,并以竹西用无所顾忌的性爱向社会发起的反抗来表征女性对附属地位的抗争与突破。作品中,铁凝赋予女性性爱为生命主体的正常需求。
王安忆和铁凝的创作“远不止意味着对女性生命经验与身体欲望的书写,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女性的视点、女性的历史视域与女性经验迥异的对现代世界甚至现代化进程的记述与剖析”。[6]5她们通过对女性生命经验的书写解构了传统的性别秩序与性别规范,显示了作为独立的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参与文化建构的厚望与能力,标志着女性写作的性别自觉,为今后的女性小说创作欲望化叙事开辟了道路。
三、充满“私语”特征的身体叙事
20世纪90年代,是女性小说创作的繁荣期与丰收期。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的转轨,把文学挤出了社会的中心舞台,文学在改革的阵痛中摆脱政治的束缚,回归于自身。相对平等和进步的社会机制促进了女性对自身处境的反思。林白、陈染、斯妤、残雪、池莉、方方、徐小斌、海男、徐坤等一批女性作家以独有的审美视点为依托,开始了“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7]203的时代。她们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具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话语,呈现出了与长久把持话语中心地位的男性话语迥然不同的言说姿态与叙述方式。无论是方方、池莉的新写实的风格还是斯妤的童话寓言式的表述,也无论是徐坤的自省自嘲还是残雪的臆想式表达都以独特的方式表征着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与决绝。
其中,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的“私语”化小说的出现尤为令人瞩目。她们认同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的主张,把艺术触觉从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空间、转向女性自己,将女性个人经验从历史文化背景中剥离,“将那些曾经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8]125在根深蒂固的男性文化包围中,开掘女性个体隐蔽已久的身体经验,在作品中重新审视女性自己,直接呈现女性躯之美与躯体感受,奠定身体叙事的基础,以此解构和颠覆男权文化。
这时期女性小说创作有一种鲜明独特的倾向,就是沉浸于女性细密的情感世界与身体世界,以诗性的沉思与呓语来张扬女性意识。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致命飞翔》《说吧,房间》《子弹穿过苹果》、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海男的《我的情人们》《女人传》等作品均属此类。
林白认为:“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这二重的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我所竭力与之对抗的,就是这种覆盖和淹没。淹没中的人丧失着主体。”[8]125林白在“对抗”中不断发掘独具特色的女性经验,以私语的方式,用身体的动作展示了女性的奇观世界。《一个人的战争》是这一系列小说的代表。小说通过一个具有极端自恋倾向的女孩林多米成长历程中不为人知更不能为人所道的女性隐秘的经验的叙写,揭示女性内心的渴望、欲求、绝望和祈祷。林多米三岁就没有父亲而又缺乏母爱,内心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她孤独无奈地躲进那顶白色的蚊帐,也躲进自己的内心。无论是小说开篇处林多米在蚊帐中那只手的动作描写,还是小说结尾处自我抚慰时充满梦幻的片段,我们都不难感受到躲进自我内心中的林多米对男性社会的拒绝,也不难感受到她如此极端自恋的深层原因,以及在极具私语性的空间里她所体验到的生命存在、挣扎与反叛。
与林白相似,陈染的《私人生活》等系列小说均是知识女性内心深处的诗情独白,它们从主人公内心真实的体验出发,揭示在平凡生活中的女性们诸如惶惑、压抑、激动、无助等种种情绪体验。笔调幽怨苍凉又不失细腻真切,丝丝缕缕中传达出女性内心的不堪重负。
《私人生活》是主人公倪拗拗身体和精神的成长史的展示。它突出的价值在于袒露了倪拗拗与邻居乔寡妇、男教师T、母亲尹楠等同性与异性之间交往中所表现的“杀父冲动”“恋母情结”及“少女成年期的性期待与性恐惧”等这些一直为男权社会所精心规避的事实,呈现出女性内心深层次的情感纠结。小说中的倪拗拗更倾向于同性间的恋情,因为她体察到男女性爱中心心相印的短暂与灵肉分离的痛楚,从而转向对同性爱的寻求。但同性爱真的就是女性理想的归宿?作品从她与乔的一场性爱高潮最终却是一场虚幻的梦境的描写来看,陈染的质疑也是存在的。
像林多米、倪拗拗这样拒绝外部世界,在一种近乎幽闭的状态中守护甚为脆弱的自我过程,所表征的既是女性反抗男权社会的决绝,也预示着女性们所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存在着有待于艰难跋涉的漫漫长途。在这一方面,林白、陈染们的思考是严肃与认真的。
毋庸讳言,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上,女性作家过分地沉溺于对身体经验、内心感受的谛听、冥想与触摸,试图通过私人化的追忆与私人生活的袒露来抗拒外部世界的挤压,造成描写幽闭隐晦生命体验和欲望作品泛滥,尤其是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极力描摹性隐私等内容,以致于将女性的一切均赤裸裸地暴露在菲勒斯审判的目光注视之下,难免又落入“被看”的陷阱之中,满足了男权中心主义的窥探和畅想的需求。女性小说创作新一轮的“飞翔”成为摆在女性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充满女性气息的底层叙事与历史叙事
进入21世纪,愈来愈多的女性作家开始反思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的得失,她们看到了小说题材的偏狭、视野的逼仄、想象的单一使轰轰烈烈的女性“私语”性身体叙事面临“失宠”甚至“堕落”的危机。如何使日益下滑与沉寂的女性小说创作走出困境,如何将女性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对接,从而获得创作激情与张力,成为每一位女作家不容回避的问题。
困境之处往往也蕴含着生机与希望。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三农问题、下岗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等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负面问题也浮出历史地表。这种改革过程的阵痛势必让许多人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承受。女作家们告别了曾经的“一个人的战争”和隐秘的“私人生活”,敏锐地捕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同形态的女性生存状态进行深刻的描摹与知性的思考。同时,女作家们又在承接现实与未来的维度之上,进一步拓宽自己的视野,走近百年血与水的历史之中,把目光投向国家与家族的历史,致力于寻找与描绘女性历史文化的努力。底层叙事与历史叙事成为新世纪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并显示出丰厚的创作实绩。具有代表性的是孙惠芬的《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富萍》《土种红菱下种藕》、林白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张洁的《无字》、虹影的《上海之死》等。
《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均以农村底层生活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万物花开》中,林白通过脑瘤患者大头的视角展示了王榨人——一个奇异、怪诞、贫困但又充满活力的乡村风貌。大头叙述着王榨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小说没有过分渲染在城乡边缘游走的三躲、小梅等女性的困顿、无奈,而是更多表现底层生活的安详与欢畅,一幅陌生然而又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图景便跃然眼前。《妇女闲聊录》中,林白让农村妇女李木珍现身说法,在看似平淡、质朴而又杂碎的言语中,呈现王榨人的生存状态,来自底层的倾诉让人感受到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经济萧条、农民心灵家园日益颓败的现状。
王安忆的《富萍》以独特的视角描述了底层女性融入城市的过程。小说没有过多渲染底层的伤痛,却以乡下女孩富萍用不动声色的倔強与坚持摆脱了被他人安排的命运开始新生活这一过程来礼赞小人物生命的坚忍。
孙慧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通过歇马山庄男性缺席之后两位新媳妇潘姚和李平的情感纠葛,表现山庄男人们集体离家打工后所造成的乡村女人们情感世界的失落与荒芜及难以言说的悲哀与惆怅,反映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交汇碰撞之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及这种矛盾中女性生存困境。
新世纪女性小说底层叙事围绕着性别展开,但又不局限于性别意识的传达。在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描述中,突破了叙述女性身体体验的范畴,强化了阶层意识与日常生活气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反思。
铁凝的《笨花》虚构了冀中平原的一个小乡村——笨花村,通过它展现了清末明初至19世纪40年代中期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将宏大的历史融入凡人俗事的叙写之中。小说精心刻画了向喜的三位太太同艾、顺容、施玉蝉及女儿向取灯等女性形象。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与命运抗争,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同艾和顺容用母爱遮蔽和治疗自己(女性)婚姻的隐痛,迈进了人类大善的目标;施玉蝉反叛和摆脱了依附于男性的命运,显示女性主体性要求;向取灯最终死于抗日救亡的第一线,用生命抒写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们的生命虽不轰轰烈烈,但刻在历史的画卷上却也淡定从容,熠熠生辉。
虹影的《上海之死》把女性的命运与历史的命运相契合,讲述了太平洋战争前夕发生在中国上海孤岛的国际谍报战。女主人公于堇在谍战中用自己的勇敢与智慧获取日军情报,改变了整个世界及中国的命运。《上海之死》与虹影的《上海王》《上海魔术师》一起以“上海三部曲”的形式表现上海不同阶层女性的生存、命运和作为,谱写了上海女性的历史。
此外,徐小斌的《羽蛇》把一个家族五代十二个女性的命运置放于一百多年中国历史变迁中呈现,小说大胆颠覆了母亲的神圣形象,揭示了母女血缘关系不仅有亲和力而且有杀伤力,“母性”一旦变成“母权”,那么,它与父权一样面目可憎。张洁的《无字》以女性血缘维系的家族谱系诉说四代女人的生命历史。小说“理性地破除了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不仅是男性的自私与伪善,更在于女性自身对爱情的生死依赖、自我独立精神的丧失”。[9]128这是对一个世纪中国女性婚姻命运的深刻洞察。
新世纪女性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在家族或民族国家的历史纬度上来塑造女性形象,将女性的成长与蜕变设置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之下,在细腻委婉、充满女性气息的描写之中拓展了女性小说的叙事空间与叙事视野,从而填补女性历史的空白之页。
综上所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多年间,女性小说创作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又一次人类精神文化领域的探索与历险。小说叙事形式的嬗递,反映了在时代文化语境下女性小说自身发展的必然。纵观新世纪女性小说,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未死,90年代的性别坚守犹在,新世纪社会性别意识的彰显更凸显了多面立体的“她”。相信女性小说将保存女性的那份丰富与灵动,在“万物花开”中呈现、绽放更加丰富多彩的“她世界”。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福柯.什么是启蒙[C]//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
[3]陈纯洁.戴厚英把人当作一本书[J].前沿,1996(12).
[4]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0.
[5]乔以钢,林丹娅.女性文学教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6]戴锦华.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化与女性写作·导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7][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M].转引自: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2.
[8]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J].花城,1996(5).
[9]王红旗.历史重构与自我超越[J].山西师大学报,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