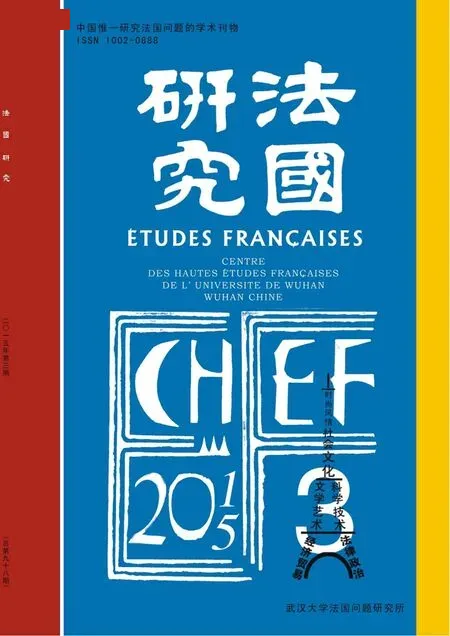试论罗曼·加里的身份建构——读《童年的许诺》
刘娟
罗曼·加里(Romain Gary,1914-1980)何许人?普通中国读者对这位二十世纪法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的了解,恐怕只局限于他是迄今为止唯一两度摘得龚古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对于这个无法三言两语概括的问题,作家的第一任妻子莱斯莉·布兰奇(Lesley Blanch)回答:“他(加里)很特别,随着时光,最终成为传奇。”①Blanch, Lesley, Romain, Un regard particulier, Nîmes: Actes Sud, 1998, p.7.让我们重新回到龚古尔文学奖上来,按照规定,同一作家不能两次得奖,加里两度“传奇”摘冠(1956年的《天之源》Les racines du ciel 和1975年的《来日方长》La vie devant soi)的奥妙之处在于后一本书是以化名埃米尔·阿雅尔(Emile Ajar)发表的。其实,在近40部的文学作品创作中,作家曾使用多个化名。“从他不同的名字中,从他在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外交界留下的不同成果中,人们也许有了对罗曼·加里的定义。然而恰恰相反,真实的罗曼·加里超越了这些定义。”①罗曼·加里:《大亲热》,李一枝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2页。
“真实的”罗曼·加里经历了多重人生和多重文化:原名罗曼·卡谢夫(Roman Kacew),俄籍犹太人后裔,生于立陶宛,童年时代在俄国和波兰度过,之后,与母亲移民法国,二战期间投奔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加入空军战斗部队,改名罗曼·加里,得过战斗勋章,重建时期在外交界工作,曾任法国驻洛杉矶总领事。传奇的经历,众多的头衔,真实和虚幻的各种“变形”间,加里是否也曾迷失自我,“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时,“我是谁”的疑问却上心头?
1945年,而立之年的加里收到英国一家出版商的电报,获知处女作《欧洲教育》(Education européenne)即将出版,直到那时,他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摘下飞行帽和手套,久久地原地痴立,眼睛一直盯着那份电报,连飞行服都没有脱掉。我获得了新生。”②罗曼·加里:《童年的许诺》,倪维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97页。由此,加里对自己“作家”身份的看重与忠诚可窥一斑,对他而言,写作就像吃饭穿衣,是一种器质性的需要,用来对抗一成不变的身份。
“写作是一种考验。”③让·热内:《鲜花圣母》,余中先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编辑手记。成为作家,通过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多体裁的创作,通过事实、想象、传记、虚构等多方法的运用,混淆自己的现实身份和虚构身份。对加里而言,身份是意愿,是忠诚,是接受改变,是遵守承诺,是“用肌肤上的每一个毛孔片刻不停地填充数不胜数的我”。而复杂的经历,仅仅是某些特定的极富偶然性的事件,真相隐藏在别处。一次访谈中,加里说:“真相?什么真相?真相是或许我根本就不存在。”作家通过虚构逃避自我,游离于存在、虚无之间,他曾借笔下人物莱尼耶(Rainier)说,生活的本质就是“一种不顾一切地迫不及待的意愿,对一种明知的不可能所怀揣的战战兢兢的希望,同时也是每一次事与愿违时的痛苦。”④罗曼·加里:《大亲热》,李一枝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3页。希望,痛苦,这二元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对自我意义的探求以及身份建构的焦虑。在加里的文学创作中,他一次次“伪装”,在虚构中叙述真相。本文试图通过对加里自传性作品《童年的许诺》的文本解读,探寻加里的身份建构问题。
(一) 诺言 - 希望:《童年的许诺》题解
二战后,当大部分作家,从卡夫卡(Kafka)到存在主义者,消极颓废而迷茫悲观时,加里发出“生命之爱即为人类处境”的呼吁,倡导用生活的欣喜和渴望、用“愉悦的存在焦虑”、用“下一次”对抗“恶心”,对抗“荒谬”。加里是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 “没有希望的世界令人窒息”这一断言的拥趸。勇气和希望构成贯穿加里文学创作始终的关键词,诺言是希望实现的手段。换而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和诺言是一对近义词,“代表乐观主义”并“具有深远意义”。⑤罗曼·加里:《大亲热》,李一枝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89页。《童年的许诺》(La promesse de l’aube)的法文标题直译为“黎明的诺言”,而黎明预示着希望。
在《童年的许诺》中,加里回忆与母亲共同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试图重新拾回那早已消失殆尽的幸福感觉。加里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后者对他寄予厚望,“去法国居住、学习、成才”,成为“法国大使,荣誉勋位骑士勋章获得者,伟大的剧作家。” 而“诺言”,是罗曼自生命之初承诺母亲要对生命的不公正作彻底回击,“我从童年时代就向母亲许下的诺言,要使母亲摆脱他们(世上作威作福的暴君)的奴役。”(罗曼·加里,2008:8)母亲对儿子的盲目信任和过高期许,曾压得小罗曼喘不过气。在母亲的要求下,他神农尝百草般地学习绘画歌剧唱歌舞蹈,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年迈的母亲,初到法国,面对困难、嘲笑,公开向儿子承诺,他将是外交官,战斗英雄,将前程锦绣。不能跟母亲的期许同步以趋,不能满足母亲的急切需要,信守承诺变成难以实现的计划,加里诚惶诚恐,转向最后的希望--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童年的许诺》其实也是作家的成长史,从一次次失败中愈挫愈勇不断获取希望。“我有猥琐的一面:渴望幸福。”《女性光辉》(Clair de femme)中的米歇尔·弗林(Michel Forain)如是说。弗林是加里所有作品中命运最悲惨的主人公,痛苦,绝望,但他百折不挠地无数次宣告对生活的信心。加里说:“第一次我从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认识了自己。这是我的心声……是我自己。”向往幸福,怀揣希望,“失去的一切给予我继续生活的理由。” 绵绵母爱赋予加里特别的命运:在文学界,外交界的成功皆源于这个承诺,要忠于母亲单纯的信任,忠于那“磐石般的柔情”。
(二) 自传 - 虚构:身份的困惑和探寻
加里在《有罪的头颅》(La tête coupable)中曾两次引用叶芝(Yeats)的诗:“我找寻曾经的我,在世界被创造之前”,“我找寻曾经的面容,在世界被创造之前。”在《童年的许诺》中,作家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过往的生活,进行身份探寻的尝试,他自始自终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没有参考任何文献资料,不停地变换叙述时空角度,确切地记录事件的时间结构和详细信息,试图让真实的事件重现,并俯视自己的内在性,而这内在性是感情生活全部事物的特性。菲利普·勒热纳(Pierre Lejeune)在《自传契约》(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中写到:“(自传)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对自己人生经历所作的回顾性文字叙述,强调个人的生活经历,尤其强调个人的历史。”①Lejeune, Pierre, 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Seuil, 1975, p. 14.按照更加注重形式的观点,自传强调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三者身份的完全合而为一。表象上看,《童年的许诺》好像完全符合菲利普·勒热纳关于自传的定义。
但同时,加里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通过想象和虚构实现自我隐藏。其实,在撰写自传性作品时,对于如何回答“我是谁?”“我去哪儿?”“我从哪儿来?”“我为什么会在这儿?”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如何填充记忆 “黑洞”,作家们各施其法,佩雷克(Georges Perec)借助于档案,加里则认为“自我创造是自我发现的必经之路。”②Gary, Romain et Konstantin Jelenski, Livres de France, in. Romain Gary, Paris: L’Herne, p.11.在加里笔下,虚构逐渐超越事实本身,从另一层面发现事实,重构记忆。在《童年的许诺》中,作者通过虚构与自传性真实回忆的交融,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历程。
归根结底,加里自传作品中的虚构成分大多源于对自己出身的隐瞒。“我写作......是为了变成我不是的那种人。”对于追根溯源的“父亲”(出身)问题,作家用了少至极致的笔墨,暗示父亲的存在,并以极其蔑视的文笔编造了父亲的死因,不过,直到卡谢夫死后,加里才承认了他的生父身份,换言之,卡谢夫在生前绝不可能获得“父亲”的身份。“只有在他死后,他才真正进入我的生活,而且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罗曼·加里,2008:83)伊凡·莫修金(Ivan Mosjoukine),俄国哑剧演员成为加里想象的父亲。作家否认“真正的”父亲,选定“想象的”父亲,再后来,加里逐渐成为“自己的”父亲,他在《笔名》中写道:“我是埃米尔·阿雅尔,我是自己作品的儿子,也是自己作品的父亲。我是自己的儿子,也是自己的父亲。”①Gary, Romain (Ajar, Emile), Pseudo (1976), Paris: Folio, 2005, p.202.关于母亲,在书中,“妮娜”是一位知名设计师的形象,而事实上母亲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女帽商人,在积满污垢的维尔诺小镇艰难度日。另外,与“父亲”身份的建构相反,在小说的结尾,加里虚构出母亲在临终前几天,写了将近二百五十封信,委托女友定期寄到儿子手中,作者得以在母亲离世后仍然可以继续与之对话,“继续汲取母亲的力量和勇气,这条脐带一直发挥着作用,它使我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罗曼·加里,2008:307)
想象具有某种超越现实,让现实望而却步的力量。加里运用自己的这件秘密“武器”为自己还有读者竖起一座座堡垒,规避令人失望的现实,还有极度残酷的生存处境,重获为信仰而斗争的力量。试想一下:一位犹太外国母亲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反犹运动此起彼伏的时代移居法国,他们如何在艰难的处境中过活?同时,母亲对儿子寄予厚望,儿子如何恪守对母亲许下的诺言?也只能借助于饱含希望的虚构,而不是带有溃败意义的现实。塞尔吉·杜布洛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曾说:“人们总是讲述自己的一些无稽之谈。自传,小说,都一样。一样的技巧,一样的弄虚作假,来迷惑大家……在某种程度上,自传比小说更虚假。”②Doubrovsky, Serge, Le livre brisé, Paris: Grasset, pp.266-267.因此,跟纪实自传中的假话相比,杜布洛夫斯基更倾向于相信虚构的自传体小说中的真实。在《童年的许诺》中,加里在自我虚构中表达真相,虚构能力是自我存在的有力证明。但如何界定“自传”中的“虚构”,加里“保留解释权”③Rimbaud, Arthur,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la Pléiade, 1972, p.106.:他必须早于文学批评界,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论,以实现自我传奇的建构。在书中,叙述者的谎言同时是真相的表述,一方面,作家在表述时编造出谎言,另一方面,当他保证叙述事实时就会讲真话。“说出”的事实就是虚构,是叙述者达到“以假乱真”效果的必须手段,亦即阿拉贡(Louis Aragon)宣称的“为说出真相而撒谎”加里是“自己文化的使者。”这与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摒弃相同”,“保持自我性”不谋而合。
另外,历史性是加里作品的另一维度。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和战争经历记录下来,他成为艺术家,加入抵抗运动,进入外交界,兑现了对母亲的全部承诺。同时,历史永久地包容了他的文学创作,对历史的叙述杂糅进作家虚构的自传作品之中。对作家来说,生活,创造,属于同一种战斗,也是生命的全部。加里的每部作品都以完全自由独立的方式,作为“我是谁”疑问的回答,加里竭力成为他人,探寻自我的身份,其作品比人生还真实,是人生的延长。他放弃父姓,改换名字,重新选择祖国,“就如蜕皮一样”,为了跟以前不一样。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加里停止写作,他感觉自己被现实世界围困,想象力被剥夺,绝望之余,还对阿雅尔事件不知所措,让他的内心更加脆弱。加里感觉无法冲破现实的难题,“我的过错是相信个人的胜利。”(罗曼·加里,2008:308)《童年的许诺》的结尾,加里写到:“(自己)一下子跳到地毯上,弯腰,直立,再弯腰,蜷曲,翻滚,我的躯体仍然应付自如,我没有忘掉老习惯。” (罗曼·加里,2008:309)他不仅仅变成了阿雅尔,还重又变回了卡谢夫,也就是他自己。
(三) 结语:“母亲的自传”① Bayard, Pierre, Il était deux fois Romain Gary, Paris: PUF, 1990.
加里在处女作《欧洲教育》的末尾曾写到,主人公扬内茨(Janek)感到“衣兜里有那册珍贵的,如同一个已经兑现的诺言的小书。”②Gary, Romain, Education européenne, Paris: Gallimard, 1956, pp.275-276.而这本小书,在 1960年揭晓,即《童年的许诺》,这是一本写给母亲的书。如果不是阿尔贝·科恩(Albert Cohen)六年前出版了《我母亲的书》一书,加里的确可以这样命名他的这本自传小说。
在《童年的许诺》中,母亲与儿子形影不离。当死亡带走母亲,别离的那种痛苦可想而知。作家借这本书向母亲表示敬意,“字里行间沉浸着对母亲深切的怀念和拳拳的眷恋。……惟有绵绵的母爱,如一眼清泉,一首清歌,润物无声,穿越时空,永驻心田。” (罗曼·加里,2008:1)在书中,加里把儿时母亲给与他的情感交还给母亲。母亲不仅生养了他,还按照自己的意愿造就了他。母亲想让他成为法国人,英雄,飞行员,外交官,作家,他在35年内完成的母亲的意愿。由此,不难看出,“母亲”是小说的主线,她无所不在,不厌其烦地说着“你将来是”, 预兆儿子的命运。“你将来是”就像滤镜,过滤着这部意义特殊的自传小说的主要事件和情节。对加里而言,“被爱,首先是被一个人饱含温情地创造和想象。”母亲的期许创造出罗曼,并决定了后者的命运:“写作,…… 获取母亲对外宣布的一切,社会成功,金钱,声誉。”③Blanch, Lesley, Romain, Un regard particulier, Nîmes: Actes Sud, 1998, p.32.加里活在母亲的愿望中,他努力成为作家,外交官,英雄。“我知道我已经下定决定,要把我最杰出的成就奉献给母亲,作为对她的报答。”(罗曼·加里,2008:34)
加里除了向母亲表达敬意,还想通过这本小说,与母亲隔开距离。“爱是重新创造。”④Rimbaud, Arthur,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la Pléiade, 1972, p.103.通过文学,通过自己的创作赋予母亲生命,这一次,加里是母亲的缔造者。在完成这部小说后,加里偿还清自出生以来的欠债,兑现了“童年的许诺”。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童年的许诺》还是一本赎罪之书,带着在母亲临终之际没有陪伴左右的遗憾和负罪感,夹杂着“一张深情的嘴贴到我的脸上或肩头上的期待”,在《童年的许诺》出版 15年后,在另一本书中,加里用另一个全新的书名,一个全新的笔名,化身主人公莫莫(Momo)服侍罗莎夫人(Mme. Rosa)。“《童年的许诺》的读者们都知道你(加里)有一位非凡卓越的母亲。”①Gary, Romain, La nuit sera calme, Paris: Folio, 2005, p.13.,同时也知道母亲有一位信守承诺的作家儿子,因为写作是加里给予母亲的承诺。
加里完成了自己的命运。管他是卡谢夫是加里还是阿雅尔,他还是他,是母亲的儿子,是那个躺在比格-苏尔(Big Sur)沙滩上,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消失殆尽,幸福的回忆涌现眼前,虽然那幸福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依旧留恋那至柔的深情。“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这句古诗似乎能部分地表达出加里的身份。母亲溘然离世,长久以来梦想的繁华、成功,似乎也变为浮云,自己的人生也悄然徐徐落幕,没有了那双激励与充满柔情的手为自己加油,一切都变得了无意义,宁愿谁也不是,不是作家,不是英雄,仅仅是母亲的儿子,在破落之地,与母亲相偎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