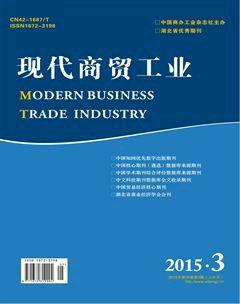跨国创业网络对国际市场势力影响研究
张建民 朱志静 王开玉
摘要: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国际市场势力直接作用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各国企业的利益分配格局,并间接影响着其技术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构建跨国创业网络是创业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实现内生可持续的技术创新从而保证国际市场势力动态获取的关键。但跨国创业网络对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机制与影响程度至今尚无充分研究。因此,从技术、市场两个维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协同互动来构建跨国创业网络对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机制,拓展SMR模型对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跨国创业网络;国际市场势力;SMR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5007303
1引言
在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直接影响着参与各国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与能力,而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关键则是参与各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势力。国际市场势力即企业通过对产品价格的控制所表现出的市场支配力量。在当前的全球竞争中,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知识产权控制、市场渠道控制、经营控制和建立企业间合作联盟等,形成了较强的国际市场势力,从而获取了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额利润。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却出现“量增价跌”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状况,企业对外“技术依赖”和“海外市场隔层”现象严重,因而缺乏国际市场势力,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技术创新是获取国际市场势力的必备前提,国际市场势力反之也能促进技术创新并防止创新被迅速模仿(Wolff,1997;Silvente,2005)。但创业企业个体面临突出的资源约束问题,技术创新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构建跨国创业网络成为其获取外部资源、实现内生可持续的技术创新从而保证国际市场势力动态获取的关键。
鉴于创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已有文献也主要局限于创业网络和国际创业两类独立的研究,鲜有学者探讨跨国创业网络(Entrepreneurial Cross-border Networks)。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际市场势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因素、对国家福利的影响以及国际市场势力的测度,并形成了三种测度理论,其中结构主义测度理论(Bain,1981;Cotterill,1995)已基本淡出主流研究,目前较为成熟的两类理论是基于新经验产业组织(NEIO)模型的测度理论(Bask等,2011;张小蒂和危华,2008)和基于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模型的测度理论(Roeger,1995;孙泽生,2009)但都集中于对卖方国际市场势力的测度,缺乏对买方国际市场势力的测度,并且学术界鲜有研究跨国创业网络对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
而改革开放以来,出口贸易作为国际化业务最主要的形式正在迅速增长,并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也为中国的国际市场势力带来了变化。这表明以出口贸易为代表的跨国创业正在通过其所创建的网络效应对中国的国际市场势力和国际竞争地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影响渠道正是笔者所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化工品贸易大国,每年有大量的化工品进出口,且进出口总量也在不断扩大,那么这期间中国化工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地位到底是怎样的呢?跨国创业网络到底对中国化工产业存在怎样的影响效应呢?本研究尝试从技术、市场两个维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协同互动来构建跨国创业网络对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机制并实证测度其影响程度,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2跨国创业网络对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机制
笔者尝试从技术和市场两个维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协同互动来构建跨国创业网络对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机制。
2.1技术维度:知识产权获取与国际市场势力
因为具有要素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技术创新被学术界公认为市场势力的基础。跨国创业企业若想在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形成一定的市场势力,需要内生的、可持续的技术创新作为其主要的动力和源泉,而创业企业很难获得资源所有者的支持。而跨国创业网络可有效整合、优化配置技术创新资源的相关要素,帮助个体企业获取和强化知识产权,提升国际市场势力。
创业企业通过对外部资源高效率的整合构建起的网络组织,以信息、知识、能力穿越企业形式上的边界以及国界而延伸到整个网络,从而发生规模、组织效率以及控制边界等各方面的变化,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网络中的企业个体相互作用并协调配合,产生协同效应,强化社会资本,因而增强网络的整体功能,并以网络的、系统的竞争代替个体间的竞争。这样不仅有效提高创业企业个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使其市场势力上升为整个系统网络的市场势力,从而获得有效增强。
2.2市场维度:渠道控制与国际市场势力
渠道控制能力是竞争市场中市场势力构建的重要环节。跨国创业网络可通过终端产品和原材料投入的纵向市场渠道控制增强对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力,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势力,也可通过中间品渠道控制和关联交易来获取超额利润,进一步企业的提升国际市场势力。
首先,通过纵向市场渠道控制增强对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力。跨国创业网络可实现国际市场渠道的整合,从而增加企业产品的国际销量,增强其作为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和控制力,并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企业创新成果的市场实现。另外,渠道的垂直整合能够缩短企业与国际市场的距离,帮助企业迅速掌握海外市场需求信息并根据需求变化及时修正研发设计,促进企业实现成功的技术创新,从而也增强企业价值链中的国际市场势力。其次,通过对中间品的渠道控制和关联交易来获取超额利润。类似地,跨国创业网络可以依托知识产权系统、网络化组织结构和供应链等中间渠道进行关联交易、转移定价的中间品贸易以及利润调整与配置,从而弥补外部市场的“结构性市场失灵”和“交易性市场失灵”,使资源配置趋向利润最大化,提高网络成员整体运营能力。
2.3两种维度之间的协同互动
技术维度与市场维度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技术为市场提供基础,市场反过来增强技术,二者的协同作用保证国际市场势力的持续提升。跨国公司依靠对知识产权体系、纵向市场和中间品渠道控制实现对全球价值链中关键价值环节的垂直预占,形成强势议价能力,获取主要分工利益,并限制其他环节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价值攀升。跨国创业网络凭借网络的系统整合能力和成员的协同效应,既能为核心技术和关键知识提供要素优化配置,提供市场渠道控制的基础,又能掌握市场需求偏好变化,提高技术成果商业化效率,从而实现技术创新的价值乃至溢价。通过这种技术与市场的良性互动,网络中的成员企业将有能力向全球价值链的上下游两端拓展,通过反垂直预占来扭转“低端锁定”的局面,增强国际市场势力,提升国际竞争中的分工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跨国创业网络通过技术、市场两个维度及二者之间的协同互动实现对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这一影响机制的良性循环保证创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力的持续和提升。
3跨国创业网络对国际市场势力的实证分析
为得到跨国创业网络与国际市场势力的准确关系,笔者运用中国化工产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选取2002-2008年中国化工产品的进出口数据,通过SMR修正模型对其买、卖方国际市场势力进行测度;其次运用本次调研所获2001-2007年的跨国创业网络效应细分数据,并结合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和前面模型得出的国际市场势力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获得两者影响效应的具体效果。
3.1中国化工产业国际市场势力的测度
基于SMR修正模型中的买方和卖方国际市场势力测度模型,笔者构建以下回归方程:
lnPMi=α0+α1lnRDi+α2lnPji+α3lnPGDP+μ(1)
lnPEi=β0+β1lnRSi+β2lnPGDP+ε(2)
其中,PMi和PEi分别是中国化工产业中的亚产业产品i的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RDi和RSi分别表示中国对国际市场上化工产品i的剩余需求量和剩余供给量,用中国对i化工品的进口金额和出口金额表示,Pji为此产品的国内最主要竞争者的销售价格,PGDP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变量主要是用来表示竞争环境下i产品的国内需求和国内供给的影响因素。lnRDi和lnRSi前的系数α1和β1即买方市场势力和卖方市场势力。在分析中国化工产品亚产业样本数据的基础上,考虑到其他产品的样本容量较小,笔者共对7个亚产业的产品的买方市场势力进行测度后,然后利用各产品的进口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后得到数据作为中国化工产业最终的买方市场势力。
3.2跨国创业网络的影响测度
(1)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根据上文跨国创业网络对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机制分析,笔者构造以下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PowerBt=γ0+γ1Size+γ2Concentration+γ3Variety+γ4Ability+γ5Government+X+θ(3)
PowerSt=δ0+δ1Size+δ2Concentration+δ3Variety+δ4Ability+δ5Government+X+π(4)
被解释变量买方市场势力PowerBt和卖方市场势力PowerSt来自前文对化工产业的测度数据。而两模型的跨国创业网络方面的数据均来自本次调研数据:本次调研针对调查企业的跨国创业网络结构、网络能力、网络治理设计了调查问卷,目的是获取调研对象所属跨国创业网络的相关信息,并用准确数据度量,以测度跨国创业网络对所属行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效应。
具体而言,笔者的主要解释变量可以归纳为三种:网络结构、网络能力和网络治理。首先,跨国创业网络结构更为具体的指标有:网络规模Size用以考察企业在其网络中能够连接关系的对象的多少,用调查问卷中企业的海外合作国家数目表示;网络集中度Concentration测度了企业与所属网络中其他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用企业与海外合作关系的维持时间进行测度;网络多样性Variety考察的是企业在网络中联系主体的多样性,用企业国际化业务的方式种类来测度该指标。其次,网络能力Ability包括企业在网络中双向关系的协调性、获取资源的各种技巧、与合作者的交流以及内部对资源的消化能力,用对企业构建跨国创业网络行为的描述数据来测度,包括国际创业导向、社会资本和海外市场知识。表1所示为网络能力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一致性检验。
(1)网络规模对买方市场势力构建具有正影响,对卖方市场势力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对于卖方市场势力来讲,重要的不是大的网络规模而是网络质量的提高;而网络规模扩大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对买方市场势力积极影响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并非网络规模越大意义更大,需要比较分析维持特定网络结构所需投入成本和从网络中获取的收益,而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都主要取决于网络规模,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网络建立和维护所需成本会提高至边际收益之上,因此国际创业者需做好网络规模与收益的平衡关系。
(2)网络集中度对买方和卖方市场势力都具有显著正影响。这表明与网络中其他参与者联系越紧密,双方关系维持时间越长,对企业市场势力的获取更有利。双方联系的过程实际上是建立信任基础的过程,网络成员间的频繁互动和长期联系,更有利于营造信任和互惠的氛围,这中间发展的桥联系是企业迅速获取更好资源的通道,为跨国创业活动提供了更有效的支持。
(3)网络多样性对卖方市场势力有显著正影响,对买方市场势力构建的影响不显著。以多种方式开展国际化业务不仅具有传统的分散风险意义,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国际业务获取资源的能力不同,对技术、市场等资源的吸收能力不同,同时不同的国际业务还能够将相互独立的点连接起来,更有利企业的信息收集和资源获取,所以开展多种国际业务更加有利于市场势力的构建。
(4)网络能力对买方和卖方市场势力都具有显著正影响。网络能力综合反映了企业捕捉和利用国际机会、获取创业所需信息和知识、在新环境中快速学习、快速反应并规避风险障碍以及对企业未来的前瞻规划等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使新创企业掌握了创造知识的优势,并促进其国际扩张,形成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实现价值创造的条件。具有良好网络能力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可以为其网络不断输送新的知识并进行整合,并充分利用获取的资源拓展新的市场,构建并提高其市场势力。
(5)网络治理对买方和卖方市场势力都具有显著正影响。合作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是对其可靠性的相信,认为对方总会采取可预测和可接受的行为,因此,信任可以在决策过程或承担复杂工作时,能够充分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信任会影响网络中资源获取的丰富度,信息交换的充分性和整体性以及网络关系的持续性,这决定着企业市场势力能否得以维持和继续提升。
4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企业面临“技术依赖”、“市场隔层”,并陷入“低端锁定”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市场势力与创新能力的双重缺失。构建跨国创业网络则成为创业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实现内生可持续的技术创新从而保证国际市场势力动态获取的关键。跨国创业网络既能促进单纯的技术创新(技术维度),又可通过渠道控制有效扩大市场规模(市场维度),且能使技术与市场两个维度协同互动,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势力,并保证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势力增进的螺旋式上升与内生性良性互动。这将对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笔者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继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引导企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方向转型;二是加强政策支持,鼓励企业融入、构
建和拓展跨国创业网络,并努力获取技术与管理的逆向外溢;三是激励企业对高附加值中间品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市场需求导向型的技术创新流程整合与再造。
参考文献
[1]方建春,宋玉华.我国在稀有金属出口市场的市场势力研究——以钨矿、稀土金属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11,(1):310.
[2]张辉.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与产业发展策略[J].中国工业经济,2006,(1).
[3]张小蒂,贾钰哲.全球化中基于企业家创新的市场势力构建研究——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1,(12):143152.
[4]Bask,M., J. Lundgren and N. Rudholm.Market Power in the Expanding Nordic Power Market[J].Applied Economics, 2011, 43(9): 10351043.
[5]Silvente, F. R.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Market Power in Export Markets: the Case of the Ceramic Tile Industry[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2005,8(2):347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