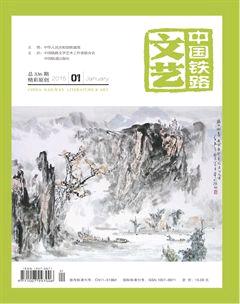吴宝三散文三题
吴宝三
1959年的那个春节
1958年“大跃进”,这是一个狂热的年代。那时,我家在松花江北岸兰西县榆林镇开一个小杂货铺,小本经营,卖点烟酒糕点、日用杂货。公私合营的浪潮卷来,镇上十几家店铺合并成一家大综合商店,留下三四家有点经济实力的,其余各户一律分流到各村屯去开小卖部,我家被发落到距镇上12里地的牛家窝棚,并勒令限期搬家。父母亲商量,如果下屯,孩子全都得辍学,只有去铁力林区投亲了。就这样,一家五口人,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拂晓,一辆老牛车拉着两个破木板箱子装就的行李,还有用旧棉絮包裹的五六十个鸡蛋,离开了老家。这一年,我13岁,弟弟10岁,妹妹只有7岁。
在小兴安岭林区铁力火车站附近,我家在父亲的朋友家院里一间小草房安顿下来,母亲将带来的鸡蛋全部送给了要临产的房东。眼看要过年了,家里任啥没有。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副食品奇缺。父母亲没有工作,户口还没落下,既无钱也无票证,母亲急得不行。到了腊月三十,家有三个孩子的长兄,出差从外地回来,送来几块钱和一块肉,母亲没有挽留,让他赶紧赶回家和老婆孩子过年。母亲给了我两角钱,让我去八里之外的县城买几棵白菜,好年夜包饺子。她对我说:“一年忙到头,再难今儿晚也得吃顿饱饭。”我领着弟弟去街里转了一大圈,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跑遍了大街小巷,也没买到一棵白菜。在一位老大爷的指点下,我们兄弟俩又走了几里路,在一个农户家买了几棵酸菜,也算不辱使命,完成了母亲交办的任务。少年不知愁滋味。此刻,我想起在老家过年的情景,贴对联、放鞭炮、供灶王爷,和小伙伴提着灯笼疯跑;搬到这个陌生的县城,一切都那么新鲜,到处是大木头,堆积如山的木柈子,还有冒着白烟的森林小火车。我和弟弟顺手在地上捡了根小木方,抬着一个破水桶里装着的酸菜,甭提心里有多高兴。全家终于能吃上这顿饺子了,我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在新学校刚学会的《远航归来》这首歌。“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袅袅的炊烟招手唤儿郎……”
刚迈进家门槛儿,看见家里来了三个人,两个大人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大包小裹,风尘仆仆,像闯关东逃荒似的。原来是山东老家一个村的远房亲戚,火车误点,换乘开往山上的森林小火车没赶上,回不了林场,知道我家新搬来,住在车站跟前,一路打听,找到我家,哪里知道我家眼下这般艰难。看来,晚上得住在这里了。住,可以在一铺炕上挤挤;吃什么呢?我不知下步该怎么办,心里暗暗叫苦,用当时流行的一句外交辞令,我视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可这时的母亲,喜出望外,忙给孩子脱衣服脱鞋,把她抱到炕头,盖上被子。然后,母亲一边和他们说话,一边开始和面,让我赶紧把酸菜从桶里捞出来,准备包饺子。表哥一家执意要去住旅店,母亲苦苦挽留,无论如何不能走,一起吃顿年夜饭,在我家过年。她话语十分恳切地说:“你们如果走了,我们也过不好这个年!”母亲的举动,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如此之大的震撼,心里的不情愿,顿时化为乌有。我忙拎起小斧劈柴生火,帮母亲做饭。两家人在窄小的茅草屋里,放上炕桌,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叙乡情、拉家常。这顿年夜饭,吃得有尊有让,其乐融融。按照母亲的叮嘱,我吃了几个饺子,便下桌了,领着弟弟、妹妹高高兴兴出去玩。
母亲的老家在曲阜,和孔子是同乡。她没有上过学堂读过书,却深明大义,在其身边生活的日子里,常常引用《三字经》《千字文》,或讲述经典古戏文,举有情有意义之人为榜样。如果说,我能学得一点点,尚能善待他人,哪怕是对讨饭的乞丐,母亲的言传身教使然。日后,每当提及过年这件事,她总是说:“最难风雨故人来。那时候咱们家过的穷困潦倒,有人来看看,那是亲情,得感谢人家!”其时,母亲未必会想到施恩图报,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这个老表,吃的用的经常接济贴补我家。1970年我结婚时,竟寄来50元钱,这相当于当时四级技工一个月的工资。
往事未必雨打风吹去。半个世纪过去了,大年三十儿这顿年夜饭,在记忆中打上深深的烙印。那顿饺子,我虽然没吃半饱,但是,母亲在1959年的这个春节,却给我上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课,她是我如何做人的启蒙老师。
小兴安岭的“欧洲小镇”
每每踏上坐落在小兴安岭西南山麓的绥棱林业局这片土地,心中便涌起一种莫名的冲动。这个昔日东北亚大森林出了名的“小老穷”局,何以焕发青春,充满朝气?
她,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或是一个高富帅的年轻小伙,还是一颗深藏大山的璀璨明珠?世界上一切比喻皆不准确,她,就是一个国有大型森工企业,建局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林业局。但是,我还是要活剥大诗人苏轼的两句诗来形容她:欲把此地比西子,浓妆淡抹总关情。
这个小镇美,美得与众不同。不仅仅是一片片红蓝屋顶的楼房,令人喟叹,俄罗斯木刻楞板房,掩映在绿树丛中,欧洲盛行的巴洛克建筑在这里安家;也不仅仅是,马路两侧的灌、乔木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遍地鲜花,争芳吐艳。小镇让你惊异的是,这里见不到拒百姓于大门之外的栅栏、围墙,大街小巷见不到一个垃圾桶,路上看不见垃圾、纸片,所有的建筑物的墙上,见不到一条被称为城市痼疾的“小广告”。你看,这边是文化园、文化广场、民俗文化一条街,那边是博物馆、文学馆、体育馆、生态园……小镇美,美在文化,处处闪烁着文化的光芒。
我行走在小镇的大街上,在这个3平方公里的大花园中徜徉,吸一口湿漉漉的绿色的空气,神清气爽,耳边,不时传来阵阵蛙鸣。抬眼望去,目光所至,那是一片塔头湿地;近前,一排排云杉、冷杉等本地树种乍吐新绿,一丛丛兰花、马莲含笑水边,一对对鸳鸯、野鸭在水中嬉戏。毗邻湿地的植物园里,从深山老林移来的原生态植物遍地丛生。园中一块块巨石之上,刻有百首从古代到现代的经典诗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入夜,蛙声不绝于耳,似一支催眠的乐曲,一忽儿近,一忽儿远,我枕着蛙声渐入梦乡。
清早起来,我独自一人来到家属住宅小区,楼间的空地皆是井然有序的小菜园。社区将菜地分拢到户,每户三五拢,责任落实到户,家家深耕细作,全无杂草。我信步走进一家住户。这是一户森林铁路退休老工人的家,楼下客厅厨房,楼上两间卧室,南北通透,窗明几净。家门口的小院里,一片碧绿,茄子、辣椒、土豆、西红柿长势喜人,爬蔓的葡萄伸出一根根细细的触须,篱笆上的一朵朵牵牛花,吹奏着粉红色的喇叭。我称赞主人家这般干净,老两口笑道:“这么好的环境谁也舍不得祸害!”由此,我联想到精神文明建设,如果农民家家如此,卧室铺有地毯,你不用说教,他自然会改变吐痰的不良习惯。林业局有人们公认的全省一流的幼儿园和养老院,孩子们唱歌、游戏,笑得那么灿烂,老人们散步、打牌,一个个鹤发童颜。面对社区盛开的花树林带,我想起《桃花源记》,男耕女织的境界令人神往,“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莫非我置身于桃花源之中?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又一个清晨,我遇上晨练的几位局领导,便一起散步。一位同行的领导,随手捡起地上的一个矿泉水瓶,几个老太太看见了,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迎面走来,这位领导摸摸孩子的头,小孩眨眨眼睛,喃喃自语:“我认识你,你是邓局长!”为什么条条大街上没有废弃的杂物,答案找到了:习惯势力是最强大的势力,然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忽见一位白发老者从后面赶了上来,递给邓局长几页稿纸,便匆忙走开了。原来,老者相中了这块福地,买了新楼,从附近的一个市里,搬迁到林业局来居住养老。老人是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小文章,知道局长出过好几部书,便经常请局长改稿,因为每天晨练都能相遇,就把稿子带在身上。这时,几个晨练的人围了过来,七言八语各抒己见。有的说:“大街小巷你见不到随地摆摊儿的”,有的说:“一年到头你见不到街头烧纸钱的”,有的说:“咱们局3平方公里之内,你见不到高空挂线。”这时,党委张书记停下脚步,用手指了指前方,告诉我“领导晨练,现场办公,遇到问题就地解决。上些日子,有几个退休老干部反映,文化大街上没地方避雨,士君局长在街上当即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建起了这个木制的雨搭长廊。”我感慨不已。天天和百姓零距离接触,这与有的领导不敢和群众对话、群众上访却从后门躲开,形成多么鲜明的反差!
无独有偶。此刻,不知从哪家哪户的窗口传来唱遍大江南北的《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深情的演唱,令人心潮起落,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上海一对夫妇从瑞士探亲归来,打电话说起绥棱林业局,不无自豪地对我说:“绥林局同欧洲的小镇相比,并不逊色!”我艳羡,生活在新林区的幸福的人们;我讴歌,引领绥棱新生活的带头人;我赞美,中国林区这个不见经传的“欧洲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