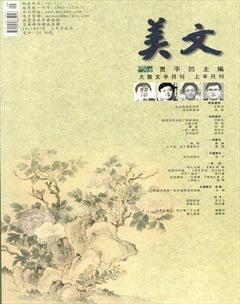在台湾巡回讲学
余秋雨

一
二〇一五年三月初,高龄的白先勇先生欣然接受台湾大学邀请,开始主持中国古典文学讲座,备受媒体关注。他既来电话又来信,命我为他开张第一讲。
我很难拒绝,因为整整二十三年前,也是他,让我作为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大陆文化人,跨越重重难关,到那里开讲中国古典文学。
我想,今天听讲的台湾大学学生,那时候都还没有出生。二十三年,时势的变化难以表述,但前后却是同一个邀请者,面对同一个课题。文化的韧性和定力,让人惊惧。
果然,三月二日那天下午我开讲后,台湾的媒体都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这在所有的媒体都在追新逐奇的今天,极为罕见。
一千多位子的演讲厅,早已座无虚席。其实那天来听讲的,远不止台大学生。前几排的听众都不年轻了,除了台湾大学的领导外,还来了很多重要的文化人。“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的创办人高希均先生和发行人王力行女士也坐在下面,他们已经顺势策划了一个活动,让我在台湾由北到南,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进行巡回演讲。演讲的总题是《君子之道》,以配合我的同名著作台湾版的发行。这次同时发行的,还有我的另一部著作《极品美学》。
本来这样的巡回演讲并不难,台湾各城市的读者对我都很熟悉,据说通告一出,报名均已爆满。但麻烦的是,高希均、王力行这两位杰出学人和他们非常优秀的专业团队都一路陪伴着我,每场必到,坐在第一排,笑眯眯地看着我,那就使我不好意思讲重复的话了,每场都必须另行准备。
这一来,我就要对“君子之道”这个话题作出更广泛的伸发了。也许有人会问,你既然已经写成了一本厚厚的书,还怕伸发吗?这就是学术研究和现场演讲的区别所在。何况,每场演讲的听众成分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台中那次,原先报名的听众坐满之后,又挤进来好几所中学的学生,连其他城市的学生也坐了几个小时的长途车赶来了,他们都只能在走廊上席地而坐。我看着这么多年轻的脸庞讲述两年多年前的君子之道,话语系统也不能不有所改变。
等到演讲结束,很多听众排队让我签名,而那些年轻人则抢着与我拍照。他们都会在我耳边说一句:“真的感谢你,余老师。”可见,他们还是听进去了。这比年长者的赞扬,更让我高兴。还有不少学生边听边给我写信,在拍照时悄悄塞给我,信上所谈,都是对君子之道的领悟。
二
我在台湾的每场演讲,听众都超过千人,有时还接近两千。我注意到,这么多人连续听二三个小时,没有一个人在滑手机。
原因之一,是我总是在开头说明,我讲述君子之道,并不是提倡复古主义,而是寻找中国人在当代世界中一种值得固守的“正面集体人格”,与每个人有关。
这种正面集体人格,是由悠久的历史沉淀而成的“基因”。我走遍全世界,深信这种“基因”是中华文化的最后主题,比肤色、语言、专业、政见都更重要。我从孔子、孟子的教言中选取了最有代表性、又最有渗透力的九条“君子之道”,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一个基本轮廓。但是,在演讲中,九条的量又显得太多了,因此减少为四点,那就是:
一、与人为善;
二、周而不比;
三、中庸为德;
四、温良坦荡。
讲清这四点,并与我们日常行为中的普遍误区相对照,现场效果很好。
我在演讲中反复提醒大家,现在讲这些君子之道,首先不是道德教育,而是文化寻根。与其说是询问“我该怎样”,不如说是询问“我是何人”。
我发现,在台湾年轻人中讲这个课题,居然能产生一种特别的气氛,在现场形成凝神屏息的宁静。这与香港构成了明显的差别。我在香港的大学兼任教授多年,深知那里的学生缺少这种感应。可能是,香港在集体人格的养成上因长期多重叠加,而产生了互相抵消。相比之下,台湾的教育更值得首肯。
那么多不同年龄的听众冲着“君子之道”的题目快速聚集,说明这里还保持着一种跨越时间和年岁的“在乎”。在乎君子,在乎孔子、孟子在二年多年前的文化设计和人格倡导。
三
由于太“在乎”了,也产生了一些趣事。
台湾几家大报在以醒目的篇幅报道我的演讲时,总会加上一句,说我认为台湾在君子之道上做得比大陆更好。
这不能不让我哑然失笑。因为我反复论述,君子之道中有一条“周而不比”,怎么转眼就“比”上了呢?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所说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总是周全而包容,小人总是紧张地与别人比来比去。“比”,如果不闹大,也就是小心眼、小算计。因此,真正要讲君子之道,就不会热衷于把人家比下去。
为此,我在几场演讲中,都引述了自己在《北大授课》一书中的一个观点:在海峡两岸开始交流至今,在文明生态的观感上,大陆民众总是高看台湾民众,而台湾民众总是低看大陆民众。我说,尤其是这些年,台湾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大陆游客“不文明”的报道,而大陆那么多报刊、电视、网络,却几乎没有对台湾民众有负面的报道。其实,多年来在大陆发生的很多电信诈骗案和伪钞案,主谋往往来自台湾。
我说,大陆游客在旅游时的不文明举动,确实应该批评,而且大陆媒体批评得更加严厉。但是,台湾朋友也应该想一想,说到底,这是大批不熟悉城市文明和国际礼仪的民众快速富裕起来,拥有了在全世界旅游的权利,才产生的现象。过去贫苦了那么久,而人数又那么多,应该可以体谅。我在演讲中举例说,我曾为日本最大的音乐家、散文家团伊玖磨的文集写序言,看到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几十年前,意大利威尼斯的很多马桶都被日本游客踩坏了,因为当时他们还习惯于“蹲”。我还说,我们不妨想想,如果自己家的长辈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也难免会举止失度。对此,恶意嘲笑并不可取,天天嘲笑更不可取。君子的办法,是帮助,是劝诫,是立规。
在一次演讲的互动环节,有一位大学教师问我孟子在“尽心”篇上所说的一句话,我就解释道,作为君子,一旦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并且感到不好意思,孟子就觉得可以了。我说,现在多数大陆游客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希望台湾、香港等地的同胞不要再夸张其事。
说到“夸张其事”,我又想到这次台湾之行所遇到的一件小事。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的妻子马兰,说她前不久陪一位大陆的文化人游览,那位文化人指着路边的花草就说:“这要是在大陆,早就搬回家了!”马兰一听就惊叫起来,说:“你去看看,大陆很多城市的街边花草,比这里更多、更茂密、更讲究,根本没有搬走呀!”可见,那位大陆文化人为了讨好主人,提供了错误信息,“比”得不伦不类,造成外界的负面判断,不像是君子言行。可惜这样的文化人还不少,我劝台湾朋友不要上当。
我说,天下任何文明人,都不应该鄙视一个庞大的人间族群。我曾经考察过世界上全部重要的古文明遗址,发现从长远看,中国人整体上很不错。从来没有远征过别的古文明,因此也成了守护住了自身文明的唯一族群。从近处看,每次遭受巨大自然灾害时都展现了全民自发的互救壮举。我说,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虽然也有很多共同的毛病,却拥有大量共同的优点,例如勤奋、顾家、重友、随和、知足、乐观。就大陆民众来说,十几亿人口在不长时间内大幅度地摆脱了贫困和极端,或者正在努力摆脱,成果如此惊人,这不是世界上别的族群都能做到的。
我说了那么多,为什么台湾媒体还会报道我更为称赞台湾的君子之道呢?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演讲中反复申述,君子之道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应该集中体现在文化人身上。中国古代的优秀君子,几乎都是文化人。而现代君子的典型,我报出一些自己熟识的名字,恰恰更多的是在台湾。例如,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汉宝德、高希均、蒋勋、王立行、隐地、陈文茜,以及佛门君子星云大师、慈惠法师等等。
这些名字在台湾是公认的,几乎妇孺皆知。公认,正是体现了一种推崇君子之道的社会气氛。这些名字,把文化“人格化”了,渗透到了大街小巷。更重要的是,这些名字,并不包涵权位和财富,并不与官职和半官职相连,因此又体现了文化人格的纯净度。与大陆相比,台湾那么小,却能长久地支撑起那么多无可争议的文化梁柱,确实令人深思。其实,这也正是大陆文化的差距所在,只能等待时日了。
一个社会的君子之道,大于君子的存在。君子到处都有,却需要一种大道,把他们与小人区分开来,并把他们推到万人瞩目的安全地位。于是,抬头瞩目的万人,也就会受到他们的光照。反之,如果无此大道,那么,即使出了不少君子,也会被淹没在“优汰劣胜”的泥潭中。
四
我把这次巡回演讲的最后一场,放在台湾南部的高雄。理由之一,是要再度拜谒星云大师创建的佛光山。我和妻子很早就熟识星云大师,知道他近年来已经失明,也离不开轮椅了,不少医学指标都有点严重,非常牵挂。星云大师在这种身体情况下还坚持在世界各地弘法,着实感动了各国无数信众。听高希均教授说,他近日带着医生在澳大利亚主持“南天寺”的开幕,不一定能见到。我说,我们可以在佛光山等一些日子。如果等不到,来过也就表达了敬意。
坐高铁,从台中到高雄的半道上,高希均教授接到电话,兴奋地告诉我,星云大师为了迎接我们,昨夜已经澳大利亚赶回,旅途辗转,花费了十几小时。这让我很震惊,设想着他在飞机上的艰难状态。
我们是在三月六日中午十一时二十分到达高雄的,有两位法师在车站接我们。他们一见就说,将有一个惊人大礼。我看了一眼马兰想,会是什么大礼呢?莫非,是安排了两大捧鲜花来迎接?
一出车站西门,我们看到“大礼”了,那是星云大师本人。他拄着拐杖从轮椅上站起,已经在这里等了二十五分钟。从佛光山到高雄车站,路并不近,他居然亲自来迎接。车站里外所有的民众都惊呆了,看着他高大的袈裟身躯,却又不敢靠近。他们都在猜,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要这位已经失去视力和脚力的年迈宗教领袖站在这里?
高希均教授附耳对我说,星云大师讲究礼仪,但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对国际上任何一位高官和企业家,像今天这么隆重。
一一见过后,星云大师要我们与他同车上山。上山后住下,他又要在茶室接见叙谈。接下来几天的情况是,凡是我们的活动,他都会先到一步在门口迎接。等到那天我终于要开讲,满场子千余名听众还没有见到我,却看见星云大师已经坐着轮椅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听众惊诧万分地站立起来,欢呼鼓掌。
这场演讲的听众,集中了台湾南部各个高校和文化机构的专业人士,但毕竟会场设在佛光山,因此我事先作了一个特别安排:在我演讲前,先请马兰演唱我写的《寻找菩提树》。那是十五年前我到印度和尼泊尔寻找释迦牟尼的行迹后写的一首长诗,马兰选唱了前面一段。
马兰上场后简单讲述了长诗的来历,然后开始没有伴奏的清唱。她唱得平静、深沉而高华,把在场的听众全都镇住了。过后几天,星云大师一再盛赞她唱得好。台湾的报纸,也争着刊登了马兰演唱的大幅照片,照片的一半是坐在轮椅上仔细聆听的星云大师。
我的这场演讲,也因地制宜,讲了君子之道与佛教的关系。我介绍了自己已经写在《中国文脉》一书中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在诸子百家时代已经出现超浓度的精神聚集,为什么还会让一种异地来的宗教深深扎根并广泛风行?那就是因为佛教弥补了诸子百家的共同空缺,其中也包括儒家君子之道的空缺。例如,君子之道虽然设定了对立面小人,却没有探寻小人的生命误区,因此也没有触及君子的生命依据,却泛化在“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使命里了;又如,君子之道缺少戒律和团队,因此也失去了基本边界,造成了人人皆可自称君子的混乱……正因为如此,儒家在后来的发展上总要从佛教吸取宏观结构和深层理念,其中包括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划时代儒家宗师。
没想到,星云大师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在第二天喝茶时他对我说,除了孔孟的论述外,君子之道在佛门可能会更突出四点,那就是:慈悲、忍耐、无我、和平。我说,他的这个概括,真值得儒家注意。佛门君子的起点不是庞大的社会事功,而是慈悲,而慈悲的起点则是无我。佛门君子会以惊人的忍耐来实践慈悲,最终实现人间和平。这四条,在儒家论述中,除了孔子的“仁”和孟子的“恻隐之心”较为接近第一条慈悲外,其他三条都显得疏淡。因此,儒家必须获得佛教的支援。
与以前一样,星云大师很愿意与我一次次长谈。这次他说,在他眼睛失明之后,请助手们为他朗读书本,近几年读得较多的是我的《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可见,我不在的时候,他也在与我交谈。他还特别称赞了我为扬州鉴真图书馆写的书法。这一称赞让我感到悲凉,因为从时间算,那应该是他失明之前最后看到的墨迹之一。现在他已经看不见一切墨迹了,即便在写“一笔字”时,也只是隐约见到助手摆在白纸上的一条黑棒,凭心勾画。我很想告诉他,去年我的六卷书法集获得了全国金牛杯美术图书金奖,其中包括行书《心经》。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说,既然他已经看不见了,就不要再提必须依赖视觉的作品。书法,助手无法“朗读”。
星云大师在无边的黑暗中,想象着世间的各种光亮。其实,他本身就是世间光亮的点燃者和护持者。现在的他,自己越黑暗,别人越明亮。
想起在台中的亚洲大学演讲那天,正逢元宵节,晚上要举行盛大灯会。我在演讲开始时随口吟出一副一联:“台中元宵看灯火,亚大今日说君子。”
我对听众解释这副对联的构成:“台中”正好对得上“亚大”,因为一“中”一“大”是对隅之词;“元宵”与“今日”也对得上;唯一对不上的是“灯火”和“君子”,但也能对,因为君子是人间的灯火。
我这么一解释,立即引来全场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