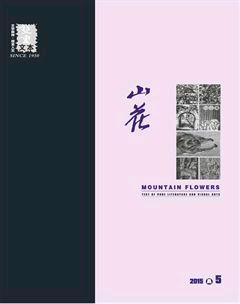文学中的伦理与人性
贺仲明
一、伦理与人性:文学的两难
人性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文学一个永恒的母题。说来也可以理解,文学的起源与宗教本就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就是源于巫(宗教),是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因此,文学需要分担宗教一定的职责,也就是说要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早期的文学往往都带有很强的道德劝诫意味,伦理色彩比较强。
但是,文学的本质是自律的。它最初之脱离宗教就是源于它独立的个性。它的追求方向是个性和自由,是对生命存在的探究和意义的追问。这一点,与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宗教是服从、是崇拜,所以宗教不能问,只能是聆听和遵循。因此,文学的发展道路是对宗教的不断远离,对自我的不断强化。它将“人”作为基点,以对自由的追求反抗所有规范,以对未知世界的不懈探索表现充分的独立和自信[1]。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既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又对文明的约束构成一定的对抗和背离。它除了美和善之外,还具有对真的追求特征。因为文学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探索和追问,就必然会以真为追求目标,探索人性的深邃处,揭示人性的复杂和多元。在一些情况下,真与善和美之间是和谐的,通过真的探索可以更好地实现美和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的关系是矛盾对立的,不同的侧重点致使它们之间存在有必然的裂隙和龃龉。这既构成了文学与社会伦理的冲突,也造就了文学某些内在的冲突。而且,文学作为一种强烈个人化的创造,本身就与伦理的社会化特征形成某种对立。伦理所考虑的主要是群体,需要的是和谐、规范,而这些特征肯定会对文学构成限制,文学追求个人化,只有在个人化的追求中它才有生命力,才能有创造性。因此,文学对伦理的反叛和对抗几乎具有某种天然性。或者说,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伴随着文学发展的全过程。
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人类逐渐走出神学为主导的“中世纪”,进入到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时代,追求人性表现、突破伦理禁区的文学层出不穷。许多优秀的作品打破了传统的伦理禁区,在帮助人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上起到了探索和先锋的作用。在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文学著作,它们在问世的当时受到社会道德颇多谴责,后来却被视为人性解放的先驱,成为著名的文学经典。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文学中很多。如卢梭的《忏悔录》,拜伦、雪莱的诗,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等,都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命运。中国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情形。如《诗经》就曾为秦国国君查禁,元稹的《莺莺传》在当时也颇受非议,柳永的词更曾被作为有伤风化的艳词为文坛所鄙视。包括20世纪前期的郁达夫,当前莫言的某些作品,也受到较多的道德伦理批判。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国文学中的这种情况不是太显著。真正在道德上、伦理上反叛的作品不是没有,但这些作品的意图似乎主要不在揭示人性,而在肉欲或宗教的宣传等,如《金瓶梅》等色情小说。
当然,文学创作不都是以人性探索为指向,也有部分作家作品(从数量来说,这样的作品甚至要远胜于人性探索类作品)更侧重于关注现实,他(它)们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比较和谐,甚至构成了时代伦理中的一部分。它们通过与政治、文化、经济等的联姻,以文学的美的形式,承担着善、爱、恕等伦理责任,化解矛盾,抚慰人心,为社会文化的稳定承担某种伦理的责任。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尤其突出,因为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文学就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道德责任,伦理色彩也更浓郁,所以在中国文学中,“文以载道”的观念一直影响很大,在今天许多人的心中也依然潜藏着。不过中国的情况并非特例,其他国度和时代的情况虽然不尽一致,但作家作品之间存在人性和伦理追求上的差异确实很普遍的。
这样,在文学生态中,除了人性探索与社会伦理尖锐冲突的极端现象,在更普遍情况下,文学中的人性和伦理之间也常有颉颃和矛盾。从作家层面来说,许多作家都有自己比较明确的人性或伦理追求和创作指向——虽然就大部分作家来说,很难截然将其归为单一的某一类型,但总体而言,基本的倾向是存在的。而如果说作家创作是个体行为,创作旨趣上的差异并不会对作家关系和文学环境构成多大影响,那么,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就有所不同。正如有学者所说:“文学描写社会和人生,始终和伦理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也是和道德的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的”,[2]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作为一定价值观念的体现,它们背后蕴含着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文化态度,以及更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它们也必然会包含人性与伦理评判上的分歧和冲突。由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是一种理性主导的行为,价值评判的立场会更明确,因此,它不可避免会直接接入到人性与伦理的矛盾之中,并可能会影响到时代的文学生态。所以,检省文学历史,审视如何看待文学中的伦理与人性追求,以及尽可能公正客观地进行文学史评价,是值得认真探究的事情。
在这里,我想以萧红与张爱玲两位作家为例来谈谈自己的思考。之所以选择她们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们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女作家之列,但创作方向却是比较典型的在伦理和人性领域各执一端,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和深度,而文学史对她们的评价也经历了复杂而巨大的变迁,可以说,在其评价背后正体现了伦理和人性在文学中的价值转换。所以,对她们的比较审视应该具有代表意义。
二、萧红与张爱玲:两个典型的个案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伦理感色彩比较强烈的作家之一。她作品中的伦理层面比较丰富,其中,由于家乡沦陷、异地逃亡的独特经历,她的早期作品较多关注民族国家主题,拥有比较强的民族伦理特征。此后的作品则更多集中在以善和爱为中心的伦理主题,表达出对人(特别是女性、儿童、老人等弱者)的同情和关爱上。而张爱玲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着力于人性揭示的作家。她的作品以人性为中心,结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探寻人性的复杂和阴暗,特别是对知识女性的心理,表现出特别的犀利和深刻。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以及《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等,都以此为特色。
不同的创作追求以及特征上的差异,决定了两位作家在不同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在“文革”结束之前的几十年间,是伦理批评(而且是狭义的、政治化的)占绝对主流的时期,探索人性的作品毫无例外被贬斥和批判,只有遵循狭义伦理的作品才得到承认。因为民族感情是重要的社会伦理,因此,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萧红也受到攻讦,但总体来说,她还是因为爱国主题而得到较多的肯定(除了极端的“文革”时期外)。以《生死场》为代表,萧红被塑造成了一个“爱国女作家”的形象。但张爱玲却远没有这样的幸运。在“人性”被整个社会作为最大污点的时代,也因为与政治、文学观念相关的一些因素,张爱玲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几乎被文学史忽略,甚至被作为“色情作家”和“反动作家”打入另册。
但1980年代中期之后,两人的文学史地位发生了较大迁移。这时候的文学环境有了很大变化。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表现人性的作品受到文学家们的一致推崇,创作界出现了一些大胆探索人性世界的作品,文学史界也开始积极评价那些因为书写人性而被打入冷宫的作品。其中,张爱玲是最为突出的。随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引入中国,他所给予张爱玲和《金锁记》的盛誉获得广泛的认同,特别是对张爱玲人性表现上的成就高度称许,其文学地位显著上升。在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和著述中,张爱玲不但成为现代文学中成就最突出的女作家,甚至也被誉为新文学历史上最卓越的作家之一。与之相应,萧红的文学地位却日见其低。如果说在1990年代之前,爱和善的伦理特点使萧红在“爱国作家”的光环褪下之后,依然凸显了“人道主义作家”的魅力,能够赢得许多文学青年的心,那么,近年来,文学史界对萧红的评价则基本上以否定为主体,不少学者对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进行了质疑。其中比较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其作品与现实太近,太侧重伦理,没有表现出人性之深[3]。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相当的合理性。“文革”前狭隘伦理文学观念是对文学本质的否定,其对人性的完全摒弃更是对文学的极大伤害。在这种背景下,“文革”后文学对人性的关注和认同是一种文学常态的回归,是文学在努力挣脱政治束缚下后艰难的自我独立,对人性书写的重新肯定和积极倡导也是文学发展的自然之举。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事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在文学回归人性的正常潮流中,也存在着需要思考的现象,就是一切以人性为标准,完全排斥伦理于文学的意义,以及忽略人性类文学的某些缺陷。我以为,当前文学界对张爱玲与萧红评价极为显著的冷暖变化,就可以看出某些矫枉过正的趋势。也就是说,她们二人的文学成就固然有别,但并非显著,更重要的是,张爱玲的创作也远非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完美,其缺陷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张爱玲的作品确实有其卓异处。她以犀利深刻见长,透彻地烛照人性的幽深和阴暗,再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细致和少见的冷峻,确实是现代女作家中突出的另类,特别是在普遍关注社会、忽略人性揭示的新文学历史中,她的价值不可忽略。而且,在艺术上,她的作品融现代与传统一炉,在写实、心理和景物描写上都体现了很深的造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张爱玲作品没有缺陷。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两点是明显的:其一,也是最突出的,其作品过于表现人性的阴暗,却缺少温情和温暖。她对人性的批判犀利透辟,却缺乏善的光芒和理想精神,部分作品甚至悖逆于一般的民族国家伦理(当然,这一评价并不适合于张爱玲的所有创作,但其绝大多数作品确是如此,而且,正是这类作品最得到文学史界的认可和好评);其二,其作品题材和思维范围都比较狭窄,人性揭示也多集中在婚姻家庭等情感层面上,没有表现出更博大、丰富的精神内涵。此外,张爱玲的某些艺术表现也存在刻意雕琢的痕迹,没有达到自然圆融的境界。这一切,决定了张爱玲虽然优秀,却难称伟大,没有达到文学的最高境界。
反过来说萧红。作为一个英年早逝、创作时间仅仅10余年的作家,萧红的作品当然有其局限。比如说在艺术的磨合上尚不很充分,有略显青涩处。但她有自己显著的个性特色。其一,萧红的作品以情感的真诚、真切而感人。在其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的心灵投射,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情感关注。它可能不缜密和深邃,却决不乏艺术感染力。与之相应,其艺术表现上不饰雕琢,却能得自然率直之美;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萧红作品浓郁的人性关怀气息,以及善、爱和美的维护精神。萧红作品以人道主义为基调,传达出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强烈质疑和批判,以及对理想世界的期盼和渴慕,蕴含着对平等、互助、温情和友爱的强烈向往和追求。
所以,萧红作品确实有缺陷,但说其“浅”则完全是误解。她的作品内涵单纯但决不浅显,她不着力于人性的复杂和深度,但张扬人性中的善和爱,是与人性深度揭示不一样的文学追求,是对人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将萧红与张爱玲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用各有千秋、各擅胜场来形容。她们应该属于同一文学高度的作家。
三、伦理与人性之间
萧红和张爱玲的创作评价虽然只是个案,但是,在其背后却包含着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内容,也就是说,文学中的伦理和人性冲突,以及由此涉及到的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不只是体现在她们二人,而是更普遍地存在(比较典型如对“十七年文学”和路遥等作家的评价,包括所谓的“《平凡的世界》现象”等),因此,对其涉及的理论问题,很值得深入探索。具体说,有两个问题是最值得思考的:
问题之一,究竟如何判别人性与伦理类文学作品价值之高下,是否揭示人性的作品就一定比表现伦理情感的作品更优秀?
对于两类作品的价值判断,一些人可能会认同前者,但在我看来,答案也许不是简单而是复杂的。首先,文学中人性和伦理表现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可以(或者说应该)共存和互补——也就是说,以揭示人性为中心的作品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伦理,以表现伦理为中心的作品也要深入到人性世界。事实上,很多优秀的作家既致力于社会伦理,又同时揭示了深刻的人性。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优秀的作家作品在这两方面都有兼顾,达到相互的交融。比如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有非常深切的伦理关怀,对民族国家、战争和平以及家庭、宗教等多方面的社会伦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但同时,这些作品也抵达了人性深处,其伦理思想与人性探究很难截然分开;再如美国的福克纳,他的《喧哗与骚动》以展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见长,但同样对种族、家庭等社会伦理有深刻的思考,他的《熊》等作品更对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进行了非常深邃的探究;其次,伦理与人性类作品的价值高下也不能做简单的判别。客观说,人性探索的文学往往走在时代文学的前面,对人的震撼力更大,思想内涵也往往会更深刻。相比之下,侧重伦理的文学作品可能在思想震撼力上稍弱一些,它的价值魅力在思想之余还较多依靠情感的力量,依靠作家在作品中传达出的强烈道德感染力,真诚和向善的精神。两类作品的特点和魅力不一样,但可以相通,也都可以抵达文学的顶峰。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致力于人性揭示,思想内涵确实非常深邃,但优秀的伦理关怀并非不能抵达思想和情感的深处。比如卡夫卡的作品,以深刻的伦理关怀见长,其对人类生存的困境、特别是高度发达的官僚和物质制度下人的困境做了特别深切的揭示,这种关怀的深切以及所蕴含的悲悯和忧患情怀,足以使这些作品超越时代和国度的限制,成为跨越时空的经典,卡夫卡也因此成为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所以,在我们的文学评价中,当然应该重视对人性深度揭示的作品,特别是由于受到过多的限制,人性探索作品严重匮乏的当代中国,但是,却也不可将人性内涵作为评价文学的唯一目标和标准,不能简单将人性标准凌驾于伦理标准之上。
事实上,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既缺乏深度人性书写,同样也匮乏具有优秀伦理关怀的作品。长期以来,过于强烈的政治伦理严重挤压,也深重地伤害了正常的伦理表达,其受伤害的程度较之人性书写虽然略有差别,但实质完全一样。当代学者陆建德借纪念契诃夫表达出这样的期待:“我心里深深地渴望,当代的中国文学中有人能够像契诃夫这样,写出来的绝对不是简单的心灵鸡汤,而是对善良有着一种深深的同情和体验,把充满着矛盾纠结的心情以及他对善良的复杂关怀,通过天才的戏剧家的笔法呈现出来。”[4]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中国文学伦理书写匮乏上的警醒。我们在重视人性探索的同时,同样应该鼓励作家在伦理书写上有大胆的创新和突破,创作出真正有深广伦理关怀的作品。
问题之二,文学的人性和伦理书写是否都有一定的标准需要遵循,以及是否存在各自的限度?
我以为应该有。也就是说,文学可以选择主要探寻人性,也可以选择主要关注社会伦理,但它们都不是完全随意,而是应该遵循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是否很好地遵循了这些原则,直接关系到作家的成就,也关联到对作家创作的评价。所以,对于文学来说,选择表现人性还是伦理也许不是最主要的,最关键是表现得如何,是否遵循了必要的度。
从伦理方面说,文学绝不能将自己的脚步停留在单纯伦理层面,而是要与人性的探索以及独立思考精神结合起来,体现出文学的独特个性。如果放弃自己的独立精神,一味迎合社会的主流伦理和感情,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平庸,从而丧失文学的独立存在价值。这其中,需要特别提出单一政治伦理对文学的危害。不能说政治伦理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它往往裹挟着权力前行,内涵狭隘而具有暴力排他性,因此,对于政治伦理,文学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否则很容易堕入为其奴仆的格局。另外,作为一种理性色彩更强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有着自己更突出的伦理要求。一方面,批评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伦理立场,以独立的价值观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批评,而不是一味地做文学的“表扬家”,无原则地四处说好话,更不应该背弃文学的原则和标准,成为某些权力或金钱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将文学批评误作为社会伦理批评,以道德批判来代替对文学价值的思考。包括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态度,应该是平等的、与人为善的,不能将自己高居为道德法庭的审判者。此外,对文学作品的伦理批评,立场也应该多元和宽容,摒弃狭隘和单一。
同样,文学对人性进行揭示,也需要遵循一定的范围,不能无所节制。文学既要有独立超越世俗伦理的精神、个性,要探寻日常生活背后的灵魂颤栗,但也要顾及文学对社会影响力,对世俗伦理的必要尊重。比如,文学不能违背伦理限制,不能以高高在上的上帝的口吻和方式来窥探人的心灵,为了人性揭示而不择手段——就像新闻有其伦理一样,文学也有自己的伦理。比如有个问题被一些人认为可以彻底测试人性的底线,即“给你多少钱,你会拒绝堕落?”其实,正如有伦理学家已经揭示过的,这个问题貌似深刻,却是个伪问题,因为它缺乏对人的尊重和平等的前提,违背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伦理。再比如,文学对人性的揭示也有底线。人性探险性的、突破式的书写固然有意义,但不是永无止境。比如性,是人性的重要内容,非常值得探索,但是在书写性的时候应该防止过度渲染,不能将性无节制地展示,否则就可能构成对社会伦理的伤害。这中间的界限当然不是一目了然,而是模糊的,关键看它是为了善和美的目的,是美和善的方式,还是为了其他目的,对性进行渲染。这一点,在商业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当下中国尤为重要,稍有不慎,这样的文学作品就可能被商业文化利用,沦落为色情文学或替代品(上世纪末的女性主义文学潮流就是典型例子),对社会伦理造成伤害。
此外,这中间还存在一个如何看待人性的问题,即人性究竟是以生物性为主导还是以文明性为主导?是以回归生物性为最高原则还是应该保持人的文明属性?因为人本身是很复杂的,既有文明滋养下的社会性,也保留一定的动物性。或者说既有积极的、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方面,关键看作家如何看待,从什么角度来看待。一些作品,将回归动物性的人性作为最高指向,将完全生物化的人性展示作为人性揭示的目标,其实不一定合适。自然的生物性和社会的文明性共同构成现代人的属性,二者不可截然分割,也不应该片面渲染某一端。单纯的生物性人或单纯的社会性人都不是正常的存在,过于机械和成熟的文明会对人性构成压抑和窒息,但没有文明的社会也不是正常的人类社会。用一个比喻说,文明是人类的衣裳,穿多了会太热,但完全追求裸体的自由和轻松,也势必影响身心的健康。从根本上说,文学应该表现出人类的理想,它的指向是光明而不是黑暗,是给人信心而不是让人绝望。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以“理想倾向”作为评选的重要要求,是很有道理的。
最后,我想以《红楼梦》与《金瓶梅》的比较来归结我的观点——近年来,不少学者狂热地推崇《金瓶梅》而贬低《红楼梦》,从多个方面指出前者的优越和后者的不足,特别是认为《金瓶梅》揭示的人性更彻底、更深刻,因此价值更高。但我以为,这些学者们忘记了,文学不像外科手术,以将人体解剖得越细致、纤毫毕露为最好,文学不是以人性的深度为唯一标准(事实上,即从人性深度说,也并不能说《红楼梦》逊色于《金瓶梅》),文学还需要爱和温情,需要社会伦理。匮乏了爱和温情,人性揭示再深入也不可能达到文学的高峰——正是在这方面的严重匮乏,《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有着永远也无法跨越的遥远距离。
注 释:
[1] 几年前,我撰写过一篇评论某著名作家创作宗教倾向的文章,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和批评,认为信奉宗教的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也可抵达文学顶峰,文学和宗教之间不构成任何矛盾。我未撰专文回应,但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文学与宗教确有某些相通之处,但差异也很明显,特别是在最终指向上,文学的指向是人,而宗教的指向是神。这种指向决定了文学与宗教之间多方面的分歧。
[2] 聂珍钊《剑桥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从利维斯谈起》,《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
[3] 参见拙文《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构建中的外在因素影响——以丁玲等文学史评价为中心》,《理论学刊》2013年第8期。
[4] 引自何晶《理解契诃夫,就是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文学报》2015年1月29日。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