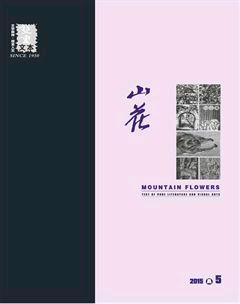驳布鲁姆
朱也旷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就在几年前,他依然笔耕不辍,活跃于美国批评界,不过他的表现却越来越像赞赏家,而非批评家。这一切其实可以从出版于1994年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看出端倪。这部颇为畅销的批评著作在重树经典意识、抨击“憎恨学派”偏见的同时,也在很多地方表现出了布鲁姆个人的偏见。11年后,江宁康先生翻译的《西方正典》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随即成为当年最值得一读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一[1]。
在西方知识界,传统的文学批评已经演变成充斥着主要源自欧洲大陆的各种主义与时髦术语的文化批评,文学经典的地位在各种力量的冲击、消解和颠覆下也变得岌岌可危。为了对抗已经走火入魔的“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倾向,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祭出了文学批评的传统法宝,用略加改进的审美冷兵器来捍卫已成遍体鳞伤状的经典作家的尊严和荣誉。虽然这是一部由大学教授撰写的批评著作,但在很多时候,作者表现出的基于阅读经验的审美洞见使他几乎不像一位学院派批评家。
但是布鲁姆所面临的问题和他自己在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完全一样:人生有涯,书海无边,哪有时间去阅读400位作家的1200本书(这个数字已经被大大压缩了)?时间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个人的审美经验和理论素养如何拥有足够的包容性与辨析力,以统摄和识别从个性到风格如此不同的作家?即便加上一个“西方”的限定语,且在时间上把希腊-罗马文学排除在外,这仍然是一件以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事情。阅读固然需要时间,直面经典的伟大则更需要时间。很多人一辈子都摸不准、悟不透一个作家,布鲁姆先生何以能拥有如此的伟力或神力?
因此偏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很快被发现的偏见是,英语作家占据了过多的位子,相形之下,俄语作家只有一席。算上贝克特,法国人分到了四个席位,但“民主时代”的法国作家如巴尔扎克、波德莱尔、雨果、福楼拜、斯丹达尔、莫伯桑等无一入选26人的核心名单,且在整体上受到轻视。其中,两位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与乔治·艾略特的同时入选,以及弃诗人夏尔·波德莱尔而取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2]的做法,令人尤其感到作者的偏见——也许用偏心更确切。偏见还不止于此。例如,当很多伟大作家只能委曲求全地呆在作为附录的大名单中时,一个与文学没有多少关系的心理学家却堂而皇之地端坐在殿堂上;还有,与诗人受到的青睐相比,以短篇小说建功立业的作家则在整体上被忽视了;还有,20世纪(即布鲁姆所谓的“混乱时代”)的作家显然人数过多——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选择标准也有问题。20世纪是一个文学花样特别多的时期,但不是一个文学特别繁荣的时期,至少比不上19世纪(20世纪的上半叶令人振奋,下半叶尤其是最后25年衰落得厉害)。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入选绝无问题,但是在将美洲大陆的灵魂人物惠特曼选入后,再以“混乱”的名义添上一个次一等的聂鲁达,可能就欠考虑了。坦率地说,把一些优秀的当代作家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格局中,本身就是一种不太严肃的行为。但布鲁姆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达朗贝尔[3]是法国启蒙时期的人物,成就主要在数学和力学上,偶尔搞点哲学、文学什么的,对于这种人们常犯的错误,这位大半个身子在文学门外的业余人士却有着清醒的认识:“文学的殿堂里住满了死去的人,他们生前并不曾住在那儿;殿堂里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活着的人,但一旦他们死去,他们几乎将全部被扫出殿堂。”道理显而易见:经典作品的产生需要时间之筛的过滤,数十年之内的影响如何与自荷马算起的近三千年的历史影响相提并论?即使自但丁算起,这一历史也有七百年之久。据此可以认为,布鲁姆的偏见与武断似乎并不亚于他所抨击的“憎恨学派”(the School of Resentment)。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缺点,就像服用抗生素必然会带来副作用一样,这是从个体阅读经验出发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喜爱的作家的落选而批评布鲁姆,或者对其开列的名单——从核心名单到数百人的大名单——肆无忌惮地嘲笑一番,但是当你独自面对如此绵长而又如此辽阔的文学大河时,顾此失彼、手足无措的窘迫情形通常只会更严重。
决定哪个作家的入选或落选虽然是个问题,却不是可以起支配作用的关键问题。本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了反击“憎恨学派”对经典的消解与颠覆,布鲁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不但努力重树经典作家们的威信,且给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戴上皇冠。此人就是莎士比亚。假如布鲁姆一口咬定莎士比亚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或者至少是中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作家,其他人也不好特别反对(谁让他选的是莎士比亚呢?),尽管这一说法是否有意义值得存疑;但在布鲁姆所捍卫的经典体系中,莎士比亚不仅安享“最伟大”之殊荣,似乎还有成为绝对君主的架势;且这位君主的权力不是继承来的,而是天生的。他就是标准,就是最高裁判,就是自然本身。布鲁姆沿袭蒲伯(A. Pope)、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哈兹里特(W. Hazlitt)、爱默生(R. W. Emerson)以及德国浪漫派自席格勒(A. W. Schlegel)以降的那种热情有余的批评观,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莎老几乎不受他人影响(“只受了一点乔叟的影响”),其他人却无法逃脱他的影响,只能在他老人家的阴影下喘息度日。在布鲁姆如痴如醉的阐述中,文学批评离偶像崇拜只差一小步了。但布鲁姆先生意犹未尽,四年后干脆跨过这最后的一小步。在1998年的专著《莎士比亚:人的发明》[4]的“致读者”中,他更是高调宣称,“莎士比亚崇拜更应该成为,其实也已经是一种世俗宗教”[5]。人是进化来的,是“自然选择”发明的,莎士比亚肯定没有发明人,布鲁姆自然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莎士比亚发明或重新发明了人性、人类情感之类的东西。但这些也不是莎翁首先发明或重新发明的,而是很久以前即已在文学中获得深刻表现的东西。如果一个作家超出了批评的界限,如果一个作家已经等同于自然本身,如果人类生活以及人性的全部奥秘都向一个人敞开了,那么这个人就不是莎士比亚了,他只能是上帝比亚,而布鲁姆先生便是拜莎士比亚教的inventor。在阿尔·戈尔成为global warming的首席宣传员[6]之前,早有一人捷足先登,成为global worshipping的首席宣传员。文学批评变成了偶像崇拜,近些年来,布鲁姆受到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约翰·凯里(John Carey)、奥布莱恩(Jack OBrien)等人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2006年5月,詹姆斯·伍德在《新共和》上感慨,作为批评家的布鲁姆近几年来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约翰·凯里一直是布鲁姆的莎士比亚观的有力批评者,2011年5月15日他在《星期日泰晤士》上批评布鲁姆的新书《影响的解剖》(The Anatomy of Influence),认为布鲁姆通过创造性的误读将自己变成了幻想家,而非批评家[7]。在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的《莎士比亚战争》[8]一书中,则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布鲁姆笔下的福斯塔夫的得失。
历史上恶评莎士比亚者不乏其人,其中以格林、伏尔泰、托尔斯泰、肖伯纳诸公尤为著名,以此来给布鲁姆的偶像崇拜(不提“憎恨学派”的“死白欧男”也罢)降温,也许是方便的手段。然而,对伟大作家的认识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反复。这个现象中外皆然。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是如此;对陶渊明、杜甫、曹雪芹是如此;甚至对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如斯特恩、艾米莉·勃朗特、巴列霍、佩索阿、寒山等,也是如此。对作家固然如此,有时对科学家的认识却也如此,像伽罗瓦、孟德尔的遭遇就是两个典型例子。有关莎士比亚的评论浩如烟海,从中尤其是从早期的评论中挑选负面、刻薄的评论实在是太容易了,似乎也能给人众口铄金的印象,但这样做既不公平,更不明智,绝对无助于认识他的天才。相形之下,倒是德莱顿(J.Dryden)、布里奇斯(R. Bredges)、罗伯逊(J. M. Robertson)、桑塔亚那(G. Santayana)、T.S.艾略特[9]等人相对客观、冷静的评价也许更有价值。顺着这个思路,倒是可以给过于热情的布鲁姆降温的,但这样做仍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如何衡量一个天才人物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这个问题古已有之,因为天才是不能用普通的尺子去度量的,正如大象不能用普通的秤去称量。如果你用菜农、瓜农的秤去称量一头大象,得到的结果就会是无穷大。这正是布鲁姆的问题之所在。如果你换一种思路,用一种新方法,譬如传说中的神童曹冲先生所使用的方法,那么你就可以准确地称量大象的重量了。不但有限的东西可以称量,就连“无穷”本身也可以分出“大小”来,例如数学家康托尔(Georg Cantor)就发明了一种奇妙的方法来区分一些无穷的大小。有人认为,康托尔可能还怀有一种奇怪的信念,对无穷的研究就像是对上帝造物的研究。这其实也不奇怪,只要把无穷置换成莎士比亚,受人嘲笑的康托尔就不再孤单,就会有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不过对于康托尔,这依然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他因此发了疯,死在了精神病院里。
因此,如果我们不过多地纠缠于文学本身,而是跳出文学的圈子,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许会有所裨益。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界的地位相当于物理学和数学界的牛顿、音乐界的贝多芬、生物学界的达尔文、哲学界的康德[10]、经济学界的斯密。人们在评价其他领域的伟大人物时,尽管会给予足够的尊崇,不吝美誉之词,却很少像布鲁姆这样用制造神话、过分突出某个人的方式。例如在提及贝多芬时,通常不会忘记巴赫;在提及康德时,通常不会忘记休谟,也许还有卢梭;在提及斯密时,通常不会忘记马克思、凯恩斯。任何领域里都有极少数最伟大、最突出的人物,牛顿的伟大尤其罕见。哈雷(Edmond Halley)是其同时代人,在天文学、数学等多个领域有建树,亦非凡人,在他眼中,牛顿虽然不是神,却是最接近神的人物。作为物理学家,惟有伽利略、爱因斯坦或可并论;作为数学家,惟有阿基米德、高斯方可比肩;就综合能力和成就而言,惟有希腊化时期的另一位最接近神的人物——叙拉古的阿基米德才是对手。然而诚如牛顿本人所言,如果说他曾经看得远些,是因为他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这个著名的比喻并非牛顿首创,却不妨碍另一位布鲁姆——艾伦·布鲁姆加以引用并发挥[11])。你可以认为这仅仅是谦词,夫子自道,不足为信,但如果你读过凯恩斯为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所写的文章[11],或者多少了解一些牛顿在炼金术上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再设想一下如果他站在拉瓦锡(Lavoisier)、普利斯特列(Priestley)肩上的情形,那么你的看法肯定会有所改变。关于牛顿和阿基米德,似乎有必要多说几句。如果考虑到两位超人的研究起点和时代背景,以及阿基米德在机械发明方面匪夷所思的能力,那么阿基米德就应该排第一位。除了牛顿外,微积分还有另一位独立的发明者,德国的莱布尼兹。但阿基米德的主要工作却是同时代人根本无法企及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阿基米德之于牛顿,犹如苏格拉底之于康德,荷马之于莎士比亚。换言之,苏格拉底的地位应该超过康德,因为他是决定西方哲学嬗变的关键人物;史诗作者的地位应该超过莎士比亚,因为那差不多是决定希腊—罗马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文明)演化的初始条件。借用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术语,他们是思想范式的创立者。
初读此书的人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位充当裁判员的批评家以及一位与文学并无太大关系的半吊子科学家能够进入布鲁姆的文学政治局呢?这个并不奇怪的问题现在有了答案:简言之,为了巩固莎士比亚的地位!没有多少人认为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作为批评家的地位比得上亚里士多德。布鲁姆推崇约翰逊为“各民族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批评家”,但即便是在英语世界里,约翰逊是否能坐上批评家的头号交椅,也不是那么确凿无疑的[13]。本来在有关莎士比亚的章节中陈述一下约翰逊博士的观点和贡献——当然是对莎学的贡献——就可以了,事实上布鲁姆先生也是这么做的,但他似乎惟恐读者不知约翰逊是何人,又为这位批评家另辟专章,并用一定的篇幅介绍起他的性情和喜好来。布鲁姆认为约翰逊比柯尔律治、哈兹里特等更堪称是莎士比亚的最佳阐释者,奇怪的是,他本人却没有从这位最佳阐释者那里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批评的客观性以及直觉与理智的均衡感。
至于弗洛伊德,他的批评家身份更是可疑。要理解在20世纪声名显赫的弗洛伊德为什么在将来不会有什么地位,我们有必要温习一下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时所说的一段话:“在遥远的将来,我会看到许多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此展开。心理学将会拥有全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对于我们逐步获得每一种心理能力都是必需的”[14]。这个新的基础是达尔文主义的核心——自然选择。虽然达尔文的理论是建立在宏观、唯象的观察之上的,奇妙的是,即便到了分子生物学时代,其理论框架依然可以信赖。这也是达尔文作为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其地位迄今未见丝毫动摇的原因。反观弗洛伊德的学说,尽管能够风靡一时,却注定不能成为学术常青树。引用对弗洛伊德的批评是容易的(与引用对弗洛伊德的赞美一样容易)。例如一位作家在给友人的信中这么写道,“初读心理分析著作会使人吃惊地产生满足感,但随后你会感到饥饿依然如故”。这位作家在20世纪是如此有名,连提他的名字也是多此一举。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艾伦·布鲁姆指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寻找创造的原动力时,一笔勾销了拉斐尔与画坛中那些无名之辈的区别。然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弗洛伊德的理论缺乏一个牢固的基础,虽然他所强调的两种本能(生存本能和性本能)与达尔文的两种进化理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表面上十分契合[15]。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眼中,精神分析理论成为伪科学的典型之一,原因也在于此。如果一种理论的内核无法持久,我们怎么期许它的外壳能够垂诸久远呢?
很多人在弗洛伊德偶尔为之的有关文学、艺术和宗教的评论文章里所收获的启发与喜悦要胜于许多职业批评家,但布鲁姆的做法依然不妥。不过就20世纪上半叶弗洛伊德的地位以及在美国的影响而言,他这样做也不稀奇。例如另一位著名的文人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就说过:“弗洛伊德为我们理解艺术所做的努力终究超过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任何一位作家”。韦勒克惊异于20世纪上半叶文学批评的巨大变迁,他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中对于弗洛伊德的论述颇具代表性: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西方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位人物。有关其学说的文献足以设立一座图书馆,在许多语言中有数以千计的条目,特别是德语和英语文献中,他对两者的冲力最大。他的著作涉及诸多学科: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当然还有包括各个分支的精神病学。弗洛伊德对邻近学科的影响也未可估量。他力求纵观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图腾崇拜所反映的模糊起源直至晚近的精神病理学的各种形态。[16]
弗洛伊德对20世纪的诸多学科的确产生过巨大影响,也曾影响过很多作家和艺术家,但作为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外宣扬的那些病例并不像他所吹嘘的那么成功,他的学说依然属于离现代医学与实证科学相距甚远的哲学或心理学范畴。他对人类性本能的强调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洞察力,但即便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完全不必理会诸如“伊德”“力比多”之类并不牢靠的哲学术语,而应该直接追溯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性选择及其有关人类起源的伟大著作那里。与拙于言辞的达尔文相比,这位奥地利人不但文学修养深厚,且写得一手的好文章。这个优点使他尽管在治疗现实中的人物失败了,却在治疗文学人物乃至神话人物那里取得了成功。“我这里的讨论是将弗洛伊德视为一位作家,并将精神分析学视同文学”,布鲁姆直言不讳地解释说。精神分析学是哪门子的文学呢?布鲁姆看重的当然是弗氏运用此法对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尤其是哈姆雷特的心理分析。他还认为:“弗洛伊德的著作描述了人类本性的总体,它远比日薄西山的弗氏疗法更具生命力。”这一回布鲁姆先生大概是押错了宝,稍微了解一点当代生物学的人都知道,对人类天性的总体描述在今天属于一门新兴学科——进化心理学的范畴,弗洛伊德在其中并无地位可言。但弗洛伊德对布鲁姆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尤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他痛批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时髦主义时,自己却为另一种曾经时髦过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所左右,且浑然不觉,于是靡菲斯特递给浮士德的钥匙成了男性生殖器,《浮士德》成了一部“充满性渴望的诗剧”,而歌德与惠特曼则是“二十世纪之前公开谈及自慰的仅有的两位重要诗人”。
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小说三大家是一个堪与希腊悲剧三大家相比肩的独特群体,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长篇小说的两座高峰,契诃夫则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短篇小说写作。要谈论近代小说,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如果为了强调莎士比亚的影响,那么最应该入选的俄国作家应该是陀思托耶夫斯基,而非托尔斯泰。谁都知道,陀思托耶夫斯基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挖掘深度堪与莎士比亚相比,即便认为在某些方面超过莎士比亚亦不为过。还有,如果选择陀思托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能派上用场了,且肯定比用在浮士德身上更恰当。陀氏善于写梦,而弗氏善于释梦,著有一部《梦的解析》,仅此一点,就可以让弗洛伊德在文学政治局的出现更具说服力;还有,陀氏笔下带有病态色彩的人物,以及陀氏本人奇特复杂的性格,如犯罪感、受虐倾向、难以抑制的赌瘾以及时而发作的癫痫病等等,都是弗洛伊德极感兴趣的焦点。可以说在作家当中,很难找到比陀思托耶夫斯基更适合于作为精神分析的对象了。但布鲁姆选择托尔斯泰也有一个重要理由,这个理由是,托尔斯泰公然蔑视莎士比亚,且为此写了一篇《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长文。为了建立一个以莎士比亚为核心的文学专制帝国,布鲁姆需要制服很多人(对于那些根本无法与莎士比亚扯上关系的人,布鲁姆干脆佯装不知),这位来自偏远地区的俄国伯爵尤其需要制服。如果不能制服这个留着大胡子、浑身上下散发着野人气息的俄国巨人,整个帝国就有土崩瓦解的可能。
对托尔斯泰的定位与解读或许是本书最具策略性的部分,这种策略甚至会令人怀疑,是否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政治手段。“19世纪的小说家中无人能比得上狄更斯,即令托尔斯泰也比不上”,布鲁姆如是说。此言在贬低一位俄国巨人的同时,还悄悄地贬低了一位法国巨人:托尔斯泰尚且比不上,况巴尔扎克乎?虽然布鲁姆多次提及托尔斯泰的伟大,但对他的承认总体而言显得颇为勉强;有一次,这种承认是在与次一等的诗人华兹华斯相比时才给予的:“当我步入老年时,这些诗[17]在表现个人苦痛时精心控制的悲情与审美尊严让我比阅读其他任何一首诗都更受感动。它们散发着华兹华斯早期创作的气息,这种气息惟有在托尔斯泰晚期及莎士比亚的某些阶段出现过,即一种普遍的共同哀伤,简单质朴,没有沾染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显然,这话不是为了赞美托尔斯泰,而是为了抬高华兹华斯。我们知道,托尔斯泰的现代史诗《战争与和平》与古代史诗《伊利亚特》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内在互文性(intratextuality),这绝非偶然巧合,传记材料显示,托尔斯泰在动手写作这部史诗之前的两次游历欧洲期间,就已经越来越喜欢荷马了。而荷马之于托尔斯泰的特殊性还为下列事实支持:1875年之后,亦即完成《战争与和平》六年后,托尔斯泰醉心于学习希腊文,为发现一个真正的荷马而激动不已,那“不是茹科夫斯基和沃斯(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一类的翻译家用呕哑啁折、如怨如诉、柔声细语的调门唱出的荷马”,而是另一类诗人,“他咏唱时旁若无人,声若洪钟”[18]。再者,托尔斯泰的小说具有一种天然的质朴性,诚如20世纪的一位莎学学者威尔森·奈特(G.W.Knight)所形容的,自始至终呈现出一种“磐石般的单纯”[19]。这种质朴性在他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三死》《舞会以后》以及篇幅稍长的《霍尔斯托梅尔》《伊凡·伊利奇之死》)中是显见的;其实,即令他的长篇小说,也是质朴与繁复的统一体。正是这个特点,使他在事实上大大远离了复杂多变的莎士比亚,而与希腊艺术建立了一种深刻的乃至血缘上的联系。因此,如果要在托尔斯泰身上发现所谓“影响的焦虑”,显然更应该到西方文学的源头而非莎士比亚那里去寻找。布鲁姆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对它的吹捧不遗余力,目的是为了使人相信,《哈吉·穆拉特》才是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中最伟大的。托尔斯泰写于《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的中短篇小说,几乎篇篇都是杰作,《哈吉·穆拉特》自然也在杰作之列,然而在多数人眼中,它并非巅峰之作:既不是最深刻的作品,也不是构思最奇特的作品[20]。布鲁姆对此心知肚明。他之所以敢于坚持异见[21],是因为他认定“《哈吉·穆拉特》是托尔斯泰作品中最具莎士比亚特色的叙事之作”。一个憎恨莎士比亚的大人物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反驳了他对莎士比亚的批评,还有比这种自打耳光的事更能够说明莎士比亚的绝对伟大及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吗?
除了托尔斯泰外,但丁是另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人物。但丁比莎士比亚早生三个世纪,不可能受后者影响,既然把包括荷马和悲剧作家在内的整个希腊-罗马文学都排除了,为什么惟独要给一位中世纪的诗人保留一席之地呢?为了这个但丁,布鲁姆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让他成为仅次于莎士比亚的核心。这样做看似破坏了体系的完整性,其实不然,因为事实上这个体系从来就没有完整过:除了泛泛而论外,布鲁姆从来就没有令人信服地指出过,莎士比亚对其身后的二十几位作家有着怎样的具体影响,更谈不上明确的内在互文性。但布鲁姆确有必要为但丁设立专章,不仅仅因为《神曲》十分伟大和独特,在风格上迥然不同于莎士比亚,也不仅仅因为但丁上承古罗马的维吉尔,下启文艺复兴的先驱彼特拉克;更重要而又说不出口的原因或许是,布鲁姆必须和另一个人竞争,此人就是艾略特(T.S.Eliot),一位在布鲁姆之前影响甚大的诗人兼批评家,按照韦勒克(Rene Wellek)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的看法,是20世纪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批评家[22]。布鲁姆不但憎恨文学界大谈主义的后辈,似乎也同样憎恨这位不谈主义的前辈,一有机会就捎带地蔑视他一下。然而我们知道,艾略特对但丁的论述相当有力,堪称一颗强有力的心灵对另一颗更有力的心灵的感悟和探索;非但如此,他还下了一个显然会令布鲁姆不快的著名论断:但丁代表了探索人类情感之高度和深度的极限,莎士比亚代表了探索人类情感之广度的极限,两者的工作同样艰难,因此不存在谁比谁更伟大的问题[23]。而要建立以莎士比亚为核心的经典体系,这个论断就必须被推翻,至少被部分推翻。布鲁姆在但丁身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心血和才力,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强悍的对手站在他面前。当然,读者也得以因此领略其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批评家的风采。
对“混乱时代”的作家难以判断的一个原因是距离过近,时间之筛还未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因此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显得单薄、局促、底气不足和人云亦云是必然的。但对布鲁姆而言,还有一个特殊的障碍即审美包容性问题需要克服。布鲁姆早年是研究英国浪漫派诗人起家的,在我看来,一个喜欢雪莱、济慈的人如果要充分领略20世纪文学的全部妙处,必定要经过一番特殊的内心磨练,在审美上获得质的变化才行(以我个人的经验,一个人可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分别喜欢雪莱和卡夫卡,却不大可能在同一阶段同时喜欢这两个人);说得夸张些,就像孙悟空必须要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上一段时间,才能拥有一双火眼金睛。布鲁姆是否拥有这种火眼金睛呢?好像没有,至少炼得还不够,尽管他的审美视野与研究雪莱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例子不在少数,在此仅举一例。布鲁姆虽然承认卡夫卡在20世纪的经典作家中居中心地位,但对他的论述却十分乏力。《西方正典》成书于1994年,距离最初的卡夫卡热已有半个世纪之久,此时有关卡夫卡的研究已颇具规模,称得上是一种工业。但在这些研究中,胡言乱语的却占了多数,于是如何从沙海中拣出少数的真金就成了问题。对于自己有把握、有心得的作家,个人的审美经验会使研究者的论述清晰有力,信心十足,他的旁征博引也会显得恰如其分,相得益彰;而一旦这个前提或基础不那么牢靠,博学可能就不再是优点了。这正是我们在布鲁姆的卡夫卡评论中所见到的情形。卡夫卡主要的长篇小说均未完成,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是自然的,但如果认为卡夫卡主要是一位格言作家,那就是舍本逐末了——对于大象,如果我们不去赞美它庞大的身躯,那么至少也应该赞美它的长鼻子,而不是附着在鼻腔里的鼻毛。布鲁姆称道卡夫卡的小篇幅作品,但短篇小说《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地洞》《致科学院的报告》等均不入其法眼,实在是一件怪事。布鲁姆认为卡夫卡的短篇“开头的文笔一般都比结尾更细腻”,据此认为他“不是一位纯粹的短篇小说家”,这个判断值得商榷。诚然,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如《判决》《乡村医生》等,结尾部分有些粗糙,你也可以认为那是一种毛病。但对短篇小说而言,是否结尾一定要像开头那样细腻呢?也不尽然。对于像《变形记》《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等作品,结尾部分的速度比开头快,正是卡夫卡叙事能力强大的明证,因为惟有一个速度较快或者具有加速度性质的结尾,才能取得最佳的艺术感染力。
这篇文章也许是以个人的偏见历数布鲁姆的偏见。笔者之所以敢于写这样一篇苛刻的评论,并不是以为自己具备和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对话的资格,而是基于自己的阅读体验以及一个特殊的借口:有时候最渺小的人物也可以觉察到伟大人物的局限性。记得雅斯贝尔斯在撰写《大哲学家》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像爱德华·吉本满怀激情地凭吊由大理石等材料建造的罗马帝国的遗迹一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满怀激情地凭吊了另一种遗迹——由西方主要语种的文字所建造的文学帝国的遗迹。带着对帝国式微的伤感,以及对文化哥特人(“憎恨学派”与大众文化)大举入侵的憎恨,布鲁姆恣肆汪洋、泥沙俱下的理论叙事获得了很好的阅读效果,部分章节,尤其是论述20世纪以前的英语作家的章节(如果你不在乎他们在世界文学中多少被拔高了的地位),将审美直觉、术语创新和理论阐述有机地结合起来,倒也值得人们像对待经典作品那样读上两遍。[24]
注 释:
[1]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本文多处引用了江宁康先生的译文,为行文方便,没有标注具体页码。
[2] 波德莱尔是开现代主义先河的一位关键人物,或如美国诗人温特斯(Yvor Winters)所言,“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所能发现的真正的人文学科领域的两三个主要源头活水之一”。狄金森尽管也是一位先驱者,但无论就历史上的实际影响还是就感受力的敏锐与强度而言,波德莱尔都在狄金森之上。
[3] 歌德认为孟德斯鸠和达朗贝尔均属于文学爱好者。
[4] Bloom, Harold. Shakespeare: The Inven
-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Riverhead, 1998.
[5] 原话是,Bardolatry, the worship of Shakes
-peare, ought to be even more a secular relig-
ion than it already is. 英语里有一个词bardolatry专指“莎士比亚崇拜”。
[6] 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讥讽戈尔语。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与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中落败后,转而投身环保事业,所制作的纪录片《不方便的真相》颇具说服力,且影响广泛,但在科学上也存在不甚严谨的地方。戴森于耄耋之年坚决反对“全球变暖”之说,因而给戈尔馈赠了这么一顶高帽子。不过需要指出的,戴森的观点是与科学界的主流观点相悖的。
[7] 约翰·凯里的原文值得一读:He regards Shakespearian characters as real people, who exist outside the plays. Hamlet, for example, has a will of his own and “rebels against apprenticeship to Shakespeare”. Those who object that Hamlet is just a figment of Shakespeares imagination are quickly dismissed: “I brush aside all academic critics — dryasdusts and moldyfigs.”As real people, the characters are free to become quite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Shakespeare wrote. Blooms Falstaff is “an incessant and powerful thinker”and his Hamlet “knows everything”.Apparently Bloom once wrote a fantasy novel,and in these creative misreadings he becomes a fantasist rather than a critic.
[8] 该书的英文名较长,The Shakespeare Wars:
Clashing Scholars, Public Fiascoes, Palace Coups。
[9] T.S.艾略特为《哈姆雷特》专门写有一篇文章,题目也叫《哈姆雷特》。艾略特认为《哈姆雷特》“远非莎士比亚的杰作,而确确实实是一部艺术上失败了的作品”,原因在于“莎士比亚处理的是一个并非他力所能及的难题”。见《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9-14页。此文的基本观念并非艾略特首创,而是来自J. M. 罗伯逊的见解:在原始的故事素材与莎士比亚在改编过程中赋予的人物性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这一见解其实也非罗伯逊首先提出)。《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难以理解的悲剧,其中有关王子复仇的一再延迟更是令人费解,成为著名的“哈姆雷特之谜”。这个谜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无数的作家、批评家提出过各种解释性或批评性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布鲁姆再次表现出了崇拜者的心态,干脆置之不理,并于2003年出版专著《哈姆雷特:无限之诗》(Hamlet: Poem Unlimited)。
[10] 必须指出的是,在哲学已死的时代,对康德的评价可能会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他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开山大师的地位,也是为一般的哲学史认可的。
[11] 艾伦·布鲁姆有一部名为《巨人与侏儒》的文集。但艾伦对这个比喻做了一定的改动,强调巨人的肩膀不是那么容易站上去的。
[12] 经济学家凯恩斯收藏有大量牛顿的手稿。这些手稿起初不受史家重视,但凯恩斯独具慧眼,对它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据此写成一篇非常有创见的演讲稿。该文遂成为牛顿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参见《牛顿其人》,郝刘祥译,《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1期,99-106页。这个译文要好于收录在凯恩斯文集中的译文。
[13] 在英国文学中,如果要举出三个最伟大的批评家,约翰逊必定在其中。
[14] 参见D. M. 巴斯:《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第二版),熊哲宏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页。这段文字引自《物种起源》1859年第1版,原文如下:In the distant future I see open fields for far more important researches. Psychology will be based on a new foundation, that of the necessary acquirement of each mental power and capacity by gradation. Light will be thrown on the origin of man and his history.另可参见中文版《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555-556页。商务版的这段文字是据《物种起源》1872年第6版译出的:“我看到了将来更加重要得多的广阔研究领域。心理学将稳固地建筑在赫伯特·斯潘塞先生所已良好奠定的基础上,即每一智力和智能都是由级进而必然获得的。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也将由此得到大量说明。”看来达尔文的确是个谦谦君子,他竟然把心理学的这个全新的基础归功于斯宾塞的一篇肤浅的论文,也难怪《物种起源》的第1版现在更多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15] 对精神分析疗效的系统性怀疑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见端倪,但最大的打击来自1950年代中期的一项涉及1269个案例的庞大调查。使其走向日薄西山的不仅是临床应用上的问题,它的一些基本理论也受到了来自实证研究的挑战。
[16]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25页。
[17] 指《康柏兰的老乞丐》《荒屋》与《迈克尔》等诗。
[18] 参见《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郑克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6页。
[19] 参见《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赵少伟译,229页。奈特在文中详细分析了托尔斯泰不喜欢、不理解莎士比亚的原因。
[20] 《伊凡·伊里奇之死》现在是、将来也是托尔斯泰最深刻的中篇小说。对海德格尔感到晦涩难懂的读者,可以把《存在与时间》中有关死亡的章节(“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与向死亡存在”)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对照阅读。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是从哲学家的角度阐述了小说家托尔斯泰已经阐述过的东西。
[21] 这个异见如果始于布鲁姆本人,倒也能够说明他的眼光和胆识。但欧美批评界对《哈吉·穆拉特》的推崇至少可以追溯到流亡到伦敦的俄国学者米尔斯基那里。在出版于1926年的英文著作《俄国文学史》(下册)中,米尔斯基在过于贬低对晚期托尔斯泰具有转折意义的《复活》的同时,高度赞扬了《哈吉·穆拉特》。但米尔斯基未能对《哈吉·穆拉特》在托尔斯泰晚期作品中的位置给予充分理解和讨论。事实上,晚期的托尔斯泰是一个尤为特殊的现象,仅就创造力而言,也许只有晚期的贝多芬才能与之并论。2014年5月24日补注。
[22]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278页。
[23] 在公开的场合,艾略特不仅将但丁与莎士比亚并列,甚至认为他们两人“平分了现代世界,再也没有第三者”(Dante and Shakespeare divide the modern world between them; there is no third)。见《艾略特诗学文集》,97页。对于向来斟字酌句的艾略特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惊人的断语。不过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第十章中,却有这样的一段话:“艾略特更喜欢但丁而不是莎士比亚,因为在他看来,但丁的哲学似乎比莎士比亚的哲学更完善些”。参见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邢培明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28页。
[24] 叔本华有一个见解,任何有价值的书都应该立即通读两遍。参见《叔本华论说文集》,范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