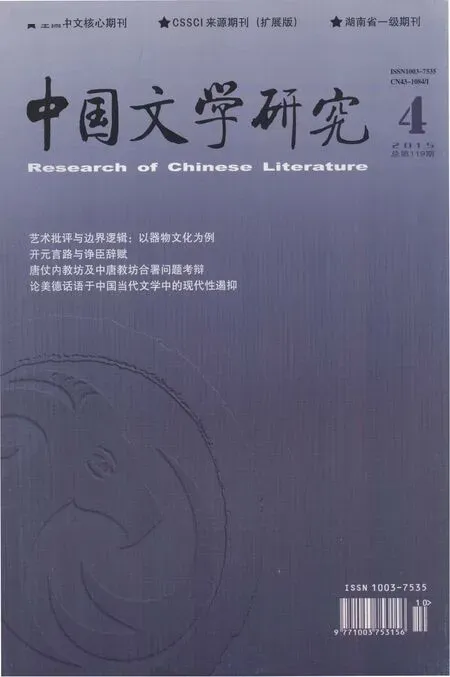文本与接受:论《春秋左传集解》的诗学意义
丁太勰 刘运好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因记载了大量引诗、赋诗的材料而具有特殊的诗学意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下称《集解》)也因阐释引诗、赋诗且渗透了时代与自己的诗学观念而具有特殊的诗学意义。然而,学界研究多瞩目于《左传》诗学而忽略了《集解》。近三十年来,唯有封富《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 年第3 期)一文,然其论述略显粗疏。因此,重新探讨《集解》的诗学意义非常必要。本文在重新考索《左传》用诗的基础上,集中论述《集解》对《诗》文本原始意义、接受生成意义的解读,分析其诗学思想的基本倾向。
一、《诗》学研究的津梁:《左传》引诗、赋诗再考索
《左传》诗学是杜预诗学产生的基础,是论证杜预诗学的逻辑起点。关于《左传》诗学研究的论文积案盈箱,20 世纪前期,顾颉刚、朱自清、夏承焘即发表相关论文;80 年代后,不仅专论文章层出不穷,而且相关专著也列出专章深入探讨,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有详细介绍。无疑,这些研究对于揭示《左传》诗学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本文认为,如果从纯粹诗学的观念上看,《左传》的诗学意义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保留了部分逸诗,具有《诗》学的文献学意义。二是《左传》所载之引诗、赋诗,一部分表达用诗者之志,具有现实语境的意义;另一部分阐释《诗》中之志,具有历史语境的意义。因为《左传》与《诗》产生时间最为接近,故对《诗》中之志的阐释也最为接近《诗》的原始意义,因而成为研究《诗》之津梁之一。
《左传》的诗学文献意义,首先表现在对逸诗的保留上。统计《春秋左传正义》,《左传》引“逸诗”计15 首,因现有诸家专论统计有误,故列表如下:

?
从上表可以看出,《左传》引诗15 首中,10 首有辞无目,5首有目无辞。其中大雅6 篇,小雅4 篇,风5 篇。周诗1 篇,不详分类,或为周颂。另有襄公二十一年引《小雅·采薇》“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二句,杜预注:“案今《小雅》无此全句,唯《采菽》诗云:‘优哉游哉,亦是戾矣。’”或为逸诗,或为异文,疑不能明。勾稽《左传》佚诗,对于考察《诗》之原貌及删诗、编诗都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
赋诗言志是春秋贵族特有的一种话语方式,其形式也有不同。《左传》所涉及的用《诗》,实际上并非止于“赋诗言志”,而主要包含赋诗、引诗两种类型。也有学者另列“歌诗”、“诵诗”,其实与赋诗并无本质区别,唯有歌诗(乐工奏诗)与礼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已,故本文皆归于赋诗一类。
所谓赋诗,即因事用诗。《左传》多以“赋”标志之,内容有诵古,有造篇。孔颖达曰:“郑玄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然则赋有二义,此与闵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皆初造篇也。其余言赋者,则皆诵古诗也。”“诵古”即赋者引用成诗,多为外交、宴饮,揖让之时,赋诗言志,微言相感。“造篇”即赋者自作诗章,多因具体事件,作诗以表达情志。《左传》赋诗共40 场,73 次,去其重复,涉及诗66 首,其中逸诗5 首。其中造篇8 首,分别是《卫风》之《硕人》、《载驰》、《清人》,《小雅》之《常棣》,《秦风》之《黄鸟》,《周颂》之《时迈》、《武》、《赉》、《桓》。虽然造篇所占比例不多,但是可以据此考定作者及诗之本事,故既具有文献意义,亦具有诠释意义。所谓引诗,即援引他人之诗以说理。《左传》多以“曰”标志之,主要表现在叙述性说理和评论性说理之中。举凡评论性说理,都用“君子曰”、“孔子曰”、“子思曰”之类;叙述性说理,则在叙述人物对话中出现,如“卫彪傒曰”、“昭子叹曰”之类。《左传》引诗共122场,155 次,去其重复,涉及诗93 首,其中逸诗10 首。此外,《左传》引诗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暗引《诗》义。如文公七年:“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孔颖达疏:“此引葛藟,《王风·葛藟》之篇也。”这一类引诗题意不显,惟以取某诗篇之意而暗示之,通过联想方得明了其诗篇。这其实也是另一种解《诗》的方式。
赋诗与引诗,虽然从阐释学上说具有相近的意义,但是二者毕竟有所区别。第一,在表达功能上,赋诗以言志为主体,说理熔铸于言志之中;引诗以说理为主体,取经典的话语方式,或证明、或深化所说之理。第二,在表达语境上,赋诗有明确的现实情境,《诗》的意义主要显现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因此赋诗所取大多是《诗》的比喻义和引申义;引诗则是按照说理的具体内容和逻辑次序,《诗》的意义主要显现在经典的历史语境中,因此引诗所取大多是《诗》的原始涵义。第三,在表达方式上,赋诗偏于“主文而谲谏”,常是意在《诗》外;引诗偏于义正而辞严,常是理在《诗》中。第四,在表达场合上,赋诗多发生在重要的外交、礼宴的场合中,承载着更为严肃的政治意义;引诗可以发生重要的场合中,也可以发生私人对话中,主要在于说理的明晰、透彻。第五,在诗学意义上,赋诗属于延伸性诗学阐释,凸显了文学的多义性,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空间;引诗属于文本性诗学阐释,凸显了文学的经典性,对后来的《诗》学研究提供了历史的依据。而无论是赋诗还是引诗,都有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分别,表达者因《诗》而达意,接受者则藉其赋《诗》而观人,这也就为表达与接受的错位提供了可能,这非常有助于深化阐释学的理论研究。
此外,本文虽将“歌诗”归于赋诗一类,但二者毕竟有所区别。《左传》之歌诗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大夫歌诗,如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杜注:“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孔疏:“歌古诗各从其恩好之义类,高厚所歌之诗,独不取恩好之义类,故云齐有二心。”以从歌诗的类型考察赋诗主体的内心世界,是一种《诗》的特殊解读方法。二是乐工奏诗,如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聘于鲁,请观于周乐,乐工为之歌,季札对周诗的长篇评价,最为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对于《周诗》及其音乐的审美认知,尤其具有《诗》的诠释学意义。乐工奏诗与礼的关系密切,孔颖达曰:“若使工人作乐,则有常礼。穆叔所云《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燕礼者,诸侯燕其群臣及燕聘问之宾礼也。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如彼所云,盖尊卑之常礼也。”所奏诗歌,必须遵循森严的等级次序,不可僭越。
综上,《左传》引诗、赋诗既具有诗学文献学意义,也具有诗学阐释学意义;既可以从《诗》的文本上考察其历史语境意义;也可以从接受上考察文学的现实语境意义。这两个方面也恰恰是杜预《集解》阐释《诗》的主要着眼点。
二、历史语境的还原:《集解》对赋《诗》的文本解读
“诗无达诂”,诗歌文本的意义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在接受中呈现出来。“历史的距离”是影响经典解读的重要因素。经典的文本意义产生于特定时代,并且随历史的发展和接受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开放特征。因此,不同时代、不同接受主体,对于同一种文本可能作出截然不同的阐释。但是,努力追寻文本的本来意义,最大限度地追寻读者当下呈现的文本语境与可能存在的历史语境的“视界融合”,亦即追寻读者解读的意义与文本意义的尽可能的叠合,是经典诠释的主要原则。杜预因循古文经学的治经路数,“原始要终”是其基本学理特点,因此其语词训诂、章句辨析以及本事考索,都试图在可能的历史语境的还原中揭示文本的本来意义。
先言训诂语词。语词训诂主要是探求语言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概念意义,可以称之为“历时性意义”。通过对语言在某一历史区间概念意义的阐释,在历史语境中,追寻文本的本意。因此,语言的历时性意义是理解文本意义的连贯古今的信息载体,从而使文本超越时间界限而为后人解读提供了可能。古文经学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最大可能地再现文本的历史语境。《集解》这方面特点非常突出,如僖公九年,“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杜注:“帝,天也。则,法也。言文王暗行自然,合天之法。”“僭,过差也。贼,伤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则可为人法则。”前诗引《大雅·皇矣》,是周人叙述祖先的开国史诗。其“帝”、“则”二词,毛传未单独训释,郑笺则将语词训释融合在章句阐释中。关于“则”之训释,古今并无异议。然而“帝”的训释则微有不同。《字汇》曰:“帝,上帝,天之神也。”故今人高亨解释:“此二句言文王不知不觉地自然遵循上帝的法则。”那么,杜预何以训为“天”?因为远古时上帝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虚拟存在,它是以天的形式显示其力量的存在,因此天的法则也就是上帝的法则。所以杜预补充“帝,天也”的训诂。而高亨的解释则胶着于本意而背离了语言意义的历时性。后诗引《大雅·抑》,告诫周朝贵族修德守礼、谨言慎行。毛传:“僭,差也。”郑笺:“当善慎女之容止,不可过差于威仪。女所行,不不信、不残贼者少矣,其不为人所法。”杜注“僭”取自郑笺,补充“贼”的训释,其句意阐释又紧扣上诗所言之“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而来,心有所忌则言必“过差”,志在克人则威以伤人,惟有不忌不克,则为人效法之榜样。因为《左传》与《诗》处于一个相近的历史区间,杜注不离《左传》的历史语境,又抓住《诗》的整体语境,所以其语词训诂,句意阐释,都能呈现《诗》之语言的历史语境意义。
次言辨析章句。杜注训诂语词,实则为辨析章句服务。而辨析章句也特别凸显《诗》意阐释的历时性特点。如昭公八年,“叔向曰:……《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谓乎!”叔向所引乃《小雅·雨无正》。毛传:“哀贤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可也。可矣,世所谓能言也。巧言从俗,如水转流。”郑笺:“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于舌,其身旋见困病。巧,犹善也。谓以事类风切剀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过,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乱世之言,顺说为上。”《集解》:“不能言,谓不知言理。以僭言见退者,其言非不从舌出,以僭而无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哿,嘉也。巧言如流,谓非正言而顺叙,以听言见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征,自取安逸。师旷此言,缘问流转,终归于谏,故以比巧言如流也。当叔向时,《诗》义如此,故与今说《诗》者小异。”显然,关于此《诗》阐释,毛传郑笺与杜注大相径庭。不仅训诂不同,如“哿”,毛传训“可”,杜注训“嘉”,而且句意阐释也不相同。毛、郑认为,“不能言”者,是“不能以其正道曲从君心”的贤者,“能言”者是“阿谀顺旨,不依正法”的小人。杜预认为,“不能言”者,是“不知言理”、“僭而无信”小人,“故身见困病”而可哀之;“能言”者是“巧为言语”、“其言信而有征”的贤者,故能“自使其身处休美之地”而可嘉之。杜预还特别指明:“叔向时,《诗》义如此,故与今说《诗》者小异。”古今说《诗》的不同,乃因为《诗》意的阐释也同样具有历时性的特点。故孔颖达疏:“云‘叔向时《诗》义如此’者,但叔向此言在孔子删《诗》之前,与删《诗》之后,其义或异。”叔向所说《诗》意是否一定是孔子删诗前的《诗》之原意,难以确论,但是由此却也可说明,杜预辨析章句,能够自觉地在历史语境中探求《诗》的本意。杜预对赋诗“造篇”的研究几乎全是探求《诗》的本意,如《载驰》、《常棣》等。这种研究的本身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再言本事考索。由于文本生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对某种特定历史背景的语言阐释,因此文本的意义并非仅仅是语言的历时性的概念意义,同时又承载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意义。因此考索诗歌本事,一直为诗学家所瞩目。虽然受注释体例及书写条件的限制,《集解》言简意赅,有关《诗》之本事,往往也点明即止。凡毛传郑笺详细明确而无异议,则不另注;若间有争议,疑不能明,则说明之。如宣公十二年,“《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杜注:“《汋》,《诗·颂》篇名。铄,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须暗昧者恶积而后取之。《武》,《诗·颂》篇名。烈,业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无疆之业。”汋,毛诗作“酌”。关于此诗本事,毛传:“《酌》,告成《大武》也。”郑笺:“于美乎文王之用师,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养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恶。是周道大兴,而天下归往矣。”毛传以为是告《大武》之成,乃歌武王之事;郑笺则以为是赞美“文王之用师”,二说不同。杜预弃郑笺而取毛传,明确指出,《酌》诗乃赞美武王能遵循天道,纵养纣之暗昧,待其恶行满盈而后诛之以定天下。从后两句“时纯熙矣,是用大介”看,此诗所表达的逻辑次序是:周经过“遵养时晦”,而后“于铄王师”,最终是“时纯熙矣,是用大介”,即既诛殷纣而周道明盛。完成这样的历史转折,显然是武王而非文王。因此,杜预取毛传而弃郑说,是完全准确的。同样,《武》诗亦是奏《大武》之歌,象武王伐纣之事,诗云:“于皇武王,无竞惟烈。”诗意较上诗更为明确,故杜曰“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无疆之业”。通过考索本事,能够从历史语境上解读诗歌,因此所阐释的观点也就大抵切合诗歌原意。
可见,《集解》关于《诗》的研究,无论语词训诂,章句辨析,还是本事考索,虽阐释方法未脱古文经学家的路数,但是阐释内容又常与古文经学家不同。然而,由于杜预解《诗》能从历史语境出发,所以异于古文经学者,也大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后代《诗》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注重语词、章句、本事的历时性与对应性,对于文学创作的词语选择、句意锤炼、本事表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三、现实语境的呈现:《集解》对赋《诗》的接受阐释
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历史语境都具有不可还原性。因为经典文本的解读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空间和阅读主体中展开,所以接受者或研究者在解读时所呈现的文本语境,都带有当下的时效性、强烈的主体性。杜预对《左传》用诗的研究都带有二度阐释的属性:一是用诗者的一度阐释——无论是引诗说理或赋诗言志,所用之《诗》意实际上是用诗者接受生成的意义,而不可能完全是文本的原始涵义。二是杜预的二度阐释——既包括对经典原始涵义的阐释,也包括对用诗者接受生成意义的阐释。而后者则主要着眼于引诗者当下的现实语境。
赋诗言志或者引诗说理常常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也包含着一种独特的隐秘的心理现象:赋诗言志或引诗说理的发生,其深层都包含着用诗者的前心理阐释的过程。因此,用诗所呈现的意义都是用诗者接受生成的意义,亦即由文本原始涵义衍生而来的当下的现实语境意义。这种特殊的文学史现象以及文学批评现象,不仅影响了后代摘句式批评的产生,而且也影响了后代自由引申式批评的产生。杜预对这类用诗的研究,特别注意揭示用诗者当下的现实语境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诗》比兴义的阐发。《诗》之比兴所涉及的诗学本质是象与意的关系问题。杜预不仅揭示“比”的特点,剖析其象中之意,而且汲取郑笺的研究成果,特别注意揭示“兴”中所包含“比”的意义。如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来聘且拜公之辱,告将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杜注:“《摽有梅》,《诗·召南》。摽,落也。梅盛极则落,诗人以兴女色盛则有衰,众士求之,宜及其时。”《摽有梅》是一首情歌。杜预认为,此诗是从女性角度,女色盛则有衰,宜及时而嫁。毛传以为“摽有梅”是兴,郑玄虽也说是兴,但具体阐释却又是比。如首章“摽有梅,其实七兮”,毛传:“兴也。摽,落也。盛极而堕落者,梅也。”郑笺:“兴者,梅实尚余七未落,喻始衰也。”毛传认为是兴而赋,郑笺认为是兴而比。杜预采纳郑笺,凸显了兴中所包含的比之意义。又如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杜注:“《黄鸟》,《诗·秦风》。义取黄鸟止于棘桑,往来得其所,伤三良不然。”意取毛传,又融合了郑笺“兴者,喻臣之事君亦然”的阐释方法及内容。其实,大多数《诗》之起兴多带有比的意味,因为一切物象如果与主体情感没有产生心理上的联系,就不可能转化为诗歌意象。如文公七年,“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廕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杜注:“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荫庥之多。谓诗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孔颖达曰:“《王风·葛藟》之篇也。彼毛传以之为兴,此言君子以为比者,但比之隐者谓之兴,兴之显者谓之比。比之与兴,深浅为异耳。此传近取庇根理浅,故以为比。毛意远取河润义深,故以为兴。由意不同,故比兴异耳。”孔氏取刘勰关于比兴的观点,认为兴与比不可分割。“兴之显者谓之比”,比是兴的表层意;“比之隐者谓之兴”,兴是比的深层意。“传近取庇根理浅”为比,比是诗的局部意;“毛意远取河润义深”为兴,兴是诗的整体意。所以出现“兴”与“比”理解上的差异,乃在于理解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是非常有创新意义的阐释,对于理解杜预对《诗》之比兴的阐释也不无裨益。注意揭示“兴”中含“比”的意味,就使诗歌解读由象而意,渐次展开。
第二,对用诗者当下语境义的补充。举凡以诗言志皆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或断章取义,引申发挥;或言此意彼,联想暗示。若依《诗序》,三百首每篇都有一个集中的主旨。举凡主旨单一,不易产生歧义的作品,杜预先概述《诗》的比喻义或引申义,如上文所引的《摽有梅》、《黄鸟》、《葛藟》等,然后再揭示引诗的当下的语境意义,如《摽有梅》“宣子欲鲁及时共讨郑,取其汲汲相赴”之阐释。然而一首《诗》的主旨往往又是从不同层面表现出来,而不同层面又可以引申出不同的意义阐释。对于这类引诗,《集解》多藉引诗的前后语境,先补充所引《诗》的意义落脚点的诗句,然后阐释其当下的语境意义。如文公四年:“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杜注:“《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晞,干也。言露见日而干,犹诸侯禀天子命而行。”《湛露》出自《小雅》,是一首宴饮之诗。《序》曰:“天子燕诸侯也。”毛传:“露虽湛湛然,见阳则干。”郑笺:“兴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叶低垂。喻诸侯受燕爵,其仪似醉之貌。”杜预解释诗句本意虽取毛传,则阐释的比喻意则与郑笺大异。郑认为以枝叶低垂喻似醉之貌,杜却认为“阳”喻天子,“露”喻诸侯,阳出而露干比喻“诸侯禀天子命而行”,凸显天子令行即止的无上权威。显然,杜预所阐释的并非《诗》之本意,而是用诗者当下的语境意义。因为“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此二乐乃天子宴饮诸侯之歌,文公令乐工奏之,即有僭越君臣伦理之意,故宁武子谓此诗乃“天子当阳,诸侯用命”。杜预特别呈现用诗者所取阳之于露、不可僭越之意而引申发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昭公十六年,分别有两次大型的赋诗活动,最能体现春秋赋诗言志的特点。赋诗者藉赋诗以言志,主持者藉赋诗以观人。赋诗者抓住诗意的某一点,引申发挥,言此而意彼;主持者在赋诗者所取诗篇及诗意中考量赋诗者的道德人品。如襄公二十七年:“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杜注:“《草虫》,《诗·召南》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以赵孟为君子: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序》曰:“《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孔颖达曰:“经言在室则夫唱乃随,既嫁则忧不当礼,皆是以礼自防也。”本是一首爱情之诗,与治国御民毫无关联。赵孟所以认为子展为君子,是因为诗有“我心则降”云云,表现出子展忧心于礼,居高位而降心于民,故可为民之主。显然,杜预阐释着眼于赋诗者当下的语境意义。杜预阐释《左传》用诗,并非专门研究诗学,所以特别注重揭示用诗的现实语境意义,是为了阐明《左传》的意旨。本来,对当下语境意义的阐释,与探求《诗》的原始涵义也并无必然联系,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史现象——文学效果与文学接受之间在这里获得了统一。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也应该成为文学史描述的重点。这种文学史现象,清人谭献概括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前有《论语》对诗之“巧笑倩兮”的阐释,后有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说,都是属于这种特殊的文学接受的现象。这也为“诗无达诂”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注脚。
补充说明的是,杜预解诗,实际上还包含着用诗者当下的语境意义和诠释者当下的语境意义的双重性。也就是说,杜预在对用诗者当下语境意义的揭示中又表现了杜预对用诗者接受生成意义的再度诠释。因此,杜预在解读用诗者当下语境意义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投映了西晋时代的《诗》学观念。如上文所引对《大雅·皇矣》“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解读。杜预认为:“言文王暗行自然,合天之法。”而郑笺则曰:“其为人不识古,不知今,顺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诚实,贵性自然。”比较二者的阐释,可以看出,郑玄“顺天之法”,强调文王“贵性自然”的自觉性;杜注虽意取郑笺,但以“暗行自然”突出文王“不识不知”的自然之性,突出“合天之法”的本然情性,显然渗透了玄学的思辨方式。
春秋用诗,或取《诗》比兴义;或取《诗》引申义。前者呈现的是诗之象与意、表层意与深层意之间的关系;后者显现的是《诗》之创作与接受、原始义与衍生义的之间关系,是《诗》在接受、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文学史现象。杜预对前一种语境意义的呈现,深化了文本原始涵义的阐释;对后一种语境意义的呈现,揭示《诗》接受生成意义的特殊性。前者为诗歌文本阐释提供了摹本,后者为研究诗歌接受史提供了范例。
四、情志合一:《集解》的诗学思想倾向
纵观杜预《集解》,“诗以言志”是其一以贯之的诗学思想,“情志合一”则又是其基本思想倾向。这种诗学思想及其倾向,一方面直接受《左传》诗学观念的影响,间接接受汉代诗学观念尤其是《诗序》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自觉带有西晋《诗》学观念的印记。
《左传》所言之“志”涵义相当丰富,除去“记载”一类与情无关的义项外,其中与情感有关的义项约有六种:(1)意愿、遗志。如“盖隐公成父之志,为别立宫也。”(隐公五年)(2)思想、想法。“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襄公二十五年)(3)本性、性情。“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昭公二十五年)(4)希望、期待。“吉过于其志。”杜注:“志,望也。”(哀公十六年)(5)神情,精神。“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昭公九年)(6)心意,神志。“疾不可为也,是谓近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孔颖达疏:“以丧失志意也。”(昭公元年)以上六个义项基本上可以囊括先秦典籍与情相关的“志”的概念意义。由此可见,《左传》之“志”与“情”并无判然界限。故孔颖达曰:“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
然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左传》也特别强调以礼法约束本然性情,如“以制六志”、“使不过节”。第二,《左传》所言之“志”与“礼”又几乎完全叠合在一起,如“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哀公十六年)失礼“则昏”,“失志”亦为昏,故知礼志一也。第三,《左传》所言之“情”与“志”是统一关系,而不是分离关系,如“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节其制而序其情。”(隐公五年)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皆是言志的载体,所谓“序其情”亦即言其志,情志一也。《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表达的情志合一、以礼约情的诗学观念,实际上是对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诗学观念总结。
《集解》数次强调“诗以言志”,然在具体使用情、志概念时,意义又几乎不加分别。如《集解序》“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情”即志;“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志”即情。所以情志合一也就成为杜预诗学的基本思想倾向。但是《集解》与《左传》亦有细微区别。《左传》所言之“志”意义宽泛,几乎可以涵盖一切之“情”;《集解》所言之“情”意义宽泛,几乎可以涵盖一切之“志”。这与陆机“诗缘情”之“情”意义相近,表现出情志说在西晋诗学中的微妙变化。
在《左传》中,不仅诗之“比兴”有两种类型:一是原诗所用之比兴,二是用诗所用之“比兴”,而且“诗言志”也有两种类型:一是作诗者之志,所表达的是《诗》文本的原始意义;二是用诗者之志,所表达的是引《诗》的当下语境意义。杜预情志合一的诗学观也因此而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造篇、议论之用诗——论作诗者之志。造篇乃作者因事而作,表达特定的明确的情感,杜预对这类诗歌主要是阐释其所包含的原始涵义。如闵公二年,“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杜注:“《载驰》,《诗·卫风》也。许穆夫人痛卫之亡,思归唁之不可,故作诗以言志。”《诗序》曰:“《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
许穆夫人因为宗国覆灭而不能救之,思归吊唁其兄而不合礼义,因作《载驰》以抒发这种复杂的情感。杜预所言“诗以言志”即是以诗抒情,乃以揭示作诗者之志为旨归。又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謂乎!”杜注:“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所谓“诗人之作,各以情言”,此之情乃作诗者之情,亦即志。考其诗意必须兼顾作诗者的历史语境和用诗者的当下语境,“不以文害意”是解诗的基本原则,不求“与今说诗者同”是其创新。
第二,赋诗言志之用诗——论用诗者之志。如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杜注曰:“诗以言志。”此所谓“诗以言志”,意义与《载驰》所谓“诗以言志”意义完全不同。此乃赋诗者之志,而非诗人之志。赋诗言志,既是藉诗抒情,也是藉诗说理。所以,志与情在杜注中常常不加分别,如昭公二十年,“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杜注:“齐侯甘于所乐,志于不死,晏子言古,以节其情愿。”享乐现实,期于不死,是齐侯之“志”,而此之志就是指情感、愿望。杜注言“志,望也”,亦即此意。情志合一,杜注又泛谓之“意”。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杜注:“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所谓“因古诗以见意”,也就是赋诗言志的意思。所以杜预所言之志,也包含“意”,如襄公十四年,“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杜注:“穆子赋《匏有苦叶》,意惟取‘深则厉,浅则揭’二句,言遇水深浅,期之必渡。穆子赋此诗,言己志在于必济也。”亦即必渡河而取之。此之“志”即“意”。襄公十五年所引“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杜注:“是后妃之志,以官人为急。”亦同此意。
综上,杜预所言之情即志,志即情,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而且所言之情、志,又包含意、理,且受礼的约束。这种情志合一的诗学思想倾向,既继承了前代的诗学观念,也带有较为显著的时代特点。西晋前期,复古之风甚嚣尘上,于是“诗言志”的诗学观念成为文学批评主流,傅玄《答潘尼诗序》强调“盍各言志”,挚虞《文章流别论》“言其志,谓之诗”,正是这种复古诗学观念的代表。后来,陆机虽从诗歌发生上提出“诗缘情”(《文赋》)的理论,然而在思想表达上仍然强调“作诗以明道述志”(《遂志赋序》)。所以李善以“诗以言志,故曰缘情”阐释陆机“缘情”说。而情志合一也是西晋初期基本的诗学思想倾向,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在表达形式上,以四言为正体,为雅韵;在思想内容上,“以情志为本”,从而成为西晋复古主义诗学观念的代表。“以情志为本”与杜预情志合一的诗学思想倾向是完全一致的。杜预正是强调在“诗以言志”又凸显情志合一的诗学思想倾向上显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审美契合点。
概括地说,杜预从历史语境的角度,解读《诗》文本的原始涵义;从当下语境的角度,解读用诗者的接受生成意义,而且二者互相依存,互相印证,既深化了《诗》的文本阐释,推进了《诗》的研究,也揭示了文学接受的一种特殊现象,为文学接受史研究提供了别一角度。又杜预注《诗》紧扣《左传》,不自觉地采用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使其诗歌阐释,时时突破旧说,自铸新论,尤具有创新意义。其“诗以言志”、“情志合一”的诗学思想及其倾向,虽在理论上创新不足,却也反映汉魏以来诗学主流的诗学思想形态。补充一点是,杜预《集解序》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概括《左传》叙事特点,在审美属性上与《诗》之比兴有密切关系,也特别具有诗学意义。
〔注释〕
①笔者据《春秋左传正义》统计:赋风31 次,涉及诗27 首,逸诗2 首;赋小雅32 次,涉及诗27 首,逸诗2 首;赋大雅8 次,涉及诗7 首,逸诗1 首;赋颂2 次5 首。此未包括季札聘鲁,乐工为之所歌之《诗》。现有著述或论文统计皆有讹误。
②笔者据《春秋左传正义》统计:其中引风诗23 次,20 首;小雅47 次,26 首;大雅,57 次,24 首;颂19 次,13 首。另引逸诗10 次,10 首。现有著述或论文统计皆有讹误。
〔1〕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J〕.湖南大学学报,2007(4).
〔2〕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六臣注.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刊明州本,2008.
〔7〕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中国文学研究的其它文章
- 开元言路与诤臣辞赋——从《贞观政要》看张九龄辞赋的谏诤困境及其书写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