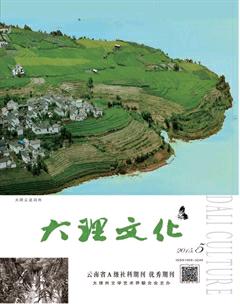往事二题
杨汝骅
那年三月街
1959年,在一年一度的三月街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比平常生活中对节日的期盼更增添了几分莫名的喜悦,平淡的日子里仿佛飘来一道彩虹。因为电影《五朵金花》正在三月街上拍摄。小伙伴们奔走打探,争先恐后用一个个新鲜的细节把听说变得生动真实。那些平日里只存在于电影银幕上的人们,正从银幕上走下来,活生生站在我们面前。他们走向三月街上,蝴蝶泉边,演绎白族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每天,看热闹的和被组织去赶街的白族乡民陆陆续续从四乡八寨涌来,乡村田埂小道上,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一个个行色匆匆朝着县城北门外的三月街街场直奔而去。
正是春末夏初的日子,天气晴朗,日头很毒,外婆领着我在村边收割过的田里翻洋芋。我很想到三月街上凑热闹,但外婆不准。生产队的洋芋地昨天刚刚收完,会有少量漏网的洋芋隐藏在田边地角和松软的土中。趁这个时候去翻拣,或许会拣到一些,过了今天,就会成别人家的菜了。我强忍住心头的欲念,不争气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咕噜噜叫唤了几声。连平时说话要大声吼才听得到的外婆都听见了,她把一个小篮子塞给我:闫王不收饿死鬼,去哪里也先把肚子填饱再说。那年的春天,大锅饭后的饥饿感越来越强烈。灰条、荠菜、黄花花、马齿苋这些山茅野菜都掺进麦麸细糠里成为人们的主食,何况洋芋这种既当菜又当饭百吃不厌的食物就在身边,我没有理由不去。浪漫主义距离我们很遥远,而最现实主义的是找食物填饱肚皮。收获过的地块一片黑土,连洋芋杆都收得干干净净。偶尔在田边地角会有一两个核桃大小的洋芋,它们裹满泥土,混杂在结成小块的土粒中,很难被发现。我跟在外婆身后,眼睛死死盯着一个个可疑的土块,期待着那层浮土扒去,会有一个圆呼呼白嫩嫩带一层薄薄红皮的洋芋出现,到田边小溪中洗净,放进铜壶中煮沸,不用剥皮,轻轻咬一小口,又面又沙又甜的感觉直达心田。可惜早来的遇到不睡的,地块早已在天朦朦亮时就被饥饿的乡亲拉网式的清理过很多遍,很多时候狂喜地奔向目标,扒开浮土,里边只是一块小石头。
日头慢慢指向正午,肚子又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早上出来时吃了一小块麦麸面饼,现在肚里早已空空荡荡,就指望着捡几个洋芋回去当中午饭吃。看着篮子里连篮底都铺不满的几个小洋芋,外婆叹了口气:算了,多就多吃,少就少吃,前头几拨人本事太妤了,连漏沟水都没有留一点。她边说边转身走上田埂,正好和一个从城里返回的男人迎面相遇。这个人三四十岁,穿一件白对襟衣裳,背一顶手编草帽,在田埂上与我们擦肩而过时,他边和外婆打招呼,眼睛却瞄着外婆提篮里地那几个小洋芋。尽管是收过的庄稼地,但毕竟是公家的田,万一遇上个公社干部,没收都是轻的。外婆警惕地把篮子换了下手,用身体档着那个男人的目光,边匆匆走了几步,边回头向我喊道:还不饿噶,走快点。“大妈,”男人喊道:“等一下。”外婆不情愿地回过头,双手紧紧攥着装洋芋的小篮子,生怕被来人抢去似的。“大妈,我跟你商量个事,”男人边说边从身上摸出一张小纸片,跟外婆讲:“我在月街上参加拍电影,结束时人家发了这张饵丝票,端饵丝处人太多,排了个把小时的队还隔着老远老远,心里又记挂着家里生病的媳妇,只有赶紧回去了。为吃这碗饵丝这明天再来一转也划不着,干脆换给你,你把这几个洋芋给我,回家煮给媳妇娃娃吃吃。”外婆听清楚来人的意思,紧张的心情慢慢放松下来,再听着一个大男人讲得这样可怜,眼眶早已湿润,紧走几步来到男人身边,连声说:就几个洋芋嘛,拿去拿去。边说边扯过男人的草帽,把篮子里的洋芋全部倒进草帽里。男人把那张盖有国营大理饮食服务公司红章的饵丝票往我身上一塞,捧起草帽在田埂上头也不回一路小跑,像怕外婆反悔似的。
外婆让我拿上票到月街上去打一回牙祭,具体地点那个男人交待得很明白,不会摸错。而且我去拍电影处凑热闹时,无数次被那个大棚里飘出的肉香味馋得直流口水。别处记不住,吃的地方打死也不会忘记。看着外婆盯着饵丝票那眼馋的目光,我有点不忍心,我跟外婆讲我拿个口缸端回来一起吃。外婆说:从南门到北门大老远的路,再说一碗饵丝又能有多大点。你一个人去吃吧,多少日子没有见着油荤了,我回家可以随便做点吃的。于是我紧紧裤带,咽口唾沫,揣好那张票,进南门过大街出北门,脚杆走酸了才来到拍电影的地方。赶三月街的地方原本在西门外,这里是为拍电影临时搭的街景。估计上午的镜头已经结束,松树枝搭成的牌坊下行人稀少,一溜帆布扯起的大棚外面,几个工作人员正在收拾东西装上马车。饥肠辘辘顾不得东张西望,直奔牌坊右侧的饮食公司摊位。虽然早已过了午饭时分,仍然有一长串人顶着正午的骄阳在摊位前缓缓前行,我赶紧站到队伍后边。前方不远处就是煮饵丝的柜台,饵丝用秤称好,一团团匀称地排列在大簸箕中。一口大锅中汤正在翻滚,浓浓的肉香味直刺鼻孔。眯缝双眼正贪婪地吸吮着这股难得的味道,不知不觉中我已站到柜台前,交上那张被汗水浸湿的饵丝票,身着白围裙的厨师拿在手上仔细端详了好一阵,又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才不情愿地抓起一团饵丝丢向锅中。左手用笊篱在翻滚的大锅中簸了几下,盛到一个土碗里,右手掌一把大勺舀一勺汤浇上去,喉咙里低沉地吼出一声:端稳点,莫烫着!
一碗饵丝几乎是直接倒进肚里去的,三口两口就吃完,甚至没有品出它的味道,只觉得返回时脚没有来时酸了。回到家里外婆问我,有多大的一碗,我说很大,吃得饱饱的。多少年以后看“水浒”,看见梁山好汉喝酒的浅浅的土碗有点似曾相识,才想起那年三月街吃饵丝的碗就是那个样。外婆问盖了什么“帽”?我说我记不清了,但汤很浓很好喝。外婆又问汤里放了猪油还是香油,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浓很油。外婆说:你记着,猪油漂上来的是油星星,放了香油,汤上就是一些小网块了,网块越大越多,证明油放得多。
长大以后,吃饭时我都会盯着汤盆看,漂着的油花是什么形状。但大多数时候油都是浮着一层,没有任何形状。
灶台
从小生长在农村,又出生在那个贫穷困苦的年代,那个越是谗嘴想吃越是吃不上吃不饱的年代,对灶台就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灶房里那个灶台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灶门前度过的。
印象中那个灶台又高又宽,中间那口大锅外边镶着一块硕大的大理石,从大锅里端出来的甑子可以直接放到灶台上,平时炒菜做饭用的盆碗盘碟都可以放在上边。灶门口摆着一个草墩,草墩里靠墙位置放着一个大筐,用来装烧火的燃料。之所以不称它为柴,是因为那时基本没有像样的柴,冬天烧松毛、谷草、包谷芯、包谷杆,夏天烧麦秆、谷糠、草皮、牛粪,这些燃料大多生命力极短,放进灶里一瞬火光后很快熄灭,这就需要有一个人专门在灶门前烧火添柴,而这个人基本上是我。
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那个时候简简单单的一顿饭,为什么会花那么长的时间?上小学前在院子里跟小伙伴玩得正高兴,午后的太阳还有老高,就听见外婆扯着嗓门喊我,莫玩了,烧火做饭了。听见她叫,我就乖乖地站起身,并不是我有多乖,只是因为听外婆的话,我就有好吃的。
用谷草或松毛把火点着,红红的火苗从黢黑的锅底向外扩散。烤粑粑和炒菜适合用不耐烧的草杆,炒菜不用多长时间,几把猛火就成。烤粑粑也需要火苗一会大一会小:一会着一会熄,发面粑粑就在锅底的冷热变化中自然膨胀松软,在谷草的烟火气息中慢慢成熟。如果是煮米饭蒸馒头,就要准备好硬点的柴火,一般是平时舍不得烧的柴疙瘩,或者是耐烧点的包谷芯和松球,烧火时注意力要相当集中,把火烧熄了是要挨骂的。米在锅里正涨着,一熄火就会煮成夹生饭:落过气的馒头也就成了死面疙瘩,把狗都打得死。在粮食极度紧缺的年代,如果烧坏了一锅饭,犯的错几乎是不可原谅的。阴雨绵绵或是冰冻严寒的日子,在灶门口烧火是一种享受。灶洞里红红的火苗烤红了我的脸,双手凑近熊熊燃烧的火焰,全身都感受到来白灶台的温暖。再找几个核桃大的白沙洋芋,用火钳放进锅边的灶灰里,捂上一小会,拿出来轻轻拍打去焦脆的外层,咬一小口,满口甜香。有时用一根竹棍,把剥开的青蚕豆糖葫芦般穿成一串,在松毛火上烧熟,蚕豆的鲜甜和烤出的清香让人垂涎欲滴。当然,大多数时候大锅里煮的好吃的东西,第一口都是我先偷着去尝。
灶门口有一根火通,比大拇指粗一点,二尺多长。它是一根直溜的水冬瓜树枝干,枝干中心有一根细细的松软的树心,用细铁丝轻轻一捅,枝干中心就有了个网孔,把一头用刀修削成扁形,就成了家家户户灶门前必备的物件——火通。每当灶洞里的火熄灭,就要用火通重新吹燃。遇上七八月连天雨,麦杆茅草回潮,火通就要随时使用,煮一顿饭经常吹得头晕目眩,小脸憋得通红。
大姐小学毕业就跟着大人到苍山上砍柴,松树不能砍,只能修点松枝,到杂木林里割点细柴禾。虽然也不经烧,但好歹也是正经柴火,烧起来舒服多了,而且干净卫生。可惜一背柴也烧不了几天,只能留着逢年过节才舍得烧。读小学以后,下午放学早,我就跟伙伴们一起去拾牛粪。严格地说,也不是到处去拾,是去守。生产队的耕牛都散养在各家各户,每天清晨由一位放牛老倌在村头吹响牛角号,各家就把自家养的牛牵到村头由他赶到山坡上去放。下午,牛群从山坡上下来,全部集中到村头的空地上,等待着从田里归来的主人领回家,如同幼儿园的孩子焦急的期盼着自己父母的到来。这个过程很漫长,收工晚的要到太阳落山才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牵上牛踏着暮色返回家中。我们放学的时间与牛群归来的时间基本一致,放下书包,背上背篓粪筐,就与牛群一起在村头会合了。吃饱了的牛慵懒而又百无聊赖地分散在空地上,或卧或站,或磨牙反胄或挑逗追逐。伙伴们站在大青树下的石阶上,目光在每一条牛的尾巴上扫描,只要牛的尾巴一往上翘,就是它要准备排泄的信号了。赶在牛粪从牛的身体分离时用粪筐接住,这是我们练就的本领。一旦让它落到地上,混杂了泥土沙石,再去拾就麻烦了。况且黄牛的牛粪还比较完整,有硬度。水牛则不然,落到地上稀成一片,根本无法拾。比较起来,牛粪是很好的燃料,无烟无味,耐烧。雨水天柴草回潮,但晒干的牛粪不会,冬天在大灶里烧过,火苗燃尽,还可以放在火盆里取暖。
就这样,四季谷物的枝干,松枝刺蓬,树叶草根,包括牛粪,灶房里的灶台混杂了各种各样的气味,这些人间烟火让我痴迷。因为有了它,才有大锅里升腾的热气,才有各种食物经过煎炒熬煮后散发出来的浓香,才有小山村里那一缕缕令人魂牵梦萦的炊烟。以后我用过很多新的燃料:木炭、木柴块、蜂窝煤、液化气、电;使用过各种各样的灶具:鼓风机灶、回风灶、蜂窝炉灶、煤油炉、液化灶、微波炉、电磁炉,每一种新的燃料和厨具让我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失去了那些温馨自然的甜蜜,远离了那些泥土青草豆杆松球的气息。
多想找一个童年时的灶台,搬个草墩坐在灶前,抓一把松毛投进灶里,在熊熊灶火中找回那些遥远年代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