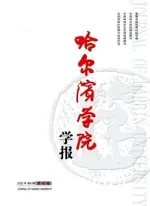魏晋时期武威地区少数民族的迁入及影响
张 露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一、大量少数民族迁居此处的地理因素
早在汉朝以前,包括凉州在内的“河西”主要是以地理名称出现的。如《春秋左传·文公》载:“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1](P595)《孟子·告子章句下》亦有载:“昔者王豹处於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於高唐,而齐右善歌。”[2](P243)可见,先秦时期的“河西”是以水为参照物的,是指某个河流以西的地方。直到汉朝打败匈奴、对黄河以西地区进行管理之后,“河西”才作为一个地名出现在史书中。河西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引起了西汉政府的重视,通过打通河西,不仅可以据险设关、抵御外敌,还可以此作为根据地,以备出击匈奴。其中“武威”就是以汉军在此显示了武功军威而得名。[3]除了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河西地区还具有水资源丰沛、自然条件优越的条件。纵横河西大片地区的祁连山脉,为河西提供了丰沛的水资源,其山区气候冷湿,有利于牧草生长,为畜牧业提供了良好场所。当匈奴失去祁连山、焉支山①时,发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4](P1022)的感叹。可见,河西水源丰沛、土地肥沃,战略地位重要,其在历史上曾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西亚等地方的必经之路,是闻名的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5]
凉州是武威的历史称谓,这里自古便是西北的战略要塞,“其地接四郡地,控三边冲要”,[6]作为关中和内地的屏障,有“河西捍御强敌,惟敦煌、凉州而已”[7]的说法。早在西汉政府对武威进行有效管辖以前,这里长期是西戎②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4]在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以前,武威有休屠和姑臧③两座城池,其中休屠城是当年匈奴休屠王的宫殿所在,而姑臧是现在的武威城址西汉政府在张骞出使西域后,决定开辟河西,以此作为关中的有力屏障,首先采取的措施便是迁入大量汉人以充实当地。④在几代人的耕耘下,出现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⑤的一派繁荣景象。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迅速,中外交通畅通,“使武威和河西其他三郡城不仅是汉王朝在西北边境的重要军事据点和地方行政中心,而且开始在经济上承担起中外贸易中转站的角色”。[8]
二、少数民族迁居武威的目的
在众多外来者中,西域胡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长途跋涉来到武威的主要目的便是经商。武威之所以在那一时期里社会繁荣,经济比较发达,一个重要的基础因素便是其与西域商人频繁的商业往来。商业在武威有着悠久的历史。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内地与边境、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武帝在武威建郡设县,武威成为内地与西域各国商品交流的重要商埠之一。中原丝织品等经武威源源不断运往西域,西域及中亚各国的物产如胡麻、核桃、苜蓿、葡萄、葱等经武威大量传入中原。东汉“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9]可见当时武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货物丰富,商业兴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不休,中原与西域各国的商业发展呈衰退局面。但河西较为安定,割据河西的统治者对于对外商业交易非常重视,加之前凉、后凉、南凉、北凉都先后建都于凉州,武威便成了西北主要的商品集散地。西来使者及商人在河西往来不绝,因交通阻隔,道路不宁,去长安洛阳不成,便将所携带商品运至姑臧(武威旧址)出售,姑臧就成了贸易的终点。英国探险家斯坦因20世纪初曾在敦煌烽火台遗址中发现一件纸质文书,叙述中亚商人去长安未果而在凉州等地作买卖的商业活动。此文书是用粟特文写的,由西晋末一个大商团从姑臧发出的。其中有一段文字记载:
尊贵的大人,安玛塔撒其在酒泉一切顺利,安萨其在姑臧也好。但是大人,自从一粟特人从内地来此,已有三年。
尊贵的大人,自从我们失去了来自内地的支持和帮助,已经过去了三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和毛氈(毛毯)。携带金钱和米酒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受阻。
另外,我已派范拉兹马克去敦煌取三十二个糜香袋,这是为我个人买的。他将把这些麝香袋交给您。⑥
从这可以看出,西晋初年有大批粟特商人来到河西地区,并以姑臧为主要基地,在河西地区和内地进行商业贸易。而且他们已经在此活动了三年。在这期间,有西域商人长期留居武威,甚至安家落户,史称之为“胡商”。西域商人多携药品、毛织品、珠宝等,换取丝絮、布帛铜铁器以及皮革制品之类,武威也随之成为了群富麋集的商品价换市场。除了胡商,还有大批鲜卑、羌、匈奴等少数民族迁入,他们不仅在当地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带来了很多塞外的农禽产品。清代学者张澍的《凉州府志备考》中记录大概有鸟类六种、兽类十六种来自塞外,可以说这些远方而来的少数民族为当时的武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北魏文学家温子升的《凉州乐歌》曰:“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就是对当时武威经济、商业繁荣的描绘。
除了经商,胡人来河西的另一个目的便是传教。魏晋时期的武威不仅是一个经济重镇同时也是一个交流文化、传播各民族教义思想的聚集地。其中在武威产生较重要影响的是火袄教。火袄教又称拜火教,是基督教出现以前中亚最有影响的宗教,约在公元226年前后波斯王国定火袄教为国教,于是在中亚诸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昭武九姓。⑦各国也随之奉行此教。在8世纪中叶穆斯林统治波斯、占有中亚后,大批教徒向东迁徙。新罗僧人慧超适路过中亚,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当时中国新疆的高昌、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也流行该教。
西域胡人来到河西生活经商,能够长期稳定的聚居此地,除了他们积极发展自身实力、拥兵自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教信仰的传播。比如昭武九姓中的安氏与武威有着莫大的渊源,《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载:
武威李氏,本安氏……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难又徙武威。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为萨宝。生兴贵、修仁,至抱玉赐姓李。
《晋书》卷八六张轨附张实传载:
京兆人刘弘者,狭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实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弘谓之日: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
火袄教崇信光明和天神,刘弘燃灯悬镜为光明,枉言天意,“其为火袄教决无疑问”。从这段可以看出,安氏初到武威其目的是“避难”,但在当地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安氏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将带来的宗教传播到汉族中,让其拥有共同信仰,并成为本地区的火袄教首领——萨宝。⑧不仅加强了自身的势力,并且还以这个身份加入到当时的地方政权——张轨阵营中参与政治,这就使得其地位进一步提升,为日后的强大,甚至诛杀张轨、为李唐收回河西地区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迁入的少数民族与当地胡汉的融合
从上文可以看出,不管从西域还是从中亚而来的各少数民族,都对当时的武威在经济、政治、宗教信仰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济方面之前已提到胡商来到姑臧(武威旧址)地区所带来的繁华景象,再加上其积极传播宗教文化,成为当地火袄教首领,不仅使胡人站稳了脚跟,还一点点的积蓄起力量,加入到当地政治活动中,甚至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是,武威的少数民族并非全部来自西域或中亚,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武威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武威的“三种胡”。这个名称较早出现于《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武威三种胡复叛。武威太守毋丘兴告急于金城太守、护羌校尉扶风苏则,则将救之,郡人皆以为贼势方盛,宜须大军。时将军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诏不得西度。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谋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有胁从,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离而归我,我增而彼损矣。既获益众之实,且有倍气之势,率以进讨,破之必矣。若待大军,旷日弥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善恶就合,势难卒离。虽有诏命,违而合权,专之可也。”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
在《三国志》卷16《魏书·苏则传》中提到了武威的“三种胡”之乱:
后[麹]演复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进、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於是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於张掖。演闻之,将步骑三千迎则,辞来助军,而实欲为变。则诱与相见,因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及其支党,众皆降。演军败,华惧,出所执乞降,河西平。乃还金城。进封都亭侯,邑三百户。
陈国灿先生在其《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袄教》中认为,在这里提到的三种胡很有可能就包含武威土著的月氏胡与西域来的康居胡。根据《刘禅诏》所载“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⑨榎一雄先生认为所谓凉州诸国王,大概是指河西地区的月氏、康居等集团。除了月氏胡、康居胡,另一种胡很可能是卢水胡。而“三种胡”在武威与汉族的生活交流中,渐渐改变了他们的游牧生活习惯,不断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慢慢地在武威占据一席之地。所以说,在武威地区民族融合过程中,不仅是胡汉融合,还有各少数民族间的融合。
魏晋时期是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阶段,具体到河西武威地区,在其特定历史环境、经济水平、文化发展的条件下,有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域特点。这既表现在胡汉融合的过程中,也表现在其表现方式上。总的来说,在魏晋时期迁入的各少数民族不管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对武威的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外来者通过传播宗教信仰、积极与汉统治者合作等成功加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并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间差异逐渐减少,实现了汉化。在当时中原大乱,中央政府无力有效控制整个河西地区的背景下,在河西这一特定地理环境下,出现了各民族轮流执掌政权的局面,在这种趋势下,包括武威在内的河西地区就有了境内、境外之分,也就形成了除经济外另一种以地域为纽带的政治联合,当受到外部的压迫时就会自觉地联合在一起,使之联系更加紧密。总之,不管是谁控制武威,他们都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注释:
①亦称燕支山、大黄山、删丹山。《凉州志》云:“焉支山在武威郡西界,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张澍,《凉州府志备考》上册,第54页。
②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氐,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
③盖臧,后人讹传为姑臧。《西河旧事》:“姑臧城,秦月氏戎所据,匈奴谓之盖臧城,语讹为姑臧也。”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十二》:“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
⑤班固,《汉书·地理志》:“地广民稀,水草益畜牧,故凉州之畜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⑥原图版藏于英国图书馆。中文译文参王冀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⑦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康国条言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世为九姓’皆氏昭武。”
⑧火袄教的教长称作萨宝,宋敏求《长安志》记唐长安布政坊“胡袄祠”下注云: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袄神,亦以胡祝充其职。是萨宝为袄祠官。
⑨参见《三国志》卷33,《蜀书·蜀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1]杨伯俊.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刘方元.孟子今译[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3]班固.汉书·地理志:卷28(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胡建芳.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的联系[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10).
[6]李吉甫.凉州大云寺古刹功德碑[A].元和郡县志[M].
[7]袁翻传[A].魏书:卷六九[M].
[8]王乃昂,蔡为民.论丝路重镇凉州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4).
[9]范晔.后汉书·孔奋传[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