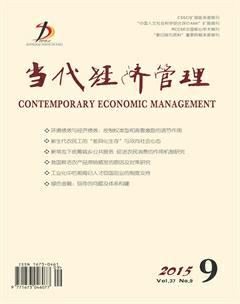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化生存”与双向社会心态
刘博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数年的城-乡务工经历形成了明显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生活模式,“差异化生存”正成为这一群体的显著特征。这种差异化不仅体现在群体外部与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的不同,同时在其群体内部也因职业、性别、技术、社会网等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差异化生存”主要表现为身体化的工作状态、固定化的居住条件与联网化的人际交往。其形成根源是职业的被动选择与网络技术的负作用,运作的线索是身体的实践,塑造的结果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双向社会心态,即产生在群体内部分化基础上的城市融入观与乡土回归观。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社会心态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9-0027-07
当前,我国城市农民工群体正处于稳定的代际交换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城市外来务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如何科学合理、全面有效的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将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与实施规划中的重要议题。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转变身份、融入城市”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工作的主要目的,许多相关调查研究也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意愿上验证了这种观点,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长时间的城乡二元生活模式以及各种非预期性因素开始影响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社会的理解与认同,也同时影响到他们对于自身的定位与未来的选择,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主观心态与社会行为。
一、相关文献与研究问题
自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正式在中央文件提出之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研究基本是从两条主线开展的,其一就是城市社会融入,其二是城乡社会流动。两条线索互有交叉并衍生出很多具体的研究问题支线,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在不同区域、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差异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自学术界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概念以来,经过10余年的时间,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的工作与生活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转变,即社会融入的效果与社会流动的后果开始逐步显现出来。两种结果的出现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形成密不可分,这种体制的形成实际上不仅宣告新老农民工代际交接的完成,也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10年来生活方式塑造的第一阶段完成。这种体制包括“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和“工厂专制政体”两个方面,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等安排交由他们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1]这种再生产模式确保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过去近30年间将全球范围内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过来,推动中国迅速转变为“世界工厂”。
正是在这种体制的影响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被吸引到城市中来,并被规训成为熟练劳动力。一方面,新老农民工的代际转化结束,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开始凸显,群体的身份认同与自我意识越发强烈,对待城市生活的独立性、明确性社会态度开始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融入情况明显表现出代际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经历过前改革时代,他们更加看重积累,将打工所得寄回家乡盖房子,期待以后回乡置业,他们任劳任怨也可以接受吃苦受累是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的说法,但新生代农民工则与父辈不同,他们从小受市场逻辑和文化消费影响,个体意识强烈,打工过程让他们的个体自我认同建立起来,并习惯采取多种的方式来实现自我。[2]一些研究者已经发现,90后农民工普遍性的从事一项工作时间较短,他们的选择背后是制度因素与生活现实的双重影响。[3]如果是按照这种选择,那么农民工的生活、农民工的家庭模式只是他们生命中某一阶段的生活方式,即年轻时到外边挣钱,有了钱就回家乡办工厂、做买卖,这实际上是农民工的一种心理态势,这种心理态势显然受到了地位、身份、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以及落叶归根等传统观念的影响。”[4]同时,这种选择也反映了出了整个农民工群体对自身社会地位底层化的认知,所谓“ 底层化意识”,不仅在于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在于农民工从意识上觉得难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其社会底层地位,城市打工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纯粹的赚钱与长见识。[5]由此,在关于农民工自身社会认同研究的发展趋势上,基于城市生活融入的社会结构路径和自我身份认知的主体建构路径的融合势在必行,这将成为未来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6]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过程,即市民化发展表现出多样性、复杂性与模糊性。一般来说,农民工社会融合包括职业融合、政治融合、民生融合、文化融合、关系融合和身份融合6个方面,这“六个融合”是市民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必经过程。[7]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8]在打工城市受住房制度上的排斥和与内地城市买房政策吸引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的制度动因;乡土情结及家乡亲情的羁绊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的文化动因。[9]在流动的选择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权利诉求明显,个体化的抗争行为增多,一种观点认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个体化是一种政府、市场和全球资本主义联手的结果,这种联手的巨大力量使得他们从原有社区脱域,但又无法重新融入新的社区,只能依赖个体的努力抵御传统现代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后果。[10]还有观点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抉择是与其家庭角色调适相伴随的决策过程,家庭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11]另外,个体化抗争手段的表现则是新工人抗争行动中的“实用主义”团结文化,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即灵活的运用并定义官方意识、审慎的选择斗争策略、借助日常生活资源构造团结形态、积极的推动建立市场议价机制。[12]也有观点认为,许多农民离开了农村进城打工,他们身体和心理在城乡之间以分裂的方式存在着,城市就如同一个和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法律的地方,对于这里,他们既不爱也不恨,既没有尊敬也没有恐惧,不过,一旦他们回到原本的村庄,或者在同乡、亲友圈子里,他们又会变得规规矩矩、淳朴善良,因为熟人社会的乡土世界有他们熟悉的规范与准则。[13]endprint
通过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效果与社会流动后果的关注展现几个特点: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已经至少完成了一个阶段的过程,正逐步向更加深层化与复杂化的阶段发展;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代群特征开始凸显,对城市社会生活的认知也更加多样化;第三,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意识的不断发展正在影响其群体认同的走向。但是,一些新的现象与问题也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开始在这一群体中显现出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分化开始越发的明显,这种分化与3个因素密切相关,即职业的选择、生活方式的塑造与新媒体的应用,分化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化生存”。
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化生存”的基础是群体内部以职业分化和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为区隔的生活方式定型。这种“差异化”不仅体现在传统意义上他们与城市居民的各方面差别,也开始体现在这一群体内部的不同生活方式与生活选择的差别上。最近的一些研究包括媒体宣传已经发现,在对待城市社会融入这一问题上,不同事业目标、生活预期、心理定位的形成预示流动人口劳动力队伍自身已经分化,即分化为准备回乡的农民工和不准备回乡确定要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由此形成了农民工的两种生存策略,即前者对城市社会完全没有认同感,脱离城市主体社会,后者积极沟通准备定居城市社区。事实上,利益主体多元化与利益的自我累积特征决定了即使是同一利益关系的主体之间必然也存在差异性,差异性的扩大既塑造了不同的主体意识和心理状态,也使不同主体具备了不同的获利能力以及行动方式。所以,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差异化生存”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影响这种生活方式的因素及其根源是什么。
在此问题基础上,本文课题组在2013至2015年对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访谈调查与参与观察,调查范围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具体对象包括苏州的汽车生产配件基地,宁波的轮船货运码头,杭州的服装销售公司,上海的建筑工地、电子设备配件制造厂、餐饮娱乐服务行业以及部分流动商贩,访谈对象均为在城市务工至少半年以上、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其中男女比例为8:2。
二、新生代农民工双向社会心态的表现及其根源
通过调查发现,不同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和自我处境的理解存在不同,这与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性质以及不同的家乡来源地有紧密的联系。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差异在3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从工作时间来看,服务业工作更换频率更加明显,平均从业时间不及半年,制造业次之,建筑业时间最久;其次,从工作待遇来看,建筑业收入最高,制造业服务业,最低次之;第三,从工作程度来说,制造业最辛苦,建筑业次之,服务业较低。这其中,影响三大行业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性的因素既有传统性的也有新出现的,比如建筑业、特别是一些特定建筑项目的务工人员一般都具有血缘与亲缘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即是如此,承接具体施工项目的工人多是以家族式的方式进行招工与分工,同族、同乡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也是建筑业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比如服务业,本身的门类多、低技术要求、提成厚的工作性质往往吸引较多初来城市年轻打工者,但是工作时间的不固定以及工作中的身份尊严问题又造成大量从业者迅速转换工作,加之最近两年强力的反腐形势冲击各种餐饮娱乐场所,所以进一步加剧了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同样,制造业近两年的招工困难与频繁工人离职也与整体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紧密相关。而家乡来源地的区别则与不同省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关国家政策支持力度有关,中东部一些省份的外出务工者比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务工者有着更少的家庭负担以及务工顾虑。
职业性质的差异进一步影响并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意愿,在调查中发现,经历了城市打工生活后,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体心态上的“反市民化”与生活方式的“流民化”构成了他们对现实处境与自我定位的两种对应的极端性表现,实际上这两种表现方式源自于他们主观上的生活感受与客观上的身份界定。
(一)个体心态的反市民化
个体心态上的“反市民化”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生活中有几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如对城市文化内涵与价值规范的不了解,对城市居民的不信任,对外来流动人口相关政策的不关心,对市民身份的不认同等。这种多重拒绝融入城市的心态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所出现的分化现象,也反映出他们对城市生活所存在的主观理解差异,同时也包含了对乡土世界的重新认识,所以,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把城市生活作为自己人生的最终归宿,“过客”心理与“回流式”发展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现实的选择。在调查中,从许多年轻打工者那里听到这样的表述“我最终还是要回到家里(农村)的,家里有房还有地”,“在城市待两年,学学东西,长长见识”,“城市什么消费都高,不如家里,父母还等着回去”,“回家去做个小买卖,开个店”,“想回家里,家里现在发展也不错,机会都差不多”,“城市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素质低,我们也不买他们的账”等等。
当然,在调查中也体会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主观意愿上的理解并不意味着他们最终一定会做出与之相匹配的行动,很多时候对于今后职业的表态与规划还带有很多的情绪性和冲动性,而且最终生活流动的选择还取决于他们城市生活时间的长短以及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与特殊事件影响。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农民工城市工作与生活的固定化与单一性会在很大程度上累积与传递这种情绪和心态,如果同时受到特定事件的干扰与影响,如某些排外事件,“反市民化”的个体情绪很可能蔓延成为群体普遍心态。
(二)生活方式的流民化
与心态上的“反市民化”相对立的是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上的“流民化”,即他们宁可选择在城市中频繁的更换工作、维持较低的生活条件,也不愿回到农村从事某类固定性的工作,同时他们也未能参与进城市的主流社会生活之中。通过调查发现,生活方式的“流民化”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工作短期化与职业低端化。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的第1年里频繁的更换工作,一份工作的平均时间不超过3个月,这一特征在餐饮娱乐服务行业尤其明显,同时,他们从事的工作普遍缺少专业技术性要求,多为直接身体劳动性行业。其二,居住地的碎片化与边缘化。从居住方式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依附于打工的工厂与公司,但是因为工作的频繁变动使得他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期的居住,现实生活条件也迫使他们在不断地变换居住点,同时他们居住的地方也经常出现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其三,社会交往的封闭化与内卷化。“流民化”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比较固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圈,一方面,其社交网络主要还是以亲缘、地缘与业缘为联系纽带,具有相对的封闭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们新认识的朋友中也包含城市社会底层年轻人,相同的生活处境与相似的工作经历利于他们形成一致的兴趣爱好、趋同的价值取向以及固定的生活方式。其四,生活预期的迷茫与冷漠。尽管不愿意离开城市,但是对于如何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并没有很明确或者说很正确地认识,一部分人寄希望于“童话式”的社会身份逆转,更多的人则抱着尽量享受乐趣,直到实在混不下去再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调查中发现,在服务行业与制造业,由于工作遭遇的复杂化,极端性心理与冷漠的社会认知态度已经开始逐渐影响这些年轻打工者的价值判断与日常行为。endprint
(三)双向社会心态的内生根源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反市民化”与“流民化”这两个特点有其内在的生成根源与发生路径,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们城市生活所面对的现实情况以及对自我角色身份的认知与定位。这其中有3个因素决定了他们生活的主要特征并促使其群体内部产生了分化,第一,身体性的生存状态构成了城市生活的基础。几乎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首要条件在于他们富于劳动力价值的年轻身体,在健康身体条件的基础上因为各自所拥有的专业技能、关系网络以及实践经验使得不同的打工者进入职业分化的渠道,身体素质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选择的唯一条件,与此对应的是,身体能力以及身体技术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生活时间的长短,因此,“反市民化”心态与“流民化”生活出现的共同背景在于打工者对于自我身体条件与身体能力的现实判断。第二,社会生活范围的固定化与差异化形成了城市生活方式。从农民工进城的流动轨迹来说,初期城市生活的“缘化”(亲缘、地缘、业缘)特点有利于他们尽快熟悉城市生活,并为其在物质条件与心理条件上提供相应的支持与保障,但是,由于缺少合适的社会交往平台与沟通渠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很少有人可以有效地融入所在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甚至很多人不了解、不关心所在地的文化习俗与行为方式,同时工作、居住条件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时间与空间的范围,进一步促使他们逐渐强化本群体内部的价值认同与行动选择,扩大了他们与本地居民的社交距离与心理距离。第三,互联网效果正逐步拉开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的现实距离。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每天都要登陆互联网络进行各种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他们群体沟通、娱乐消费以及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渠道。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网络塑造
随着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广泛普及应用,以微信、微博、QQ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工具正在将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人们囊括进一个统一的互联网世界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和更为普遍的使用率,无论是从事建筑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年轻打工者们,他们在接受与应用新媒体工具的热情与熟练程度上与城市中其他年轻人群体并无差异,值得关注的是,调查发现,新媒体在为他们日常生活提供便利与增添乐趣的同时,相伴而生的负效应也在逐步地发酵并显现出来。
(一)新媒体营造的城市生活景象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从乡村到城市首先伴随着的是一种空间差异上的感受,事实上,这种感受对于任何一个初入特大型城市的个体来说都会带来一种观念上的冲击感与新鲜感。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并不是出生或者长久地生活于他们所工作的城市,所以对于城市当地文化的认同归属缺乏时间的累积效果,同时,职业性质所带来的工作要求一般将他们限制、甚至封闭在了一个固定的生活空间中,塑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他们在工作之余缺少相应的精力与时间去充分体验城市其他部分的生活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新媒体工具快捷、便利的使用特点成为他们了解这个城市、了解这个城市其他群体的主要途径,并在此基础上营造了他们对于城市生活景象的认知。
这种景象的营造与认知具有特殊的效果,对城市社会的想象并不是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那一刻才开始建构,在家乡他们就已经对个人未来出路有了初步的打算,而所要选择的城市在他们的脑海中存在一个自我设定的想象,这种想象的来源可能是多途径的,但势必是与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进入城市之后,新媒体技术就成为他们去检验这个最初设想的主要方式,也成为他们认识自身所处环境的主要工具。然而,新媒体环境下所营造的城市生活景象具有一定的虚幻性与理想化特点,这很容易误导年轻打工者的个人价值观取向,并使得他们对现实生活产生认知上的偏差。
(二)信息无限展示所带来的身份焦虑
新媒体技术平台的身份虚拟性与即时互动性可以在短时间内将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们纳入进同一个话题中,同时,在新媒体所创造的网络社会空间中,信息的制造与传递远远的超过了现实社会的速度。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群体或者个人在这里获取各类信息,同时也传递着各种消息,“封闭性”在互联网社会似乎难有立足之地,再私密的圈子或者话题在新媒体环境中都有传播的契机和渠道。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新媒体提供的平台是一个了解其他群体生活情况并与之交流的有效窗口,但是,也正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中,各个阶层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的无限展示带给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焦虑。这种身份焦虑体现在3个方面:
首先,身份存在感的焦虑。这种焦虑与“他人关注”紧密相连,既指对“他人”(包括同学、同乡、工友、偶像、名人等)的一种持续关注,也指时刻注意“他人”是否对自我的持续关注,这在以微信朋友圈为代表的新媒体工具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日常活动实际上希望的是引起他人的评论与观看,在他人的围观中得到一种内心的成就感与身份的存在感,而经常不自觉的刷新微信,也包含着对错过他人生活重要信息的恐惧,尽管这些信息大部分是无意义的。
其次,身份实现感的焦虑。城市社会中的其他青年群体可以通过多种的日常活动方式来缓解新媒体所带来的身份存在感焦虑,而新生代农民工则缺乏这些方式来缓解这种身份情绪,他们面临自我身份实现的困惑与焦虑,也即是说,阶层之间的生活差距借助网络清晰的展现在他们眼前,目前打工生活的现状使他们清楚的意识到融入城市社会比融入网络社会需要面对更多的现实困难。
最后,身份双重感的焦虑。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双重感的焦虑包括内外两个“双重性”,一个是传统的城乡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双重性,另一个是新媒体工具所造就身份双重性。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实际职业中从事着默默无闻、平淡无奇的工作,但是在新媒体网络中,他们可能是一个意见领袖、一个贴吧版主、一个游戏联盟的盟主等等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这种反差巨大的身份角色往往加剧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与痛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自我认同的混乱。endprint
(三)虚拟与现实的差距催生社交困境
新媒体工具所创造的虚拟生活世界给予了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多次选择个人生活的机会,而且这种选择机会的成本与代价具有较小的付出性,尽管这种选择是一种虚拟的选择,但是与现实生活的反差进一步的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首先,虚拟平台的无限开放性并不能取代现实社会生活带给人们的亲密感与安全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越是在新媒体环境中风光无限的生活越是会更加感觉到现实的落差与内心的紧张,这反而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和自己身份地位相近的群体以获得心理轻松与安全感,而不是去尝试接触城市社会中其他群体。
其次,新媒体工具在带给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广泛的各种信息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失去了甄别与筛选信息的能力,流言与谣言的传播不仅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与信任增加了障碍,也加强了他们各自内心的猜疑感与自我保护意识,群体间的分歧经常会在新媒体平台中因为一些琐事而引发大规模的地域攻击与身份攻击,这加重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疏离与冷漠。
最后,新媒体环境中一些底层暴力事件的渲染与传播会形成逆向的典型引导效果,当新生代农民工在遭遇生活挫折时,他们不仅更愿意借助新媒体来宣泄个人情绪,同时也更容易模仿这些网络中的事件来寻求自我价值的彰显以引发社会关注效应,这不仅极大的影响到他们城市社会的正常融入,也损害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运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的塑造来说,互联网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现代生活条件,丰富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网络上虚假的信息、夸张的报道以及扭曲的价值渲染也极大的影响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知与判断,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环境与社会身份的误解,同时也将这种自我观念以单一化的模式逐渐固定下来,拉大了城市融入的距离,加深了本外群体的矛盾。
四、新生代农民工“差异化生存”的社会效果及应对思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双向社会心态产生于他们差异化生存状态,同时这种差异性的城市生活方式也进一步影响与分化他们的社会流动意愿与预期。可以说,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以及政策的效度来看,虽然经过20余年、两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发展阶段,但是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急需再城镇化。[14]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出现的双向社会心态,甚至是逆向社会流动对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带来了新的挑战。
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差异化生存”产生了3种社会效果,这3种社会效果相伴而生、逐次递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持续放大及发酵的影响。第一,社会心态的双重化。这是在目前实地调查反应最明显的问题,同时也是基于地域性、职业分化、人际交往关系基础而形成的“差异化生存”方式所体现的第一层社会效果,这也是本文所主要探讨的问题所在(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第一层社会效果)。第二,社会群体的分类化。尽管从整个群体特征来说,不同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致性与趋同性,但是,职业类型的差异开始借助时间的累积,通过技术、社会网和亲族关系等因素逐渐改变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阶层流动渠道与空间,这也是该群体内部逐步分化的一种表现,初入城市社会所遭遇的职业被动选择效果开始在不同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来,进而决定他们在城市社会留存时间的长短。第三,社会行动的趋同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伴随个体权利意识觉醒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形塑,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并采取社会行动的动机意愿与实际操作日渐增多,而这种社会行动更多地借助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同时实施空间也更多地集中在网络平台之上,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活动从“线上”到“线下”的转变将是未来他们社会行动主要趋势,三方面因素将影响这一趋势的速度进程,其一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体国家政策实施的效度,其二是城市社会各个阶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认知度与接受度,其三是特定事件的社会舆论宣传影响。
事实上,对于一个进城打工、谋求新的生活机会并希望开拓人生视野的年轻打工者来说,要想真正为城市文化所接纳,必须在改变自身的状况的同时具备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这些生存条件在更多时候应当由国家和所在城市予以必要的支持。首先,他应该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不仅能够支撑其基本的生活要求,例如居住、收入等,还应当能提供其一种相对有尊严的身份认同,从而使他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最后,由于这种社会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他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进而塑造对于社会现实的争取判断。[15]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虽然大部分进城农民都能在城市中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他们的经济收入也有相应的提高,但是职业变动中经济地位提高后,社会地位没有明显变化,与城市居民相比,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处于明显低下的位置[16]。这种低下的地位直接导致他们与当地居民接触、交往困难,而无法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应当说,城市社会具备更多的生存机会以及相应的更为多样的社会阶层上升渠道,这是吸引年轻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最根本因素,同时,城市社会的多元的、主流的文化也是不断影响、改变并塑造青年价值观的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然而,目前摆在新生代农民工面前的却是一方面阶层固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上向渠道封闭,与城市其他群体社会交往关系的冷漠与隔阂;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越发地与城市原有贫民阶层相一致,并且互相交织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城市生活中部分亚文化模式在青年人群体内开始无差别的传染与模仿,并直接作用于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观念理解上,扭曲生活预期,对自我定位产生误识。
因此,在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差异化生存”所造成的双向社会心态现象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形成多角度、全方位具有积极导向意义的宣传氛围。一方面在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培育与理想信念的塑造上强化与拓展传播的力度与广度,充分发挥新老各种媒介的功能,尤其重视互联网的宣传效果,营造正向的、积极的舆论环境,在充分尊重各个群体发言权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共识;另一方面,更为广泛地报道与宣传农民工本群体的日常事件与生活经历,注重正面人物和典型事例的宣传,从贴合他们实际生活体验的角度去关怀、帮助他们,推动他们自觉地将个体身份与市民身份所具有的责任匹配起来,为他们提供更多有意义信息的同时也让城市社会其他群体更多地了解他们。endprint
其次,建立具有针对性与人性化的社会流动机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方面,需要社会组织的引导和帮助,社会组织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依靠,应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中建立健全正式组织。[17]城市社会应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更加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并提供相应的职业培训,对不同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应当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更具人性化的工作与生活保障条件,同时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他们的劳动,无论他们最终是回到老家还是选择城市,良性社会流动机制的目的都在于为他们城市生活的每一天提供发挥自身能力与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第三,创造合理、合适、合情的群体交流与沟通平台。现代城市社会应当具有更加包容的文化态度与更为内聚的精神气质,吸纳与融会各种群体在城市共同生活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创建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其他群体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并不是简单地将各类群体的利益与权利进行分界明显的划分,事实上,就某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来说,许多身份不同的群体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的行动也具有共同的理性特征,例如环境保护问题等。因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效的社会融合关键是要为他们和所在地居民的交流提供必要的渠道与平台,在合适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互识与互信,同时注重情感层面的交流,从具体生活方面来加深群体之间的了解,从而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其他居民的熟悉感与亲切感,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参考文献]
[1] 沈原,等.困境与行动——新生代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R].清华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48.
[2]渠敬东.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 [A].柯兰群,李汉林.都市里的村民[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40.
[3] 文军.“被市民化”及其问题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4).
[4]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58.
[5] 王春光.警惕农民工“底层化意识”加剧[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5).
[6] 汪新建,柴民权.从社会建构到主体建构:农民工社会认同的路径转向与融合期待[J].山东社会科学,2014(6).
[7] 杨聪敏.新生代农民工的“六个融合”与市民化发展[J].浙江社会科学,2014(2).
[8] 姚植夫,薛建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4(3).
[9] 聂洪辉,周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动因及评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4(2).
[10] 董敬畏.个体化: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新趋势[J].浙江学刊,2014(4).
[11] 张世勇.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流动:转变的发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4(1).
[12] 汪建华.新工人的生活与抗争政治——基于珠三角集体抗争案例的分析[A].沈原.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C].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3] 杨英新.网络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的现状与问题[J].农业经济,2012(4).
[14] 刘玉侠,高俞奇.外来流动人口的“再城镇化”研究[J].浙江学刊,2014(4).
[15] 王毅杰,童星.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J].社会学研究,2004(2).
[16] 刘林平,外来人群中的关系运用 [J].社会,2001(5).
[17] 胡宝华.组织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2).
The Differential Survival and the Two-way Social Menta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Liu Bo
(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hanghai 200233,China)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have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and "differential survival" is becoming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is group. The differentiation doe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at,externally,there is differences in their living condition between the group and urban residents,but also in that inside of the group,the member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due to the factors of occupation,gender,skill,social networks. The "differential survival" mainly manifests itself in three aspects as physical labor working status,static living condition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ing. It is stemmed from the negative effect caused by passive choice of profess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ies,and the operational clue of it is the labor practice. The result of it is the "two-way menta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immigrant workers,that is,on the basis of internal apart of the group,the view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urban life and the view of returning their home land exist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life style; social mentality
(责任编辑:张积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