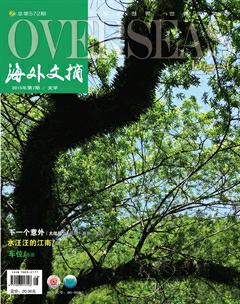水汪汪的江南
朱以撒
又是一年暮春,莺声渐老,柳条不动声色地垂了下来,已经可以拂到行人的脸面了。在江南的小镇上走,雨就沙沙沙地落了下来,很缥缈细腻,像一架细密的花洒,绵长地飘了下来。地气原本就滋润的江南,只不过一小场的雨,就使小镇水汪汪地一片了。白墙遇水,渐渐就润泽中多了一些浅黄的晕化,而灰瓦遇水則一律呈现出深重的黑色,使一座座老式建筑更多了古时气象。烟水中的江南,人在街市上走,心思沉了下来,心弦不那么铮铮作响,生出一堆慷慨。想想当年东晋偏安于建康,渐渐地朝廷官员再也没有刘琨、祖逖、庚亮的壮怀激烈,而清谈、采药、宴饮、品藻等闲情行为多了起来。我想是雨水磨钝了长枪大戟,软化了曾经坚硬无比的脾性,他们融在江南的烟水之中了。现在,每一个来江南的人,抱着闲适之心,品尝江南美食,把玩江南美景,这里精致的生活,或者小巧的情调,会因了一场细雨下来而更为淡素。试想,一个人坐在古旧的楼台上,隔窗看着外边水汽浮沉,真会如当年王羲之所说的———我卒当以乐死。
每一处私家园林都是湿漉漉的。早年的私密性已经不存,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购买门票踏了进去,甚至他们出来之后,还没弄清楚主人是谁。当年的筑园者,不是有权势,就是有银两,弄一块地,花很多时日,细细打磨。这当然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具体的一处园林,与主人的意图———鲜明的、隐晦的,都连在一起,这也使一处园林玄机很多、寓意很多,使导游小姐一路说个不停,把曾经的秘密都钩沉而出。一个园林解密了,那些曾经的玄妙、幽微,是不是都随风随水而走,还是需要自己琢磨,不可止于大众口味的解说。一座园林总是要面对来自各方的追问的,这很像当今有人盖一幢大别墅,毕竟是张扬之举,是无法可藏匿的,而不像花几百万买个手镯可以藏于腕下,袖子放下来遮住了,只有肌肤能够感受到它的圆润。身份往往由某一种与之密切的物体来象征、暗示,园林就是旧时江南最好的物证。主人喜好呼朋唤友于园林内相聚,觞咏兼具,其乐融融。很多用意,都入酒中,不说罢了。赴宴者各有各的想法,也是盛在酒里,更不说出———园林本来就是闲情之地,阴柔四处弥漫。这里比外界潮湿得多,还有些阴郁、幽森,亭台楼阁都在滴水,壁上的书画都起了霉点。草木生长疯狂,尤其是爬藤,卷须上扬,很快就包裹了一个墙面。一户人家居住此间,人气再旺,佣人再多,也经不起阴柔的浸润。园林的后裔都如何了,上哪里去了,无人问津。在一个缺乏阳光的空间里,草木蓄积着水汽,久久不散,连只字片纸都附着了太多的潮润,生出点点滴滴霉花。他们必须走出来,到阳光之下晒晒。世事变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换了主人,换了一种对待园林的态度。如今每一天的园林都是闹哄哄的,如果一个人一天走上几个园林,都会生出许多的模糊,感觉都是一个模样,像不断下来的雨,水汪汪一大片,都是湿淋淋的。
园林里让人产生兴趣的就是盆景,盆景由于病态深重而让人称奇。有的下边薯块凸鼓,而上边的枝条只是简略地三枝五枝。有的枝条九曲回肠,可见被强制扭转过,夺了物性。雨水如此充沛,土壤如此肥沃,生长却如此艰辛,根脉之气、之力终究不能长风般的送到枝叶顶端。如此挣扎多年,一株植物生机减损,再也没有挺拔轩昂的仪态了,暮气上来,形容苍老,已不是自然生长态。人对于病态的欣赏由来已久,反自然生长而行,看它们奇了怪了,走向非常。一些人由此成为专家,把常态引导为病态。一株榕树,本来是有成为参天大树之潜质的,一放到这些人手里,就再也没有长大的可能。病态纳于盆景,显示出惊心动魄的美感,残缺、畸形、不合比例、一反常道。一定有这么一套教材,传授如何反常而行的。这些人深资了,看法就异于常人,到朋友家里,见到一株抽枝展叶的榆树,就认为太缺乏美感了,就想着拿铁线来扭转。园林里集中了许多病态的植物,营造着诡异丑怪之美,许多陶盆附着了厚厚的青苔,捆扎的铁线早已解除,可是这些榕树、榆树、梅树再也没有气力回复初始的模样。当年雕琢它们的工匠们早已故去,也再无人来打理,如今天生天养,无所谓春去冬来,就像一个人老了,对四季根本没有什么感受,日子就是这样,随它去。
老太太一天到晚都在忙着,这个小城有不少像她这样的人,终年与泥土打交道,到老了还是手不离泥。她打开一层塑料布,里边是一坨潮湿的泥,她扯了一块,搓一下,拗成一个弧形:“你看,这泥的韧性多好。”一个这么热爱泥的人,就是不停地捏造、上彩,再捏造,再上彩。捏完了王宝钏、薛平贵,再捏包公和陈世美。日子如风呼呼过去,柜子里摆满了她捏的泥人。古代戏曲中的人物,眼见着就精彩起来了,大红面底的关羽,自额至鼻梁以小曲线修饰,而白底黑纹的张飞,就以笔法流畅的大弧线了。道在民间,三笔两笔,就把民间的侧向抒发得酣畅淋漓。一个人无声地面对一坨泥,需要有适合的态度、技巧,最终成就某一个活灵活现的泥人。我总是觉得这是需要等待的,等待与之相适宜的人来,喜欢泥,也喜欢捏泥,渐渐人泥合一。去年,我见过一尊旧日的泥质陶俑,大嘴龇咧,两眼眯歪,圆肚前撅,臀部后翘,缩颈扭腰,极尽夸张诙谐、幽默滑稽。我惊讶一坨泥土可以捏出如此生动的表情,那么,人和泥在情性上肯定是相通的,泥中有她的体验,她的手指里总是或多或少粘着泥屑,那特有的泥巴气味,是天下最好的味道。
离开时我得到了一组泥人,正气凛然的包公和神情有些躲闪的陈世美,很是精彩。世间有那么多的悲剧、喜剧,都可以成为艺人手中的泥人形象。她们根据自己朴素的理解,确定一个人的身条、神情,包公自然是一脸的正气迸发,而陈世美也不猥琐,一表人才,似乎在申辩着什么。题材如此丰富,泥土如此富足,又有为此而一生不辍的捏泥艺人,那么,素朴的泥化为神奇也就成了必然。我拎着礼品盒走在街上,盒子里是包公和陈世美,他们相互映衬,都成了史上人物,为各类艺术所塑造。和其他陶泥制品不同的是,泥人无需过火,它是慢慢干透的。这样,它会更具有泥的气质,放在手心里沉甸甸的,而拎在指掌中,又分外地小心翼翼,担心一失手,它们又回归泥土了。
紫砂壶在这个雨天里格外地深沉,烧制过的,未曾烧制的,都有一种雨水沁入的凉意。泥不能太干了,又不能太湿了,它们交融得当,在艺人手中,就可以成就一件艺术品。一个宽泛的理解是———一团泥必须不断地捶打,让它成为厚薄均匀的泥片,才能构成一把好壶实现的基础。传说当年顾景舟一口气做了四把壶,烧制后好事者称了称,其中三把不差一钱,而另一把重了一钱,尽管这已经是绝妙之作,顾景舟还是有些懊恼,正是做这把壶的泥片少打了两记。人泥合一,真能运用到这个程度就是大师了,感受着泥性的柔韧,听得到泥片的呼吸,掌握着正确的姿势和手法,讲究着松紧相生的拿捏分寸。这时,泥片就含纳艺人的格调、脾性了,一把壶摆在那里,很像它的主人,气息、格调皆不可掩。把许多壶混在一起,善感的人还是可以凭着器物的形、神,分出张三所制,或者李四所制。一团泥的脾性是缄默的,不会直接地表白,它不动声色地在案板上,形容它们的多是一些很通俗的字眼儿,不需要什么修饰。和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是,它有自己的命运,它遭逢哪一个艺人了,他把它带到哪里去,结局会有许多的不同。
许多人归结为技法,因为过人的技法可以使一坨泥变成一把名壶,只要不与硬物磕碰而瓦解,它的确是可以天长地久的。后人评说一把壶,也大都集中于技法之上。是技法阻止了我们的想象,让我们止步于此。我觉得有些匠气了。顾景舟的名字是这个雨天里人们多次提起的,似乎舟随水往,人们见不到了,才愈发要用话语把他拉回到现实的日子里。如果留心一下,顾氏与其他紫砂匠人的大差异在于他的满腹诗书,他喜欢手不释卷,喜欢朝右边睡,右边点着煤油灯,晚间隔着蚊帐看书,右边的蚊帐渐渐浅黄了、深黄了。壶内功夫好、壶外功夫也好,这个时段,还有谁能和他相比。我见到他的壶已经是烟火遥隔的晚近了,我还是固执地想———这把浑圆的壶,泥色呈暗肝色调,沉郁而从容,含纳着一个怎样的情怀?这样的情怀对后人来说,都被技法渐渐销蚀殆尽了。顾氏做得最久的一把壶花了两年多。费时的确是太长了些,也是最彻底贯彻了一种慢的精神,让自己的感受情致,悄然地沁入其中。此时,是全然没有功利因素的,悠悠然,闲闲然,有感才动手,烟水把慢动作都遮掩起来了。对于每一个反复拿捏泥片的人来说,动作都是一样的,手感都是一样的,重复复重复。只有灵心善感的人,会感到许多幽微之别———如果一个人到了把制壶作为一种乐趣,数年一壶并不是夸张。一个人的精神在这么漫长的过程中优游,像普鲁斯特式的漫长追忆,实在是很可以品咂的,此情闲,此意远,游于心,不知处。江南有着多雨的记录,人在里边捏壶,看着外边潇潇雨下,透明的雨线和阴郁的泥色,都是使人能够心安心定的。门前的香樟树才脱去旧叶,新叶薄而嫩,吹弹即破,有香叶从树干的折缝飘了出来———一团沉实的泥消失了,由实而虚,一个饱和的圆器,藏日月于其中,盛满一个艺人的希望。我喜欢纯手工壶,弯曲指头抚摸壶的内壁,可以微微觉察出凹凸顿挫,它是一个人的手感,手感是有魅力的。一个人不是神,也不是機器,他用手感表现了自己的存在,也把自己和神、和机器作了一个区分。
一些紫砂瓶、壶、笔筒摆了上来,让我在上边题几个字,然后找一个好的刻手,刻后烧制。史上通过合作而成为名壶的当然有,因为壶的信息量大了,后人观之,又生出许多枝条,成为故事流传下来。我只是想试试笔,因为太陌生了,反而生出一些好奇。未曾烧制的紫砂壶只是一个泥胎,润泽得留不住笔,而字迹又小,更需要沉着提笔。如果一个人题写时把一个壶给压塌了,今生恐怕就再也没有缘分了。一个人在陌生材料前调动着自己的经验,也用手感进入这个世界。缓慢地消磨了一个宁静的下午,全不闻外面的风来雨往。一个外乡人在这么一个水淋淋的时光里,被紫砂器皿所包围,紫砂沉稳的色调,使人不至于兴奋,就像雨水的天气里,那些晴明时四处飞舞的尘泥,此时翅膀被水气浸湿,飞不起来了。题完字的这天晚上,我才看到顾景舟的一则往事,七十岁之后,他就不愿意与人合作,不让那些书画家在自己的壶上题词作画了。从乐意到不乐意,个人的清高、孤傲、纯粹这些情绪大大地提升了。有些门类,譬如制壶,还是单干更能见出个人才华。个人有着许多的隐秘,不与外人道,只是会渗透到他的作品里,就像一个壶被盖子捂着,里边会更引起人们的兴致,生出一些想象和联想。如果壶盖丢了,或者打碎了,那就永远敞开着,里边罄露无遗,没有一丝悬念了。每一个人都像一个有盖的壶,里面盛满了丰富,决不轻易倾倒而出。对于如顾氏这般身怀绝技的人,单干是最适宜的。一个人醉心于自己的手下,无需借他人力、借他人色,自由自在而为,以壶说话,真是再好不过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独行的乐趣成为主导,拒绝合作的复杂,走入一个无人之境。
水汪汪的城市里,过日子的速度似乎要慢下许多,使人们在这里的行脚放慢了许多,还有许多其他的动作。江南几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特点,才有与之相适应的戏曲、书画、泥人、紫砂,以及细细地品茶、饮酒,轻声轻气地说话,都携带着慢条斯理的色彩。就像有了相应的土壤,与之适应的植物就齐刷刷地生长起来了。现在看起来,像捏泥人、制壶的手艺,也只能出在这种地方。
在这个雨幕把人的视线遮拦得扑朔迷离的时候,经过一些作坊,还是依稀可以看到那些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动作、姿态,在反复地运用着。一个动作反复的次数多了,就会因为熟练产生了许多的美感,成为这个小城的品牌。可惜的是,如今这些动作产生的商业价值会更让人津津乐道,就如顾景舟留下的壶,不欣赏它古淡的简朴之美,看不到壶里壶外的动人心思,而是关注市场上的一堆数字。这时不能不说———世道变了。
来时是雨,离开时也是雨,在烟水的漫幻中,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人,变得温和而柔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