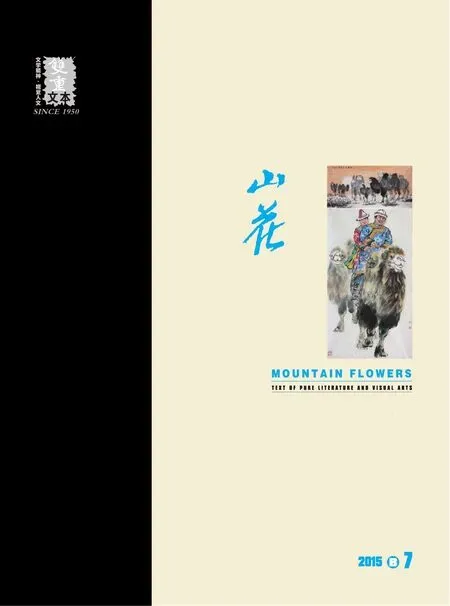硬汉文学中的女性诗学
——试析张爱玲译《老人与海》中的东方女性诗学
胡 妤
硬汉文学中的女性诗学
——试析张爱玲译《老人与海》中的东方女性诗学
胡 妤
理论综述
女性主义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末西方女性为争取平等地位而发动的女性运动。正因为“女性与男性”的社会地位差异与“译者与作者”的文学地位差异之间的相似性,在20世纪后期,女性主义视角被引入翻译研究。如蒋晓华老师指出,女性主义翻译论的核心问题是翻译的性别及性别的翻译。“性别”意识融合于所有文化中,并不单纯指向自然性别,而“更重视的是性别角色、性别的文化规定以及社会是如何被强制性地划分为两性的全体”[1]。因此当翻译研究与性别研究牵手时,翻译的主体及地位便不可避免地被抹上了性别色彩。在传统翻译理念中译作要“忠实”于“原作”,而父系社会中的男女性别概念同样强调女性对男性的“忠诚”,在这两种理念的结合下,原作被置于统治的男性主导地位,而译作则处于屈服于原作的女性地位。因此,翻译被定为女性性别,译者也相应地被定义为“作者的侍女”。所以当女权主义轰轰烈烈地展开时,改变译者和译作低人一等的“女性”地位便成为翻译界女权主义者的首要任务。要改变译者及译作的女性地位,就要改变二元论观照下原作不可动摇的终极地位,因此女性主义强调译者在自然性别上的差异必然导致相应的“社会性别”的差异,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原文不同甚至迥异的阐释,即译者主体性在性别上的体现。女性主义以此为着力点以推翻原作主导的、不可动摇的男性地位。为了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的目的”[2],女性主义译者往往采取“增补”、“加写前言”及“脚注”和“劫持”手法,刻意追求翻译中源于性别的差异并改变翻译本身的“女性性别”。
然而张爱玲的女性诗学观却区别于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具有典型的东方主义温和色彩。张爱玲自小接受了古典文化的熏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对于这样一位有着敏锐眼光的现代知识女性有着巨大的触动,她看到了女性身上背负的封建枷锁,也看到了女性的奴性心理——她们身为男性附庸却又无力或是无心挣脱。因此张爱玲是一个具有明确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但同时她又是一个不彻底的女性主义者,“她用一种冷静的、超女性的语调坦陈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压抑处境,但并不欲指出明确的出路或给出斗争的途径。”[3]同样的,在她的翻译文字间并不刻意追求女性特质的显达,却影影绰绰地闪现着她的女性身影。
张爱玲与海明威
张爱玲译《老人与海》可谓是一次硬汉风格与女性诗学的奇异融合。海明威的作品主题一贯是对以男性为代表的人类的勇气的讴歌,由于他本人一生命运多舛,所以他认为人生中最值得讴歌的便是无畏艰难的勇气。无论遇到怎样的险境、经历怎样的煎熬,他笔下的男主人公们都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反观张爱玲,她的小说脱不开爱情、婚姻和两性关系,她笔下的主角多是压抑、无助的女性,渴望着这苍凉社会中一点胭脂红般的爱情,最终却屈服于物欲,扭曲了灵魂。
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碰撞在一起,是互相的毁灭,还是奇异的交融?张爱玲在1955年第三版《老人与海》中译本的序言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是她“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张爱玲对于此书的喜爱溢于言表。究其原因,一方面,海明威平淡的文字下蕴含着饱满的张力,这与张爱玲本人自然流畅却又字里行间暗藏锋芒的文风十分相近;另一方面,《老人与海》中大海的苍茫、人类的孤独与张爱玲身逢乱世的飘零孤寂的心境正好暗合。张爱玲的成长轨迹使她形成了敏感、孤僻、悲观,甚至冷漠的性格,她曾说过:“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4]《老人与海》中勇者的悲壮与生命的苍凉赋予的是悠远的人生启示,怎不让饱尝人世辛酸的张爱玲心生共鸣?
对于张爱玲译《老人与海》,著名文学评论家止庵曾将其形容为如两股洋流的汇合,一刚一柔,相互影响,相互诠释。张爱玲作为一名以敏感、细腻而见长的女性作家来担任《老人与海》的译者,一方面能更细致入微地捕捉到人物情感的波动,另一方面行文遣字中其女性情怀不自觉流露,同其自身文字风格的交织,显现其特有的女性主义诗学。
张译《老人与海》中的女性诗学
张爱玲温和的女性主义诗学不以操控文本、凸显女性声音为主观目的,而是以女性译者的敏锐触角与女性作家的独特语言在译文中自然的展现。下文通过张译本与吴劳、海观两位男性译者的译本进行比对,从情感体验和语言表达两方面来剖析张氏的东方式女性主义诗学。海观的译本是大陆公认的第一个中译本,与张爱玲译本时间间隔最短,历史文化语境相似的前提下更能凸显译者性别因素的差异;而吴劳译文成文于改革开放之后,思潮的自由赋予了译者更多的独立性,译文更能显现译者个人风格,包括性别因素。通过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张爱玲的女性主义诗学在其译作中的映射——相较于西方激进的文本处理方式,她以女性的目光来解构传统男性主义的文本,并通过文字的把玩、句式的调整等比较温和的方式将女性的声音渗透到译文中,实现了硬汉文学与女性诗学的奇异融合。
1.女性情感体验的糅合
女性所独有的敏锐使男性和女性在对同一事物的阐释中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而以细腻、犀利的心理描写见长的张爱玲在翻译过程中更能将女性独有的情感体验糅合于译文中,如原文介绍老人出场时使用了三个“old man”:“He was an old man who fshed alone …the boy's parents had told him that the old man was now defnitely and fnally salao…It made the boysad to see the old man…”。[5]第一次人物出场,张译为“老头子”,是从读者角度出发,看到一位老人出现在眼前,用较随意的口吻引出人物“老头子”;第二次却从男孩父亲的视角使用“老头子”一词,传递了随意而轻蔑的感情色彩;而第三句从男孩视角下看见的老人,却多了一份尊敬,改称“老人”。正是通过前面两个“老头子”来衬托第三个“老人”中孩子对老人的敬重,这也为下文两人之间的交情埋下了伏笔。但海译与吴译中分别作“老头儿”与“老人”,无用语变化。可见张爱玲对原文有更多的情感领悟,凸显了女性的敏感、细腻。
同样的差异在对文中“alone”一词的处理上也得到了体现,海、吴两位都采用了“独自”,但张爱玲却选用了“孤独地”一词,相信以张对英文的造诣不会不知道“alone”与“lonely”的差异, 但正是这别具匠心的曲解使得译文更多了一份苍凉,增补了隐含的情感色彩。此类以女性视角来阐释原文并加以情感增补的例文不胜枚举。
2.女性语言特征的闪现
“女性在语言交际中使用了比男性多得多的描述性词语……会比男性使用更多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词。”[6]张氏译文中的一大特点便是散文体风格的融入,其中运用了大量“的”字结构形容词的串叠。如:“永久的失败的旗帜”、“日炙的有自信心的眼睛”、“小小的悲哀的鸣声”、“野蛮的恶毒的事情”。而相应的海、吴两位译者译文中“的”字结构的连续使用要少得多。
张译本另一用词特色便是女性化叠词的使用,如 “那么你活得长长的,好好当心你自己”,“那些呆木木的大傻瓜”,“来来,……你闻闻看。……好好地吃它们吧……吃吃那鳍鱼。硬硬的,冷的,可爱的。…… ”而另两位男性译者的相应译文中只使用了“闻一闻”这一个叠词。这种AA式叠词充满了女性化的轻柔软糯的口吻,连同在译文中所用到的诸如“掖掖好”、“腻搭搭”之类的吴侬软语,张爱玲通过独特的女性词汇将女性译者的声音融入到了作品之中,悄然实现了“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的目的。
除了独特的女性用词,在句式上女性也更倾向于使用一种试探性的方式,更多使用委婉、征询或疑问的方式。如:
例1 … Make another turn. Just smell them. Aren’t they lovely? …
【张译】 ……这沙丁鱼可爱不可爱?……[7]
【海译】……那些小鱼儿不是很美吗?……[8]
【吴译】 ……它们不是挺鲜美的吗?……[9]
例2 If you love him, it is not a sin to kill him. Or is it more?
【张译】……杀死就不是罪恶。还是更大的罪恶?[7]
【海译】……把他弄死了就不是罪过。不然别的还有什么呢?[8]
【吴译】……杀死他就不是罪过。也许是更大的罪过吧?[9]
例1 原文采用的是反义疑问句,本身表达肯定含义,但张译中却将它处理为更委婉的疑问句,期盼得到肯定的回答。无独有偶,例2中原文虽然是疑问句形式,但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感叹语气,故两位男性译者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反问句的形式,唯独张译保留了疑问形式,并期待回答。
3.张氏女性主义诗学特点
无论措词还是遣句,张爱玲的译文中处处闪动着译者作为女性的身影,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的目的悄然而合,但在采取的策略上却有所差异。她同样采用了“增补”和“加写前言”的手法,但是较少采用激烈的“劫持”手法,更多的是采用隐晦而温和的情感折射及女性化语言特色来彰显女性译者的主体性,在保持对原文的忠实及摆脱“男性”文本控制以改变“翻译女性性别”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点,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温和的女性主义诗学。
相较于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张爱玲的温和女性意识源于特定的东方文化。首先这是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决定的。西方女权主义进入中国后发生了形式与本质上的改变,由女权主义运动转变为妇女解放运动,前者是以女性为主体发起的以改变男女不平等现象为标的的独立的女性维权运动;后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主要追求阶级的平等,而男女平等只是民主思想的一个部分,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相较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要温和得多。其次,张爱玲本人虽然有女性意识的觉悟,但从她的字里行间、她的生活方式依然可以看到她对传统社会的依恋与不舍,加之她对于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淡然,她始终不能将自己融入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之中。这注定了她的女性主义意识是一种东方式的温和的映射,而不是西方式的颠覆性的解构。也因此在译文中其女性译者的声音以温和的融合方式流露于译文的字里行间,而没有采用极端的“劫持”、“增补”等女权主义手法。
结 语
在硬汉风格与女性诗学的融合中,张爱玲的《老人与海》译文点缀着女性特有的词汇及句式,融合在非显性的女性主义“增补”、“加写前言”等手法之中,这样自然温和的女性主义处理既让文章中隐现柔和的女性身影,又无损原文勇者的刚性之美。与西方颠覆式的激烈的女性主义翻译观相比,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温和的女性主义诗学观正体现了东方的哲学观,与东方女性的温婉柔韧相契合,在翻译风格上独树一帜,令人回味。
[1]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176.
[2]蒋晓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7):10-15.
[3]陈吉荣,张小朋.论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J].外国语,2007(6):50-55.
[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12-14.
[5]Ernest Hemingway.The 0ld Man and the Sea[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8:1.
[6]张玲玲.浅论女性语言的风格特点[J].焦作大学学报,2010(3):15-16.
[7]海明威.老人与海[M].张爱玲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8]海明威.老人与海[M].海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9]海明威.老人与海[M].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胡 妤(1979— ),女,浙江海宁人,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