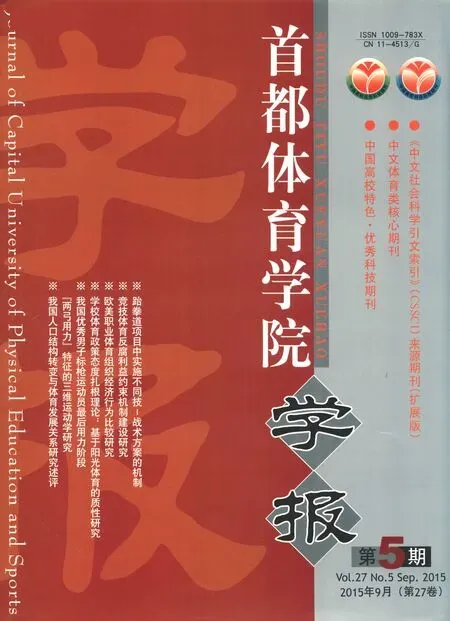广西南丹那地村“地牯牛”运动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谭分全,陈 奇,王成科
代表中国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正随着不可抗拒的现代化而黯然逝去,或是脱离其存在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或是从生存状态中被抽取出来,成为一种戏剧化、仪式化观赏性的文化商品,失去了其鲜活的生命力[1]。
本文通过对各数据库的检索发现,我国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多用标语式的简单表述,缺乏系统化、立体化的体系特征,抑或对民族传统体育本体研究得多,对生成本体的复杂因素分析得较少,重果不重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此,本文针对某一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本文选定广西南丹地区 “地牯牛”为切入点,以南丹县芒场镇拉者村及吾隘镇那地村特有的 “地牯牛”运动为研究对象,基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剖析,经过 “解剖麻雀”的方式来对 “地牯牛”的文化内涵进行系统考察,阐述它所能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以期开拓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新视野[2]。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各数据库的检索,收集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与归纳。
1.2 田野调查法
对广西河池市、南丹县等地参与“地牯牛”运动有关的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材料。调查范围为河池市体育局工作人员、南丹县体育局工作人员、南丹县文化馆员工,吾隘镇中学师生及文化站工作人员,那地村民等共计140余人。
2 结果与分析
2.1 广西南丹那地村“地牯牛”运动简述
南丹县位于广西西北面,总面积3 916m2,辖7镇4乡,有壮、汉、瑶、苗、毛南、水、仫佬等23个民族,总人口27万6 000人。那地村是广西南丹西南面一个相对闭塞的小村庄,紧靠红水河东。南丹县吾隘镇那地村距县城52km,东与大厂镇扬洲村交界,南与昌里村毗邻,西与吾隘村接壤,北和同贡村相连。那地村村名是由汉译壮音而来,壮语中称水田(稻田)为“那”,居民形成了一个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的生产生活模式即“那文化”体系[3]。
由于行政中心的转移,那地逐渐萎缩成现在的一个村庄。行政中心的转移,使当地文化随之受到影响。“地牯牛”运动因其竞技性、民族性、传统性及它本身所含有众多内涵,得以有幸保存至今。
“地牯牛”运动是当地每年在4月8日举行“敬牛”活动时,在村中坪场必须要开展的一项活动。在古代,对于壮族的先民来说,它还是一种神圣的艺术形式,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土司时期,他又是土司、土兵及当地居民热衷的高级消遣。因此,地牯牛不仅是一项运动,它还是壮族文化中,颇具民族性的一部分。
民间将公牛称为牯牛,因此,“地牯牛”就是表示公牛在地上相互争斗。“地牯牛”运动由多对未婚男性或是小男孩扮成有牛头的牛,开展一系列的赛跑和同顶活动。“地牯牛”运动不仅在“敬牛”活动时开展,在其他节庆日时也多开展,如当地的“蚂拐节”,甚至在闲暇之余壮族青年或儿童聚集在一起也进行“地牯牛”运动。
在闲暇之余进行的“地牯牛”运动,规则很少,只要把对方的“牛”顶散即可,但在节庆时节,则显得隆重很多。地点多在村中坪场指定圆形区域进行,双方各自有自己的服装,并且每队都配有鼓手,通过敲打鼓点来控制自己队伍。此时的“地牯牛”运动不是一般的戏耍,而是对战双方真正力量的对抗,对未来美好的愿望之战。双方进行格斗时,围观的群众用歇斯底里般的呐喊声为自己支持的一方加油,直到把对方的“牛”顶散或是顶出指定区域。

图1 参与“地牯牛”运动的壮族青年

图2 激战正酣的“地牯牛”

图3 节庆期间的“地牯牛”

图4 休闲期间的“地牯牛”
2.2 “地牯牛”运动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由于传统体育“所蕴涵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决定了其具有巨大的社会、文化、教育及军事等多种价值。它对人的锻炼是系统、全面的,对人的发展和影响是全方位的,早已深深地扎根在各族人民之中”[4]。对于“地牯牛”这类脱胎于原始宗教信仰仪式的运动,体育文化人类学并不仅仅关注这一运动本身的特征,例如该运动的起源、定义、分类、传播与发展、表现形式等,而是隐藏在这一仪式背后真实的社会事实及该仪式与社会事实之间的有机联系。更多关注的不是一个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是什么样的,而是为什么是这样。为此,本文的侧重点,并不在于描述“地牯牛”运动本身,而是试图揭示“地牯牛”运动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本文对“地牯牛”运动的文化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科学实验,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是一种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5]。
针对“地牯牛”运动历史沿革的文献资料,很少见诸于正式文献中,在没有现成正式资料可参考的情况下,本文充分利用田野调查的资料、当地电视台的影像资料及口述史等,结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地牯牛”运动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分析,从生殖、生产、生存3个最有代表“地牯牛”文化内涵的角度来阐述“地牯牛”运动所蕴含的文化。
2.2.1 生殖崇拜是“地牯牛”运动的起源
从古老社会流传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需要不断地使用文化创造,将神圣的传说、历史、民族信仰等加以整合,最终变成现有的一项充满活力的传统体育运动。现代体育出现以前,宗教与体育的联姻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里,许多身体运动都根植于原始宗教仪式,并没有脱离原始宗教的范畴而形成独立的体育文化表现形态[6]。“地牯牛”运动便是原始宗教仪式中为祈求族群繁衍发展的产物之一。
2.2.1.1 生殖崇拜产生的原因
周予同先生认为:“所谓生殖崇拜,实是原始社会之普遍的信仰,盖原始社会,知识蒙昧,对于宇宙间的一切自然力,每每不能求得合理解释,而遂加以人格化。他们对于这产生生命之生殖力认为不可思议,因予以最高的地位,而致其崇拜”[7]。与此同时,生殖崇拜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极端低下,人就是生产力的全部,人口的多少、体质的强弱决定氏族或部落的兴衰,生殖是关系到氏族存亡的大问题,人们对生殖十分重视,因而形成了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风习,它不仅是原始先民追求幸福、希望事业兴旺发达的一种表示,也是对人类繁殖能力的一种赞美和向往[8]。
2.2.1.2 壮族地区的生殖崇拜
不合理信念的三个因子(概括化评论、地挫折忍耐、糟糕至极)均与专业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回归模型F值等于7.752,R2=.273,调整的R2=.074,Durbin-Watson=1.586。
从民族学的资料来看,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与生殖崇拜相关的神话、传说或风俗习惯,例如,古希腊和罗马的普里阿帕斯、古印度的湿婆、中国的送子观音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生殖崇拜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虽然日趋衰落,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出于众多原因的影响,至上世纪中期,生殖崇拜文化、农耕文化、以及巫傩文化依然是构成壮族文化的三大主体[9]。不难发现,直到现在,生殖崇拜文化在当今壮族社会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反映壮族生殖崇拜的材料很多,根据内容加以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1)生殖神崇拜,例如,壮族始祖布洛陀和姆六甲便是壮族的生育之神。2)生殖器的崇拜,如壮族供奉灵石(象征女阴的石制物件);3)生殖能力的崇拜,这一类主要体现在对具有很强生殖力的动植物上,如对花婆神、蚂拐神(即青蛙)的崇拜等[10];4)性行为崇拜,这一类崇拜主要体现在崖壁上的交媾图及部分舞蹈或运动中,例如,蚂拐节中蚂拐舞的繁衍舞部分。以此来驱除妖魔,使人丁兴旺,五谷丰登[11]。
2.2.1.3 “地牯牛”运动所代表的生殖崇拜形态
“地牯牛”运动的发源地是广西南丹。当地主要以壮族为主,从“地牯牛”运动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上,无论是其准备部分还是竞技部分,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性行为崇拜”的影子。由于年代久远,又无正式文献现著于世,它具体的形态、内容和形式究竟如何已很难确定。也许只有流传下来却屡经后世增删的“神奇、传奇和传说”这部分反映,或代表原始人的想象和符号观念的“不经之谈”能帮助我们去略微推想远去仪式和活动的面目[12]。经过田野调查和研究,笔者认为,这种带有“生殖崇拜”的“地牯牛”运动之所以残存至今,除了经济、文化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宗教上的因素。壮族的“地牯牛”运动的表现形态已被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壮族中的“地牯牛”运动和生殖崇拜文化的原始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2.2 生产劳作为“地牯牛”运动注入精神文化
物质生活的生产劳作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一定地域内的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长期繁衍生息的空间条件,加之长时间的民族政策与高山多险的地理环境,使得古那地州的文化意识形态有着极强的封闭性与原始韵味。正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壮族先民通过生产、劳作,满足自身求食、生活的需要[13]。在当地长期的稻作文化中,通过对牛的顺化,使整个壮族地区的稻田耕作技术有了极大提高。牛作为生产劳作的主要助手和伙伴,当地人逐渐把牛神话为“王”或“神”。“地牯牛”运动正是在生产劳作下产生的特有的牛崇拜表现之一。

图5 最早期地牯牛运动,人作蛙状期望具有蛙的生殖能力
2.2.2.1 稻作文化与牛
中国的古书记载中指出了壮族人的祖先西瓯、骆越是水稻种植的最早发明者。壮族神话故事《布洛陀经诗》《摩经布洛陀》《布伯》等,也反映了稻作生产是壮民族生存的重要生命线[14]。广西各地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人类遗址,都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稻种化石。壮族稻作文化发达,体现在地名上的稻作文化最为著名。“那/纳”(水田)、“板/潘/版/阪”(村寨)、“布”(泉水)、“南”(水、河流)、“岜/巴”(石山)、“罗/录/骆”(山谷)等字的齐头式地名,这些地名的出现,是与稻作农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是稻作文明出现的历史印记,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壮族稻作农业文化的本来面目。现代壮学研究已经就壮族的稻作文化作出许多探讨和论证,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问——“那”文化[15]。虽然水稻源于人类对于野生稻的驯化培植,但在壮族先民的心目中,水稻的来历不仅具有植物学上的意义,还具有非常浓厚的神奇色彩和重大文化意义;于是,人类在培植水稻的过程中就与本民族文化的产生及其变迁紧密相连。这样在壮族地区,一方面形成了以“那文化”为特征的稻作文化,同时,以牛为代表的动物由于在壮族稻作生产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而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进而形成了对牛等动物的崇拜。2.2.2.2 牛崇拜的具体形式
从“地牯牛”运动的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到,双方队员头顶上的2个“牛角”,有其特别的含义,据那地村村长宁显跃介绍,它是壮族人民对牛的崇拜方式之一。牛崇拜文化贯穿壮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较之其他民族更鲜明突出,更有自己的特点。在壮族传统文化中,有关牛的来历和神话传说屡见不鲜。历史上,壮族并未曾形成统一的宗教,他们的信仰是多种的,凡物不管有生命与无生命,皆具神灵,保有自然崇拜的本质特征。这种万物有灵的思维,加上牛作为生产工具的无可替代性,为牛崇拜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16]。
牛作为壮族所信仰和崇拜的动物,每年各地都有许多围绕牛而举行的各种习俗活动,如在当地每年农历4月8日都要举行“牛魂节”,又称脱轭节,流行在红水河流域一带壮族山村,那地村更是不例外。
然而,在那地村除了上述活动外,还会进行“地牯牛”运动,这一天的“地牯牛”运动比较特别,他们将崇拜的牛演变成牛角形戴在头上,希望借助 “地牯牛”这一肢体活动实现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并以此获得祖先和神灵的保佑,祈求六畜兴旺、农业丰收、生活富裕。节日里,人们用五彩糯饭、红鸡蛋挂在牛角上,节日的那一天不能让牛劳动,还用柚子叶煮水给牛洗脚,并牵牛到村中参加“相牛过佛门”,通过跳牛舞,唱牛歌,训牛等活动,以示人们对牛的敬意。

图6 喂食牛的五彩饭

图7 “敬牛节时”表演“地牯牛”
2.2.3 生存斗争是“地牯牛”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政策,即由中央政府册封当地少数民族中的首领为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各族人民进行管理,以达到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的目的[17]。土司军事制度下的土兵是亦兵亦农,既耕田又服兵役,既要听从朝廷的征调抗御外侮、保疆守土,又要维护土司的统治,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所以经常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战事连绵不断[18]。因此,为了适应当时的生存环境,“地牯牛”运动成为当时土兵普遍开展的日常训练项目。
2.2.3.1 壮族土司制度
壮族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壮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19]。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历史对古那地州地区实施的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的士官土吏,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消亡于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长达千年[20]。虽然那地州消失了,但对那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管是那地保存的古代营盘,土司衙门遗址中的照壁,还是当地村民津津乐道的四棒九子的人文轶事(四棒指那地土司的何、韦、兰、宁四大心腹,九子指罗家势子、熊家金子、周家银子、黄家谷子、朱家排子(要面子,讲排场)、陆家色子(喜赌)、何家才子、韦家浪子、宁家穷子),都离不开土司。可见,土司文化对那地的影响源远流长,那么源于那地的“地牯牛”运动也必然被土司文化深深影响,尤其是土司的土兵政策。
2.2.3.2 土兵政策
那地土司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与维护自己的利益,便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称之为“土兵”,以便安境保土。土兵是土司拥有的个人武装。土官分给服兵役的土民一份土地耕种,这些土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若有差遣,土兵自备军粮、武器,在土官的带领下保护地方安全,服从朝廷征调,协同官军四处征战,共同承担保家卫国的使命[21]。土司的这种军事制度完全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他们没有太多的自由和权力,完全听命于土官。一般情况下,各级土司均拥有自己的武装,少者成百上千,多者上万。具体人数已不可考,根据当时那地的规模和当地的口述史,那地土司的“土兵”不少于千人。这么多土兵除了种田之外,还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来应付战争的需要。壮族土司为了提高土兵的战斗力,还引用、创建了一些适合壮族土兵的军事体育项目,用以训练或是闲时娱乐。作为当地祭祀时的活动项目之一的“地牯牛”运动,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娱乐性及健身效果,便走进了土兵的军事生活[22]。随土司的不断发展,在古那地州相沿传习,蔚然成风。因“土兵”闲时为民,战时为兵,所以这一项目,便很快传入“寻常百姓家”,并不断传承发展。它不仅是一种军事训练项目,也是一种文化生活,因其内容精彩刺激,过程激动人心,并且无须取材,所以很快在古那地州发展开来,从此具有了广泛群众性与传承性。
3 结束语
任何一项古老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之间的碰撞及观念的革新,从来都是渐进式的。任何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体育项目,必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条件、文化习俗及以往的社会实践的轨迹,而且还要面临众多的挑战。在面世之初,它的意义必须有可变通或是商榷的余地,而一旦展现出它的活力,它将需要从社会组织中获得“一个持久的框架”,将所有细节拟合一致。本文的着力点也在于这个“持久的框架”分析综合。首先,是对“地牯牛”运动进行追根溯源,其次是这一运动的理念支撑为什么会发生改变,最后这一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与社会习俗或习惯进行了怎样的社会互动[23]。
对某一项具体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客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为了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其所追求的是析解,是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壮族的“地牯牛”运动,在表现形式和内容方面都保留了较完整的原始形态,但它在不同时代所代表的含义却迥然不同。在面世之初,它是原始宗教中人们为祈求延续种族、繁衍族群,而进行的一种仪式。进入农耕社会后,牛成为帮助人们耕地犁田,成为了稻作农耕名族须臾不离的生产工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牛逐渐被“王”化、“神”化,古那地州的人们用人化身为牛,来表达人们对牛的顶礼崇拜与图腾膜拜。随着历史的推进,形成于宋,完善于明的土司制度在古那地州确立,使这一地区的“土兵”制度也应运而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开展了一连串的诸如血亲仇杀、部落械斗、以蛮攻蛮及抵御外来侵入等生存斗争。为提高土兵的身体素质、军事技能与丰富军营生活,孕育于古那地州的“地牯牛”成为当地士兵为在生存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天然选择。
壮族的“地牯牛”运动,保留了较完整的原始形态,它是那地壮族历史文化的沉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在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受特定的原始宗教、劳作生产、生存斗争等特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其独具的民族特色。
[1]肖焕禹,李长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基础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J].体育科研,2003,24(4):43-45.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24.
[3]王明富,赵时俊.“那文化”:稻作民族历史文化的印记[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2(2):17-20.
[4]林叶微.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我国少数民族体育习俗的功能[J].体育科学研究,2007(9):36-39.
[5]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5.
[6]万义.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文化生态学分析[J].体育科学,2014,34(3):54-61.
[7]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12-132.
[8]卡纳.人类的性崇拜[M].智弘,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25-34.
[9]韦晓康.浅谈原始宗教对壮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J].体育文化导刊,2004(4):74-76.
[10]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1.
[11]李富强.壮族的生殖崇拜[J].广西民族研究,1993(3):91-96.
[12]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5.
[13]韦丽春.壮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渊源及社会功能[J].体育科学研究,2008(12):39.
[14]肖谋远.壮族传统体育与稻作文化探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22):44-46.
[15]覃彩銮.试论壮族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J].学术论坛,1999(137):115-119.
[16]陈小波.壮族牛崇拜出现的考古学考察[J].广西民族研究,1998(54):23-37.
[17]韦顺莉.广西壮族土司研究现状及展望[J].广西社会科学,2006(133):189-193.
[18]张延庆.从土司的军事制度看壮族武术的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5):92-95.
[19]李世偷.明朝土司制度述略[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1):37-41.
[20]谈琪.壮族土司制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21]韦顺莉.清末民初壮族土司社会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339.
[22]张延庆.从土司的军事制度看壮族武术的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5):92-95.
[23]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53.
——以宁波市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