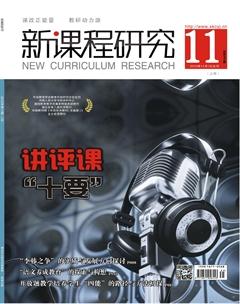语文教学中的认识论、主体论和价值论问题
【摘 要】 语文教学之“正道”,须从认识论、主体论和价值论加以谈讨:从认识论来看,要追求多样性的统一,既强调真理的多样性,也追求真理的统一性;从主体论来看,要坚持“公话”与“私语”的统一,尊重“私语”,但一定要坚持正确导向,最大限度地促进和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从价值论来看,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以培养适应现代生活的良好公民为取向,而不是以创新本身为取向,以反权威沾沾自喜,培养出一大批无视社会秩序和正义的“癫狂的蘇格拉底”。
【关 键 词】 语文教学;“韩李之争” ;认识论;主体论;价值论
【作者简介】 许可峰,甘肃镇原人,教育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民族教育问题。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 (2015) 31-0020-06
近日拜读四川师范大学李华平教授与清华大学附中教学名师韩军老师等人关于《背影》课文解读和语文教学“正道”的系列争论文章,从双方的观点中,都颇受教益。这场争论涉及了语文教学乃至教育学中很多经典而至今难解的基本问题。“如果抛开斗气的因素,‘韩李之争的核心之争是很有价值的。”正是基于对这些价值的考量,笔者不惮于在这已然情绪化的“浑水”中再蹚上一脚,谈谈自己对语文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语文教学中的认识论问题: “一个”还是“多个”?
“韩李之争”的焦点之一,是朱自清《背影》这篇课文的主题解读,而核心问题则是:一个文本的主题解读,是只能唯一,还是可以多样?
我们先看韩军老师《背影》的教学实录片段:
师:(多媒体)让学生选择:
本文的主题是赞美父性,还是喟叹生命?
生:有了前面的引导,学生很快就得出了喟叹生命这个主题。
师:本文发表了87年,很多人都是解读的父子情,我们有了喟叹生命的解读,为自己鼓掌。
韩军老师对《背影》主题的解读,是对他自己2000年时提出的“新语文教育”论纲的实践。在“新语文教育”论纲中,韩军老师对传统语文教育做了大胆的批判 :“我们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几亿孩子学着这大体一样的文章”,“对所有的文章的阐释几近完全一致”,“说话、写作,也惊人一致”。能够推翻87年来对《背影》几乎全国一致的“父子情”解读,另辟蹊径得出“喟叹生命”的新结论,从韩军老师的角度看,无疑是“新语文教育”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又一次胜利,自然值得“为自己鼓掌”,也说明他是主张文本解读的多样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韩军老师对《背影》主题的解读,却又似乎是反对文本解读的多样性。“赞美父性,还是喟叹生命”,这本不是一个“此是彼非”的单项选择题。这两种主题即使有深浅之别,却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并且可以相得益彰。但韩军老师却非要学生做出“二选一”的判断,从而否定了文本解读的多样性,追求的还是文本解读的唯一性。从这个角度看,韩军老师对《背影》的解读,并非潘璋荣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体现,倒更像是绝对主义,一种与“全国一致”式的绝对主义不同的“全班一致”式的新的绝对主义。事物的综合性被片面性所取代,认识和真理的多样性被唯一性所取代。
认识可能无限接近真理,但永远不可能完全等于真理;真理可能在自己一方,但它只是“可能”。盲人摸象,人人都占据了部分的真理,这是认识的多样性。认识的多样性与认识主体的多样性有关,更受真理本身的多样性所决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事物多方面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事物的表象与本质(也有观点认为事物本无表象本质之别,如现象学),不是唯一的。恩格斯指出:“存在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这是真理的多样性。“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西谚,已经形象地告诉我们,正道也可以有千条万条。
谈到“正道”,套用目前政治生活领域一句熟语,透露着足够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我们需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没有这种自信,既不能言,也难以行。但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都不以排他性和唯一性为前提。过去的语文教学,长期迷失在对真理唯一性(表现为“标准答案”)的迷信之中,现在锐意语文教学改革的人,自己首先要从对真理唯一性的迷信中走出。
因此,当我们谈论“语文正道”的时候,需要心存敬畏。敬,是因为对于正道,人人心向往之。李华平教授提出“语文正道论”,自然是出于对正道的向往。韩军老师提出“新语文教育”,也未尝不是出于对语文教学正道的追求。畏,则是因为任何排他性的对正道的指认和过度自信,都可能意味着对其它可能性正道的忽视,以及对尝试走这些正道的人的排斥,甚至迫害。人类历史上并不缺少对“正道”的自信,然而往往正是许多过度的自信,造成了无数的专断和灾难。远如秦皇焚书、汉武崇儒,近如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一句顶一万句”,西方某些国家时时以“正道”自居而对其它国家的指手画脚,以及当代其它许多类似的现象。韩军老师在我国语文教学界获得了深远的影响和广泛的声誉,这本身说明他的教育教学思想与实践中有着丰富而宝贵的财富,值得深入学习、研究和推广。同时,像韩军这样影响深远、广泛的老师,如果他们的教育教学思想中存在某种程度和范围的问题,其影响也是深远而广泛的,因此也就更有了批评与反思的必要。我们对韩军老师语文教学的认识,也需要将之看作是多方面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任何简单化甚至粗暴化的讨论,都需要警惕和拒绝。
另一方面,语文教学除了要强调认识和真理的多样性,更要强调统一性。只谈多样性而不言统一性,就会坠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一些语文课堂上,教师一味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偏颇怪诞至极,也不予以纠正,就是这种相对主义的表现。至于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借用韩军老师的术语,就是一个如何实现“公话”与“私语”统一的问题。
二、语文教学中的主体论问题:“公话”还是“私语”?
课文解读究竟应该是唯一的,还是多样的?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但也与参与教学的各主体在教学中的地位有关,从而表现为主体论问题。如果教学以文本为中心(实质是以作者为中心),或以教参为中心(实质是以编者和专家为中心),则文本的解读主要表现为唯一性,容易“全国一致”;如果教师居于教学的中心地位,则相对“文本中心”和“教参中心”而言,文本解读会表現为多样性,而在同一教师的课堂之内,仍然表现为唯一性,即“全班一致”;如果学生居于教学的中心地位,则文本解读容易出现千人千面的多样性。文本、教参、教师与学生在语文教学中的相互关系如下图:
教育学界所谓“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的二元对立,反映的是西方教育的状况,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界曾经长期盛行“教参中心”,教师不过是教参的传声筒,何来中心地位?韩军老师的“新语文教育”反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的“教参中心”,树立了“教师中心”。“新语文教育”还主张“举三反一”,从反对语文教育阅读量小的角度看,不无积极意义。但这个“举三”,主要还是表现为教师对文本的解读与分析,是从叶圣陶先生的“解剖一只麻雀”,变为“解剖三只麻雀”。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明显加强。李华平教授批评韩军老师是“用自己的人生感悟代替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是击中肯綮的。但是,让几十个学生与文本对话,对其解读的多样性是完全保留,还是予以统一?如果完全保留,教师何为?教学何用?如果予以统一,是统一于教师,统一于教参,还是统一于文本?这是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的。潘璋荣主张教师在解读文本时,至少要无限地接近“纯文本”,反对文本解读的“相对主义”,无疑是主张统一于文本。但是文本进入教材,还是需要编者加以选择,教参编者、教师和学生加以解读的。从操作的角度来看,所谓“纯文本”的解读究竟如何可能,是存在问题的。韩军老师努力参考朱自清先生的大量其他著作,无非也是想尽量接近文本。而从目的论的角度看,“纯文本解读”也存在问题。读者阅读一篇文章,其目的在于增进自己对社会和人生之品味感悟,而不在于文本的科学主义研究。虽然李、潘二人都批评了韩军老师的“教师中心”,不过潘主张向文本靠拢,而李则主张向学生靠拢;潘倾向解读的唯一性,李倾向解读的多样性。二人的立场有不尽一致之处。总体而言,潘璋荣老师的主张可以概括为“文本中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语文教育曾经长期表现为“教参中心”,韩军老师的做法更接近于“教师中心”,而李华平教授的主张则接近于“学生中心”。无论哪一种“中心论”,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语文教学究竟应该以谁为中心的问题,韩军老师将其表述为“公话”与“私语”的关系问题。韩军老师说他的“新语文教育”的价值论,是要由强塞“公话”到张扬“私语”。这里的“公话”,主要应该是源于教参对课文的解读。笔者相信,他的本意,“并不一般地反对言说公话,反对的是缺乏私人真实精神体验的异口同声”。但是申明不反对言说“公话”,却把“私语”而不是“公话”作为语文教育的价值论基础,客观上将“私语”和“公话”对立起来,并毅然决然选择了后者,其实还是反对“公话”。当然,如前所述,他反对的只是全国“异口同声”的“公话”,而对于全班“异口同声”的“公话”,则并没有反对。或者,在他看来,这种于全班“异口同声”,就是张扬“私语”了。这又给了李华平教授一个批评的理由,因为在这种全班异口同声的课堂上,看不到学生“私语”的张扬。在反对“异口同声”这一点上,韩、李二人有一致的地方,只是韩反对全国异口同声,李反对全班异口同声罢了。在反对异口同声这一点上,李更为彻底。
笔者认为,对于“异口同声”,需要区别对待。“异口”而能“同声”,可能是由于强制,可能是由于灌输,可能是由于引导,可能是由于对话,也可能是基于人之本性或者社会惯性的不约而同。我们固然要反对强制的同声,灌输的同声,但如果反对一切同声,包括基于引导的同声,基于对话的同声,不加辨别地反对一切不约而同地同声,一切教育和教学也就不能存在。基于引导、对话或不约而同地同声,“异口”时是“私语”,“同声”后即成“公话”。“私语”与“公话”,并非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实现统一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一文发表87年,很多人都将其主题解读为父子情,这样的“异口同声”,从何证明它不是基于每个人的“私人真实精神体验”,而是“强塞公话”的结果?语文教学可以鼓励“私语”,但鼓励私语不应属于价值论,而应属于方法论,应该通过鼓励“私语”,建构“公话”,丰富“公话”,发展“公话”。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是取得共识的工具,这就决定了语言的本质,在“公”而不在“私”。自言自语只是语言的极端形式而非常态。
如何促进“私语”向“公话”的转变,实现“私语”与“公话”的统一?我们不妨从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公话”中寻找解答。在外交领域,我们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对抗西方的话语霸权;在内政上,文化领域,我们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指导方针;在统一战线领域,则要求“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
语文教学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即尊重“私语”,但一定不能放弃坚持正确导向,最大限度地促进和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没有共识的私语的世界,与只有共识没有私语的世界一样,都是可怕的。“坚持正确导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都是手段,“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才是根本目的。而社会思想共识,就是一种“公话”,一种建构而成的公话,而非强塞的公话。通过坚持正确导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私语,最终都可能向公话发展。私语与公话,由此实现统一。
换句话说,文本解读是作者、教材编者、教参编者、教师、学生的多主体间的“圆桌对话”,谁也不是中心。对话的结果,是不断实现“私语”向“公话”的转变,促进“公话”的形成和不断发展。
三、语文教学中的价值论问题:“求新”还是“求善”?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的角色,主要是上述“圆桌对话”的主持人,引导学生在文本、教参(体现学界共识)和师生个体感悟之间,形成和发展新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无须刻意追求教学的原创性和私人性,从而刻意回避教学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举例来说,学术著作强调创新性,但是教材则强调共识性。这就说明教学与学术研究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单纯从文本解读的角度看,韩军老师对朱自清先生《背影》一文的感悟不能不说很深刻:“背的影是生命的虚幻,由背到影,生之背,死之影,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命轻,才愈珍重。”但是这样的解读,用之于学术论文则可,用之于教学则需要慎重。教师在教学中当然可以谈自己的一家之言,不过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一是不能挑战社会基本政治共识和道德共识,如个别教师在课堂上否定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而自以为高明,范美忠公然挑战师德准则(教师保护学生)和私德准则(救母亲于危难),这些做法都需要坚决抵制和反对,以免动摇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繁荣发展的环境;二是在尊重社会基本政治共识和道德共识的前提下,如果自己的一家之言是对现有某社会共识的补充,可以并行不悖,应该首先让学生了解这一共识,不能让“补充”喧宾夺主;三是如果自己的一家之言是对现有某社会共识的纠正,非此即彼,则需要首先对现有某社会共识展开充分的批驳,先破后立。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学生对现有社会共识有充分地了解并给予他们对现有社会共识给予辩护的权力和机会,而不应把教学搞成对现有社会共识的“缺席审判”。
在韩军老师的《背影》教学实录中,关于父性之爱的主题解读被一笔带过,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否定了87年来大多数人的共识,而接受了教师的一家之言。这与强塞的“全国一致”一样,都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需要反思整个教育系统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没有充分的批判和反思,没有深入的民主对话的课堂,无论是韩军老师所反对的“强塞公话”,还是他自己所主张的“张扬(教师)私语”,都不是语文教学的正道,都为青少年成人之后走上邪道留下了一定的“后门”和“漏洞”。所有的教育者,包括韩军老师,都是教育和社会这个系统安全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我们的目的不是指责,而是不断查找“安全漏洞”,打上“安全补丁”,共同完善教育系统。
韩军老师之所以要努力在87年来的“公话”之外,努力张扬自己的“私语”,除了是基于他自己对文本解读多样性统一的认识不够,还基于他对创新的刻意追求。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一个人人言必创新的时代,甚至是一个“创新即正确”的时代。这种对创新的推崇,发轫于近代列强用舰炮对中国的“启蒙”,接着在“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话语体系中得到了加强,后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创新力竞争的潮流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这种背景下,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自然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把教师或学生的创新当成了语文教学的本质或根本目的,各种教学比赛、名师授课和演讲,“创新”“首倡”满天飞,则并非好事。
我们必须明确,创新本身不能作为目的。创新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更好的生活,而继承也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更好的发展、更好的生活。因此,继承与创新,可以而且应该结合起来。
说到教育与创新,不妨从东西方古代的两位伟大哲学家、教育家说起。孔子讲“述而不作”,又说“温故知新”。他在夏、商、周三代流传下来的、以“六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了儒学。他从来没想到要自称“首创”或者“首倡”过什么,但是后人从他的学说中,很容易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伟大贡献和创新。后世儒家也很少动辄言新,你可以说这是造成中国保守落后的原因,但是它又何尝不是中华文化千年延续的根由。
至于苏格拉底,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上和学术上存在两个苏格拉底。一个是少年苏格拉底,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充满“哲学的癫狂”,学了哲学就要揍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一切权威的象征,而哲学要的就是鄙视任何权威。后来雅典法庭审判的,就是这个癫狂的苏格拉底。另一个是成年的苏格拉底,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开始从“癫狂的哲学”发展到“清明和溫良的政治哲学”。少年苏格拉底以哲学的名义、知识的名义反对意见,把知识看作是高于意见的东西;晚年苏格拉底接受法庭的判决,尽管这个判决不过是一些“无知者”意见的综合。这体现了晚年苏格拉底对正义、虔诚和秩序的自觉尊重和维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哲学王”,以代替“无知者”掌握真理的判决权;杜威根据资本主义变化了的民主化形势,主张通过教育培养每一个公民理性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这3位西方伟大教育家的主张虽然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在如何处理好教育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同,但是我们的教育,在需要培养未来公民善于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这一点上,与西方是一致的。我们的未来公民需要追求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但现代化标准,应问好坏,不在新旧。
如果说古代常常把“好”的标准等同于“古老”的,因此“古”就是“好”,而“最古的”(上古、太古)就是“最好的”,那么现代性则恰恰倒过来,把“好”的标准等同于“新”。由此,现代性的逻辑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因此青年必然胜于老年,而创新必然胜于守旧。在这样一种强劲“历史观念”的推动下,现代性必然地具有一种不断由“青年反对老年”、不断由今天反对昨天的性格,从而现代性的本质必然地就是“不断革命”。在这样一种万物皆流,一切俱变,事事只问新潮与否,人人标榜与时俱进的世界上,是否还有任何独立于这种流变的“好坏”标准、“对错”标准、“善恶”标准、“是非”标准、“正义”与否的标准?还是善恶对错、是非好坏的标准都是随“历史”而变从而反复无常?
韩军老师通过“喟叹生命”的《背影》主题解读,完成了对87年来“赞美父性”这一传统的权威解读的革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未为不可,但是用之于教育教学,用之于人的培养,我们究竟是在培养创新能力,还是在培养“反权威”的斗士?反权威者所需要的,不就是“很多人如何如何”,而“我(们)却如何如何”的沾沾自喜?“本文发表了87年,很多人都是解读的父子情,我们有了喟叹生命的解读”,而不明白前者究竟何以“误读”,后者究竟高明何在?这样的成就,如果是学术研究,我们也许可以“为自己鼓掌”。但在课堂之上,任何对传统和权威的颠覆,虽然可以允许,却都需要慎之又慎。
这样说,不是反对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是给教师和学生天马行空的“创新”,寻找避免剑走偏锋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苏格拉底所“首倡”的对话式教学,是后世学者所提出的知识的社会建构,而非“强塞公话”,也不是“张扬私语”。通过对话,让学生自己学会思考,學会辨别,学会表达和倾听。让任何的“私语”和“公话”,都通过理性的辨析,通过多主体多形式的对话,寻找成为共识的可能。无论观点新旧,他们都应该以好坏为标准加以选择。
如此,一个教师备课和教学,何必过度关注所谓创新,而不敢采取“拿来主义”,在互联网时代,兼采百家之长,为学生提供一盘美味可口的“教学”大餐呢?正是我们的各种以“创新”为最高标准的教学大赛,在造就一大批教学名师的同时,也毁掉了他们,逼他们走上了刻意求新的歧途,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正道。笔者在组织师范生教学技能比赛中,首先强调学生要学会对现有优秀教学资源的搜集、借鉴和运用,而将创新放在其次,正是基于这一思考。
参考文献:
[1] 王君. 好好说话才最“语文”,最“人文”[Z].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9b3def0102vka3.html
[2] 韩军.《背影》课堂教学实录[EB/OL]. http://www.xiexingcun.com/mingshi/HTML/41480.html
[3] 韩军. “新语文教育”论纲——兼论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的三重误区[J].语文教学通讯,2000,23(17):5.
[4] 李华平.迷失在学科丛林中的语文课——兼评特级教师韩军《背影》教学课例[J]. 语文教学通讯,2014,37(29):9.
[5] 韩军. “新语文教育”论纲——兼论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的三重误区[J].语文教学通讯,2000, 23(17):5.
(编辑:杨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