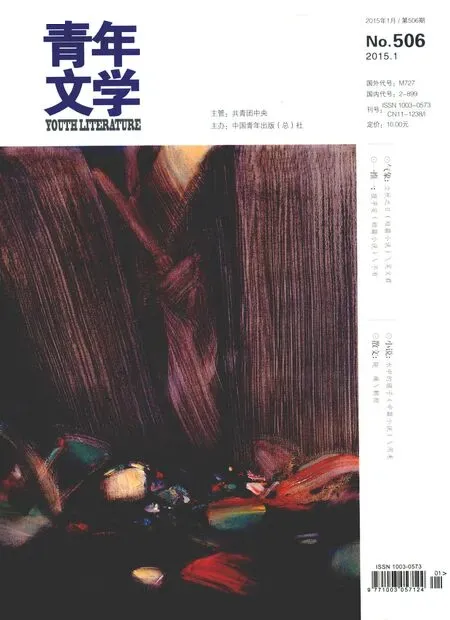灯盏照寒夜
⊙ 文 / 陈崇正
她走进来,一把揪住我的耳朵:“你需要自己对自己说话。”
我的耳朵被揪痛了,我感觉自己应该站起来了,所以我站起来。我看着她,说:“你揪我耳朵?”我感觉这样说的语气似乎不够强烈,于是又重新说了一句:“你刚才揪我的耳朵?”
但她的手还揪着我的耳朵不放,也没有退缩的意思。她瞪着我看,我也就瞪着她看。结果她手上一用力,我就被她提了起来,脚尖都离了地。
她终于开口:“是的,你不应该回来。”
我伸脚朝地上蹬了蹬,但就是靠不到地。看来她真把我提起来了。耳朵要被揪坏了,那可就听不了音乐,于是我用我的手,抓住她揪着我耳朵的那只手,以此来减轻耳朵的受力,防止受伤。她的手像一根丫枝,我像一只猴子吊在上面。
她大吼一声:“废物!”把我甩向墙角,我的头不知撞到什么东西,咯噔一声响,眨了两下眼睛,才看清楚我所在的位置。又想我应该爬起来,地上有点冷。于是我就爬起来,站着。
“你不应该回来,你回来了就必须写作。”她对我说,“在这个地方,你不写,你不自己对自己说话,就只能被揪耳朵。你说,你存在,就是为了给人家揪耳朵吗?”
我连忙回答:“不是的。”
“那就好,那就回你的桌子上去,去写你的东西!”她看到他的食指和拇指又扬了起来,做了一个揪耳朵的动作,心里一惊,赶紧坐到桌子前面去,把电脑的子流线插到我的臀部上。
电脑的子流线插上臀部的感觉很不舒服,但为了不被揪耳朵,我只能这样做了。
她看我已经端正地坐到桌子前,满意地环顾四周,房间里并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于是她就走了,门被重新关上,屋子里黑了一些。
我坐在椅子上,微弱的电流通过我的电脑,把我想到的每一个情节都带走,并自动形成文字。我在想,我真不应该回来。我看着桌上的电脑屏幕上,已经把我刚才想到的这一句话也打了进去,“我真不应该回来”。桌子上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著名小说家傻正。牌子上还有颁发单位和日期。最下面是电话,还有一句话:本公司竭诚为你提供最新潮的感觉服务。
我把臀部上的子流线拔下来,一阵舒服。电脑因为创作中断,发出了嘟嘟的叫声。我没管它。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这个城市,好凄凉的夜。外面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但我感觉到有飞鸟在空中飞舞。但只是飞舞,这些生灵已经不知道鸣叫了。
读者对我的评价很高。第二天有读者到公司来找我,要求见我一面,老板同意了,他没有理由不同意。他带她上了楼,来到我那间黑暗的房间。
这是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她走进我的房间,一进房间她的眼睛就没有离开我。
“你就是傻正?”她弱弱地问道。
老板跟在她的身后,一见我没有回答,挥起巴掌:“顾客问你话呢!”我头上挨了一下。老板又对小姑娘鞠了一个躬:“他已经很多个月没见生人,有点……呵呵……你知道的。”
“你别打他!”
“不打……不打!”
“我能单独和他聊聊吗?”
“当然当然……”
“耽误他创作时间的费用,我会承担。”
“当然当然……”
老板就出去了。
这个样子腼腆的读者,又看着我,说:“你懂得说话吗?说汉语?”
我说:“能,我用汉语写作。”
她似乎很高兴。她说:“难得你还用汉语写作,很多作家早就抛弃语言了,他们只会用电脑,直接用电脑和读者说话,直接传递感觉,甚至直接复制回忆卖给读者。”
“他们赚的钱比较多。”
“但他们比较贱。”她笑了。
我也皱着眉头一笑:“我不见得有多高贵……你也看到了,他们打我,但我怕疼。”
“不,他们用这里写作,你用这里写作。”小姑娘瞪大了眼睛,先用手指了指头脑,表示他们的写作,又用手指了指心窝,表示我的写作。
我对她这个动作表示感激,正想说什么,但被她打断了:“一分三十秒,你们公司的创作时间很贵,我没有多少钱,买不起那么多,但我会常来看你的。”
话一说完,她一溜烟地跑下楼去,不见了踪影。
我站在房间的中央,感觉空荡荡,怅然若失。
“我真不应该回来。”我喃喃地说。
管事的女人又进来了,再一次伸出了食指和拇指:“你需要自己对自己说话。”我下意识就跑回桌子上,把子流线插到臀部上,开始工作。在我的故事里,此时正是寒冷的冬季,落魄的秀才在桥头卖对联。
管事的女人这一次没有过来揪我的耳朵,她对此做出解释:“我其实也不想揪你耳朵。”她接着又说:“谁会老想着揪别人耳朵,揪了你的耳朵,我又没有赚一只耳朵,所以你要听话,多写一些,多为公司制造一些产品,自然就会有读者来看你。你不知道,刚才那位小姐付了双倍的价钱,说起来你会羡慕的,她可是一位妓女!”
“她是妓女?”
“羡慕吧?这样的职业你一辈子想都别想,别说你是个男的,就算女的,像我,要登记当妓女,那要考试,要等多少年啊!”她一脸神往之情,关了门出去了。
我低下头,想到妓女,我的屏幕上就跟着出现“妓女”两个字。这真是低劣的写作,没有什么速度,还要经过一段文字转化,用老板的话说:“你这人……没意思!”
是没意思,我的故事也在没意思中展开。故事的基本架构是:明永乐年间(一四○三年),一个在湘子桥头卖字的书生,因涉嫌谋杀桥楼里的一个妓女,被杀头了。
湘子桥,位于潮州古城东门楼外,曾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它建于宋,初为浮桥,由八十六艘巨船连接而成,开始名为“康济”。后历代太守不断修建,筑建桥墩,改名“丁公桥”“济川桥”。至明代,遂筑成“十八梭船廿四洲”,更名为“广济桥”。假如你是永乐年间的潮州人,你对这个书生不会太过陌生。每天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他搬了一张只有三条腿的破桌子,来到湘子桥头卖字。桌子的一条腿坏了,于是他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是去捡了几块砖头,垒起来当桌腿,将桌子固定住。接着他就从麻袋中取出笔墨纸砚,中规中矩地在桌子上摆好,又在麻袋中摸啊摸,取出以前写过的对联,一幅幅挂在桥栏上,作为生意的宣传。这些字写得不是太精彩,但也不难看,只有不认字的老太太啧啧称赞。这一点,和我的小说又有一点相似,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不尴不尬,乏善可陈。
湘子桥最热闹的时段,是在每天的早晨和夜晚。——早有早市,晚有晚市。到了夜里,桥上楼台上的妓女就开始出来活动,出门在外的商人也就往这里挤,总少不了打情骂俏,酗酒闹事,争风吃醋。有了出远门的人,就有家信可以写;出远门的人闹出了事端,就有文书可以写;事端闹大了,又有人来请他写讼词;闹得出了人命,就需要写悼词;打赢的起了脾性,把妓女赎回家,又有贺词可以写……
但这个冬天静得像鬼一样,整整一个月,书生只为人写过一封休书,生意惨淡,眼看便要家中无粮,袋中无钱,书生眉头紧皱,只看着一江流水,从桥下流过,一筹莫展。
这种境况,和我又有几分相似。
甚至我觉得,对于像我现在这样一个职业——为公司赚钱的小说家来说,我比一千年前湘子桥头卖字的书呆子要糟糕百倍。
地位是要低些,但我这里的天气毕竟比较好。是的,这一日夜晚降临,湘子桥头寒风怒号。桥楼之上灯火很亮,桥上却人烟稀少。书生在桥头搭了一个小帐篷,在里面哆嗦着用火折点灯。这已经是他第四次点灯,风太大,灯火总是命若游丝,站也站不稳。
油灯终于又被点起来了,但就在此时,帐篷的门被撩起,一阵寒风扑入,灯又灭了。只隐约看见一条人影闪身而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说道:“张公子,奴家冒昧,把你的灯火给吹灭了!”书生先闻到油灯熄灭的呛鼻味儿,再闻到一股很浓的胭脂香气,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摸索着把灯点上,这才看清楚来人是甲号桥楼的妓女,姓柳,经常来找他写家信,便作揖道:“柳姑娘!”
“这寒冬腊月也没有什么生意,公子为何还搭着帐篷,在此逗留?”说完,柳姑娘在怀中一掏,掏出一包瓜子,递给书生,“给!”灯光之下她笑容灿烂。
书生讷讷地接过,脸上一红,答道:“实不相瞒,家中西墙已经倒塌,小生怕哪一日睡梦之中会被压死在里面,还不如带着帐篷来桥头露宿,明日也无须为早起担忧。”他话刚说完,灯又被风吹灭了。
柳妓女边吃瓜子,边摸出火刀火折,帮书生点了灯。帐篷中一亮,书生又一次看到她那张俏丽的脸。但他此时还真不知要说些什么。他和我一样,讷于言辞。
我又心情浮躁地拔下子流线,走到窗前。这是白天,外面很亮,但我已经习惯了房间里的黑暗,对着刺眼的亮光,我什么都看不到。其实即使我习惯了亮光,外面一片浓雾迷茫,也必定是什么都看不见。数月前我就是沿着这个窗口爬下楼去逃走的,我明白外面的情形。或者说,没有外面,房间之外还是房间,这个世界是由一层又一层的房间构成的,谁都弄不清楚,这最外面的房间是哪一间。
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没有谁需要看清谁的脸,没有人阅读文字,没有人需要灯光,人们靠电脑和电波交流,脑与脑自由连通,所以这里的黑夜很黑,白天很白。
每个夜晚,站在窗前,我多么希望能看到一处灯光。——我发誓,只要能看见一处灯光,看到一盏灯,我会奋不顾身地向着灯光奔去,而不像几个月前一样,在黑与白之间挣扎,最后饥饿又把我带了回来,回到这个房间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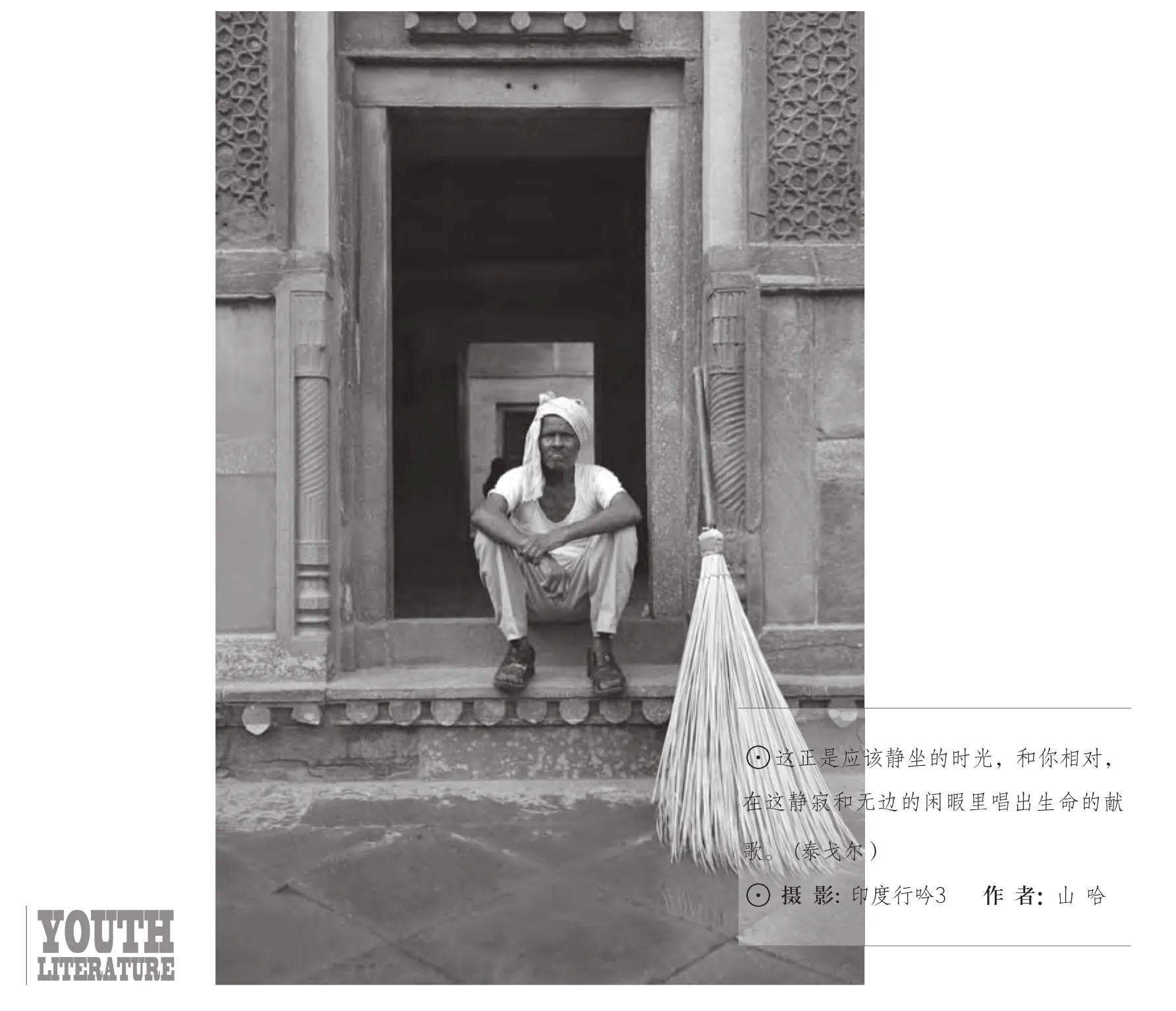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丧失了谈话的欲望了。但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应该不会是等待一个人。
那个腼腆的小姑娘又来找过我几次,但我真不知道跟她谈些什么,她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来和我聊天。有时候,她只是上楼来,在椅子上静静地坐着,坐了一会儿,就慌慌张张地走了。
从别人的口里我隐约知道,她没什么钱了,老板对她的态度也渐渐恶劣。
这一次她又来了,我注意到,爬上楼她有点喘,鼻孔撑得很大,胸脯起伏着。她呼噜呼噜喘完了,竟然笑了起来,把手撑在膝盖上,眼睛笑得通红,嘴角一拉一拉,笑得有点断断续续。
接着她长舒了一口气,仰面坐在我的椅子上。
我总感觉她这几个动作,和平时有点不一样,这不是一个腼腆的女孩所具备的动作。
她仰着脸,在椅子上斜躺着,开始瞪着天花板,后来,又用一个手掌,把眼睛都盖住了。我想,她可能是刚才笑得过了头,把眼睛都笑痛了。她的眼睛那么红,藏在她的手掌下面。
“你不问我为什么笑吗?”
“你为什么笑?”
“我刚才去了一趟医院,出来的时候,看到路边居然有一朵大红花,开得好漂亮……不!不是漂亮,是好美!真的好美!”
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是看到花,我没有当作家之前,是种花的,见得多了。”
她把盖住眼睛的手拿开,我看到她的眼睛照样很红,像两盏灯照着天花板。她说:“那你猜猜,我没有当妓女之前,是干什么的?”
“不会也是种花的吧?”
“不是种花,是养花。也不单是养花,我还是个作家,跟你一样,作家。现在都不叫作家了,叫感觉服务。后来……后来有了更高的追求,就当了妓女。”
“那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我问。
她突然坐起来,看着我说:“那你呢?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我答不出来,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只得说:“你……你今天超时间了,你应该回去了。”
“不重要了。”她的视线落在没有景色的窗口,“那朵大红花好美。”
她依然在椅子上坐着,坐了很久,也再没说什么话。又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脸色有些颓然。
我总觉得有些反常,心里动了一下。但还是把子流线插到臀部上,继续工作。再不把任务完成,我就可能没饭吃了。桌子底下的抽屉里,我还藏了一个红薯,那是最后的救命粮食。
“那朵大红花好美。”
天气干燥,很多天没下雨。我咳嗽了,咳了两天,而且拼命地咳。这些天,我倒是对医院外面的那朵大红花感兴趣,花的样子最近老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心神不宁,所以我想去看看。
老板说,去看病吧。
我点了点头。我本来想申请到自费的医院看病,但老板不肯。“一点小病,到免费的医院看得了。”我知道,在自费医院一次能看好的病,到了免费医院得看五次,如果遇到兽医,次数会更多。
但总算能够出来了。我在灰蒙蒙的空气里,绕着医院走了三圈,没有看到那朵大红花。
我彻底地失望了。那个小丫头骗了我,我是这样想的。
果然,那丫头真的再没来了。
明朝永乐年间,每一片土地上都在生产故事。在湘子桥头,一个糜烂的地方,这是寒夜,桥楼上人已经不多,但冷风肆虐,呼呼地吹着。在小帐篷里,姓柳的妓女是一个健谈的女孩,而书生却一直哈欠连天,睡意沉沉。后来妓女意犹未尽,说:“公子稍待,奴家去去就来!”
书生在帐篷中抱着膝盖坐着,他很想一头倒下去睡,但心里又不踏实。——妓女是他的老主顾,要是得罪了,那可不好办。帐篷上薄薄的布帘被掀起,柳姑娘走了进来,在浓浓的胭脂味中,竟闻到一股酒香,书生精神一振,睡意全无,定睛一看,果然,柳姑娘怀中抱着一个酒壶,右手还提着一个纸包。书生口水都流了下来,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姑娘破费了,姑娘破费了,破费了!”
柳姑娘把纸包一打开,更是香满帐篷,这不是一只烤鸡吗?“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烤鸡一只,哈哈……”酒还没喝,书生已经兴奋得开始摇头晃脑,胡言乱语。
柳妓女看到一只烤鸡一壶酒就把书生高兴成这样,心头不禁一酸。
她又从怀中掏出两个酒杯。掏酒杯的时候,她故意把衣服往下一拉,露出胸口一片白皙的肌肤,但她发现书生眼睛只盯着烤鸡,竟对这个动作视而不见。
她斟了酒,举杯:“公子,请!”
“请,请!”书生一举杯,一饮而尽,一股热流蹿入体内,让他不自觉呵了一口气,皱了皱眉,耳边依旧风声大作,但听来已经是舒服无比了。
书生的酒越喝越多,话也越来越多,妓女的样子已经越来越恍惚。大风在吹,而他已经人事不知。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这个妓女想干些什么,就如我不知道那个来看我的小丫头想干什么一样。我走到窗口,眼前依旧白茫茫的一片,我从白茫茫中看出去,仿佛看到一朵又大又红的花朵,正在恣意地开放。
她很久没来了。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些想她。她就如命运之神,忽喜忽悲,忽紧忽慢,忽腼腆忽……忽什么呢,一时也找不到恰当的词,总之让人琢磨不透。
年华似水,日子正在流走,只记得她最后说:“那朵花好美。”
也不知她在什么地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也许是我太粗心没找到那朵花,也许是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医院。
书生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中醒来,喝了太多酒,头痛得厉害,他睁开了眼睛,似乎对这个世界都不以为然。
这一天是阴天,书生花了很大力气,才发现这已经不是自己温暖的帐篷,而是监狱。
“你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吗?”监狱里有一个问话的。
“不知道。”书生显得很诚实。
这是永乐年间,这一年的天气出奇的冷,很多人都在猜测,大雪就要从天空中砸落下来,但这个猜测最终还是猜测,没有雪,只有大风在天与地之间毫不费劲地运行。
“不知道?那你昨晚都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喝酒了,醉了。”
“喝谁的酒?”
“甲号桥楼上的柳姑娘……”
“她人呢?”
“不知道。”
“不知道?那好,我告诉你,她死了。”
书生心里咯噔了一声:“死了?”书生抬起头,看着坐在上面问话的那个人:“老爷,她真的死了?”书生看过去,老爷其实也和他一样的疲倦,眼里布满血丝,不难猜测,老爷也喝酒了。于是书生问:“老爷,你昨晚也喝酒了?”
“大胆奴才!竟敢用这样的口气和老爷说话!”师爷在一旁咆哮。
书生竭尽全力争辩,但老爷还是决定要把他拉出去,剁掉他的头。对此书生据理力争,说为什么老爷喝了酒还可以继续当老爷,我一个书生喝了几口酒就要被拉去剁掉头颅。
老爷道,小孩子,我想砍你的头,随时都可以砍,不需要理由的。来人啊,拿酒来!
书生睁着眼睛看一坛酒被抬了进来,心里充满疑问,但很明显他并没有猜到这个故事的结局。老爷把眼一抬,大喊一声:给我灌!
四个彪形大汉冲了过来,给书生灌酒。书生开始反抗,又哭又闹,但后来就没有了力气,变得很乖,再后来,他又笑又闹,瘫在地上,伸出手要酒喝。
再一次醒来时,书生觉得身体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他眯着眼看了看自己的拇指,果然,拇指是红的。——他已经在供词上按了手印,认了罪了。
他摸了摸脑袋,还在。但很快就会不在了,书生想。
这些日子我再没有想到灯,我一直想着花。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见过花了,也没有见过鸟,连蟋蟀也没有了。我写书生要被拉去剁头,并没有交代背景,比如,那妓女是怎么死掉的呀?是书生醉酒杀了她吗?是她自己逃跑的吗?是有人先奸后杀再诬陷书生的吗?……但我想这些都不用去讲它,我的读者会明白这一切,这个世界本来就模糊之极,谁都看不清楚,他们也不会要求我一定非得把每一个细节都交代清楚,他们只要知道书生的头最后被剁下来,在地上滚了几圈,他们就能高兴得拍手欢呼了。
头总是要被剁掉的,鲜血总要喷出来的。——鲜血喷出来时像什么呢……像,像一朵盛开的鲜花。用了这个比喻句以后,我心中又咯噔了一声:那个小女孩,到底看到了一朵什么样的鲜花,大红的花?
这一个推论让人心惊胆战,“那朵大红花好美”。我想起那个女人坐在我的椅子上说的最后一句话。那种眼神,仿佛她透过天花板,看到了书生的头被剁下来在泥地里滚动,鲜血同时在空中盛开一样。
但那毕竟是一千年前的事。头被剁掉时,很多人都围着看热闹;但头被剁掉以后,书生就再不被人提起。人们要买对联就会走远一点,要写什么文书,就会到西马路找黑瘸子。有人认为黑瘸子的书信写得要比书生好些。
在一个没有人点灯,也没有人种花的世界,我把子流线再一次插上臀部,故事静静地流淌出来,书生、柳妓女、老板、读者小姑娘都适时地出现。
那个来看我的小妓女,果然病死在医院里,有人为我送来她的一方白色手帕,上面有她咯血画成的一朵大红花,此时,我对此并不以为然。老板还警告我注意病人的手帕可能有细菌,可别传染给公司里的人,于是那天夜里,我当着老板的面,把手帕给烧了。
手帕燃烧发出啵吱啵吱的声音,像一只蟋蟀在叫,让我想起童年书桌上那盏煤油灯。手帕的亮光照出了窗外,第二天新闻说,有两个人看到亮光,跳窗遁逃,脱离管制,至今下落不明。兴许,他们会逃到森林里,在寒夜,围着篝火饮酒高歌,乏了,就讲一讲明朝永乐年间的陈年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