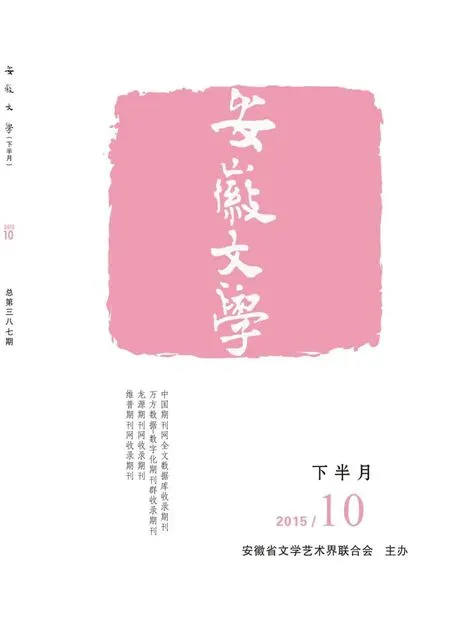枯木逢春:新诗对古典资源之回溯——浅析废名的诗学路径
王静怡同济大学中文系
枯木逢春:新诗对古典资源之回溯——浅析废名的诗学路径
王静怡
同济大学中文系
摘要:废名从“温李”的诗学理路中探析出“诗的内容”之意义,并将其作为新诗的根本质素,建立了独特的新诗主张。以“诗的内容”为基点,废名一方面重新对新诗、旧诗的界限进行了划分,另一方面又以回溯的姿态对旧诗、佛禅等古典资源重新审视,在意象联结、用典等方面拓展了新诗的表达。
关键词:废名新诗古典资源诗的内容
新诗如何脱离旧诗母体,在诗的本体意义上建立自身的合法性,成为贯穿新诗理论发展的重要命题。站在中国最活跃的新诗现场之中的废名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回溯“温李”(温庭筠、李商隐)等古典资源,建立了独特的诗学理路,使旧诗的这株“枯木”在新诗书写中重获新生。
一、“诗的内容”与“诗的文字”
废名将“温李”的诗词视为“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①1633,正是由于他从其诗作中感受到旧诗中少有的“诗的感觉”:“真有诗的感觉如温李一派,温词并没有典故,李诗典故就是感觉的联串,他们都是自由表现其诗的感觉与理想。”①1645这种“诗的感觉”在废名的诗论话语中更明确地被表述为“诗的内容”。废名指出,“有一天我又偶然写得一首新诗,我乃大有所触发,我发见了一个界限,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②1629不同于新月派把格律等外在形式等同于新诗的本质,废名从内容出发对新诗合法性进行诠释,他认为新诗只要有“诗的内容”便无须受制于格律等外在形式的“束缚”,是以“散文的文字”和白话的“文法”进行“自由”地书写。
孙玉石以30年代新诗诗坛的“晚唐诗热”为研究对象,认为“温李”诗中的“暗示”、“朦胧”,符合现代派的审美要求,这种内蕴之美正是废名追求的“诗的感觉”。③但笔者认为“诗的感觉”并不等同于文本的晦涩,废名所强调的“诗的感觉”指的是文本被书写之前,已存于温李的想象之中,先于文字而为“第一性”的“诗”性本体。正如他评价温庭筠的词:“好比一座雕刻,在雕刻家没有下手的时候,这个艺术的生命便已完全了,这个生命的制造却又是一个神秘的开始,一开始便已是必然了,即所谓自由,这里不是一个酝酿,这里乃是一个开始……”①1635
由于“诗的内容”的先验性,废名亦将胡适《两只蝴蝶》这一浅显直白的诗视为新诗。废名论及《两只蝴蝶》时,对“诗的内容”有所定义:“作者因了蝴蝶飞,把他的诗的情绪触动起来了……这个诗的情绪已自己完成,这样便是我所谓的诗的内容”。④而废名评价自己的新诗时也有类似表述:“我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还是诗的。”⑤可见,废名“诗的内容”在创作之前就具有自足意义,指向某种超验的心理经验。正如李健吾指出:“他(废名)从观念出发,每一个观念凝结一个结晶的句子。”⑥废名在落笔之前已具有某种诗的理念,呈现为某种“意在笔先”的创作过程。废名对新诗的阐释一贯遵循从诗性本体到语言文字的过程,并通过对诗性理念的第一性的强调,把新诗从旧诗传统中分离出来,获得了自身的独特意义。
“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②1629这并不意味着“温李”之外的旧诗在废名眼中就不是诗,而是“旧诗之成其为诗与新诗之成其为诗,其性质不同。”①1633西渡在《废名新诗理论探颐》一文中通过辨析废名语境下的新诗和旧诗,得出“新诗对实际经验是开放的,同时又是一个自足的存在。旧诗是一个封闭的修辞系统,它所表达的经验是修辞的自我增值”⑦的结论。新诗是先在诗人的想象中有某个“诗的感觉”,再通过“散文的文字”进行记录,旧诗的创作逻辑与新诗相反。
正如废名所指出的,旧诗“要写出来以后才称其为诗”,旧诗把“诗”性本体和语言表达这两者间“体用”关系颠倒了,“诗的文字”是使旧诗之所以为诗的“体”,而诗意只是用典故性的意象拼凑而成的意境,或直接由“文字的音乐”⑧构成的诗的调子,与传达的意思无关。所以旧诗一旦脱离了“诗的文字”这一模具和“情生文、文生情”的方法,那么原本分散而延宕的诗情或思绪只能以散文表达。
旧诗能够达到“情声文文生情”是“在一个性质之下运用文字”的效果,废名在晚年论述杜甫等人的旧诗,曾将这一性质总结为“文字禅”,“夔州诗才开始突出老杜的文字禅(庾信、李商隐是这方面的能手),就是说从写诗的字面上大逞其想象,从典故和故事上大逞其想象。”⑨旧诗的“文字禅”在废名的论述中包括“字面”和“典故和故事”两方面。我国古典诗词的对仗便属于第一种“文字禅”的形式,废名以杜甫“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一句为例,上联是对眼前长江之景的生动描绘,下联则是根据律诗的对仗,由上联的文字对应而成,只符合诗人内心的某种意境,并不是对现实物象的描绘,形象之间也没有想象力的联结。后一种“文字禅”则是由于中国传统诗词中固定的意象系统,众多字词在旧诗中成为“诗的文字”。例如“古道西风瘦马”中的三个词汇的所指不再是具体的物象,而是成为凝结着中国审美意趣的典故,它们以类似“蒙太奇”的方式拼凑起某种凄凉萧瑟的意境,或废名所说的“调子”。
废名之所以认为旧诗是用“诗的文字”,正是在于旧诗遵循着“文字禅”的“把戏”,形成了“情生文文生情”的书写方式。废名不禁感叹道:“我个人承认中国的诗的文学(除了新诗)是中国文字上发达的最光明的产物,充分的发展了中国文字之长。”⑩“诗的文字”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旧诗的原创意义,代替了诗人创作之前的诗性思考。但庾信、李商隐、温庭筠等人虽然是“文字禅”的“高手”,但并不停留在文字表层,而出于自身表现。
二、视觉的盛宴
废名评价温庭筠的词时说:“长短句才真是诗体的解放,这个解放的诗体可以容纳得一个立体的内容,以前的诗体则是平面的。以前的诗是竖写的,温庭筠的词则是横写的。”①1633“竖写”指的是上文提到的对仗模式,温词则在文体上突破了格式限制,形象的编织完全由作者的想象力推进而成,所以是“横写”的。
废名将新文学的命脉“依附着‘修辞立其诚’的‘诚’字”,他强调“诗的内容”在于诗人真实地生命体验的“直接书写”。“诗人的感情碰在所接触的东西上面,如果所接触的东西与诗感最相适合,那便是天成,成功一首好诗。”废名认为“天成的”新诗应从“当下观物”中获得,即眼前的物象与“诗的感觉”刚好符合,形成心物合一的“心象”。废名在新诗讲稿中常以“新鲜”夸赞卞之琳、林庚等人的诗,也在于词语所指称的形象与诗人当下的情感形成对应,能够统一于诗的幻想之中,而不是为铺陈情感或寻求某种诗意的“调子”,从经典化的意象系统中择选出的。
“温李”从“诗的感觉”出发,以独特的幻想形成了“感觉的联串”,使文字突破了传统意象系统的框架。废名如此表述道:“温词无论一句里的一个字,一篇里的一两句,都不是上下文相生的,都是一个幻想,上天下地,东跳西跳……”①1640。例如,《更漏子·柳丝长》一词中“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便是借诗人幻想,又美人梳妆写到遥远之境。可见,在温庭筠创造的“视觉的盛宴”的背后隐匿着幻想的流动,这一思想的流动自然地串联起形象,从而构成对诗性理想的召唤。
废名《十二月十九夜》更是突破逻辑的界限,描画了一个立体的梦境,可谓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星之空是鸟林,/是花,是鱼,/是天上的梦,/海是夜的镜子。/思想是一个美人,/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废名由眼前一盏灯写到日月星辰,使遥远之物变得近在咫尺,咫尺之物又遥不可及,现实的时空感被新的文本逻辑覆盖,好似是“乱写”而成的。如果仔细寻觅此诗内部的流动的思想,又可从“乱写”的字句中感受到逻辑的缠绕与丰富。
深夜流动的灯影恰如“高山流水”,富有动势,引领诗人幻想到“身为之海”的美好之境,之后便进入到“天上的梦”的书写之中。第三、第四句(以句号为一句),都在“是”字结构的牵引下形成喻体的不断转化,“把诗人的情绪流动组织得如行云流水,有一气呵成的动势”。但这两句中都有两个主词,诗人通过主词的置换开始新一轮想象,可见线性结构之中又包含曲折。
废名通过自身的幻想把零散的心象编织起来,沿着这种曲折、交叉、断裂的逻辑,使语词之间更富诗意的褶皱。这种打破时空逻辑的“画梦”式书写,是30年代现代派诗人突出的语言特色。“满天的星/颗颗说是永远的春花。/东墙上海棠花影/簇簇说是永远的秋月。”(《星》)星辰是永恒的物象,废名将其命名为“永远的春花”,但春花乃是短暂之物。墙上的花影是短暂的,却“说是”具有永恒性的秋月。在视觉性的意象之中形成了关于“短暂与永恒”的逻辑交错,勾勒出富有辩证性的思想结构。
三、典故的字面与新诗情境化
虽然用典是旧诗“文字禅”的重要方式,但废名并不否认典故之于汉语语言的巨大效用。典故丰富了语言的内涵,延展了意境的时空维度,“有时有一种伟大的意思而很难表现,用典故有时又很容易表现。”李商隐“獭祭鱼”式的写作便是“借典故驰骋他的幻想”,他从先定的“诗的感觉”出发,把故纸堆里寻出的典故串联成新的诗句。废名认为“沧海月明珠有泪”用典的巧妙在于“这七个字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句子不算不通,但诗人得句是靠诗人的灵感,或者是有本事,然后别人联不起来的字眼他得一佳句,于是典故与辞藻都有了生命。”
废名用典亦是寻求新诗语词的丰富,而不是简单地借鉴旧诗传统。他主要师法李商隐“不是取典故里的意义,只是取字面”的用典方式,以“断章取义”方式将典故的字面直接挪用至新诗的语境之中。张丽华通过对《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两部小说的语言的研究,指出废名的小说正是使用的了“文字禅”这一联想方式,“在‘能指’层面上别取新义,不断衍生”,从而形成一种“‘能指’符号的接龙”。例如《桥》中的小林仅从“鸡鸣寺”这一字面上,空想出“意境中的动静(鸡鸣)”。这种“文字禅”在废名的新诗之中,不再是“情生文文生情”的文字的敷衍,而将“诗的文字”化为新的辞藻符号,重新纳入到对诗性感觉的记录中。废名所用的“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我的诗情没有两个叶子。”(《寄之琳》)、“春花秋月也都是的,/子非鱼安知鱼。”(《星》)都是将旧诗诗句糅合在新诗书写中,把原来“诗的文字”嫁接到符合白话汉语的语法的“散文的文字”中,割裂原有的“能指—所指”的结构,使文字符号在当下的幻想获得新的“所指”。
特别在废名1931集中创作的新诗中,“镜花水月”、“灯”、“海”等佛禅用词大量“复活”。“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佛教的“好看的字面”对应的是理念化、普遍性的禅意彼岸,而非对现实的描摹,废名借用佛禅典故的字面也在于对诗性的理想追求。以《掐花》为例,“我学一个摘华高处赌身轻/跑到桃花源岸攀手掐一瓣花儿,/于是我把它一口饮了。/我害怕我将是一个仙人,/大概就跳在水里湮死了。/明月出来吊我,/我欣喜我还是一个凡人/此水不见尸首,/一天好月照彻一溪哀意。”“摘花高处赌身轻”出自吴梅村的《浣溪沙》,废名只提取典故的字面意义,用悬崖边摘花这一行动的紧张感写逃离现实之冲动。而“此水不见尸首”源于《维摩诘经》“海有五德,一登净,不受死尸”的典故,但废名此处也只取用了字面所呈现的美丽场景,成全此首新诗中死亡的寂静之美,正如废名说“若没有这个典故这诗便不能写了”。由于“不见尸首”,“一天好月照彻一溪哀意”的洁净的悲美才圆满,本诗最后一句好比庾信“霜随柳白,月逐坟圆”中描绘的诗境,写出了超脱现世生死的大境界。
随着诗艺的进步,废名对典故字面的活用更加精妙,把典故与现实相互勾连。“理发匠的胰子沫,/同宇宙不相干/又好似鱼相忘于江湖。”(《理发店》)在这句诗中,废名活用了庄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典故的字面意义。“胰子沫”是理发时人人所见的现实实物,胰子沫确实“同宇宙不相干”,这既是诗人的主观判断,也是最寻常的观念。废名解释这首诗时说:“就咱两人说,理发师与我可谓鱼相忘于江湖”,因而“我”和理发师之间也如“胰子沫”和“世界”是不相关的。胰子沫正是借用“相濡以沫”中“沫”的字面义,从普通的物象变为诗人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如果没有“相濡以沫”这一典故的过渡,“胰子沫”和“鱼”的语词关联就无法指向诗人主体的情感,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想象,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隔膜感的主题也无法呈现于文本中。
废名在《再谈用典故》中也谈到用典的弊病,“这都是适宜于写故事,而作者是用典故,故晦涩了。”典故把原本可以展开叙述的情节凝聚在几个文字符号上,在丰富了新诗内蕴的同时,也加深了诗的晦涩。因而废名尝试在新诗中,用符号把典故故事性、戏剧性的成分展现出来。“嫦娥说,/我未带粉黛上天,/我不能看见虹,/下雨我也不敢出去玩,/我倒喜欢雨天看世界,/当初我倒没有打把伞当月亮,/自在声音颜色中,/我催诗人画一幅画罢。”《画》这首诗便是废名对李商隐“嫦娥无粉黛”、“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两句诗中典故故事的展开,是“从古人的心事中脱胎出来的”。
然而,佛教典故正是借助公案故事的讲述,通过“棒喝”、“机锋”等相悖相容的对话,获得对“禅”本体的顿悟。废名师法于佛教故事,尝试将机锋式的对话融入到诗人幻想的场景之中,从语言的内部玄机中参悟出“诗的感觉”。
《海》这首诗颇有佛教公案的色彩,废名喜爱《海》既有“担当的精神”又有“超脱美丽”,这两种情感通过“我”与“花”之间的对话,在诗中构成“复调性”戏剧结构。“我立在池岸/望那一朵好花/亭亭玉立/出水妙善,——/“我将永不爱海了。”/荷花微笑道:/“善男子,/花将长在你的海里。”“荷花”是圣洁之物的象征,因而“我”在岸边而荷花于水中亭亭玉立,既带有“可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内在的心理设定,又获得“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距离感。“我”与荷花之间微妙的空间设定,是为对话布置的情境。废名以破折号的方式形成内部叙事的突转,“我将永不爱海了”的告白缘于见花之后,“我”对花的美丽和洁净产生的执念,因而忘却了“花”之外的美丽世界。为一朵花抛弃世界,是对世界的超脱的同时,对花的爱有所担当。但这一执念却被花一语点破——“花将长在你的海里”,这里的“海”有“觉海性澄圆”之意,指自己的内心智慧,即心海澄澈而美自生,因而何必执着外物而忘却自己内心。废名便是以这一“不涉理路”的方式,在“我”和“花”对白的交锋之中,传达出一瞬间“诗”性的顿悟。
四、结语
不同于旧诗将“诗的文字”作为诗的性质,废名对诗性理念的强调使新诗获得了独立的文体意义。废名对新诗的诗学认知与温庭筠、李商隐的写作路径相契合,他一方面从“温李”的诗作中寻觅到不同于其他旧诗的“诗的感觉”,并将其视为“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另一方面在废名新诗文本中表现出对“温李”诗艺的自觉征用。
在新诗写作过程中,废名利用自身幻想将物象材料转化为与“诗的感觉”相呼应的“心象”,并以复杂多变的逻辑将其编织入诗,在语词之间形成某种诗性的张力,创造了温词般“视觉的盛筵”。而废名对传统资源的征引的独到之处,在于师法李商隐“断章取义”的用典方式,将旧的意象化为新的文字符号,丰富了白话汉语的语词。此外,废名对旧诗只有典故,没有情节故事的展开抱有质疑态度,他在新诗中利用机锋式对白和公案式的场景,延展了诗性本体的表达空间。
可见,废名试图在新旧诗之间建立沟通而非沿袭之关系,他力图使古典资源在新诗中重获新生,为诗并以此反拨新诗日渐西方化的发展趋向。
注释
①废名.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废名集·第四卷[M].王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②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废名集·第四卷[M].王凤, 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③孙玉石.对中国传统诗现代性的呼唤——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关系的思考[J].烟台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④废名.尝试集//废名集·第四卷[M].王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10.
⑤废名.《妆台》及其他//废名集废名集·第四卷[M].王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22.
⑥刘西渭.《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冯文炳研究资料[C].陈振国,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76.
⑦西渡.废名新诗理论探颐[A]//新诗评论·第2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⑧废名.草儿//废名集·第四卷[M].王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10.
⑨废名.夔州诗//废名集·第四卷[M].王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06.
⑩废名.周作人散文钞//废名集·第三卷[M].王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79.
参考文献
[1]废名.废名集[M].王风,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3]孙玉石.思想是一个美人[A]//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7)[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吴晓东.镜花水月的世界[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3.
[5]张丽华.废名《桥》与《莫须有先生传》语言研究[A]//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6]西渡.废名新诗理论探颐[A]//新诗评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
[7]孙玉石.对中国传统诗现代性的呼唤——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关系的思考[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旧诗新作